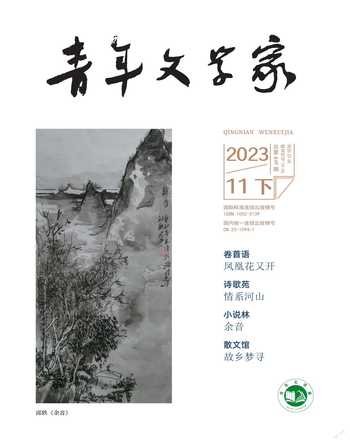小说《棋王》中的人物比较分析
2024-01-02张永国
张永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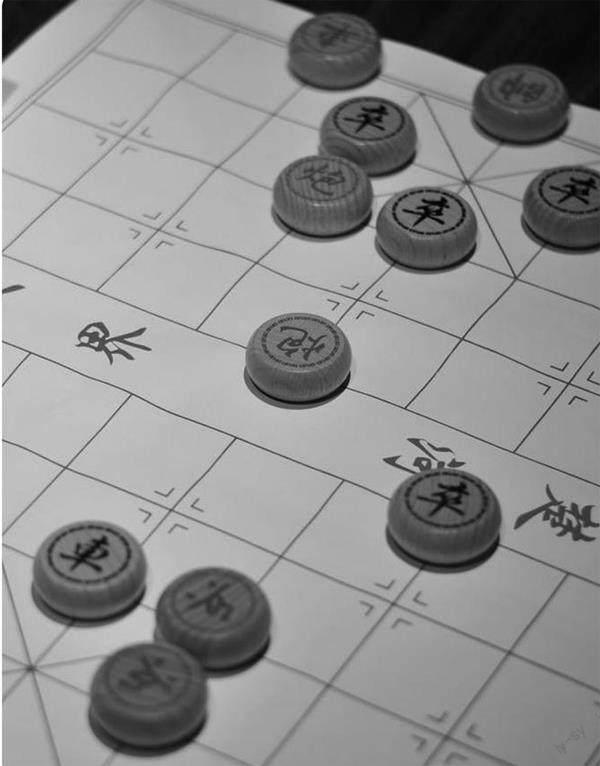
阿城的小说《棋王》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小说以白描的叙述方式和自然朴素的语言塑造了“棋王”王一生这一人物,也简洁地刻画了“我”、脚卵(倪斌)、捡烂纸的老头儿、获得地区棋赛冠军的老者等人物。本文紧贴小说情节内容,对比分析了小说中一些人物的异同,解释了部分人物的镜像关系,以及各人物所属的务虚、务实的不同“阵营”。本文的研究对读者深入理解小说《棋王》中人物的特点,体悟小说的艺术魅力,不无帮助。
一、小说人物的异同
(一)饥饿的“孤儿”:“我”与王一生
小说中的“我”与王一生因互相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而成为朋友。
“我”与王一生都是父母双“亡”。“我”的父母因有些污点,在“运动”一开始即被打死。王一生的生父在其出生之前就不见了,继父靠卖力气挣钱,但身子骨儿不行;王一生上初一时,母亲去世了,继父有了钱就喝酒骂人。当王一生规劝他时,他无奈地表示生活艰难,很烦恼又没文化,只能靠喝酒安慰自己。他对王一生说,“对老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下辈子算吧。”母亲的临终嘱咐加上继父的生活情况,都要求王一生初中毕业就挣钱养家。王一生在母亲死后,基本算是父母双“亡”了。
“我”与王一生还有的共同经验是都有一种“饥饿感”。当“我”父母在世时,家里尚能品尝美味;而在父母死后,“我”在城里转悠一年多,有时饿到晚上才有吃的。王一生家里穷,他上学时为了省钱,不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看电影等活动;王一生对吃的要求很实在,他信奉“半饥半饱日子长”,认为“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他认为“我”讲述的小说《热爱生命》的故事中,作者杰克·伦敦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的人写成发神经,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认为“我”讲的巴尔扎克小说《邦斯舅舅》是个“馋”而非“吃”的故事;认为“我”说的“一天没吃东西”不准确,因为没超过24小时。
“我”与王一生的不同,首先是家庭状况。“我”的父母(或其中一人)在机关工作,家具上有机关的铝牌编号。王一生的母亲以前是窑子里的,他继父是卖力气的,两人都不识字。其次,“我”与王一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消费需求有差异。“我”读书多,能讲中外文学作品,在农场还想看书、看电影。而王一生读书不多,讲的故事也是他们院儿五奶奶讲过的老套情节;他主要想下棋,一方面是“呆在棋里舒服”,另一方面应该与下棋成本低有关系,即使没有棋盘棋子也能在心里下。他的家庭条件限制了他文化消费的范围,所以他认为“我”到了农场还想看书、看电影,“想的净是锦上添花”。后来,当王一生在文化馆画家的帮助下,有机会在礼堂舞台的边幕上免费看演出时,他也很入戏,张着嘴,脸上表情随着舞台上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全然没有在棋盘前的镇定。
“我”与王一生成为朋友是有预兆的,当知青们挤在火车车厢靠站台一面的窗前说笑哭泣时,只有“我”与王一生坐在车厢冷清的另一面。随着交流的深入,“我”发现自己与王一生之间有着相互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而当王一生请“我”继续讲故事,“我”因他误解杰克·伦敦,表示不高兴时,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升上来,我还是喜欢他的”。“我”与王一生在下乡的火车上相识,下火车,坐汽车,两人从总场奔赴各自分场时,说有事没事要互相走动。后来,王一生果然走了近百里路来找“我”,“我”也直接从伙房领回自己当月五钱油的配额,盛情款待他。王一生在地区棋场与九人下棋前,把像性命一样重要的无字棋交“我”保管,是真朋友才有如此托付,同时也是因为我知道无字棋的意义,这是他母亲用牙刷把儿磨成并在临终时留给他的。“我”也真心爱护王一生,在他与九人下棋前,“我”走过去给他拍了拍头上、脸上的土;在他下棋过程中,“我”担心他身体,找了凉水,悄悄走近让他喝;在他下完棋后,“我”用手揉他僵了的双腿,搀着他慢慢走。
“我”是父母双亡、落难底层的机关子弟,了解饥饿,了解苦难;王一生是父母双“亡”、身处寒苦的平民。“我”与王一生都是饥饿的“孤儿”。
(二)机关子弟与世家子弟:“我”与脚卵
“我”与脚卵的家庭都曾有能力和闲暇品尝美味,但两家也存在明显差异,是“机关的铝牌编号”家具与“古董字画”的差异。“我”是机关子弟,但未必是名人后裔。“我”父母在世时家道尚好,父亲做菜好吃,常邀同事在星期天来家里品尝。外号“脚卵”的倪斌是世家子弟,祖上是元代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脚卵的爷爷在世时吃燕窝,甚至专门雇一人从燕窝里拨脏东西;脚卵父亲年年中秋节约名人到家里吃蟹、下棋、品酒、作诗;脚卵家有字画古董,他来插队时,他的父亲给他一副极其考究的明朝乌木棋。
“我”与脚卵的文化性格不同。“我”待人接物通达平和,文人气不浓。这应该与“我”生来的秉性和成长环境有关,也可能与“我”在父母死后吃喝“没什么着落”地混过两年的经历有关。脚卵则常常衣冠楚楚,动作文气,见人会握手,讲起话来总是“蛮好,蛮好”,会用“乃父”这样的雅词;他认为周围的人文化水平低,认为象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打篮球是野蛮运动。小说中的“我”说,脚卵“神神道道”。
与“神神道道”并存的是脚卵身上的世家子弟风范。脚卵是“我”所在分场的象棋高手,他与王一生下棋时用了祖传的乌木棋。输了棋,他说自己的棋路生了,碰到王一生这样的高手蛮高兴的,要做朋友,并给王一生分享了他珍藏的巧克力、麦乳精、精白挂面。脚卵提前把地区的棋类赛事告诉王一生,当听说王一生没能报上名时,他就主动找地区的文教书记疏通关系,帮忙取得参赛资格(虽然被王一生放弃了)。王一生与九人下棋,棋罢身体发僵,脚卵“用大手在王一生身上、脸上、脖子上缓缓地用力揉”。
脚卵的过分斯文让人忍俊不禁,他的友善助人则值得称赞。
(三)无字棋与乌木棋:王一生与脚卵
王一生與脚卵差异明显,前者是平民子弟,带着母亲用牙刷把儿磨成的无字棋,认为在农场能吃饱就是莫大的福气;后者是世家子弟,带着祖传的乌木棋,吃过山珍海味,在农场竟藏有巧克力、麦乳精等稀罕物。两人下棋,王一生因衣服洗了没干,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儿;脚卵则穿得笔挺,实际上他平常就总穿得整整齐齐。
两人的学棋方式、棋道所宗也有差别。王一生是跟天下人学棋,从街头巷尾、垃圾站、学校、少年宫,到名手家里,到边境农场,总之从古人到今人,从凡人到名人,细大不捐,博采众长。尤其是捡烂纸的老头儿,王一生获得了对方祖传的棋道。老头儿无儿无女,说自己日子无多,看到王一生酷爱下棋,脑子好又有琢磨劲儿,就把祖传的棋谱赠给他,还以道家阴阳之说,从道、运、势等方面点拨他。小说有处细节能体现王一生博采众长的学棋特点,获得地区棋赛冠军的老者评价王一生棋道“汇道禅于一炉”,如果说王一生的“道”来自捡烂纸的老头儿,那么他的“禅”出自哪里?小说没有明讲,但很可能来自脚卵的“家棋”。脚卵的祖上倪云林家道破败,卖了家产到处游走,与一个会下棋的村野之人相识,学得一手好棋,后来信佛参禅,将棋炼进禅宗,这棋只有脚卵家族这一宗传下来。王一生与脚卵下过棋,应是学到了后者棋中的“禅”意。
王一生与脚卵的差异是“无字棋”与“乌木棋”的差异,一个寒苦而有骨气,一个“富贵”而不逼人;一个学“天下”,无为而无所不为,一个承“禅”棋,因家传而自成一路。
(四)穷苦真切与文雅得体:老头儿与老者
捡烂纸的老头儿与获得地区棋赛冠军的老者都很传奇,他们并未谋面,但都遇到了王一生。老头儿有祖传的棋道,老者是山区一个世家的后人,他们都是象棋高手,都认为公开棋赛的水平不高。老头儿看了王一生从垃圾堆找到的以前市里象棋比赛的棋谱,认为“这棋没根”,是愚者下的棋路;老者“出山”玩儿棋,不想就夺了地区棋赛冠军,评了比赛的大势,直叹棋道不兴。
两人又有差别。老头儿遵祖训“为棋不为生”,没学过什么谋生本事,老来捡烂纸为生,生活寒苦。但老头儿谈及棋道时,言语畅达,“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老头儿平常说话则简洁尖锐,他见王一生翻垃圾就说,“你个大小伙子,怎么抢我的买卖”;当他听王一生说想到自己那儿看看时,就白了一眼说,“撑的?!”而老者有世家风采,从其言谈举止判断,日常用度当不堪忧。老者讲派头(也身有不便),听说王一生要与包括自己在内的九人同时下盲棋,就在家里命人传棋。待棋盘上只剩几个棋子,而王一生的黑子儿峙在老者的棋营格里时,老者赶来,看完八张定局残子,轻抻衣衫、跺跺土,昂了头,由人搀进棋场。他首先向王一生道歉,“身有不便,不能亲赴沙场。使人传棋,实出无奈”,然后称赏,“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棋道,我看了,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最后求和,愿成“忘年之交”,“棋下到这里,权做赏玩”,可否“平手言和,给老朽一点面子?”王一生同意言和,老者说,“今晚你是不是就在我那儿歇了?养息两天,我们谈谈棋?”老者表达的是对王一生的感谢、爱护,以及请教之意。前后两段言辞,老者都说得文雅得体、滴水不漏。
二、小说中的镜像人物
小说中有两对镜像人物:捡烂纸的老头儿与王一生,获得地区棋赛冠军的老者与脚卵。两位老人的人生状况似乎分别对应了两位年轻人的未来;两位年轻人的言行举止似乎有两位老人各自年轻时的影子,虽然老者与脚卵并未直接交流。
(一)“为棋不为生”:老头儿与王一生
老头儿与王一生都身处寒苦之中,除了棋艺,都无一技傍身。老头儿遵祖训“为棋不为生”。王一生固守清白,不接受脚卵贿赂文教書记帮他取得的棋赛参赛资格。当王一生想在棋赛结束后再登门与高手下棋时,脚卵想去跟书记说一下,组织一个友谊赛,王一生反对,“千万不要跟什么书记说,我自己找他们下”。王一生不主动“谋生”,也不接受朋友帮“谋”,只是不求名利地下棋,就是老头儿所说的“为棋不为生”。老头儿与王一生应该能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二)承“古”不泥“古”:老者与脚卵
老者与脚卵都是世家后人,言谈举止都有文人气。老者爱护后辈王一生,脚卵帮助同辈王一生,这都是世家风范。老者讲派头、重名声,勇于棋上求和,言语得体,文雅周全;脚卵炫家世、重斯文,言辞虽有点儿食古不化,但会办事,“勇于”以棋谋路。文教书记一暗示,脚卵就带来古董棋,解决了他自己谋职以及朋友参加棋赛资格的问题。老者年轻时的言辞或许也像脚卵那样“食古不化”,而脚卵年轻就已然“懂事”,历经世事后必能臻于老者那样得体练达、文雅周全的境界。
三、小说人物所属的“阵营”
前文提及的人物总体可分为务虚、务实两个阵营。王一生与老头儿都务虚,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坚守和追求,“为棋不为生”;但两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务实,王一生视吃饱为头等大事,老头儿要“务实”地捡烂纸为生。与之相对照的是,脚卵与老者更注重名利,是“务实”派,他们起码都很看重世家的名声,或以之为荣,或积极维护。在“利”方面,小说明写脚卵利用家庭的人际关系和自己手中的古董棋,与地区的文教书记进行利益交换,谋求自己职务的变动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小说中的“我”是中间派。在农场“我”很后悔用油甚至用书和电影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来表示对生活的不满。然而,“我”对看书、看电影“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当王一生与九人下盲棋入夜时,山民和地区的人举火把、打手电,围观棋赛;待王一生取得八胜一和的战绩时,人们争睹“棋王”丰采,跟随王一生到他的暂住地,挤着围观。当晚“我”悟到“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如果把人谋求衣食水平的提升(如从“吃”到“馋”)视为务实,那么“我”逐步清晰地认识到,人只是务实是不够的,还要有务虚的一面。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分析小说《棋王》中的人物,能够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理解这些人物的特点。他们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既有传奇,也有凡俗;既有镜像,又有阵营,可谓参差多彩,这是小说《棋王》艺术魅力的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