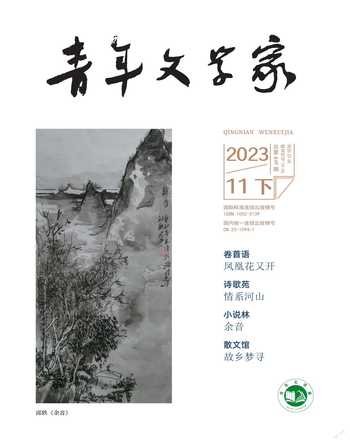徐悱之父睹文搁笔的文化溯因
2024-01-02王凡
王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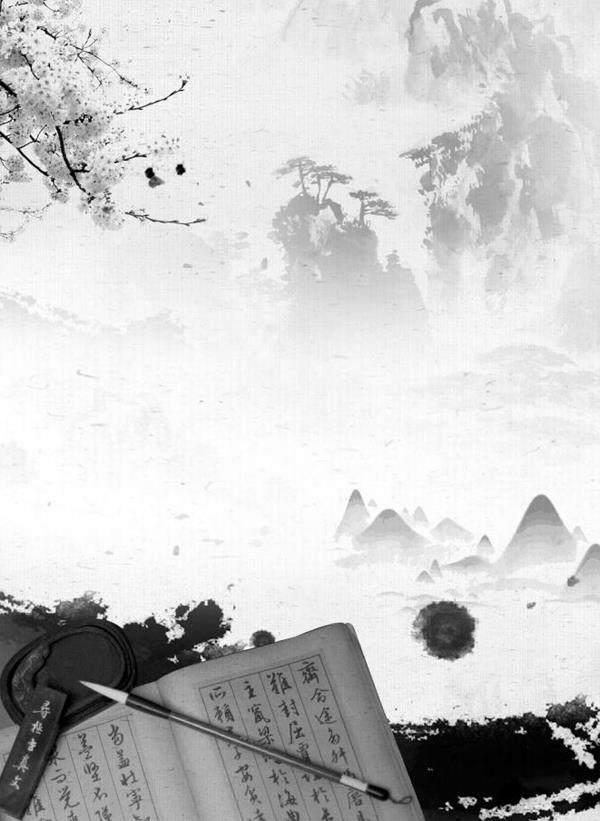
徐悱之父睹文搁笔一事源于史书关于南朝女诗人刘令娴作《祭夫徐悱文》的零星记载。本文通过对徐悱之父睹其文而搁笔的开明举动进行文化溯因,剖析了搁笔举动背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男性对女性价值体认的新视野与两性婚姻伦理观念的新维度,并归纳概括了造成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的原因,即当时佛教的众生平等观、道教的和合观,以及庄子的真情论等时代思潮的共同影响。
一、徐悱之父睹文搁笔之缘起
据《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载:“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琊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凄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搁笔。”刘令娴乃南朝梁时期的女诗人,及笄之年嫁与东海望族仆射徐勉之子徐悱为妻。婚后,夫妻二人情趣和谐,十分恩爱。后徐悱英年病逝,刘令娴悲痛不已,提笔而成《祭夫徐悱文》。祭文悲怆凄婉,但辞采斐然。徐悱之父徐勉本欲为儿撰写祭悼文章,但阅过儿媳之作,深为赞赏,于是叹服搁笔,不复再作。
现将《祭夫徐悱文》全文引录于下:
维梁大同五年,新妇谨荐少牢于徐府君之灵曰:
惟君德爰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成,辨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仪许中,声高洛下。含潘度陆,超终迈贾。二仪既肇,判合始分。简贤依德,乃隶夫君。外治徒奉,内佐无闻。幸移蓬性,颇习兰薰。式传琴瑟,相酬典坟。辅仁难验,神情易促。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乾,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从军暂别,且思楼中。薄游未反,尚比飞蓬。如当此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
刘令娴之《祭夫徐悱文》,笔者曾于《〈祭夫徐悱文〉对〈柳下惠诔〉的艺术突破》一文中给予过文本文学地位的探析:在中国古代祭悼文史上,夫悼妻文佳作迭出,妻悼夫文则屈指可数。从文体上说,刘令娴此文在自我个性的凸显、夫妻情爱的价值觉醒、我向思维的书写等方面都对以“礼”见长的春秋诔文实现了艺术突破,在妻悼夫文一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徐悱之父搁笔之举,首先应是对其文学才情的肯定。但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而言,女诗人因夫丧而挥毫作文,家翁因睹文而叹服搁笔,这种私人化的个体行为亦能透视出其背后所属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场。从社会性别角度而言,徐悱之父所睹文章乃是刘令娴的女性书写,是在以男性为书写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徐悱之父睹文搁笔的态度则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時期,尤以南朝梁时期,男性对这种女性书写举动及其书写内容的某种宽容与欣赏,也体现了徐悱之父所属阶层对女性的形象期待与文化诉求。
二、徐悱之父睹文搁笔的文化溯因
徐悱之父的这种宽容与欣赏折射出了当时社会中男性士人的价值观念转变,而转变本身离不开当事人教育背景与整个社会思潮的综合影响。
(一)睹文搁笔背后的价值观念转变
1.才智:魏晋南北朝女性价值体认的新视野
刘令娴是一位才女。有关她的生平,从《南史》《梁书》记载可知:刘令娴出身彭城刘氏,家学颇丰,从小即有诗名,后嫁与同样为诗书门第的丈夫徐悱,二人唱和之作在文学史上亦为佳话。从《隋书·经籍志四》载“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旧唐书·经籍志下》载“徐悱妻《刘氏集》六卷”,可见刘令娴的诗作颇为丰厚,但由于历史久远多有佚失,仍可阅查的诗作只有其《玉台新咏》中的存诗八首。即便存诗不多,其《光宅寺》与《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也独具特色,引人关注。
中国古代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先秦至两汉受礼法及儒家思想影响,男性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为“德”,汉代郑玄注“妇德”曰“谓贞顺”,班昭《女诫》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也即“幽闲贞专”的德行为是社会赋予女性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
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时易世移,男性对女性的肯定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要求,开始出现“才智”这一新的评价维度。余嘉锡曾指出:“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世说新语笺疏》)故一批博闻强识、才情卓越的女性亦开始于此时争奇斗艳,如《世说新语》中记载如咏絮之才的谢道韫,目光如炬、善于识人的许允妇,远见卓识的山涛妻等,更有一批风雅灵秀的女诗人走进了女性文学史,如左思之妹左芬、鲍照之妹鲍令晖、沈约之孙女沈满愿,也包括徐悱之妻刘令娴。
一个时代是否有才女大量涌现,并不取决于其时女性本身是否聪慧,而往往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是否给了女性以更宽容的表现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思想相对活跃,精神相对自由的一个阶段,此时儒学衰微,玄道盛行,男性对女性的期待与评价也颠覆了传统儒学礼教对女性“三纲五常”的思想枷锁,对具有个性与才情的女性给予了开明的宽容、欣赏,甚至颂扬。刘令娴的家翁徐勉,出身东海徐氏望族,虽儒学传家但也崇道尚佛,贵为一代贤相,文名声播遐迩,他的搁笔之举可视为一种人文思想上的进步,侧面反映了女子有才也是德的社会心理,为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女性才智体认的新视野。
2.情爱:魏晋南北朝两性婚姻伦理的新维度
刘令娴的诗歌最具文学意义的其实当推《答外诗二首》。这两首诗缘于其夫徐悱孤身一人任职晋安时,久居异乡思念娇妻,望春晖、夕照、幽林、芳草,而提笔作《赠内》与《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赠予刘令娴。刘令娴见字如面,思绪万千作《春闺怨》与《咏佳人》回赠。这两首诗均抒发了诗人不在夫君身边的轻愁,风格清拔明秀,与徐悱的两首赠内诗相得益彰,可谓文人与才女的天作之合。联想到刘令娴于前述祭夫文中关于夫妻间的伉俪情深的恩爱日常的回忆表达,可窥二人婚姻的深情与和谐。
而同样具有表达夫妻深情且具有示范意义的诗作于汉魏六朝时期远多于前朝,如以相互酬答形式存在的秦嘉与徐淑的赠答诗、贾充与前妻李夫人的联句诗、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的破镜重圆诗等,还有以一方抒写形式而存在的苏伯玉妻的《盘中诗》、苏蕙的《璇玑图诗》、孙楚的《除妇服诗》、江淹的《悼室人诗十首》、刘孝威的《郄县遇见人织率尔寄妇》等,这些诗作无不以诗为媒,将夫妻之情写得温婉多情、情深意长。而刘令娴《答外诗》的文学意义即这种文学潮流的体现。
这种文学潮流实则是汉魏六朝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观念转变而出现的新维度。自周代以来,夫妇结合的重要意义及社会功能只关系门第与繁衍。在传统观念中,婚姻只具有合二姓之好与繁衍后代的伦理功能,夫妇相处之道在于“礼”,“夫妇之义”“二姓之好”的伦理禁忌制约着“夫妇之情”与“二性之好”的自然之情。婚姻中女性仅承担生育与抚养后代的责任,地位低下,独尊夫权,为男子的附属与工具,夫妻之间几无真情实意可言。而这种尊礼轻情的婚姻观念却于魏晋之际开始得到某种改变。在《世说新语·惑溺》中,士人荀粲夫妻感情深厚,大冬天为高热妻子降温,竟不顾严寒于庭院中自冻再以身熨之,后竟殉妻;王戎之妻当众以“卿卿”亲昵相称,王戎初认为于礼不合,其妻以“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回应;潘岳《悼亡诗》中怀念妻子的情深意长;刘令娴《祭夫徐悱文》与《答外诗》展现出的夫妇间亲密的生活日常与平等的精神契合,以及徐悱之父搁笔的赞赏等,无不显示出某种任情越礼的倾向。男性能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人予以尊重、爱护,婚姻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更加入了一份真情,实则是人性的复苏。
(二)价值观念转化背后的时代思潮
无论是对女性才智的肯定,还是婚姻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相对平等,都属于女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放,而任何世俗层面观念的转变,一定是滋生于所属时代更深层次思想、信仰的土壤。“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在哲学思想层面,儒学日渐衰微,老庄日渐兴盛,佛教日渐普及,秩序新旧交替,思想推陈出新。在女性观方面,非主流伦理思想的佛道与儒家学说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对世俗观念的解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启迪。
1.佛教的众生平等观
在两性关系上,佛教不但没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反而由于其“众生平等”的理念,使得在佛祖面前,善男信女皆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而间接给予了女性身心的撫慰。佛教的“众生平等”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佛法普济众生层面,无论男女,人人都具有佛性可慧根,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法平等教化一切众生,佛法平等对待每一个信徒,即无论男女都有成佛意愿的平等;二是在修行、学习佛法的道路上,女性也有与男性平等修行的权利,佛教把男女信徒区分为“善男人”与“善女人”,无论男女,在行善修行上没有区别、没有歧视,只要心诚勤修,都能获得福德,最终成佛。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在当时社会中蓬勃发展,民间信众极多。这种宗教层面在意念、修行上的平等观,一定会对唤醒当时女性观念造成良性影响,从而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以及男性对女性在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与尊重。
2.道教的和合观
道教对待女性的态度比佛教更加开明。道教理论主要源自道家思想,而《老子》一书则体现出强烈的女性哲学色彩,推崇阴柔,如老子把“道”视为万物之母,将“道”比作“玄牝之门”,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德经》),书中屡屡出现“母”“玄牝之门”“谷神”等女性词汇,显示出老子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生命哲学的崇拜思想。同时,他还推崇“贵柔守雌”的阴柔哲学,认为柔能克刚,上善若水,世上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但它能穿透最坚硬的石头,在阴阳关系中,不似儒家重阳抑阴,而是崇阴贵柔,而崇阴则成为后世道教尊崇女性的思想来源之一。
之后,道教从阴阳和合的理论出发,形成了重阴阳的两性和合观,认为女子只要精修勤练,都能最后得道成仙。故在道教伦理文化中,女性是具有独立地位且享有独立人格的重要社会角色,这种观念不仅影响着女性的宗教修行,也启迪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开明与重视态度。
3.庄子的真情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家经学因社会变革呈成颓败之势,士族阶层更多盛谈“三玄”。作为“三玄”之一的《庄子》亦给当时精英阶层的思想提供了精神支持。
对于人类的情感问题,庄子在本质上是肯定情感的,但在表达方式上,他提倡返璞归真,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否定矫揉造作,认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对于感情的“贵真”,实际上是对儒家“礼”的否定。孔孟儒学主张人应遵循礼法,以“仁”释礼,以“义”释礼,其最终目的是维护统治和国家的安定。但“礼”也易为窃国之诸侯所利用,他们借仁义道德之名行不义之事。所以,庄子认为儒学之礼有违人性的本真,背后其实隐藏着欺诈与丑恶,反而有违自然之道,束缚了人性。
在老庄学说盛行的魏晋以降,知识分子们对待情感开始承袭庄子“贵真”的思想态度,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越名教而任自然,否认伦理纲常。文学领域则出现了如陆机“缘情说”的文学理论,他认为诗歌源于情感,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如不能尽情抒发自身喜怒哀乐等内心情感,文学创作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突破儒家传统“诗言志”文学观念的理论,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无论男女,作文咏诗,不再局限于伦理怀抱和道德情怀,而是自由自在地袒露其心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诚挚心灵、热烈情爱。刘令娴能在祭夫文与赠答诗中坦率地表现对夫君徐悱的一往情深,徐悱之父能以开明的举动并流露对刘令娴其人其文的欣赏,个中缘由,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