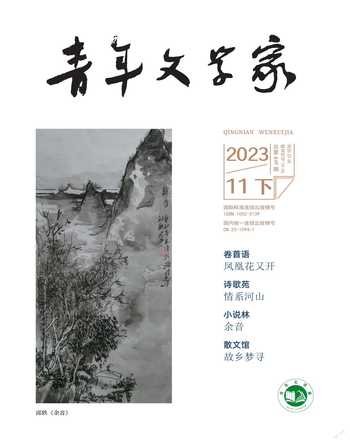意象与意象派及诗歌的三维解读
2024-01-02孙健男
孙健男
意象是诗人创造的诗之外部形态,是诗歌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呈示方式,是诗歌结构里的一个基本单元。诗人通过意象的创造,可以生动地传达审美理想和情感;诗论家通过对意象的解析,可以让受众了解诗歌微妙而宏阔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意象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知诗歌的门户。但对“意象”这一诗学概念,人们存在不同认知。有人说,“意象”这一词语中国古已有之,不是什么新概念;有人道,“意象”是地道的舶来品,是标准的洋货色。有人对意象派诗歌十分钟爱,有人却对它颇有微词。既然诗界对意象和意象派诗歌存在不同理解,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梳理,并对意象派诗歌作品进行审美解读。
一、意象在中国的发展演进
“意象”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三千年前的《易》书里就出现了“象”,不过这里的“象”是卦象。到了三国时代,王弼在他的《周易略例·明象篇》中论及了“象”“意”“言”三者之间的关系,王弼虽然把“意”与“象”的关系论述得比较透辟,但“象”仍然是《易》中的卦象,属于哲学命题的范畴,还不具备诗学特征。即便如此,它还是对后世中国诗学意象的构建起到了推动作用。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第一次把“象”与“意”合并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但刘勰的“意象说”仍然属于一种粗浅的直觉把握,显得有点儿宽泛,缺少对意象的内在机制和审美规范的总体透视与验证。意象理论渐趋成熟的阶段,大体上应在明清期间。明代“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对“意”与“象”关系的论述甚多,也颇为妥当。他主张诗作须有超妙而又衡当的意象,关键在于“要外足于象,而内足于意,文不减质,声不浮律”(《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四《于大夫集序》),也就是要求外在的物象和内在的情意都必须充分地表现,但赋象而不直露,意深而不见滥,保持一种维系“衡当”的张力。
以上笔者简略勾勒出“意象”这一概念在我国古代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意在说明意象理论在我国确实源远流长。
“意象”作为诗学概念演进到现代,首先是在欧美出现的,其后迅速传播到中国。回顾其传播历程,它对中国诗坛产生过三次较大影响。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当时胡适留学美国,也正是意象派诗歌风靡美国的时候,胡适非常推崇意象派诗歌,并把它译介到国内。第二次在中国诗坛掀起意象派诗风的代表人物是施蛰存。1932年,他在其主编的《现代》月刊上着力推介美国意象主义诗歌。他在译介的同时,自己还用创作实践它。其后又过了大约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意象派诗风又在中国诗坛劲吹,一些崇拜西洋诗歌的诗作者们,把这种在西方早已式微的意象派诗歌奉若神明,争相仿效。针对这种现状,老诗人郑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对西方意象派理论理解得过于简单狭窄的话,那么有可能会束缚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创作实践中,诗人们只会写一些单调贫乏的小诗,导致诗歌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诗人余光中对意象派诗之短也毫不掩饰地表示:意象派诗往往沦于为意象而意象,他们的诗只能使受众感受到一时的新鲜,却不能诉诸人们的性灵,因而使诗缺乏想象性功能。
通过以上论述,大家基本可以了解“意象”这一诗学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现代学者对它的研究状况。
二、意象及意象派诗歌在欧美
西方学者和诗人对意象的论述颇多,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诗人庞德,他给意象下的定义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合物的东西。”(埃兹尔·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他提到的“复合物”又是什么意思呢?庞德在他的《关于意象主义》一文中扩展了“复合物”这一概念。他认为意象可以有两种:一、意象是“主观的”,它们被吸收进诗人的大脑之中,而后又被转化了,成了与它们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意象;二、意象又可以是“客观的”,它是旋涡一般的或集结在一起的转化了的思想。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象不仅仅是纯思想的,而且是蕴含着主客观的一个“复合物”,是诗歌里充满着能量的符号。庞德给意象下定义时还经常引进潜意识的成分。
意象派是1908年发端于英国,第二年盛行于美国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在美学追求上,意象派反对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后期的内容空洞、形象浮泛、冗长累赘、缺少真情的诗风,呼吁用简洁、直接的形象和语言,表现刹那间呈示的理性于感情的情结,达到让人的精神在瞬间获得释放的诗感。在具体创作实践中,意象派诗人F·S·弗林特提出了三条规则:一、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二、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三、节奏上用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而不是用节拍器反复演奏来进行创作。在弗林特三规则之后,庞德又提出了《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在语言方面,主张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不能揭示事物的形容词,不要用所谓好的装饰;在节奏和韵律方面,主张不要过分依赖音乐,不要把材料剁成零散的抑扬格,节奏结构不应该损毁文字的形状,或它们自然的声音和意义等。以上这些原则,基本反映了西方意象派的诗美理想。由于意象派诗人具有自己独特的诗美观,所以意象派诗歌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被休姆概括得最为直接明了。休姆认为意象派这类诗不像音乐,更像是雕塑。他还作了一个更为形象的比喻,说意象派诗像是竖立起一个像石膏似的意象,并把它交给读者。
以上内容是笔者对意象及意象派在中西诗坛的发展脉络进行的简笔勾勒,意在让大家明白“意象”已成为中西诗坛一个重要诗学概念。不过,现今我们使用的“意象”一词的含义,就像老诗人流沙河所说的那样,它既不是纯粹的老古董,也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诗学新概念。
三、西方意象派代表作品解读
西方意象派诗人众多,作品丰富,本节选择两位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及其他们的诗作进行解读。这两位诗人分别是庞德和希尔达·杜利特尔(以下简称H·D)。他们都是美国有影响力的意象派诗人,而且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笔者选择庞德和H·D的作品进行解读,并非他们曾是恋人,而是他们都是意象派的优秀诗人,而且所选择的这兩首诗,也是意象派有影响的代表作。
首先看庞德的《一个姑娘》。此诗篇幅不长,共十行,分两节。请看全诗:“树进入我的手/汁液升上我的臂/树长入我的胸/向下长/枝梢从我身内长出,像手臂一样//你是树/你是青苔/你是煦风轻拂的紫罗兰/一个孩子—这样高—你是/于这个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是愚蠢。”据说这首诗是庞德写给H·D的。前面说过,H·D是庞德的恋人,只因H·D父亲反对,两人未能修成正果。但庞德深爱着H·D,这首《一个姑娘》就是明证。
诗题是“一个姑娘”,可诗歌并没有从“姑娘”落笔,而是从“树”开始抒写。诗人把“树”作为主体意象,以树为喻,把树喻以姑娘。因诗人采用暗喻和象征的手法,这一切都抒写得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庞德以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为受众创造了一个魔幻的世界,你看:树的汁液可以升上我的胳臂,能够长入我的胸中,枝梢还可以从我身内长出,这都是诗人幻想的结果。在这一节里,诗人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存在,是诗人以浪漫的情思创造的一个神奇幻象。这里的“树”就是“姑娘”,“姑娘”就是“树”,二者合二为一。树进入“我”的身体,“我”和树交融在一起,“我”又和树合二为一。诗人巧妙地把“姑娘”“树”和“我”三个意象叠置在一起,使诗产生巨大的张力,为受众创造出一个奇幻的艺术世界。
第二诗节,诗人转换抒写角度,从超现实的幻象中拉回到现实。诗人选择“树”“青苔”和“紫罗兰”三个意象来比喻“姑娘”,极具美感。树,修长、苗条、蓬勃、旺盛,比喻姑娘甚贴;青苔,青翠、幽冷、柔润,以喻姑娘极妙;紫罗兰,馨香、摇曳生姿、曼妙无比,以喻姑娘最佳。诗人对姑娘赞美就是通过三个精心择取的意象来实现的。这样的暗喻写法避免了直露的歌颂和赞美,使诗更具蕴藉和含蓄。在受众正沉浸在美好意象的体验与想象时,结句突然一笔“于这个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是愚蠢”,情感指向突然来了一个逆转,如此美好的这一切,于这个世界竟都是愚蠢。这一切为何都成了“愚蠢”?诗篇戛然而止,给受众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意象派诗人的美学追求就是以意象取胜,通过选择意象来实现诗人的情感传达的。在《一个姑娘》这首诗里,“树”“青苔”“紫罗兰”等优美意象作为姑娘的替身,不仅给受众造成视觉美感,而且创造了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诗人运用浪漫手法,把姑娘的化身“树”进入“我”的身体,通过超现实手法的运用,更能书写出对“姑娘”如痴如醉的情感状态,这比写实更为有力。从结构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写作手法的转换,从第一节的魔幻转入第二节的现实,虚实的变换,境界的转移,既造成了诗美空间的变换,又造成了结构的摇曳多姿,更体现了艺术上的多样性,这也是这首诗的一大亮点。
我们再来看H·D的《海上的玫瑰》。“玫瑰,刺人的玫瑰/饱受蹂躏,花瓣稀少/瘦削的花朵,单薄/疏落的叶子//比一根茎上唯一的/一朵淋湿的玫瑰/更为珍贵/你给卷入了海浪中/开不大的玫瑰/叶子这样小/你给扔到了沙滩上/在风中疾驰的/干脆沙粒中/你又被刮了起来//那芬芳的玫瑰/能滴下这样辛辣的/凝于一片叶子中的香气?”这首《海上的玫瑰》篇尾注释道:“改写自欧里庇得斯的《陶洛人中的伊芙吉妮亚》。”伊芙吉妮亚命运悲惨,被父亲作为祭品杀害。显然这“海上的玫瑰”是伊芙吉妮亚的象征。我们暂且抛开象征意蕴不议,就诗的审美向度足以让我们叫绝。
我们也先分析诗题。诗题“海上的玫瑰”告诉了受众这朵玫瑰的特殊境遇,她既不是花园中的玫瑰,也不是荒野老林里的玫瑰,这为我们理解这朵玫瑰提供了现实背景。大家知道“海”意味着什么,这就给受众一种悬想:娇弱的玫瑰竟置身于凶险的“海上”。标题乍一看很有诗意和美感,但稍一琢磨,实则令人惊悚和唏嘘。
在第一诗节里诗人刻画了一个可怜的弱者形象,尽管她“刺人”。你看,她“飽受蹂躏”,说明她命运不幸;她花瓣稀少,花朵瘦削且单薄,说明她并不娇艳;她叶子疏落,说明她颇为憔悴。诗人通过“饱受蹂躏”“花瓣”“花朵”和“叶子”几个视角,把一个被践踏、被损害的弱者形象凸显在受众视野中,让人感慨之余不禁心生怜悯。第二诗节重点书写“玫瑰”的不幸与遭际。她被“卷入了海浪中”,她被“扔到了沙滩上”,又被疾风“刮了起来”,大海就是这样对玫瑰进行无情戏弄和摧残。诗篇在第一节静态描写的基础上,在这一节进行动态刻画。“海”是一个施暴者,极尽暴虐;玫瑰尽管被蹂躏,被践踏,但她没有丝毫的屈服,因此她“比一根茎上唯一的/一朵淋湿的玫瑰/更为珍贵”,她的珍贵来自她坚毅的品性,来自她对命运的坚决抗争。
在前两节凄惨凶暴的静动描写后,第三诗节出现了昂扬的调子与靓丽的色彩,诗人热情歌颂这朵“海上的玫瑰”,用“芬芳”修饰“玫瑰”,用“辛辣”修饰“香气”。这时,玫瑰的娇美可人令受众为之一振。“芬芳”和“辛辣”本是两个意味不同的词语,两个异质的语汇,点出了玫瑰的两种内在品质:“美”和“刚”。在那凶险的海上她没有被击垮,没有因海的暴虐而屈服,依然散放着芬芳,流溢着香气,尤其是第一诗节的“刺人”一词,更能说明玫瑰“刚”的品性。
在艺术上,诗人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开始极力表现玫瑰的孤单弱小、貌不惊人和饱受蹂躏,其后极尽讴歌和赞美,颂扬玫瑰的顽强不屈和芬芳馨香,这种抑扬手法的运用,除了产生情感结构的跌宕起伏外,也给受众带来阅读心理的张弛感。
《一个姑娘》和《海上的玫瑰》从诗题看似是一个写人,一个写物,实则二者都在写人,都是以曲笔来书写对象。《一个姑娘》是从物(树)写起,以象征和比喻来书写美丽姑娘;《海上的玫瑰》也是从物(玫瑰)写起,以海上的玫瑰喻指伊芙吉妮亚。象征和暗示手法的巧妙运用,在艺术风格上都给受众以委婉含蓄之美。
笔者在上文对意象、意象派及代表诗人的诗作进行了三个维度的解读,以期给受众打开一扇了解意象与意象派及诗歌的认知窗口。意象派诗歌和意象派诗人的研究还有许多课题,亟待诗歌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去做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