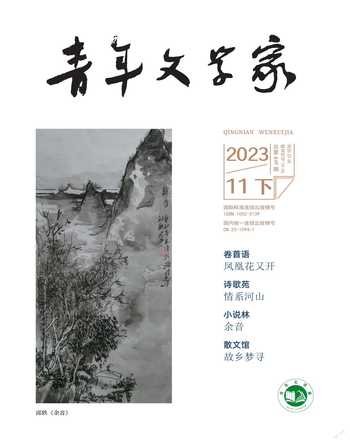入世,治生,归隐
2024-01-02李婉琦
李婉琦
陶渊明作为一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隐者,最终过上了看似自然和谐的归隐生活。然而,在东晋与刘宋易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他的人生经历和切身遭遇在不同的维度上均产生了矛盾冲突,并引发了他对于入世、治生和归隐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于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出来的独特的人格范式是陶渊明给予后人的精神归宿,而在追问的过程中陶渊明还实现了关于人格对话的诗性抒写,将生存状态与人格主体在平淡的诗语中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与平衡。
一、入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为天下念的情怀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集体意识的体现,身处太平盛世的文人承平日久,壮志踌躇,往往在作品中书写着意气风发的时代自信;而生逢易代之际的文人,由于江山易色,王朝更迭,理想与现实发生剧变,其奉行的人生哲学也受到巨大冲击,导致其心态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不过,即便陷入理想与现实不能两全的窘境之中,他们依旧能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超乎一己之得失的胸襟与气魄,无论是处于庙堂之高还是沦为江湖之远,依旧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此在易代之际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大济苍生的政治宏愿在陶渊明的思想体系中根深蒂固,年少时的陶渊明曾渴望手持宝剑,周游四方,一展宏图,足以见其欲建功立业的迫切理想与热血气概。但陶渊明的一生经历的正是东晋与刘宋交替的易代时期,这个时期更多的是政局动荡与民不聊生的黑暗,政权多次易主。因此,陶渊明想要在如此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他的人生理想而大有作为显然困难重重。他的一生中总共经历五次仕与隐的抉择。陶渊明在《饮酒》组诗中的第十首讲述了他第一次做官的经历,即出任江州祭酒。而陶渊明最后一次出来做官是出任八十余日的彭泽县令,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便选择与官场诀别,决心不再涉足。辞官归隐后的他终于有了久在樊笼,终返自然的如释重负和安然自得。除去陶渊明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做官经历,中间三次面临仕与隐抉择的内心矛盾非常值得关注。隆安三年,孙恩于会稽叛乱,江州刺史桓玄起兵讨伐孙恩,平定乱贼,代替桓玄上表文书之人即为陶渊明,这是他第二次做官。而桓玄实力壮大后,篡夺了东晋政权,自立为帝,建立桓楚政权。东晋的镇军将军也是后来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刘裕正要讨灭桓玄,陶渊明此时任刘裕幕下镇军参军的职务,这是他第三次做官。此后虽仍有两次做官经历,但他已经远离了政治官场的中心。“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在仕途中经历了希望与失望,最后终于绝望而去。现实中的仕进与隐退同时也是他内心中矛盾挣扎的历程之外显。《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可以称得上是他矛盾心理的代表,这是陶渊明在出仕刘裕幕下做镇军参军前的内心独白,这一次他的心情是复杂的、犹豫的,陶渊明顾虑颇多,但挣扎过后还是迈出了这一步。所以,陶渊明在出仕之前有疑虑也有担忧,甚至做了最坏的假设和打算,但内心深處还留存着缥缈的希望。可惜的是现实与理想在刘裕大肆清除东晋余党势力时再度断裂,他备受冷遇,处境困窘,人人都深感自危,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让陶渊明不得不再度抽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不断淡化自己在政治舞台中的位置。
弃官归隐后的陶渊明,一生都在想要完成出仕的理想和必须忍受出仕后的现实痛苦之间的矛盾挣扎。曾经的踌躇满志在《咏荆轲》当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可是,为什么陶渊明每次做官的时间短暂,但他仍选择辗转多次呢?实际上,陶渊明选择出仕的时间和地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陶渊明入桓玄幕到解绶而归这段时间正是晋末政局最动荡、最混乱的八年,可这期间并不是陶渊明生活最为困窘的时候,根本没有达到需要去乞讨的地步,这是其一。而此时荆州与京口又是军事重地,陶渊明所居之处相距甚近,陶渊明有着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政治敏感度,所以他的几次出仕都表明了他愿意为了人生理想而去尝试和突破,这是其二。但从陶渊明始终未能升迁,每次都以不堪吏职而收场的经历中可以窥见满怀希望的陶渊明是如何在政治官场中受挫的情景。鲁迅对此的态度曾在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犀利地指出:“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由此可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混乱动荡的政局既是陶渊明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是他无法脱离的苦海,而相比于穷困而言,仕宦之途需要付出违背本性的巨大代价更使其无法忍受,在出仕的理想与实际出仕的现实之间他选择了用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去对抗那个时代的不幸。虽然他的行为与时代背道而驰,但他的内心始终充盈满足,获得了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二、治生:初名与实名的矛盾
“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在文学作品中亦可探作者的人品与节操。而名节之坚守在某种程度上又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最初的名节和实际的名节往往会因时因势而发生改变,甚至二者会在一个人的内心之中发生矛盾冲击,进而影响人的心态,并倾注于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中。
陶渊明并不是一开始就沦落到贫困的需要乞讨的地步,实际上,陶渊明出身于贵族之家,他的家族只是在陶渊明的这一辈逐渐没落了。虽无昔日的辉煌,然而身份地位仍存,这就是为什么刘裕篡位后仍然三番五次想要陶渊明出任做官,陶渊明代表的是一派势力的政治态度。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和祖父陶茂都曾出任高官要职,并且二人均淡泊名利、自强进取。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陶渊明自然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这表现在他对于儒家思想的深入学习。根据学者朱自清统计,陶渊明在他的诗作中对于《论语》的引用就有三十余次。由此观之,陶渊明的那种极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他的家庭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可是,家族的没落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陶渊明的仕途,且在当时动荡的政局下掌权者也频繁更换,没有了强大的家族势力作为后盾的陶渊明只能屈居幕僚,没有施展的空间,就连自我保全都成了一件需要多加忧心的事情,所以他更不可能期盼在政治上大有作为。易代之际,陶渊明生不逢时,回望晋室之暮,只能是徒增慨然。
原生家庭除了在精神上会给予陶渊明一丝坚守的希望之外,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帮助。然而,陶渊明悲惨的实际遭遇不仅在官场仕途中,其实易代之际的痛苦也蔓延在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在他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更为不幸的悲惨遭遇。陶渊明二十岁时遇到世难,三十岁时丧妻。屡有风灾、水灾,收成不足,难以维持一家生活。生活的坎坷贫困原因在于自己,何必怨天?但又不能不为目前所遭遇之忧感到凄然。于是,他感叹死后的声名如浮烟一般,对自己毫无意义,身后之名也同样无所谓了。除此之外,陶渊明在身体上同样遭受折磨,生命焦虑始终伴随着他,常患疾病且不断服药,只好以菊入药,专注养生。名节的坚守必然要付出心灵和身体上的代价,陶渊明的人生轨迹显然是有志氣、立名节、成大任的真实写照。
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决心躬耕隐逸,想要独善其身必然会面临生存条件每况愈下的窘境。而陶渊明的“忧道”并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遐想,在《荣木》这首诗中他迫切地希望这种“道”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早日实现。而“忧道”与“忧贫”相比,“忧道”永远都是他最看重也是最忧心的。建功立业的理想对于陶渊明来说从未忘却,但独行坚守总是孤独的,他从先师中寻找精神寄托,又在古圣先贤中寻觅知音,并以此为榜样学习。诗中表现了秉性贞刚的诗人由于身处昏暗之世,知音难觅而感受到的孤寂愤懑。这些都是陶渊明在建功立业的理想未能实现后选取的另一条坚守心中的“道”的道路。
三、归隐:守拙与顺化的矛盾
潘江在《木厓文集·小隐轩记》中将隐逸分为心隐和迹隐两类,心隐侧重于意识的趋向,而迹隐则是具体的行为。从仕宦的角度看待吏隐,不难理解吏隐属于心隐的一部分,但这种分类方法又不足以说明陶渊明的归隐行为。陶渊明与长沮、桀溺之类古隐士的遁世是有巨大差别的,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隐逸类型。而入世与出世是截然不同的对立关系,当他在一个人身上的矛盾交战之时,便会出现不同人格间的对话。
魏晋时期是一个玄学思想快速发展渗透的重要时期,玄学聚焦于人的生死无常,其核心是对生命的理性探讨,同时也是当时士人借此排解死亡恐惧的产物,以对抗人们对死亡产生的焦虑之感。陶渊明生活在玄学思想盛行的时期,受到玄学的影响非常大。《形影神》组诗集中展现了陶渊明立善求名的生死观念,借助人格对话的形式提出了对于人生荣辱穷达的深刻且独特的思考,书写了其心中关于生死的矛盾斗争的过程。“形”指物质生命及其感情欲望,“影”指生命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神”指生命达到自身存在的本体的反思能力,陶渊明通过这种反思使生命达到自足又自觉的境界。对死亡的焦虑、恐惧,以及淡然转变在陶渊明心中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而在人格对话的过程中陶渊明最终认识到了死亡的价值,这种清醒理性的认识让他超越了死亡本身带给他的恐惧和感伤,也使他在精神上不再孤独,并尝试直面死亡的必然性,将生命归还给自由和自然。陶渊明的文学境界始终以生命思想为核心贯穿,在其他诗作中,这种关于生与死的忧叹也时时出现。陶渊明认为人死之后,肉身与名望湮灭消失,不复为人所知,衣食之需更勿多。陶渊明在《连雨独饮》中表明他不为外物所惑,至今已努力四十年。形骸之变却让初衷更加坚守,自是无怨无悔。这首诗同样体现了陶渊明有生必有死,率真自得,顺乎自然,才真正得以超脱的生死观。对待生死,陶渊明是豁达从容的,而在《拟挽歌辞》中陶渊明流露出了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不是不看重生的可贵,而是尊重生命的顺时变化。对于长生的美好追求和期盼只是陶渊明脑海中稍纵即逝的念想,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人是无法脱离现存的时空之间的,只能将顺应自然作为自己的最终选择。
陶渊明身处魏晋生命意识的思潮之中,在渴望坚守理想时遭受了各种生命矛盾的斗争,这促使他对生命与死亡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时也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去反复确证,聚焦于人本身的意义。陶渊明的理性思考也为后代士人在努力追寻自身生命价值提供了一个模仿的人格范式,这种求同的方式确实能够让人们获得一种心灵上的解放与释怀。陶渊明的归隐选择既非消极遁世,也非愤不释怀。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用“和峻”一词评价陶之性情是非常精准的,陶渊明的“和”表现在于痛苦的人生中寻找心灵的补偿与救赎,以此获得一些安慰;而他的“峻”就表现在绝不媚俗,慎终如始,毫不动摇地坚守自己的人生选择。这种在“迹隐”和“心隐”之外的另一种独特的隐逸方式成就了陶渊明人生志向的实现。陶渊明将他的现实生活经历和独特的诗意风格倾注于文学创作之中,使当时的诗坛重新焕发出光彩,也让自己的人生选择、生命认识成为不断被歌咏的主题。归隐只是在官场中缺失了政治位置,却因此成就了陶渊明在文学创作、哲学思考,以及人格精神的高度,这可以称得上是陶渊明在顺其自然的选择中,将人生志向得以另一种方式的实现。而这种陶渊明建构出的特色人生范式也能在历朝历代的诗人身上循迹踪影,他们不断创作和陶诗,希望能够跨越时空与陶渊明实现精神与灵魂的契合,而这些和陶佳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陶渊明觉世之意义的侧面再现。
古今豪杰之士,或出或处,或达或隐,只不过是由于生逢世道的不同而作出的相应选择,时移势易,结局亦会不同。作为力量微弱的个体总是很难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强大感召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普遍积极于跻身仕途,渴望成就一番功业。然而,并非所有人的仕途经历都是一帆风顺的。从陶渊明入世、治生和归隐的经历来看,他的人生经历和实际遭遇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个缩影,他的人格范式和觉世意义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归宿,使他在仕途失意或厌倦官场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寄托情感的精神对象,并能够在此精神对象中尝试找寻新的人生价值,以此获得一种心理补偿。在陶渊明不同阶段的诗文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创作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变迁,诗文与诗人之间的渗透补充,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