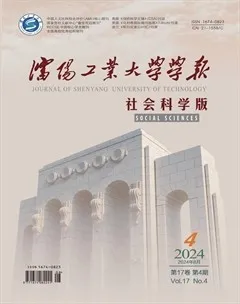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理论证成、适用界限与法律后果
2024-01-01万志前王子洁
摘" 要: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见的抗辩事由之一,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和过错责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合法来源抗辩是对品种权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制,为平衡品种权人与善意侵权人的利益,应从行为类型、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方面明确其适用界限。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人应停止侵害和支付合理开支。应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可根据具体案件采取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及取得侵权物等代替救济方式,按照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确定合理开支的数额。善意侵权人所获利益的返还,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我国应借鉴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他国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完善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
关" 键" 词: 品种权; 合法来源抗辩; 善意侵权; 停止侵害; 合理开支
中图分类号: D9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0823(2024)04-0430-10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涉法律名称均按惯例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①TRIPs协定第45条:“对于故意或有充分理由应知道自己从事侵权活动的侵权人,司法机关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力持有人支付足以补偿其因知识产权侵权所受损害的赔偿。”
②品种权通常又称为“育种者权利”(Plant Breeders′ Rights,PBR)或“植物品种权”(Plant Variety Rights,PVR),两种称谓不同,不过是“一体两面”问题:前者侧重于权利的主体——育种者,后者侧重于权利的客体——植物新品种。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日本、肯尼亚、南非等国的立法采育种者权利的称谓;欧盟、美国、新西兰、韩国、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或地区的立法采植物品种权的称谓。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植物品种权的称谓,简称“品种权”。
③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④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统计,共有18件侵害品种权案件涉及合法来源抗辩,其中有12件参照其他知识产权的规定予以判定。
收稿日期: 2023-11-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FX078)。
作者简介: 万志前(1974—),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研究。
【法律理论与实务】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24.04.11
一、问题的提出
合法来源抗辩作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抗辩事由之一,最初源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的规定,即善意侵害知识产权者免于承担赔偿责任①。为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接轨,我国200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中分别规定了侵害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的合法来源抗辩事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均无关于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简称品种权②)合法来源抗辩的规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17日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正草案)》第72条中原本增加了“合法来源抗辩”条款,即“不知道是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的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能证明该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具有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该条款在最终审议通过的《种子法》中被删除,主要原因是侵害品种权行为的认定技术性较强,比较复杂,可由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具体处理③;且合法来源抗辩会减轻相关当事人的侵权责任,增加了品种权人的维权成本,削弱了品种权保护力度,加之《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UPOV)亦未规定此项抗辩事由[1]。司法实践中,若被告提出合法来源抗辩,法院往往参照适用其他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合法来源抗辩制度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以下简称《品种权司法解释(二)》)第13条认可了这一制度该解释第13条第1款规定:“销售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是未经品种权人许可而售出的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且举证证明具有合法来源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判令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判令其停止销售并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但尚有不足。2022年11月24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征求意见稿》)第47条从行政执法层面增加了侵权人合法来源抗辩条款该《修订征求意见稿》第47条规定:“当事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是侵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收获材料,并且能够证明有合法来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侵权,可以依法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以与《品种权司法解释(二)》的规定相衔接。
合法来源抗辩是重要的侵权抗辩事由,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均有规定的情况下,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的缺失会影响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同时,合法来源抗辩通过对侵权责任的合理分配,能降低销售者市场活动风险,保障正常的市场经营活动,督促商品销售者加强进货渠道管理,在诉讼中披露上游供货者,以便权利人找到侵权源头,从根本上打击侵权行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72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631号民事判决书。。因此,在立法上设置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实有必要。现有关于合理来源抗辩制度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领域,对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的研究不多参见郭杰,植物新品种侵权中“合法来源抗辩”适用分析,种子,2022年第6期,第142-148页;周波,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独占实施许可与合法来源抗辩,人民司法,2021年第5期,第86-89页。,有待深化。基于此,本文拟以现有研究为基础,结合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参照各知识产权部门法、我国司法实践等,从理论证成、适用界限、法律后果三方面分析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并提出完善建议。
二、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的理论证成
品种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如同用专利保护工业领域的发明创造一样,是用专门法律制度保护农业领域的育种创新成果,是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促进育种创新的根本保障[2]。合法来源抗辩作为侵害品种权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品种权保护力度,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证成其合理性。
1. 信赖保护原则是理论渊源
信赖保护原则又称“保护合理期待原则”[3],其具体内涵是在交易中行为人对他人的身份资质等信息已尽形式审查义务,依此形式表象产生信赖,并实施相应的民事行为,形成相应的法律后果,即使该法律后果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但为了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法律应当保护这种信赖利益。正如拉伦茨所言:“只有当必不可少的信赖被保护时,人类才有可能在保障每个人各得其应得者的法律之下和平共处……故促成信赖并保护正当的信赖属于法秩序必须满足的最根本要求之一。”[4]合法来源抗辩制度通过免除善意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已尽合理注意义务行为人的信赖利益,从而达到保护私法秩序的目的,符合信赖权利外观保护制度的原理。基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合法来源抗辩制度既能将种业企业的知识产权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其正常运营,免除其顾虑,促进品种权交易,也有助于促使品种权人溯源维权,打击源头侵权。
2. 善意第三人理论是法理基础
善意第三人理论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理论,其作为法律上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占有,即从非所有人手中取得物品而认为该人是物品的所有人,自己根据正当原因取得占有,因而获得了整个权利[5]。按照这一理论,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主观上出于善意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则应当根据公平原则保护该善意行为人的权利。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制度设计以及制度框架下无权处分人的侵权行为具有同构性或同质性,故知识产权侵权中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可类推适用于物权上的善意取得制度[6],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在市场交易中,除了保护“静的安全”(权利不受他人随意侵害)外,“动的安全”(交易相对人对合法获得权利的使用过程)同样需要法律保护[7]。保护善意第三人能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经营,鼓励其积极参与市场交易,进而实现“动的安全”,维护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在激励育种创新与交易安全、保护品种权人与善意第三人权益之间实现适当平衡,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3. 过错责任原则是责任基础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过错作为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伦理和正义性基础,行为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是因为其主观上具有可以归责的事由(故意或者过失)[8]。该原则以过错作为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唯一归责事由,从积极方面而言,就是“有过错,或有(赔偿)责任”,从消极方面而言,就是“无过错,必无(赔偿)责任”[9]。我国侵权损害赔偿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以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为例外。《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责任形式以损害赔偿为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区分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绝对权请求权,规定了适用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10]。停止侵害等主张属于消极防御性绝对权请求权的范畴,此类请求权不以过错为前提[11],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则以侵权人过错为前提。品种权属于私权,侵害品种权作为一般侵权行为,其侵权责任应与我国《民法典》中一般侵权归责原则保持一致《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以过错为前提,而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等民事责任则无需考虑过错。因此,能证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合法来源的无过错者不承担赔偿责任,是遵循损害赔偿过错责任原则的必然结果。如韩国《种子产业法》第86条规定所体现的就是损害赔偿过错责任原则,即品种权持有人或独占许可被许可人可以向故意或过失侵犯其品种权或独占许可权的人员请求损害赔偿[12]。根据该规定,若侵权人无“故意或过失”(过错),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日本《植物品种保护与种苗法》第34条第1款也有类似规定日本《植物品种保护与种苗法》第34条第1款规定:“育种者权利持有人或排他使用权人,对故意或因过失侵害了自己育种者权利或排他使用权的侵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时……”。。此外,我国《专利法》第77条《专利法》第77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商标法》第64条《商标法》第64条第2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著作权法》第59条《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均规定了无过错者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些都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体现。因此,合法来源抗辩免除无过错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符合一般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品种权作为一种私权,同样要遵循一般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不应予以区别对待,否则会破坏整个私法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立法的统一性。
综上,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过错责任原则三者分别构成了合法来源抗辩的理论渊源、法理基础和责任基础,共同证成了合法来源抗辩的正当性。信赖保护原则是理论基础,善意第三人理论和过错责任原则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运用。善意行为人在其主观不知道且能提供合法来源的情况下免除损害赔偿责任,是保护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具体体现。善意侵权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也符合侵权损害赔偿的过错归责原则。
三、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界限
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更为模糊[13],品种权亦如此。这种模糊性往往使市场主体因担心侵权赔偿对其敬而远之。合法来源抗辩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是对品种权人请求权范围的限制,能消除市场主体的顾虑,促进品种权交易与利用。同时,这种限制也可能削弱品种权的保护力度,影响育种创新,因此,需要从行为类型、主观要件、合法来源等方面明确其适用界限,以实现品种权人与善意侵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1. 行为类型
对于哪些行为类型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各知识产权部门法以及各国法律有不同规定。一是对所有善意侵权行为均可主张。如韩国《种子产业法》第86条、日本《植物品种保护与种苗法》第34条均规定,不区分行为的类型,只有故意或过失侵权者才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亦即所有善意侵权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我国《修订征求意见稿》第47条的规定也未限制行为的类型。二是对使用行为、许诺销售行为、销售行为可以主张。如《专利法》第77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适用合法来源抗辩。三是仅对销售行为可以主张。如《商标法》第64条第2款、《品种权司法解释(二)》第13条的规定即是如此。在我国侵害品种权纠纷处理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也仅认可销售行为适用合法来源抗辩,其他行为则不适用。如在重庆奔象果业公司与九莲生态农业开发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中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1民初809号民事判决书。,九莲生态农业开发公司的侵权行为是种植和繁育,法院认定其不符合合法来源抗辩中的“销售”,故不支持其合法来源抗辩。在侵害品种权纠纷中,销售行为固然可适用合法来源抗辩,但生产行为、繁殖行为以及进出口行为是否适用,仍需讨论。
生产或繁殖行为是否适用合法来源抗辩?可以借助《专利法》中合法来源抗辩的规定加以分析。2000年《专利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使用或销售具有合法来源的专利产品构成侵权,但不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作为第63条(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第2款,逻辑上存在问题。因此,2008年《专利法》第70条将“合法来源抗辩”作为独立条款加以规定,同时增加了“许诺销售行为”的类型,但没有规定制造行为。2020年修改的《专利法》仍然没有将制造行为纳入合法来源抗辩的范围,其原因在于,制造专利侵权产品的行为是其他侵权形态的基础行为,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制造提供的是一种“绝对保护”[14]96-97,因此不论制造者是否具有主观故意,只要是为生产经营目的、未经授权且无法律规定的例外,则制造专利产品构成侵权行为,应承担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侵权责任。品种权所控制的生产或繁殖行为类似专利权所控制的制造行为,故为从源头上加强品种权保护,生产或繁殖行为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
若生产行为涉及的是农民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意见》(2019年1月4日)的规定,农民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个人,不包括合作社、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植行为,则这种行为类似专利法中的使用行为。此种情况下农民是否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需要分两种情况讨论。一是农民种植自己所留种子,若符合农民留种豁免条件,则其留种种植行为不构成侵权,无需适用合法来源抗辩;若农民留种不符合豁免条件,如留种的数量或种植的面积超过法律规定的边界,则构成侵权,农民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规定为由,主张其为善意而构成合法来源抗辩。若农民无意留种(如基因漂移),根据2002年Monsanto Canada Inc.v.Schmeiser案的判决,农民的主观意图应当作为其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考虑因素,以避免农民的善意误植被视为专利侵权[15]。但这种情况多为自然因素引起,不属于合法来源抗辩的情形。二是农民所种植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来源合法,但所购买的繁殖材料侵权。此种情况下有两种制度安排:其一,农民主张合法来源抗辩,可免除侵权赔偿责任,但要停止侵权,即销毁繁殖材料或不得继续种植;其二,农民的种植行为不构成侵权,如依据印度《2001年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第42条规定印度《2001年植物品种和农民权利保护法》第42条规定:“依据本法确立的权利受到农民侵犯,但该农民当时并未意识到该权利存在的,不应当视为侵权。”参见朱建国,邹萍:《亚洲部分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文献汇编》,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页。,农民的无意侵权行为不构成侵权,不承担侵权责任。对此本文认为,若农民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身份,且能证明被诉侵权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具有合法来源,则不构成侵权;若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农民身份(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则构成侵权,但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免除侵权赔偿责任。
进口或出口行为是否适用合法来源抗辩?此种情况可以借鉴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的判例加以分析。在丹纳赫西特传感工业控制(天津)有限公司诉赵元鸿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中,进口商(侵权人)提出了合法来源抗辩。法院认为,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外生产制造被控侵权产品,该行为本身并不侵犯在中国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但进口至我国境内并销售被控侵权产品将直接导致该产品在涉案商标受保护的法域内从无到有。进口商对侵权产品的销售构成该产品在商标注册国市场上的最初流通,其行为与生产或制造行为性质相似,因此应承担与生产商相同的侵权责任,包括赔偿责任。此外,进口商对进口商品是否侵犯他人商标权应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不能以“不知道”为由免除赔偿责任。因此,进口或出口行为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
《品种权司法解释(二)》第13条仅规定了销售行为的合法来源抗辩,2021年修改的《种子法》则增加了品种权对许诺销售行为的控制。由此推断,许诺销售行为也应当适用合法来源抗辩。既然实际销售行为都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举重以明轻,发生在实际销售行为之前的许诺销售行为更有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理由。综上,品种权类似专利权,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行为类型应借鉴《专利法》相关规定,即使用行为(种植行为)、销售行为、许诺销售行为均可适用合法来源抗辩。
2. 主观要件
关于合法来源抗辩主观要件的规定,国内各知识产权部门法以及各国立法有所不同。有的从正面规定,即“不知道”(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为适用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如《专利法》第7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5条该解释第25条第1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第2款将“不知道”解释为“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的规定即是如此。有的从反面规定,即“故意或过失”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品种权人可以向故意或过失侵害品种权的侵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如韩国《种子产业法》第86条、日本《植物品种保护与种苗法》第34条、印度尼西亚《植物品种保护法》第67条第1款印度尼西亚《植物品种保护法》第67条第1款规定:“植物品种保护权所有人或者被许可人或者强制许可获得人有权通过国家法院对无权行使本法第6条规定的行为却故意为之的任何人提出损害赔偿。”的规定即是如此。《品种权司法解释(二)》将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表述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属于从正面规定。
关于知识产权法中“不知道”的内涵,学术界和实践中有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不知道”应当被理解为“实际得知”的反义词,包括不可能知道和应当知道而实际并不知道[14]645。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知道不包括“应当知道而实际不知道”的情形[16]。两者的分歧在于,“不知道”是否包含“应当知道而实际不知道”。合法来源抗辩旨在免除无过错方的赔偿责任,而“应当知道而实际不知道”是一种主观上的过失,如果将此种情形包含在“不知道”范围内,那么侵权人很容易以此为由规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为平衡品种权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利益,“不知道”中应当排除“应当知道而实际不知道”的情形。品种权是一种绝对权,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晓他人的品种权为由而主张“不知道”。因此,“不知道”作为“实际得知”的反义词,解释为客观上的不知道更为妥当[17],即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并未意识到其行为构成侵权,强调的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
“不应当知道”的反面是“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一词被用来指称下述事实:具有正常理智与智力或超常智力的人在履行对他人的义务时,应当以审慎的态度确定有关事实是否存在,或者根据该事实存在的假设控制其自身的行为[18]。“应当”引导的法律规范属于弱强行性规范[19],“应当”作为规范性概念,可以引导涉及价值判断的规则,并为主体创设实体性义务[20]。故尽管侵权人可能确实不知道侵权事实存在,但法律不允许其因不知道该事实而主张不构成侵权。《品种权司法解释(二)》将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规定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对善意侵权人设置了较高的注意义务,可以督促其在交易前深入了解相关信息,谨慎交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品种权人的倾斜保护,这也是种子交易市场的严格监管要求使然。
法院在认定合法来源抗辩者是否符合主观要件时,往往将“知道或应当知道”之义务转化为合理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指行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依该准则而采取的合理防免措施[21]。在河南鑫民种业公司、中种联丰种业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2485号民事判决书。等案件中,因销售者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合法来源抗辩理由未获法院支持。在郑州市二七区百领水果种植园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592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百领水果种植园作为专业种植树苗的经营者,对经营行为的合法性应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将“知道或应当知道”转化为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实是将主观问题客观化,即通过可衡量的外在客观因素判断抗辩者的主观状态。法院对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判断,应综合考虑权利客体的可识别性、抗辩者的审查能力、第三方的信赖程度、抗辩者与第三方责任能力的对比以及产品的表面合法性等因素[22]。同时,法院应遵循合理限定原则,将注意义务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既要加强行为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又不能无限扩大注意义务,使人因所要求的注意程度太高而“无法注意”,从而影响其正常业务和行为[23]。由于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生产经营者对其经营的植物新品种来源有较严格的注意义务,但对此也要把握适当的度,如果太过严苛,将会影响种子交易市场的活力。
关于主观要件的举证责任分担,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抗辩人证明说和权利人证明说。抗辩人证明说主张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抗辩者举证证明“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24]。此种举证责任分担对品种权人或被许可人有利,对于侵权人所列证据,品种权人或被许可人有权举出相反证据予以驳斥。权利人证明说认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即由品种权人或被许可人证明侵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在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诉杨建忠、卢炳仙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指出:“对于主观善意的成立要件,需要侵权产品使用者、销售者证明其不知道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的是侵权产品,这是一种消极事实,根据消极事实的证明规则,一般应由权利人来证明侵权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的是侵权产品,从而否定合法来源抗辩的成立。”。有观点认为:“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作为消极事实的‘不知道’,通常不由提出该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而主张积极事实(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方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25]据此,“不知道”作为消极事实,侵权人难以直接举出证据予以证明,举证责任应转移至权利人,即由权利人举证证明侵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实,消极事实与积极事实并非相互冲突[26],二者通常难以完全区分,仅是语言文字上的转化。“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侵权”的消极事实,当其被表述为“善意侵权”时,就是一种积极事实。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采取抗辩人证明说,同时,将侵权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的主观心理状态转化为客观的合理注意义务,由侵权人举证证明其是否已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在安徽皖垦种业公司诉安徽省寿县向东汽车电器修理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初749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销售者应当在查清繁殖材料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审查该繁殖材料的提供者是否依法取得了相应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否属于法定无需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形,但销售者未尽到此种注意义务,因此存在主观过错。
3. 客观要件
合法来源抗辩的客观要件是侵权产品有合法来源,包括来源明确与来源合法。来源明确是一个客观事实判断,而来源合法则兼具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色彩[27]。来源明确的具体含义是侵权人应当提供前手供货方的具体信息,以明确侵权产品来源者身份。抗辩者仅提供侵权产品来源线索而无法确定来源主体身份信息的,不满足来源明确的要求,否则,通过合法来源抗辩制度披露被诉侵权产品、溯源追踪侵权人、打击源头侵权和维护种业市场秩序的目标难以实现。在山东登海先锋种业公司诉新绛县华丰种业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796号民事判决书。中,因华丰种业公司未提供河南太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民事主体资格和向其销售侵权种子的相关证据,法院未支持侵权人的合法来源抗辩。《品种权司法解释(二)》第13条第2款规定,销售者一般应当举证证明“存在实际的具体供货方”,实际上是对来源明确的要求。对实际供货方信息的证明要求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具体信息的要求,如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及其他个人信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商登记资料等信息。
对来源合法的证明往往需要提供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侵权产品的获得过程,该过程应当围绕侵权产品从前手到后手的交易展开,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买卖合同、转账记录或凭证体现。如在江苏保丰集团公司诉新沂市禾源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民三终字第0069号民事判决书。中,禾源公司为证明其销售的小麦品种来源合法,提供了购种协议、收款单、留村农场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以及加盖留村农场印章的购种协议等证据,以证明禾源公司系从留村农场购得被控侵权小麦品种。因此,法院支持了禾源公司的合法来源抗辩。但在种业经营领域,因经营者的证据意识较弱以及交易习惯影响,抗辩者往往不能提供体现侵权产品交易全过程的证据,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对此,应针对不同规模的抗辩主体区分证明标准。若经营主体经营规模较大、财务制度较规范,应当提供完整、规范的交易过程凭据;若经营主体为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健全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则不应苛求其证据的完备性。此外,来源合法不仅要求购货渠道合法,而且包含销售者或许诺销售者自身的销售资质合法,即要求销售者提供相关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授权书以及营业执照等证明材料。《品种权司法解释(二)》第13条第2款规定,销售者一般应当举证证明“购货渠道、价格、生产经营许可证等”,实际上是对来源合法的证明要求。当然,还应当根据证据本身与被控侵权行为及被控侵权产品之间内容和时间上的关联性判断来源是否合法[28]。
四、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法律后果
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抗辩者仍构成侵权,可以免除损害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侵害并支付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1. 停止侵害
停止侵害是指权利人要求侵权人停止正在进行(而非已经停止或尚未实施)的侵害绝对权的行为[29]。侵害绝对权的救济应以停止侵害为主[30],以制止侵权行为,防止侵害进一步扩大。但在知识产权领域,一旦侵害事实发生便施以停止侵害责任过于绝对。绝对化的停止侵害救济模式源于对知识产权的物权化理解和对知识产权排他性的错误认识[31]。不加限制地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会对自由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等造成负面影响,有悖知识产权保护的宗旨[32]。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在保护权利人权利、实现社会经济秩序安定的同时,还要使个体效率与个体成本、社会效率与社会成本达到最佳配置[33]。因此,不应绝对化地适用停止侵害,可考虑适用替代性措施。然而,尽管法院可以在认定某一行为构成侵权的同时不判令行为人停止侵害,但侵权行为的存在意味着对权利人市场份额和预期收益的继续侵占,因此,判令“不停止侵权”并不能成为法律责任承担的终点[34]。正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当不宜适用停止侵害时,可以采取更为合适的替代性措施。司法实践中,对替代性措施也多有采用在南京现代雕塑中心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销毁被诉侵权产品会使个体利益失衡,因此不支持停止侵害。在2006年广州新白云机场幕墙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考虑到机场的特殊性,停止使用不符合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准许其使用被控侵权产品,但应支付使用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一)》(以下简称《品种权司法解释(一)》)第7条第2款规定,侵权物正处于生长期或者销毁侵权物将导致重大不利后果的,可以不采取责令销毁侵权物的方法,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相较而言,《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第10条所规定的“销毁生产中的植物材料,已获得繁殖材料的,不得销售”,《品种权司法解释(二)》第14条所规定的“责令采取消灭活性等阻止被诉侵权物扩散、繁殖的措施”等停止侵害的简单处理方式值得商榷。因为此类处理方式对权利人不具有任何效用,权利人无法从该灭活处理行为中获得损害补偿,且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因此,处理有价值的侵权产品不能简单地“一毁了之”或“一禁了之”,而应当考虑其他替代性措施。
根据《品种权司法解释(一)》的规定,侵权物正处于生长期或者销毁侵权物会导致重大不利后果的,可以采取替代性措施。此外,适用停止侵害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或停止侵害难以实际履行、无益于弥补权利人损失等时,也可以考虑采取替代性措施。停止侵害的替代性措施可以是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以及由权利人获得侵权产品或收获物等。支付合理费用由品种权人或被许可人与侵权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参照品种权的许可费确定。事后许可是指由侵权人与权利人达成许可协议,支付许可费,变侵权实施为合法实施。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采取事后许可方式,可避免造成破坏交易秩序、浪费资源等消极后果,产生侵权方与权利人各得其所的“双赢”积极效果。事后许可与支付合理费用有一定相似性,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支付合理费用属于一次性行为,侵权人将其当前持有的被诉侵权植物新品种进行销售或使用等处理后,应当停止后续侵权行为;而事后许可意味着侵权人对当前持有侵权物进行处理后,仍可基于权利人的事后许可继续销售或使用。此外,还可以由品种权人或被许可人与侵权人协商取得侵权产品或被诉侵权繁殖材料的收获物,以弥补因合法来源抗辩成立而不能请求损害赔偿的损失。此种情况下,权利人应支付给善意侵权人必要费用。
2. 支付合理开支
合理开支是指因知识产权遭受不法侵害,权利人为查明侵权事实、收集证据、制止侵权行为或进行诉讼所支出的、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的各种费用,主要包括侵权行为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以及律师费。诉讼维权的合理开支体现为当事人获取(接近)正义的成本[35]。当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主张的损害赔偿虽然得不到支持,但为维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得到补偿。
品种权人或被许可人在诉讼过程中涉及查明事实、搜集材料等工作。在此过程中,权利人首先需要购买涉嫌侵权的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并对购买的繁殖材料是否与其受保护品种的繁殖材料一致进行公证和鉴定,由此产生的购买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交通费、差旅费等都属于调查取证费用,应当由侵权人支付。但并非全部调查取证费用都应由侵权人承担,必须对费用用途进行真实性、关联性、合理性审查。真实性是指权利人主张的费用必须真实存在,而不能借合理支出之名获得不义财产。权利人应对自己所主张的合理支出进行举证,出示收据或发票等能够证明交易真实存在的证据。关联性是指该支出是否与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以及制止侵权行为存在相关性。合理性又可理解为必要性,即权利人主张的合理开支是否为调查取证所必要。若来源提供者被列为案件的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则在侵权行为成立时合理支出应当由其承担,除非合法来源抗辩者自己愿意承担合理支出。因为合法来源抗辩者无主观过错,而侵权产品来源提供者具有主观过错,两者作为共同被告,若由无过错的合法来源抗辩者支付合理开支,明显不公[36]。
在侵害品种权诉讼中,权利人往往会委托律师,由此产生的律师费应计入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律师费一般由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约定,基于地域差异,律师费收费标准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对此,法院同样需要进行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审查,以确定律师费用的具体数额。对律师费的合理性审查主要包括委托合同所约定律师费是否明显高于正常行业收费惯例,服务费用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以免对合理开支的重复赔偿。真实性审查同调查取证费用一致,合理的律师代理费必须以执业律师已实际收取费用的正规票据为证据[37]。关联性审查主要涉及委托合同的内容,以查证该委托是否针对所涉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避免侵权人对品种权人的其他委托支出进行赔偿。
3. 返还所获利益
对于善意侵害品种权所获利益是否应当返还,大部分国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我国司法解释对此亦未提及。判断是否应当返还,首先需要明确善意侵权所获收益的性质。有观点认为,善意侵权所获收益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38]。按此观点,善意侵权所获收益应当返还,因为不当得利规范的目的乃在去除“受益人”无法律上原因而得到的利益,而非在于赔偿“受损人”所受的损害,故受益人是故意或过失,其行为是否具有可资非难的违法性,均所不问[39]。另有观点认为,适用不当得利实际上是变相地要求善意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将侵权收益认定为不当得利[40]。本文认为,侵权人因其善意侵权客观上获得了无法律依据的利益,权利人因侵权行为而受到损失,且权利人所受的损失与善意侵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行为人侵害他人权益纵无过失(善意),也不应当保护其所获得的利益,这是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41]。善意侵权所获利益应当返还在有关规范中也得到了体现。如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后半句规定:在适当情况下,各成员可授权司法机关责令其退还利润和/或预先确定赔偿金(pre-established damages),即使侵权人不是故意或没有充分理由知道自己从事侵权活动。
考虑到侵权人的主观善意,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应限定于现存利益。“利得人为善意者,仅负返还其现存利益之责任;所谓现存利益,系指利得人所受利益中于受返还请求时尚存在者而言;于为计算时,利得人苟因该利益而生具因果关系之损失时,如利得人信赖该利益为应得权益而发生之损失者,于返还时亦得扣除之,盖善意之利得人只须于受益之限度内还尽该利益,不能因此更受损害。”[42]“善意之利得人,惟于现存利益之限度内负返还之义务……现存利益,谓利得人所受利益中于受返还请求时尚存在者而言。现已消灭者,不问消灭原因如何,利得人不负其责。”[43]根据我国《民法典》第986条规定,主观善意的不当得利人仅返还现存利益,取得利益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利益的义务。返还现存利益时,应当扣除必要的费用。善意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会产生一些费用,如购入侵权植物品种的成本费用、经营场所的租金、运输费用等,在返还不当得利时此类费用应当扣除。
五、结" 论
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作为平衡权利人和善意侵权人利益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以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以及过错责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基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特殊性,目前我国尚未在立法层面规定合法来源抗辩,仅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规定且表述较为简单。基于上文分析,我国《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应在现有司法解释基础上,参照《专利法》《商标法》和有关立法的规定,设置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就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行为而言,应在现有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销售行为”基础上,扩展至使用行为(种植行为)、销售行为和许诺销售行为;在主观方面,可保留现有表述方式,即“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以严格界定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条件;在客观方面,应明确“合法来源”的具体内涵;鉴于《种子法》已将品种权保护延伸至收获材料,故应将侵权对象由“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扩展至“被诉侵权品种繁殖材料或收获材料”;明确善意侵害品种权所获利益应当返还,但应以现存利益为限。
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灵活适用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品种权侵权人主张合法来源抗辩鲜有成功之例,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合法来源抗辩的证明标准缺乏明确具体规定,加之通过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以实现种业振兴的战略要求,法院在认定合法来源抗辩时,往往会对相关证据进行严格审查,从而大大增加了证明难度,难以实现合法来源抗辩的制度功能。因此,法院应当结合个案对不同类型的侵权人课以不同的证明责任,对证明能力较强的侵权人课以较重的举证责任,对证明能力较弱的侵权人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在适用停止侵害时,法院应根据个案情况采取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等替代性方式,以平衡各方利益,并在审查合理性、真实性与关联性的基础上确定合理开支数额。
总之,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体现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政策要求如2021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要求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2022年,《关于保护种业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营造种业振兴良好环境的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侵害种业知识产权行为;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专门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及考虑侵害品种权特殊性的同时,立法上应设置合法来源抗辩制度,至于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的适用难点,可通过不断丰富的司法实践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刘振伟.努力提高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改 [J].中国种业,2022(2):1-4.
[2]刘振伟,张桃林.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 [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23.
[3]宋承恩.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质面向——英国法之启发 [J].月旦法学杂志,2002(4):272-286.
[4]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51.
[5]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M].徐国栋,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47.
[6]黄建文.合法来源抗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审查的合理性分析 [J].知识产权,2016,26(10):32-38.
[7]戴秋燕,宁立志.专利善意侵权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 [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2):61-72.
[8]张新宝.侵权责任法 [M].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6.
[9]程啸.侵权责任法 [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12-113.
[10]王利明.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损害赔偿制度的亮点——以损害赔偿为中心的侵权责任形式 [J].政法论丛,2021(5):15-24.
[11]吴香香.中国法上侵权请求权基础的规范体系 [J].政法论坛,2020,38(6):172-181.
[12]朱建国,邹萍.亚洲部分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文献汇编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23.
[13]张振锋.论知识产权滥用的界定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4(1):73-80.
[14]尹新天.新专利法详解 [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15]吴亮.农民留种行为与品种权的冲突及其解决——立足于美国“农民留种免责”规则的考察 [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6):73-80.
[16]冯晓青.商标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99.
[17]欧修平.知识产权法中“不知道”的含义 [J].人民司法,2012(5):91-94.
[18]许传玺,石宏,和育东.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条文部分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
[19]谢晖.“应当参照”否议 [J].现代法学,2014,36(2):54-66.
[20]麻昌华,陈明芳.《民法典》中“应当知道”的规范本质与认定标准 [J].政法论丛,2021(4):127-138.
[21]廖焕国.注意义务与大陆法系侵权法的嬗变——以注意义务功能为视点 [J].法学,2006(6):28-33.
[22]李洁.知识产权审判中合法来源抗辩之审查 [C]//最高人民法院.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460-468.
[23]晏宗武.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 [J].法学杂志,2006,27(4):144-146.
[24]徐卓斌.专利侵权纠纷中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 [J].法律适用,2022(12):96-106.
[25]吕娜.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合法来源抗辩——以专利侵权诉讼为例 [J].人民司法,2007(19):83-88.
[26]李秀芬.从诉讼证明的角度看消极事实的特征 [J].法学论坛,2006,21(4):90-93.
[27]陈中山.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认定 [J].人民司法,2019(28):36-40.
[28]王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 [J].社会科学战线,2020(8):267-271.
[29]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 [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375.
[30]黄金菊,陶恩萍.不可量物民事侵权救济制度比较研究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92-96.
[31]陈武.权利不确定性与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之限制 [J].中外法学,2011,23(2):357-368.
[32]张云鹏,张啸天,王娜,等.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4(2):58-64.
[33]杨涛.知识产权法中的停止侵害救济制度 [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01-114.
[34]王国柱.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特殊法理 [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4):114-125.
[35]陈志兴.专利侵权诉讼中法定赔偿的适用 [J].知识产权,2017,27(4):29-34.
[36]朱文彬.论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合理费用承担的认定——汪文旭诉诚立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评析 [J].科技与法律,2013(3):85-91.
[37]窦玉梅.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之确定 [J].人民司法,2008(11):42-44.
[38]张玉敏.侵害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J].法学论坛,2003,18(3):20-28.
[39]王泽鉴.不当得利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
[40]乐耀.论专利善意侵权案件中不当得利制度的不可适用性——兼评《专利法》第70条 [J].金陵法律评论,2017,26(1):197-221.
[41]邹海林.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及其相关问题 [J].法学研究,1996,18(5):153-161.
[42]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16-217.
[43]史尚宽.债法总论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92.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for infringement of variety right: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application boundary and legal consequences
WAN Zhiqiana,b, WANG Zijiea,b
(a.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ule of Law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is one of the common defens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protection, the bona fide third-party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The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is a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claim damages for infringement.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variety right holder and the bona fide infringers, its application boundaries should be clarified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acts,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objective elements. If the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is established, the infringer shall cease infringement and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The application of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should be replaced by such remedial means as payment of reasonable expenses, post-facto licenses, and obtaining infringing objects, and the amount of reasonable expense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easonableness, truthfulness and relevance. The return of benefits obtained by bona fide infringers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existing benefits. China should draw on the legislation in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fields,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defense system of legitimate source of infringement of variety rights.
Key words: variety right;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bona fide infringement;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reasonable expense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