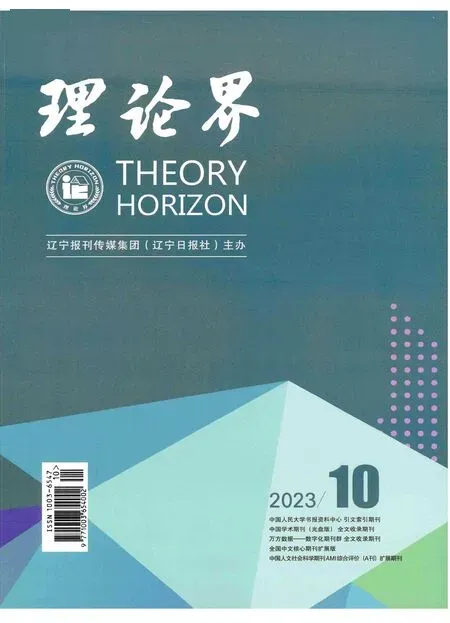主体认同的理论构想
——基于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
2023-12-29酒海明
酒海明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凝结着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论述,这一理论内容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将着眼于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分析其中的结构系统特征,进而具体论述观念性思想系统及其与主体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梳理和分析制度性机制及其具体内容,从而探究这一机制与主体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结构系统性:阿尔都塞、普兰查斯政治意识形态理论的抽象特征
在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那里,他们都将结构主义的理论特点注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分析之中。意识形态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基础,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制度性机制又内在于其中,那么就抽象特征而言,意识形态具有结构系统性,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样态,阿尔都塞作出这样的规定:“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1〕,“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2〕在以上论述中,阿尔都塞借助结构主义的理论特点对意识形态进行解读,其中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意识形态表象体系作为一套由各种思想内容构成的规范系统,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规约实践效用,成为社会现实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结构,同时作用于主体化的生成过程,主体认同内在于这一过程之中。在阿尔都塞的高足朗西埃看来,其老师所理解的表象体系亦是一套规约系统,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幻觉系统存在。〔3〕另一方面,就实践过程而言,意识形态具有“非强制”的无意识特征。借用卢卡奇有关物化意识的相关论述可以更好地理解。物化意识统摄下的主体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误认,即对物的神秘性的误认,将由本质呈现的表象错视为本质,存在一种认同的错位,而且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而主体之为象征界主体而不是处在想象界的个体,正是因为个体在意识形态结构系统之中得到了“注册”,比如阿尔都塞所述的“体验”关系就是“注册”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并非只有单向度的传播路径,以一种认识论层面的宣传教化抑或是陈述句形式的强制性命令与要求,而是凭借其外化的“文化客体”进行传播,即现实的、可感可知的客观世界的结构系统。比如,卢卡奇所言的物化的社会结构亦是这一抽象性、结构性概念的具体体现。进一步来说,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性机制具有了在社会历史结构之中普遍性、系统性及永恒性存在的意味,人们又不得不生存在意识形态之中,正是阿尔都塞所言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4〕。人们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从事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在形式上具有非强制的无意识“体验”“想象”关系。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无历史问题的论证展示出共时性的结构维度。阿尔都塞吸收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永恒性—无历史论断,在结构主义的视角切入,认为意识形态“在整个历史(=有各社会阶级存在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中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5〕,“这种结构和发挥功能的方式以同样的、永远不变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的整个历史中。”〔6〕可以说,意识形态内化在组织机构及制度性机制之中,就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构系统形式而言,具有相对无历史的特征,进而可以成为国家制度系统得以良性运作的基本构成性因素。
普兰查斯和其老师阿尔都塞一样,在结构系统维度论述意识形态,延伸出对于机构和结构的基本理解,构成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集中论述的理论先声。普兰查斯对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系统样态进行了论述。即“占主导的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形态中唯一的意识形态:有几种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子系统,与斗争中的各种阶级有关。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是它通过成功控制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子系统而形成的。”〔7〕普兰查斯的这一表述意在说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需要在各种意识形态及其系统的对抗之中占据领导权。而且,这里的意识形态子系统就是普兰查斯所理解的意识形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将诸多子系统联合起来的观念性思想系统。此外,意识形态和社会中的各种机构及其结构系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普兰查斯指出,“结构概念包括了机构组织化了的矩阵。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结构总是隐藏在它所建构的机构系统中,并被其组织。”〔8〕这一论述中具有两个层面的理解向度。其一,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机构组织化为一套“矩阵”系统,机构系统之中具有内在的结构。各种机构就其形式而言是一个尚待占据的“空位”,这就需要将机构概念放置在权力维度进行分析,因此,“机构只能与掌握权力的社会阶级有关。”〔9〕普兰查斯又指出,尽管机构和统治阶级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机构完全受动地功能化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统治的工具,服从统治阶级的组织原则,因为这些机构还有一定的自组织特点,即“自主性和结构层面的特殊性”。〔10〕其二,组织化的机构系统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规约要义。这里的机构系统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含义较为接近,“机构是社会认可的规范或规则体系,因此,机构概念不能仅为一种司法—政治机构,因为公司、学校、教堂等也构成机构。”〔11〕各种具体的机构合目的性地按既定的规则,有机地组织成为一套复杂的结构系统,意识形态性的规约要求渗透在这套机构系统之中。普兰查斯的这段论述已经展示出意识形态的系统化和规范性等特征,这点在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中得以更加详尽地阐述。
综上所述,在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阐发之中,意识形态亦是一套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的系统性构成,结构系统性就是其抽象特征。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表象体系作为价值规约的思想性内容,具有结构性的形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结构,亦是主体认同的核心中介。在普兰查斯那里,意识形态具有系统性的形式,机构又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通过制度性机制的运作,意识形态渗透在各种机构之中。需要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看似存在一种宿命论式的悲观论调,实际是展示普通大众的无可奈何,即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建构情势下保持主体认同之误认关系,呈现资本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制度化的极端异化样态。
二、观念性思想系统:诸多意识形态部门间的链接与整合
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论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其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而言,普兰查斯对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进行了明确,认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并且具有统一性、渗透性等特征。其中,普兰查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非严格意义上的“部门”,展示意识形态部门间的潜在链接关系,其整体就是一套宏观意义上的观念性思想系统。
普兰查斯指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就是他对意识形态问题思考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批判性论述。普兰查斯指出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中是被多元决定的,“在一种社会形态内,意识形态是受到各种表现、准则、意念和信仰等因素的总体支配的。”〔12〕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单一、自在的说教或理论构想,而是受到多种文化、价值等观念性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形态。普兰查斯更加具体地指出:“由于事实上意识形态(即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是作为结构统一的一个部门环节而构成的,这种结构在某一阶级中占有统治地位,因为它在阶级斗争领域中发挥其效用。”〔13〕这里的结构(统一体)就是一种总体性构成,不同的意识形态部门配合制度性机制在这套结构系统之中承担建构幻想、协调维系、掩饰矛盾等规约功用。
就意识形态的诸多部门而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等内容渗透其中,各部门间的有机联合就是一套观念性的思想系统。具体来看,意识形态可以按照性质划分出不同的部门,比如“道德、法律、政治、美学、宗教、经济和哲学意识形态”。〔14〕就诸多意识形态部门有机组合的基本线索而言,意识形态的价值性、规范性内容深深地嵌入意识形态“部门”之中,总体上构成了一套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和引导的观念性思想系统。进一步看,意识形态配合制度性机制深入人心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观念性思想系统的形成,正如米歇尔·佩肖所指出的,“‘思想领域’是以稳定点的形式在社会历史上构成的,它产生了主体。”〔15〕比如,就具体的意识形态部门——道德而言,道德往往作为法的辅助出场,促进受道德教化影响的主体形成自反式的认同。
在普兰查斯看来,尽管存在多种的意识形态部门,但总是会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部门如同“普照的光”,主导并统摄其他意识形态部门。此类意识形态部门的核心特点就是能够最好地实施“掩饰”工作,可以有效地掩盖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客观事实,促使受众保持一无所知却又勤勉为之的主体认同状态。普兰查斯以与封建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宗教意识形态为例,作为论述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部门的例子。这点在经典作家的宗教批判思想中就可以得以体现。比如,恩格斯在功能解释维度论述宗教意识形态,“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16〕也就是说,宗教呈现意识形态性,成为群众回避痛苦、聊以自慰并获得虚幻自欺性满足的精神灵药,其中就形成了非理性的“情感”认同。回到普兰查斯那里,他明确地指出宗教部门的意识形态功能,“宗教意识形态正是最适合于掩盖意识形态本身统治作用。”〔17〕“它往往执行统治作用并且需要把自己的真正作用掩盖起来。”〔18〕也就是说,宗教认同基础上的群众并未察觉到宗教所肩负的意识形态职能。
需要进一步拷问的是:宗教“掩饰”功能的实现何以可能?实际上就是因为幻象和制度性机制的强强联合。一方面,宗教的“精神鸦片”功用就是为大众提供意识形态性的幻象,为信徒提供一层由信仰所支撑的幻象,进而屏蔽苦难或创伤,形成了一层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想象性关系来链接主体对宗教以及统治制度的绝对认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的“掩饰”还需要制度性机制,即教会、仪式、传教士等要素的组合。在此基础上,意识形态性的“掩饰”功能才能进一步展开。
显然,在文化价值多元化和传统思想领域不断分化的当代,很难达到类似中世纪天主教在各思想领域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诸多意识形态部门中,仍会有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部门,绝非某些西方学者所给出的诸如“意识形态终结”一类的意识形态性论断,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无意识形态的社会。”〔19〕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境遇之中,法律政治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部门,“法律政治意识形态最适于执行掩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形态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作用。”〔20〕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部门这里,“分离”就是一重手段,普兰查斯指出在封建时代意识形态宗教部门阶段,主要是建立一种依附性的关系,“假‘自然’和‘神圣’之名推行”,〔21〕即“把神圣和宗教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22〕相较于此,资本主义阶段下的法律政治意识形态部门则是追求形式上的分离,使得大众在国家共同体中获得形式上的自由以及平等的政治身份,即“使代理人从‘自然束缚’中分离和解脱开来”。〔23〕比如,具有法律保护的劳动者进行劳作,同时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会组织之中获得集体的认同感。也就是说,在制度性机制的分离、回溯、掩饰、调和的运作线索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部门完美隐藏了非正义的剥削行为,而且不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面目直接呈现,不明所以的劳动者在法律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劳动的再生产,实际上也就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参与到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闭环之中。与此同时,普兰查斯还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幻想关系进行明确,即“政治共同体中的‘同样的’、‘互不联系的’和‘孤立的’个人一律‘平等’的幻想”。〔24〕这层幻想关系反映在主体认同和现实活动的无意识维度,不同类型的幻想有助于掩盖阶级统治的剥削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并抚平社会矛盾,而且内在于思想系统之中,亦是制度性机制的关键一环。
概而言之,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渗透在意识形态各部门之中,这些部门又分布在各个具体的思想领域,其中会有某些部门占据主导地位,诸多意识形态部门间的有机联合就会形成一套观念性思想系统,这套思想系统就是维护社会统治、维护制度运作的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套思想系统将会联合制度性机制,一同影响主体的认同。
三、制度性机制:具象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作用于主体认同
众所周知,阿尔都塞讨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受到了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启发。阿尔都塞在理论层面论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臣服”系统,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唤问个体的系统,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内容上的互补性。宏观上看,这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内部的制度性机制作为一套预先存在的系统,凌驾于主体之上唤问主体并促其在象征秩序之中进行注册,使得“主体的各种观念(好像碰巧!)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25〕而且成为在“我”之外的“他者”,如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我”就是被“抛掷”到意识形态之中的个体,主体无法作为无负荷的个体存在于意识形态的真空之中自我决定,需要接受意识形态的唤问。由此,在特定历史时期,看似人们发挥其主体性进行言说,操纵和规范意识形态,实际上早已被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捕获,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其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思想根基。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度性机制与主体认同的内在关联及其理论特点就需要从阿尔都塞的相关论述中进行理解。
在阿尔都塞那里,文化意识形态职能与暴力统治职能交相呼应,具有更加潜在的同一性塑造与规范功能。相较于在公共领域中行使直接统治职能的暴力机器,蛰居于日常空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依附暴力机器及相关制度规范为其提供的“运行的一般政治条件”,〔26〕以文化意识形态的手段满足意识形态—主体认同关系的再生产。由此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制度性机制,有助于常态化地维护、稳固国家制度及政权。
具体而言,阿尔都塞指出应该形成多个具有覆盖不同思想领域、具有内在统一性并根据不同目标进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一系列并存的机构组织,存在于私人领域而非以往的政治领域即公共领域,共同组合成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比如“宗教系统、教育系统、政治系统、等等”,〔27〕总体上构成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历时性地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历史中具有相对不变的结构形式与制度性机制,作为国家制度系统得到良性运作的基本构成因素,而具有历史性、阶段性的国家政权则会产生不断的更迭。
相较于封建时代教会机器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学校机器就是促进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典型,这套机器将个体对于政治制度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视作再生产的具体目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机制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此,它已经成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结果的机制”。〔28〕学校作为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了完整的组织内涵、培养职能以及育人格局,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剥削阶级的合法性进行维护与巩固。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机器,将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的诸多环节,将富有规范性价值以及知识性等内容输入个体,不断强化意识形态性的“律令”,从而使个体被唤问(教化—引导)为具有思考能力的、能动的主体,进入由大他者所建构的一套面向主体的幻象。被唤问的主体可以在齐泽克对经典佳片《银翼杀手》的解读中进行形象化的理解,在对复制人及其质疑活动的主体性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复制人产生在工厂的制度化操纵系统之中,它们无法脱离工厂对其的预先设定,比如记忆、意志、性格。但是,当复制人偶然踏出符号秩序,意外得知主体的不可能之后,明晰其主体性的空洞位置,他们才开始获得具有批判反思性的主体意志,即“主体就出现于它在传统体系中失去其支撑的时候”,〔29〕进而开始综合其以往的记忆碎片。在这种情势下,质疑行为就成为复制人反思、拷问制度化整体对其规训的重要活动,复制人不再只是将自身视作客体,而是作为主体开始思考自己在象征界之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从而开始殊死反抗的路途。这样的故事性内容也从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制度性机制的极端异化和误用,形象化地展示出这套机制作用于个体主体化及主体认同。
在普兰查斯那里,他在1969 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曾提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尽管论述不多,但部分观点和阿尔都塞的理解基本一致。他在论文中指出:“如果国家被界定为维持社会形态的一种凝聚力,而且通过维持阶级统治来再现社会制度的生产条件,那么很明显,有关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着完全相同的功用。”〔30〕这里就已经展示出普兰查斯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制度性机制的基本理解,这些内容有助于维护社会制度的运作。不止于此,普兰查斯指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凝结在一个结构内部的机构和机器中,比如:教会—宗教机器、政党—政治机器、工会—工会机器、学校和大学—教育机器等。〔31〕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具体分支和基本构成而言,普兰查斯写道:“政党、工会或学校本身不是机器,而是政治、工会或教育机器等的分支。”〔32〕这点同阿尔都塞的观点基本一致,意在说明某个政党是归属于政党机器范畴的,具有一层种属关系。政党是具体的,而政党机器则是一种抽象的结构系统,这一内容又构成制度性机制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政党机器这个结构系统基本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会有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制定具体的意识形态。普兰查斯指出:“意识形态(规范和规则)和政治压制(社会规训)对这些机构或机器的运作进行干预。”〔33〕从这句表述中,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中的两重意蕴:第一,意识形态作为规则和规范,就是一种广义的制度,其规约要义渗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机构或机器之中。第二,机构或机器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同义表达,都将受到政治制度的规范和意识形态的引导,都是制度性机制的具体内容。在普兰查斯看来,葛兰西已经建构了将意识形态机器从属于国家制度的理论。可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需要服从国家制度的统一导向,而且意识形态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广义的制度。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服务于一种社会制度,制度性机制内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通过其文化功用作用于主体认同并维护社会制度的有序运作。
结语
上述对阿尔都塞、普兰查斯政治意识形态思想中的结构系统特征、观念性思想系统和制度性机制三大主题的揭示,突出了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之维,以在此维度下回视主体认同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凝结在一套观念性思想系统之中,从而作用于主体认同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是表明意识形态不仅是规范性、观念性的内容,同时具有物质化发展的趋向,需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中的制度性机制的协同与配合,从而来常态化地影响主体的认同。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论述了主体如何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规训的策略方案,因为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就已存在一个争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题,十分关注接下来要“怎么办”的现实问题,比如卢卡奇认为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葛兰西强调要争夺文化领导权。回到普兰查斯这里,他认为,“只有革命组织和阶级斗争组织才能最终‘逃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34〕阿尔都塞从阶级斗争视角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结构形式进行考察,并在描述性维度指出,“要懂得利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它的某些特定形式,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定要素。”〔35〕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需要关注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制度性机制的争夺和介入,究其结构形式而言具有中立性的特征,它作为一个开放的场域可以为不同阶级所定位和使用。也就是说,对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政治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分析,既需要明确他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异化发展的批判,又需要关注观念性思想系统、制度性机制的描述性。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有助于为我国意识形态制度化建设提供积极的理论参考,对此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地推动和提升我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鉴识能力,这种认知能力是巩固和维护我国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