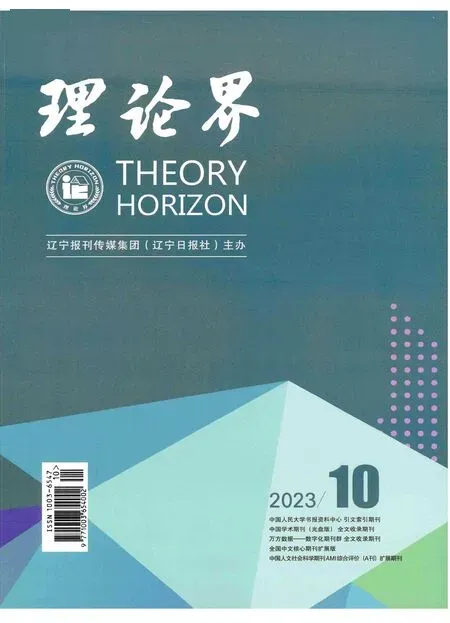新儒家构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奋勉:从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应对看
2023-12-29邱龙虎
邱龙虎
所谓新儒家是相对于原来以孔孟为代表的“旧”儒家即传统儒家而言的。根据郭齐勇先生的考证,最早提出新儒家这一名称的是冯友兰,用来指宋元明时期的理学或道学。当然,学界对于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至今仍有不同的界定。本文所探讨的新儒家指的是在西学东渐和民族危机双重压力之下,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力求恢复传统儒家文化主导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重建儒家伦理精神,以此来建构会通中西并继往开来的文化思想体系,从而成为符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独特文化出路。新儒家所倡导的新儒学一度是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立的三大思潮之一,〔1〕曾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在一些人看来,儒家文化在产生并需要它的历史社会环境瓦解之后,“无所为地只在心底象古玩般地被珍爱着”,〔2〕或者如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所言被保存到博物馆,作为一种象征性存在着的死亡。另一方面,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这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设定学术主题,彰显了全球哲学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价值的重视与期许。面对人类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往的新趋势,现代性问题于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现。儒家文化在被“祛魅”的同时能否为精神困顿、道德危机和文化割裂等提供一些解答,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参考?我们应该首先放下独断论的基调,从新儒家对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应对中抽丝剥茧,也许能寻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一、外来冲击的回应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伸张
著名学者费正清提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回应论。新儒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遭受文化冲击后的回应,还是儒学内在精神的伸张?这必须从儒家文化的发展来看。虽然总体而言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不同时期儒学的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场景各不相同,发展也有高潮与常态之分。学术界一般将儒学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先秦儒学,第二期为宋明理学或道学,第三期为新儒学。先秦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学说,与西方同时期的哲学家所追求的路线不尽相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伦理与世俗生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如果说孔子的内“仁”外“礼”作为一种处世之道的君子人格,仁是君子的内在德行,礼则是君子的社会规范,那么孟子的性善论则是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理论,为孔子的君子人格学说辩护,并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与性善论截然相反,荀子性恶论以人性本恶为立足点来弘扬儒家的教化学说。作为“礼”处理利害关系法则的运用,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与利对立,并取义舍利。作为一种普遍倡导的原则,其理论内在的自洽性自不待言。但是在先秦时期的社会环境下,儒家这一主张也在一定程度遭遇现实的困境,那就是君子必然会有生存的隐忧。这为墨家的显出创造了条件,墨家以义利合一来修补儒家关于“利”的缺失。因此,墨学起源于儒学,与儒学并称显学;就连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汉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百家争鸣的私家学说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官学的太学,并在此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到了宋元时期,经过儒道释合流,以儒家文化精神为内核的道学或理学逐渐演化而成,在追寻现象世界之后的本体和人性认识之间寻找关联。为重建儒学的形而上学,各种主张纷呈,如周敦颐和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等。在宋明理学或道学的理论体系中,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典型代表。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主张“即物而穷理”,向外寻找本体的认识。在宋代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的基础上,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通过内在良知将本体与本体的追寻融为一体,避免了朱熹的外在本体与内在良知的认识论难题。纵观宋明理学或道学,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更加成熟。虽然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标准来对比,不难发现其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的内容没有那么透彻,但是我们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这一要求本身就不符合常理。正如赖尔所言,这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所在,中国思维侧重指导如何做而西方思维侧重于知道是什么。〔3〕而且,宋明理学的旨趣也不是哲学上对理智或认识的把握,而是在于社会伦理的正当性和规范性,从而为世俗生活提供个体自觉的指引,正所谓“理性为一”。
到了新儒家时期,这种传统儒学的追求精神在外在的冲击下更加焕发出活力。如果说利玛窦来华传教化身汉儒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在官方和民间的主导地位。当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伴随传教士而东渐,中国先贤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不同,有识之士也开始研究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并不鲜见。鸦片战争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成两派:顽固派和洋务派。与顽固派坚守祖训盲目排外不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以开明的立场维护儒家文化的君主体制。与此同时,以严复为代表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子也极力宣传西方文明以启民智,科学、民主、自由等观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以梁启超的“欧洲科学破产论”为代表,对西方文化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质疑以及东方文化的优势发出强有力的呼喊,学衡派“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4〕表明了一批学人开放而坚守的传统儒家文化心态。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即是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潮论战的外溢,也是中国当时社会环境下全盘学习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与保留以儒学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纷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努力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寻找方向。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写道:“现在不是两种文化对垒的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化存亡的问题。”〔5〕面对西方文化的传入所展现的强劲态势,梁漱溟担心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否能够存续的问题,所以梁漱溟试图找出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回应文化上的问题,并由此避免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而让人生问题无法安顿。
从儒学发展的三个高潮期的表现上看,新儒家对现代性精神危机的回应不能仅仅理解为冲击—回应论。冲击—回应论有其合理的一面,看到了西方文化在传到我国的过程中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冲击,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刻影响。但是,这一理论确实属于西方中心论的基调,而且是一元论的视角,将文化视为相互冲突而不是在相互融合中发展,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实际情况毫不相符。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观点无视中国传统儒学中一直存在的为寻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所做的努力。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或道学,再到新儒学,儒家文化一直在融合其他各家文化中发展,包括外来的佛教文化,在不断融合中演化出新的文化样态。面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文化交融,儒家文化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寻求新的探索路径。
二、新儒家应对现代性精神危机的策略
无论是冲击—回应论还是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伸张,在面对现代社会的转型,儒家文化必然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涅槃重生。重思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新儒家的不二选择。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就是对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一番综合性的反思并与西方文化作对比,找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和优势,从而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文化寻找新的出路,并由此出发为中国人的精神寻找寄托。在方法上,梁漱溟通过直觉体验的方式来重建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从而对中国文化精神予以维护和创新的发展。冯友兰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诸多观点深以为然,在美国用英文发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推介梁漱溟的思想。对于梁漱溟进行东西文化比较进而为中国人精神安顿所作的努力,张君劢也完全赞同,他在《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中指出:“东方人之视其哲学,为道之寄托,可为择善信守之资……而西方人之视其哲学仅为一种学说一种意见。”〔6〕
新儒家应对现代性精神危机的重点内容是生命哲学。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心性之学的倡导价值就是做好一名君子并通过努力而成为圣人。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强调学习的功夫,再到孟子的“性本善”强调人有向善之心,再到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都是强调修性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则表现为在纷繁复杂的时局和利益面前,如何追求内心的宁静,通过自我修养以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实现人生境界的提高。梁漱溟不仅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传统儒家文化心性修炼的自觉,自身也言行一致并积极付诸实践,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家哲学课程,探索从心灵深处寻找人生意义并进行宣教。生命哲学中的人生境界学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贡献。冯友兰对传统儒学的人生意义深入研究之后,以人生觉解程度的高低为标准,提出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关于天地境界的划分从中国哲学层面上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作了精辟的归纳,完全超越了西方哲学中的道德学说对人的要求。而方东美则从人生实践的角度,依据所从事活动的价值类型高低将人生境界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形而下境界的自然人,包括“行能的人、创造行能的人、知识合理的人”,对应的人生境界又可细分为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和心灵世界;第二种是形而上境界的高贵的人或宗教境界,并在高贵的人之上还有宇宙精神的“皇矣上帝”。〔1〕必须指出的是,方东美一生致力于以人生哲学为基础重建新哲学体系,曾深入研究中西方人生哲学思想,其关于人生境界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人生哲学思想引到儒家人生哲学中来,或者说,利用西方的语言体系来描述儒家哲学思想,必然留有西化的痕迹。港台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对于人生境界的三层次划分“觉他而非自觉”“自觉而非觉他”“由自觉而超自觉”体现了生命的自在、自为和超越三种形态。这些新儒家对于人生境界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新儒学的学术空间。
新儒家们开展的第三项重要工作是结合西方哲学关注的内容对儒家文化一致或近似的地方进行丰富和深化,以呈现中国哲学的近代哲学体系特征。以本体论为例,在这方面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等做了重要工作。尽管梁漱溟一再强调儒学属于身心性命之学,不应纳入哲学范畴并讽刺熊十力的努力是“癖好思想这把戏”,〔7〕但是熊十力则持哲学定义之界定的开放态度,认为哲学以本体论为论域,中西差别仅在于西方从知识论层面追求本体,而中国从修养层面追求本体,殊途同归而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熊十力对本体—宇宙论孜孜以求。在熊十力看来,宇宙万物的现象之中有本体的存在,这一本体就是实体,它既含物质性也含精神性,从现象上表现为物质,从功用上表现为精神,实体与宇宙万物同一存在但又不隐藏于万物之后,同时“体用不二”“翕辟成变”即相反相成。从终极目标而言,熊十力的努力并非仅是为了哲学而哲学,其实质是以现代西方哲学体系来重建儒学,从而完成对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的超越。马一浮以心本体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必须指出的是,此心并非生理学的心脏,而是性、天、命、德;再通过“一心开二门”,对应形而下的功夫论和六艺论。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来重建中国哲学,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理本体”创造了程朱理学的新发展,在海内外影响深远。对于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在这方面的努力,杜维明作了高度评价:“承继了熊十力的本体探究和梁漱溟的心性修炼,完成了数百万言的有关儒家心体、性体和心灵境界的巨作,为儒家哲学注入了新理念、新范畴、新方法和新思路”。〔8〕
三、新儒家应对现代性精神危机问题的审思
以科学与民主为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挑战并大获全胜。儒家文化似乎面临着被消亡的境地,依笔者之见,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使得儒家文化得以涅槃重生:新文化运动削减了俗儒文化的消极方面,儒家文化的积极方面反而获得了重生或发展的机会。此后,以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精神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民族文化再次冲突,虽然论战的最终结果是科学主义阵营胜利,但是以“玄学鬼”张君劢为代表的主张“科学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也让儒家文化在科学主义的碾压下获得了生存的空间。
新文化运动和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给新儒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主题:儒家文化对民主与科学的应答。在儒家文化对民主问题的应答中新儒家并没有从西方的民主的实施形式方面着手去论证中国古代也有选票式民主,而是强调在儒家文化中存在着民主的文化基因和主张。在这方面观点最为鲜明的是张君劢,他提出儒家文化中的选贤任能、关注民意、自由言论、孟子王政思想主张天下为公、宋明时期儒家主导下的乡约都具有民主的种子,孟子的王政思想就是要服务于百姓。此外,贺麟力图以仁为本体论重建中国哲学、方东美等肯定儒家文化从自然人到具有宇宙精神的全人的道德境界的追求、余英时对士的传统和精神的历史梳理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儒家文化中关于民主的主张。在儒家文化对科学问题的应答中新儒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究,其一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儒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进行了追问。1921 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来的一种解释》,并于第二年发表在《国际伦理学杂志》(32 卷3 号)上,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9〕其二是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的新儒家认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能够包容近代科学。熊十力用“体用不二”的哲学体系开出知识论与外王学,马一浮以“一心开二门”的方式将科学归为“六艺”之组成部分的本体之用。〔4〕
新儒家从直接的学术主题拓展开来,挖掘西方哲学中与现代性相适应之内容的思想为参照,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类似思想之源头,并结合时代要求做新的阐发。张君劢认为儒家哲学思想中的基本概念如“理智的自主性,心的作用与思想,德性学说,宇宙的存在,现象与实体,或者道与气”〔6〕在现代社会中都具有复兴的价值,并身体力行以儒家哲学为基本,将之与西方哲学家的理论进行互相比较衡量或印证,从而使中国哲学的论证方法更加严谨,表述更加意义明确,分析更为透彻,更加适合现代生活的节奏需求,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反思中开辟了新的儒学论域,并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援佛入儒等,促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结语
发迹于轴心时代的儒家文化经几千年而不消亡,这一现象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面对现代性的精神危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以儒家文化为根本,寻找应对办法,体现了几代学人对于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空下传承与发展的艰辛求索,其探索的路径、方法和成果在现代学术史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我国的文化强国建设以及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儒家文化精神的伦理情怀,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而调和持中的态度等,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纷争,消解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化解文明冲突并参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待当代学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续写儒家文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