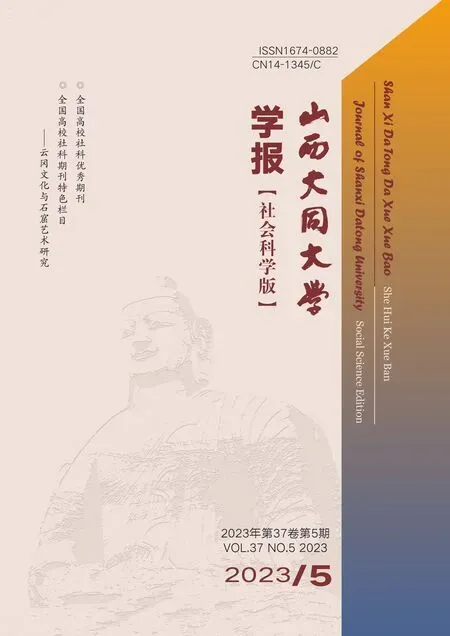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2023-12-29王俊虎张宸菡
王俊虎,张宸菡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曹禺在谈到自己戏剧创作时曾经说过:“如果我,还有田汉、夏衍、吴祖光这些人,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没有深厚的中国戏曲根基,是消化不了西方话剧这个洋玩意儿的。”[1]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话剧创作的影响之深。
一、家庭文化的影响
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曹禺的童年生活对他的戏剧创作影响极大。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曾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被授予过陆军中将军衔,担任过镇守使,当过总统黎元洪的秘书。“一般来说,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或者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的子弟就个人成长和发展来说,具有其他家庭或家族无可比拟的优越性”[2](P5)可家庭生活的优裕不但没有给他增添快乐,反而成为曹禺幼年时期精神苦闷的源头。
(一)家庭观念的异化 曹禺的家庭和许多官僚大家族交好,其中有一位周七爷和他的父亲万德尊来往十分密切,因此曹禺能够有机会观察其他官僚家庭的生活,了解这些人和事,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曹禺说“周家和我家是世交,周家的摆设很气派,《雷雨》的布景就有周家的印象在内。”[3](P9)周公馆中金黄的铜门纽、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的巨大的法国窗户和屋内富丽的陈设等就是作者根据周家摆设的印象设计的。尽管生活富足,但“家庭”这个概念对曹禺来说并不温馨,反而是压抑和痛苦的代名词。曹禺对自己家庭氛围的印象是这样的:“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3](P8)《雷雨》中的周公馆“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但气氛却是“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整个家中飘着一股死气,实在没有一个家的样子,这样的描写明显是受到曹禺原生家庭的影响。“我父亲这个人自命清高,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3](P7)万德尊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尤其是对曹禺同父异母的哥哥万家修管束十分严厉,他希望光宗耀祖的愿望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实现,因此当他发现万家修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时,失望至极,不但破口大骂,甚至下跪哀求儿子,盼他走上正道。从曹禺父子的身上,读者也能看到周朴园父子的影子。周朴园独断专横,对长子周萍十分严厉,嘱咐他“矿上的事要做就要做到底,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叫旁人说闲话的。”[4](P47)紧张的父子关系正是周公馆内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的部分写照,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作者潜意识中的家庭观念生根发芽的结果。
弗洛伊德说,“我们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一是肉体,二是外部世界,三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其中我们在与他人关系中受到的痛苦是最大的。[5]窒息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曹禺备受压抑,这在他的剧作中还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即压抑与反叛的模式,曹禺的很多剧作都是以大家族为背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雷雨》和《北京人》。作品中的家庭即是以血缘关系和宗法纽带维系起来的中国封建家族的代表,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被支配和禁锢,他们的天性往往被压抑,结局不是出走就是毁灭。这种家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尊卑关系也难以维持。在这种情景中,一旦有家庭成员要挣脱缰绳去寻求自由和解放,这种脆弱的平衡就要被彻底打破,繁漪亲手将自己和其他家人拖入了命运的绝境,瑞贞毅然决然地出走,她们都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得不和家族抗衡。反叛者的存在是这种戏剧叙事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对父权秩序的抨击 在封建家庭中,父权秩序一般以“父子”关系为轴心,表现出父权至上的特点。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曹禺渴望做个反叛者,可他的出身注定了这种反叛是不彻底的,他竭力去抨击父权秩序,却又时时受到这种思想的制约。《雷雨》中的周朴园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形象,周公馆中的大事小事都由他一人独断专行。周萍说:“父亲就是这样,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再如《雷雨》中周朴园命令周萍下跪为繁漪侍药的场面,更体现出封建大家长的专制霸道。繁漪这个形象则是受父权秩序迫害的典型,父权秩序和封建礼教把她变成了果敢阴鸷、怨恨阴郁的模样,她告诉周萍“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4](P92)作者赋予了繁漪反抗父权秩序的胆量和气魄,但这种反抗同样不够彻底,这是她个人的内在矛盾导致的。若她真正被新思想启迪,她大可直接离开周公馆,不必把周萍看做自己命运唯一的救命稻草,不会沦落到“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位置上去,若她愿意做一个传统女子,她该规规矩矩地拿出母亲的样子来,相夫教子,就是在这样新旧矛盾的压迫下,她没能真正离开周公馆,但她的胆量和气魄映射出作者对父权秩序的憎恶与抨击。
此外,曹禺还创作了一系列封建大家庭的长子形象,来表达对父权秩序的抨击,这些人往往被父辈寄予了振兴家族的厚望,但自己却沉溺于声色犬马,最终只能成为软弱无能的败家子,走向自我毁灭,他们亦是父权秩序的牺牲品。《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4](P510)《雷雨》中的周萍也是这种形象的典型,“和他谈两三句话,便知道这也是一个美丽的空形,如生在田野的麦苗移植在暖室里,虽然也开花结实,但是空虚脆弱,经不起现实的风霜。”[4](P41)
二、中国古典戏曲文化的影响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代表人物,一直被认为是受西方戏剧影响最大的中国剧作家,更有甚者认为他的戏剧是西方戏剧的嫁接与移植,然而他其实是带着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文化因素去审视西方话剧,并将话剧中的很多元素中国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因此直接将曹禺的剧作和中国传统戏曲割裂是不妥当的。曹禺自小对传统文化十分热爱,当他还没有进入中学时,诸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甚至《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小说他就都读过了。曹禺童年迷恋戏曲,与继母薛咏南有很大关系,继母看戏时往往都要把小曹禺带在身边。“天津不少著名演员的演出,谭鑫培、杨小楼、刘鸿声、龚云甫、陈德霖等名角的戏他都看过,京剧、昆曲、河北梆子以及能够在天津看到的地方戏曲,他都喜欢。”[3](P31)
(一)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 曹禺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气质突出、充满艺术感染力的女性人物形象。“曹禺把她们作为一个个鲜活而真正的“人”去描写刻画,凸显她们的人性,把她们的命运与整个时代和社会紧密联系,赋予这些女性以人格美与人性美。”[6]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剧作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注重描绘女性形象的传统戏曲中,作者往往通过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来颂扬女性的崇高精神和她们身上真善美的特质,如具有反抗精神、誓死不向黑暗和强权屈服的窦娥,具有英雄精神、巾帼不让须眉气质的花木兰,出淤泥而不染、坚贞不屈的李香君等等。曹禺的戏剧创作点往往在于从女性角度出发去寻找社会对女性的关注,细读曹禺的剧作,他关注女性所受的各种苦难,不论是受到当时封建社会的奴役,还是被男权主义思想所禁锢。[7]在现实与传统的重压下,女性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往往难以实现,她们的追求和背负的伟大使命与她们所面对的现实是矛盾的,因此她们的命运往往充满戏剧性,值得去挖掘和品味。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往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新式女性与传统女性,新式女性如陈白露、金子、繁漪等,往往带有现代女性的一些特质和意识。陈白露由一个向往自由和光明的女性,一步一步堕落为男人豢养的金丝雀,“虽然想要飞出这个金丝的牢笼,到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翱翔,但是笼子外面到处是凶兽恶禽,她恐怕根本飞不了多远就成别人的口中餐。”[8]繁漪疯狂而偏执,她对自我价值和欲念的追求将自己和他人一起带上了毁灭的道路;金子大胆而热烈,执着地想要突破现实中的枷锁和禁锢,让人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可能。这类女性往往敢爱敢恨,她们为了生存和自由向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发出了呐喊,甚至不惜以死抗争。这类女性形象的原型我们可以在李香君(孔尚任《桃花扇》)等角色上寻找到共同点。她们同样执着于爱情,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同邪恶势力大胆抗争。在曹禺笔下的传统女性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人》中的愫方,她看似柔弱的外表背后却藏着一颗金子般坚强的内心,她给予每一个人博大而无私的爱,她对瑞贞这样倾诉:“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爱,该爱,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4](P626)她具有人类最高尚而无私的灵魂,这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十分常见。除了这两种女性形象外,曹禺的作品也着重审视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悲惨女性,如侍萍、四凤、翠喜等,她们往往憧憬幸福,拥有美好的理想和灵魂,但是却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受到命运的摧残和嘲弄,这样的底层女性在传统戏剧中往往以妾或者侍女的身份出现。再者如焦母这种阴狠狡诈的封建家长形象,则与老夫人(王实甫《西厢记》)这类戏剧角色有着内在联系。多种女性形象的塑造说明了曹禺对女性的关注和解读,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女性的命运都值得思考和关注。
(二)戏剧氛围的构筑 除去女性形象的塑造外,曹禺戏剧的其他方面也受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传统戏曲具有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等特点,将唱词、美术、表演等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讲究和谐统一的表演效果。曹禺在自己的戏剧中同样融入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精华,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了本土化的特征,达到了浑然天成的效果。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唱词和小调的运用上,这在《原野》中尤为突出。第一幕开幕不久,仇虎和金子久别重逢,仇虎唱道“正月里探妹正月正,我与那小妹妹去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哟,妹子,我试试你的心哪,咦哈呀呼嘿!”[4](P359)这段小调烘托了欢快的气氛,使仇虎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紧接着不久,常五作为焦母的探子出场,他用破锣嗓子含糊地唱道“送情郎送至大门外,问一声我的郎,你多咱回来?回来不回给奴家一个信,免的是叫奴家挂在心怀!”[4](P362)这段唱词则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渲染了紧张的气氛。当仇虎开始正面和焦母对峙的时候,《妓女告状》的唱词在剧中多次出现,这段唱词将仇虎和焦母二人之间紧张的气氛渲染到了极致,仿佛就是仇虎的复仇宣言。再比如《家》中第二幕,觉慧与鸣凤在夜晚相会,二人共同在月色下朗诵苏轼的《水调歌头》,之后鸣凤说出了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幕情景的设计更能让人体会到觉慧和鸣凤的这份感情中隐藏的悲剧性。在高家的生活让鸣凤深深地感受到了二人地位之间的巨大差异,面对不可跨越的鸿沟和觉慧的理想主义态度,她明白这份感情只能走向凋零。曹禺曾多次强调自己写的话剧是“诗”。“不同于其他一些戏剧家,曹禺的创作通常不是先行确定一个明确的主题,然后再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写作,他常常是在某一瞬间心灵上获得了某种触动,产生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情绪,然后开始了他的构思和写作。”[9]综上可以看出,这些小调和唱词的运用在特定的情节中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烘托戏剧氛围和营造意境的作用,同时也给剧作增添了不少诗意。
另外,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出于表现形式的需要,各种各样的色彩也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如白色代表狡诈,黑色代表忠义等等,这些色彩的象征意义正是古代的戏剧创作者们在生活与实践中提炼总结出来的,这种以色彩为媒介的表现手法也在曹禺的剧作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如在《原野》中,不同的色彩就被作者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序幕一开始,映入读者眼帘的是黑得像乌金的铁轨,叫嚣的列车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电线杆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从序幕到终幕,从原野铁道旁到焦阎王家再到黑林子里,黑色一直都是贯穿全剧的主要色彩基调。黑色通过种种具体的物象展示在读者眼前,给人一种沉重而压抑的感觉,这也为后面主人公仇虎的出场和行动埋下了伏笔。除了烘托气氛之外,浓郁的黑色在交代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仇虎被焦阎王害得家破人亡,复仇二字也是贯穿整部剧作的主线,黑色也是仇虎整个人生的底色,他注定要在复仇中把毁灭带给所有人。在大环境里,黑色还象征着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像仇家这样的穷苦农民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注定要遭到剥削和迫害。当戏剧进行到第三幕时,仇虎与金子逃进了黑树林,仇虎在逃亡中产生了幻觉,喃喃自语道“好黑的世界!”伴随着阴沉沉的黑风和《妓女告状》的唱词,阎罗、幽灵、判官、青面小鬼等形象纷纷出现,然而金子却看不到这些,因为这都是仇虎心中的幻象,他在复仇完成后非但没有从前半段的悲惨人生中解脱出来,内心反而获得了更大的痛苦和煎熬。经过黑色的渲染,戏剧的气氛在此时到达了高潮,黑色也彻底浸染了仇虎的复仇之路,预示着毁灭和死亡的到来。
《原野》整部剧的基调是压抑和沉重的,从环境的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昏暗的色调和令人窒息的氛围贯穿全剧,然而在第三幕第五景的开头,曹禺却给读者展示了与前文不一样的环境和色彩基调,“天空现了曙白,……云海的边缘逐渐染透艳丽的金红。浮云散开,云缝里斑斑点点地露出了蔚蓝”[4](P485)这里出现了曙白、金红、蔚蓝等暖色调的色彩,与前面压抑绝望的环境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感觉漆黑的原野上仿佛出现了一丝生机与希望。“仇虎和金子在经过黑林子中一夜的逃亡后,面对着代表希望与美好的曙光,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是仇虎的自杀。不得不说,这种对物象色彩的选用和安排是符合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10]
三、儒释道文化的影响
“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戏剧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为曹禺的戏剧注入了丰厚的民族文化精神,是曹禺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消化系统,也是曹禺的戏剧作品民族化的秘密武器。”[11]因此有必要以儒释道文化为切入点,探寻曹禺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走近作者。
(一)“仁”为核心的人物精神特质 曹禺并未上过小学,父亲万德尊对洋学堂并不放心,让有儒学基础的外甥刘其珂来做曹禺的家庭教师。家庭的教学方法也不外乎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曹禺陆续读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书,儒学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渗进了曹禺的内心。他在儒家典籍中获益匪浅,“小时候读《论语》《孟子》,其中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话,我记得很牢,影响也不小。此外,‘贫贱不能移’,讲穷人要有志气,这种思想在旧小说里或者其他书里也有。孔夫子有个徒弟叫颜回,我小时候印象也很深,孔夫子对颜回喜欢得不得了,‘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虽然贫穷但不改其志,不改其乐。还有士可杀不可辱啦,士,就是穷的读书人,杀脑袋可以,受侮辱却不可容忍。这套东西,小时候,就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知道有钱人不是好东西。”[3](P21)因此每当他塑造人物形象时,对于那些具有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美好品质的人物,他往往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与同情,而对于那些为富不仁者,他往往大加鞭笞与抨击。前者如《日出》中沦落到下等妓院,却仍然有一颗金子般心的翠喜,还有天真可怜的小东西,以及善良到让人不忍直视的小书记黄省三。对于后者的描绘则更能体现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底,“剧作者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群‘生活在狭的笼里面洋洋地骄傲着’的‘可怜的动物’,他们自认为有钱有势,有本事,有手腕,在这个社会上混得不错,自我感觉极端良好,于是就处处忸怩作态:或作娇小可喜之态(顾八奶奶),或作黯然销魂之态(胡四),或故作聪明之状(潘月亭),或时显‘西崽’之相(乔治张),这都令观众鄙夷与厌恶。”[12]在这一前一后的对比中,可以见出曹禺在戏剧创作时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二)善恶因果论的体现 曹禺在童年时期有过随父亲读佛经的经历,尽管自己最后并没有成为一个佛教徒,但他对佛教思想并不陌生。他抨击世道的不公,同时也讲究做人的品德,即要扶善惩恶。打小继母薛咏南便教导他“你出去做事情,就放心地去做,该做就去做,什么都不要怕。你父亲没有干过什么缺德的事,他没有杀过人,害过人,你放心吧。”[3](P17)《雷雨》中的鲁侍萍在自己身份被周朴园识破时说道:“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正是因为30 年前自己的所作所为,间接导致了周萍和四凤兄妹乱伦的惨剧,在明白自己无法阻拦二人相爱时,她发出了这样的控诉“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人犯了一次罪过,第二次也就跟着来。”[4](P150)她将不幸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曾经造下的因。周朴园30 年前对鲁侍萍的离弃,间接导致了长子周萍同后母乱伦的惨剧;在事业上,他包修江桥,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两百个小工从而让自己获利,“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他叫警察开枪杀死矿上的工人,在矿上闹罢工的人却是自己的亲骨肉,最后唯一活着的儿子鲁大海也与他反目成仇。在《原野》中,焦阎王害的仇虎家破人亡,报应最终来到了自己的家人身上,寻仇无路的仇虎杀了阎王的儿子焦大星,而后又借焦母的手杀死了阎王的孙子黑子,然而复仇成功的仇虎也并未能得到心理上的解脱,最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同样是因果论的体现。
(三)对原始人性的赞扬《日出》开篇就引用了《道德经》中的原文,并借此点出了剧作的主题,即把众生分为“不足者”与“有余者”两个对立的群体,以表达对现代大都市所奉行的“损不足而奉有余”规则的抗衡。另外,在曹禺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的还有作者对原始自然人性的肯定和赞扬,追求人性的朴真和精神自由是道家思想永恒不变的主题。像《雷雨》中的“郁热”,并不单单指雷雨到来之前闷热的自然氛围,更暗示了一种原始的生命形式。无论是浑身充满破坏力和蛮性的鲁大海,还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周冲,抑或是陷入灵与肉的矛盾中不能自拔的周萍,都让人看到了赤裸裸的人欲,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繁漪这个形象,她是一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嘴角向后略弯,显出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4](P31)可是这种管制最后却失了效力,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她视家庭秩序如无物,她放声大喊“今天这一天我受的罪过你都看见了,这样子以后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地,以至于我死,才算完!”[4](P133)类似的女性还有《原野》中的金子,她忍受不了自己的窝囊废丈夫和歹毒的瞎子婆婆,她大喊“在焦家,自己是死了的”。单纯善良、自然爽直的她带着一种原始的神秘感,被曹禺赋予了野蛮与疯狂的个性,同时寄寓着曹禺对自由生命的渴望和原始蛮性的憧憬。[13]她们身为女性所展现出的原始生命的爆发力正是作者要大加赞赏的。
由此,不难发现曹禺在戏剧创作的过程中基于自己的个人体验,吸收和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这对广大读者与观众了解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品的深层意蕴有着重要的启示,这些创作特色与他伟大的作品一起,在人类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闪耀着永恒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