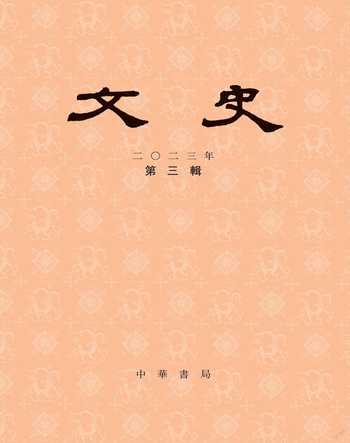王隱《晉書·地道記》斷限考
2023-12-25張仲胤
張仲胤
提要:分析王隱《晉書·地道記》各輯本,可見清代學者出於廣泛搜羅佚文的考慮,往往將佚文出處與《晉書·地道記》文字相近者一併輯録。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學者對《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的認識差異。在嚴格史料標準,重新搜集、梳理《晉書·地道記》佚文的基礎上,分析佚文所反映出的政區信息,以及沈約撰寫《宋書·州郡志》的方法和對《晉書·地道記》的運用,可推斷《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既非太康三年,亦非東晉,而是在晉武帝以後。
關鍵詞:《晉書·地道記》《宋書·州郡志》 斷限年代
一、問題的提出
王隱所撰《晉書·地道記》,是《宋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叙述晉代地理沿革的主要參考,史料價值很高。確定《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是利用其從事研究的前提。對其斷限,魏收曾道:“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地道》所載,又其次也。”據此,魏收似將《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定在西晉統一時期。現代學者對此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爲王隱《晉書·地道記》以東晉爲斷,另一種認爲王隱《晉書·地道記》以太康三年(282)爲斷。
王隱《晉書》早已散佚,學者只能搜集分析類書、舊注中所存之佚文,推斷《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清代學者在搜集《晉書·地道記》佚文方面用力頗多,形成了畢沅、王謨、黄奭、湯球四個輯本。然細按清輯本,可知其中常有誤輯,這一定程度造成了學者對《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認識的差異。因此,有必要重新搜集、分析《晉書·地道記》佚文,確定其中可靠的史料,將之作爲研究的起點。在史料可靠的前提下,分析沈約《宋書·州郡志》對《晉書·地道記》的運用方法,與《晉書·地道記》反映的政區信息,庶幾能對王隱《晉書·地道記》斷限問題略陳新見,爲研究中古時期政區沿革提供參考。
二、王隱《晉書·地道記》佚文與斷限研究
王隱《晉書》成書於晉成帝咸康年間,亡佚於唐末五代,其在中古時期曾廣泛流傳,屢被類書、舊注、地志徵引。清代樸學大興,輯此書者共有四家。細按之下,清輯本錯漏實多,正如顧江龍所言:“清人輯本主要有畢沅、王謨、黄奭、湯球四家,都存在嚴重問題。”因此,研究《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問題,應首先分析清輯本存在的問題,以及致誤之由。在此基礎上,再系統搜集、整理王隱《晉書·地道記》佚文,以確定一個符合現代學術研究標準的文本。
清輯本中有許多佚文並非出於《晉書·地道記》,這是由類書、舊注的引文方式,與清人輯佚方法共同造成的。類書、舊注徵引文獻,往往省稱書名;學者在輯佚時,爲求完備,又往往將書名相類者一併輯入。如湯球從《續漢書》劉昭注中輯録王隱《晉書·地道記》時,便將出於《晉地道記》《地道記》者一併輯入。據學者研究,劉昭所引《晉地道記》《地道記》並非出於《晉書·地道記》,而是《晉元康地道記》的佚文。
類似案例,如沈約在《宋書·州郡志》中明言徵引“王隱《地道》”,故學者在輯録王隱《晉書·地道記》時,便將《宋書·州郡志》中所見之“晉地志”“晉地記”一併輯録,湯球輯本即爲顯例:
1.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馥表立晉壽郡。
2.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表立。
3.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立。
王隱《晉書》表上於晉成帝咸康六年(340),王隱卒於晉穆帝時,因此《晉書·地道記》不當載有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之事,以上三條當屬誤輯。湯球爲輯佚大家,精研晉史,不當不知王隱卒年,但其仍將《宋書·州郡志》所見“晉地記”佚文收入《晉書·地道記》中。以理度之,其目的當在於廣泛搜羅相關材料,寧使網羅密如凝脂,亦不令其有吞舟之失。
爲廣泛搜集相關佚文,清代學者還將王隱《晉書》中的其他部分輯入《晉書·地道記》中。如從《水經注·都野澤》輯録王隱《晉書·地道記》:
涼州城有龍形,故曰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乃張氏之世居也。又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内作四時宫,隨節遊幸,並舊城爲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宫殿觀閣,采綺裝飾,擬中夏也。
查《水經注》,酈道元僅言此條出於王隱《晉書》,而未言其出於《晉書·地道記》。在《水經注》中,酈道元徵引《晉書·地道記》時,往往會標明其出處,如《水經注·河水》:“《晉書·地道記》曰:‘縣西有禹廟,禹所出也。”又如《水經注·夏水》:“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又如《水經注·淮水》:“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竝有義陽郡。”由此推斷,《水經注》中僅言出於《晉書》者,恐非出於《晉書·地道記》。且《水經注·都野澤》所引此條佚文亦不類地理志之體,復見於唐修《晉書·張軌傳》之中。湯球在輯録此段佚文時,亦對其是否出於《晉書·地道記》存有懷疑,其處理方式爲同時將其輯入《晉書·地道記》與《晉書·張軌傳》之中。同類情況,又如《太平御覽》曾引王隱《晉書》:“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鐘,聞七八里。”諦審此條内容,當出於《晉書·瑞異記》,而湯球貪多務得,將其同時輯入《晉書·地道記》與《晉書·瑞異記》中。
清代學者基於廣泛收録佚文的考慮,將書名相類者一併收入《晉書·地道記》中的做法,本無可厚非。但若將清代學者所輯佚文,一併視作出於王隱《晉書·地道記》,佚文所呈現出的斷限年代便會矛盾百出,其中既有西晉已絶之封國,又有東晉新立之郡縣,難以折中。從現代學術研究的角度,不應再受清輯本干擾,將書名與《晉書·地道記》相類者,或僅言出於王隱《晉書》者,視爲《晉書·地道記》;必須首先嚴格史料標準,將明確出於《晉書·地道記》者作爲研究對象。今重新鈎輯王隱《晉書·地道記》佚文如下:
1.《晉書·地道記》曰:“(大夏)縣西有禹廟,禹所出也。”
2.《晉書·地道記》《太康記》竝言胡縣也。
3.《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
4.案《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有中陽城。
5.《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竝言晉水出龍山,一名結絀山,在(晉陽)縣西北。
6.(南陽)秦始皇改曰修武。徐廣、王隱竝言始皇改。
7.《晉書·地道記》曰:“(高都)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
8.《晉書·地道記》曰:“(朝歌)本沫邑也。”
9.《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
10.《晉書·地道記》曰:“(肥鄉縣)太康中立以隸廣平也。”
11.(鴻山)《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
12.《晉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
13.《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陽安關,蓋陽安關都尉治。”
14.王隱《晉書·地道志》:“(上谷)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
15.(安樂縣)《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爲公國。
16.《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
17.“(坎欿)《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記》,竝言在鞏西。”
18.《晉書·地道記》,(新興縣)南安之屬縣也。
19.(雍縣故城南)《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也。
20.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
21.《晉書·地道記》曰:“天水,始昌縣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峽。”
22.王隱《晉書·地道記》曰:“(襄城縣故城)楚靈王築。”
23.(廪丘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廪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寔表東海者也。”
24.《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于魯城北泗水上。
25.《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
26.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竝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爲名。
27.《晉書·地道記》云:“(雩婁縣)在安豐縣之西南。”
28.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
29.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
30.(西陽縣)《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也。
31.《晉書·地道記》,(興古郡)治此(律高縣)。
32.《晉書·地道記》曰:“(日南)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
33.《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
34.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
35.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
36.《晉書·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
37.《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
38.《晉書·地道記》曰:“(泉陵縣)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供之以縮酒也。”
39.按《晉書·地道記》,其中水縣屬河閒。
40.《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
41.《晉書·地道記》(陽都)屬瑯琊。
42.《晉書·地道記》(蒯城)屬北地。
43.《晉書·地道記》(厭次)屬平原,後乃屬樂陵國也。
44.《晉書·地道記》(平州)屬巴郡。
45.《晉書·地道記》:“(元氏)改屬趙國,其常山郡移理于真定縣。”
46.《晉書·地道記》云:“改阜邑爲阜城。”
47.《晉書·地道記》云:“縣出美酒,隨歲舉上貢。刺史親付計吏。”
48.按《晉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汝陽郡。
49.《晉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此郡(汝陽郡)。
50.(上饒縣)《太康地志》有,王隱《地道》無。
51.(宜都郡)《太康地志》、王隱《地道》,何志並云吳分南郡立。
52.(臨賀縣)《晉太康地志》、王隱云屬南海。
53.(房陵縣)《太康地志》、王隱無。
54.(武陵縣)後漢、《晉太康地志》、王隱並無。
55.案二漢並無漢德縣,《晉太康地志》、王隱並有。
56.常安(縣),《太康地志》有而王隱無。
57.(南陵長)何志晉武帝立。《太康地志》無,王隱有。
58.《晉書·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
59.《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
60.《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
三、《晉書·地道記》斷限與“太康三年説”考辨
一般認爲,《太康地志》以太康三年爲正記載西晉政區。近年,顧江龍提出新論,依據《太康地志》載有明顯晚於太康三年的政區信息,認爲《太康地志》大致記載了西晉太康三年至太康十年的政區情況,並進而考證《晉書·地道記》嚴格以太康三年爲斷記載西晉政區。但考察沈約撰寫《宋書·州郡志》的方法,《宋書·州郡志》對《太康地志》《晉書·地道記》材料的運用,以及《晉書·地道記》所反映的政區信息,可知《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當在《太康地志》之後,並非嚴格以太康三年爲斷。
《晉書·地道記》是《宋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的主要參考,從沈約、魏收的叙述中,可知二人清晰了解《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尤其是沈約不僅徵引了《晉書·地道記》,而且還叙述了撰寫《宋書·州郡志》所運用的材料與分析方法,這無疑爲推斷《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提供了綫索。《宋書·州郡志》云:
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
胡阿祥將《宋書·州郡志》比作沈約綜合各種資料撰寫的一篇沿革地理論文,並總結沈約撰寫《宋書·州郡志》的方法爲:以何承天、徐爰《宋書·州郡志》舊本爲底本,“考覆”“辨析”各種文獻,確定州、郡、縣的沿革。具體而言,沈約以何承天、徐爰《宋書·州郡志》舊本確定了《宋書·州郡志》的基本斷限:“大較以大明八年爲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内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爲定焉。”在此基礎上,考覆“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地理雜書”等文獻,梳理政區在兩漢、三國、西晉、東晉、劉宋初的沿革。這一工作得以展開的基礎,是沈約對其所掌握資料的斷限年代有明確的認識。由此切入,分析沈約對《晉書·地道記》《太康地志》的運用,可推斷《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當在《太康地志》之後。
沈約在撰寫《宋書·州郡志》時,曾因《三國志》無志而面臨巨大困難,其解決方法是:“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其先以《續漢書·郡國志》《太康地志》確定了東漢順帝、晉武帝時期的政區格局;然後通過比較二者之間的變化,來推斷三國時期郡縣廢置的情況。從沈約以《續漢書·郡國志》《太康地志》來確定三國政區演變基本範圍這一點,可推斷在沈約所掌握的系統資料中,《續漢書·郡國志》《太康地志》當是時間下限、上限距離三國政區演變上限、下限最近的材料。由沈約以《太康地志》,而非《晉書·地道記》來確定三國政區演變下限這一點,可推斷《晉書·地道記》反映的政區斷限似在《太康地志》之後。
《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在《太康地志》之後,還可從《宋書·州郡志》“桂林太守”條中得到印證:“(桂林太守)《永初郡國》有常安、夾陽二縣。夾陽,晉武帝太康元年分龍岡立。常安,《太康地志》有而王隱無。何、徐並無此二縣。”可知常安縣見於《太康地志》,而不見於《晉書·地道記》。按:桂林郡進入西晉版籍在晉武帝平吳之後,《太平寰宇記》載太康元年晉武帝分武豐縣置常安縣:“慕化縣,本漢潭中縣地,晉太康元年分吴所置武豐縣置長安縣于此。”查唐修《晉書·地理志》,桂林郡並無常安縣,關於《晉書·地理志》的斷限年代,學界有太康二年、三年、四年三説。據《晉書·地理志》,則常安縣至早廢於太康二年,最晚廢於太康四年。學界對《太康地志》的具體斷限年代雖有争論,但均認爲《太康地志》反映的政區信息在太康三年之後。若《太康地志》以太康三(至十)年爲正,則常安縣當廢於太康四年,故《晉書·地道記》所載政區信息當在太康四年之後,其斷限年代亦應在《太康地志》之後。
此外,《宋書·州郡志》“南陵長”條亦可證《晉書·地道記》斷限晚於《太康地記》:“南陵長,何志晉武帝立。《太康地志》無,王隱有。”何承天在《宋書·州郡志》舊本中,認爲南陵縣爲晉武帝所立。沈約爲驗證此觀點、確定南陵長的設立時間,故引《太康地志》《晉書·地道記》爲證。按:南陵縣地在今越南義静省錦川地區,三國時屬吴,其進入西晉版籍在太康元年晉武帝平吴之後。查唐修《晉書·地理志》九德郡下有南陵縣。據此,南陵縣的設置時間最晚亦當在太康四年之前。從沈約言南陵縣“《太康地志》無”來看,《太康地志》此條所載必在太康三年之後、《晉書·地理志》斷限年代之前,即太康三至四年間。而從“王隱有”來看,《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當在《晉書·地理志》《太康地志》之後。沈約引用二書的目的,在於驗證南陵縣是否爲晉武帝所立,故以《太康地志》確定南陵縣設置時間的上限,用《晉書·地道記》確定下限。據此可知在沈約的認識中,《晉書·地道記》的斷限當在《太康地志》之後。
分析沈約在《宋書·州郡志》中撰寫三國政區沿革的方法,及其在“桂林太守”條、“南陵長”條中對《太康地志》《晉書·地道記》的運用,可見《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當在《太康地志》之後。若《太康地志》果以太康三年至太康十年爲斷,《晉書·地道記》則必不以太康三年爲正,此點在《晉書·地道記》佚文中亦有所反映:“《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可知在《晉書·地道記》中有東莞郡。西晉時期東莞郡的廢置情況,《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所載頗有矛盾,《晉書·地理志》載東莞郡爲太康元年晉武帝分瑯琊立:“及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縣,分琅琊立東莞郡。”但據《宋書·州郡志》:“東莞太守,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琊立。咸寧三年,復以合琅琊,太康十年復立。”則咸寧三年(277)至太康十年間無東莞郡,東莞郡復立於太康十年之後。從文獻角度來看,《宋書·州郡志》成書於《晉書·地理志》之前,所記當更爲可靠。此點亦爲顧江龍的研究所印證:其依據唐修《晉書·司馬伷傳》分析司馬伷封瑯琊王、晉武帝“以東莞益其(瑯琊)國”一事,推斷東莞郡當於咸寧三年併入瑯琊國。又依據唐修《晉書·武帝紀》所載晉武帝應允司馬伷分封四子一事,推斷東莞郡於太康十年分割瑯琊國封司馬伷四子時復立。進而得出結論:“可見東莞郡在咸寧三年的省併和太康十年重置,皆由司馬伷父子的封國發生了變化……而太康元年至四年之間其封國並無變化,應無置、廢東莞郡的理由,因此《晉志》‘太康元年實爲‘太康十年之誤。”顧説可從。據此,西晉時期東莞郡的存在時間當在泰始元年(265)至咸寧三年之間,以及太康十年之後。依據前文對《宋書·州郡志》“桂林太守”條、“南陵長”條的分析,可知《晉書·地道記》所載政區信息在太康之後。故《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的記載,所反映的當是太康十年之後的政區信息。據此,《晉書·地道記》的斷限上限不僅在《太康地志》之後,且應在太康十年之後,反映了晉武帝統治末期的政區情況。
顧江龍雖考證了咸寧三年至太康十年無東莞郡,但未細緻辨析《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的記載,仍認爲《晉書·地道記》“以太康三年斷代”。其依據主要有二,一爲《水經注·桓水》:“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顧江龍認爲此《晉地道記》即爲王隱《晉書·地道記》。並依據新都國立於咸寧三年廢於太康六年,而此條佚文有“新都”,推定《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當在太康六年之前。
其實,此論值得商榷。首先,西晉時期新都國並非僅存在於咸寧三年至太康六年之間。據《華陽國志·蜀志》:“泰始末,又分置新都郡。太康省。末年,又置新都王國,蜀郡常蹇爲內史。永嘉末省。”常蹇爲新都内史,見《華陽國志·後賢志》:“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内侯。遷魏郡太守,加材官將軍。以晉政衰,睹中原不静,固辭去官。拜新都内史。”據劉琳考證“從王起義”指常蹇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討伐司馬倫;“拜新都内史”指常蹇爲新都王司馬衍内史,司馬衍受封在惠帝永寧元年(301)之後。故據《華陽國志》記載,新都國存在的時間,並非僅在咸寧三年至太康六年之間,而是持續到永嘉末年。故不能依據《晉地道記》有新都,而認爲《晉書·地道記》斷限在太康三年。其次,《水經注·桓水》既言此條佚文出於《晉地道記》,則其是否爲《晉書·地道記》佚文便存在很大疑問。顧江龍既已指出《續漢書》劉昭注所引《晉地道記》《晉地記》不出於《晉書·地道記》,似不當徑將《晉地道記》作爲《晉書·地道記》,用以推斷《晉書·地道記》的斷限。
顧江龍推斷《晉書·地道記》以太康三年爲斷的第二個依據爲《魏書·地形志》。在《魏書·地形志》中,魏收於西晉北海郡所轄平壽、下密、膠東、都昌四縣下注:“晉屬齊郡。後屬(北海)。”顧江龍認爲《魏書·地形志》主要參考了《晉書·地道記》,故此注“晉屬齊郡”四字當源於《晉書·地道記》,“後屬(北海)”當出於他書。其又考證西晉咸寧三年至太康三年,無北海郡,故推斷《晉書·地道記》所載當爲咸寧三年至太康三年的情況。因此,其斷代下限當在太康三年。
此論理據不足。首先,《魏書·地形志》雖參考了《晉書·地道記》,但其體例與《宋書·州郡志》不同,魏收並未注明何處徵引何書。故在《魏書·地形志》的文本中,無任何證據能證明“晉屬齊郡”出於《晉書·地道記》。其次,魏收在《魏書·地形志》中雖言“晉又一統,《地道》所載”,但其在撰寫政區西晉沿革時,並非僅據《晉書·地道記》,兹舉一例以明之。《魏書·地形志》“陽平郡武陽縣”:“二漢、晉屬東郡,曰東武陽。後改,屬。”又“東郡東燕縣”條、“東郡白馬縣”條均言:“二漢屬,晉屬濮陽,後屬。”若將“晉屬東郡”“晉屬濮陽”均視爲出於《晉書·地道記》,則甚矛盾。按:《宋書·州郡志》:“南濮陽太守,本東郡,屬兖州,晉武帝咸寧二年,以封子允,以東不可爲國名,東郡有濮陽縣,故曰濮陽國。濮陽,漢舊名也。允改封淮南,還曰東郡。趙王倫篡位,廢太孫臧爲濮陽王,王尋廢,郡名遂不改。”可知,西晉時期東郡、濮陽國、濮陽郡名異實同,若以上《魏書·地形志》所記同出《晉書·地道記》,似不當濮陽、東郡同出。第三,從《晉書·地道記》佚文來看,王隱在記録政區時,往往述及沿革,如《史記索隱》引《晉書·地道記》:“(厭次)屬平原,後乃屬樂陵國也。”即叙述了西晉時期厭次本屬平原,後轉屬樂陵國的沿革。又如《太平寰宇記》引《晉書·地道記》:“(元氏)改屬趙國,其常山郡移理于真定縣。”便叙述了元氏縣由常山郡轉屬趙國,常山郡郡治移至真定的沿革。從内容上看,“(厭次)屬平原,後乃屬樂陵國也”頗類《魏書·地形志》“晉屬齊郡。後屬(北海)”。因此,即便《魏書·地形志》此注出於《晉書·地道記》,“晉屬齊郡。後屬”亦有可能出於王隱叙述政區沿革的部分。不能得出“晉屬齊郡”出於《晉書·地道記》,“後屬(北海)”出於他書的結論,更不足以據此斷定《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將《魏書·地形志》所記西晉沿革視爲出自《晉書·地道記》,已屬推斷;認爲“晉屬齊郡”出於《晉書·地道記》、“後屬(北海)”出於他書,亦爲推斷;咸寧三年至太康三年無北海郡,復爲推斷;三重推斷,皆無明文,以此確定《晉書·地道記》斷限,似有不妥。綜上可見《晉書·地道記》以太康三年爲斷的觀點,不僅與《晉書·地道記》所反映的政區信息相矛盾,且其立論依據亦存在問題。
總而言之,從沈約撰寫《宋書·州郡志》的方法、史料依據,以及《晉書·地道記》佚文所反映的地理信息來看,《晉書·地道記》並非以太康三年爲正,其斷限年代當在晉武帝太康十年之後。
四、《晉書·地道記》斷限與東晉説
在研究《宋書·州郡志》時,胡阿祥認爲《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可能在東晉時期,但並未展開論述。其後,蔣琪在研究《晉書·地道記》湯球輯本時,認爲《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當在東晉太寧二年(324)至咸和九年(334)間。細按《晉書·地道記》佚文可見,東晉説實有問題。首先,東晉説的依據並非出於《晉書·地道記》,而是來自湯球《晉書·地道記》輯本所引地理雜書,其主要論據如下:
1.《地道記》高平國下有金鄉,云:所治名金山,鑿而得金,故曰金山。
按:此條出《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晉地道記》,當爲《元康地記》佚文,並非出於王隱《晉書·地道記》。
2.《地道記》涼州下云:涼州城有卧龍城,本匈奴所築也。又張駿增築四城,相去各千步。
按:此條出於《水經注·都野澤》注引王隱《晉書》,並非出於《晉書·地道記》。其所記既非地理志之體,又復見於唐修《晉書·張軌傳》,故湯球兩輯於《張軌傳》《地道記》中。
3.《地道記》有東官郡
《地道記》東官郡有潮陽縣。
按:此條出於《宋書·州郡志》所引《晉地記》,並非出於《晉書·地道記》。
4.《地道記》苦縣下云:苦城南三十里有平城。
按:此條出於《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地道記》,並非出於《晉書·地道記》。
5.《地道記》梁州下云: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
按:此條出於《水經注·桓水》注引《晉地道記》,並非出於《晉書·地道記》,前文已述。
可見王隱《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在東晉的觀點,恐難成立。如前文所述,《晉書·地道記》斷限的上限在太康十年之後,那麽其下限是否及於東晉?從《晉書·地道記》佚文所反映的地理信息來看,《晉書·地道記》的下限應未至東晉。將《晉書·地道記》佚文與《宋書·州郡志》《晉書·地理志》比較,可見其反映的政區情況基本爲西晉時期的建置,未見東晉對政區的調整。又魏收於《魏書·地形志》中道:“班固考地理,馬彪志郡國,魏世三分,晉又一統,《地道》所載,又其次也。”可知,王隱《晉書·地道記》所載當爲晉統一時期的政區情況,故應爲西晉而非東晉。並且,在《晉書·地道記》佚文中,尚有西晉時期已絶之封國:
1.《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
2.(厭次)《晉書·地道記》屬平原,後乃屬樂陵國也。
3.《晉書·地道記》:“(元氏)改屬趙國,其常山郡移理于真定縣。”
據此三條佚文,可知在《晉書·地道記》中有趙國、樂陵國。趙國、樂陵國皆屬冀州,趙國立於咸寧三年;樂陵國見於《晉書·地理志》,則在太康四年之前應已建立。永寧元年,司馬倫篡位,同年受誅。趙國當滅於此時。由趙國推斷,《晉書·地道記》的時間下限當在永寧元年,但此條佚文似在敘述郡、縣沿革,並不能完全據此推斷《晉書·地道記》中有趙國。這一點也爲《晉書·地道記》所印證,《水經注·夏水》:
(夏水)歷范西戎墓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荆州記》、劉澄之《記》,竝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産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爲究悉,以親逕其地,故違衆説,從而正之。
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提及,《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荆州記》、劉澄之《記》均言陶朱冢在華容縣。但郭仲産在親履後,卻發現諸書所言不僅方位有誤,而且所謂陶朱冢實爲“故西戎令范君之墓”,所謂范蠡碑實爲永嘉二年(308)所立。如此,則王隱《晉書·地道記》“樹碑云是范蠡”的記載,當出懷帝永嘉二年之後。
但《水經注·淇水》所引《晉書·地道志》:“樂陵國有新樂縣”的記載,似非叙述政區沿革,而是記載西晉政區情況,故《晉書·地道記》中當有樂陵國。據學者考證,建興元年(313)冀州淪没,則樂陵國至遲當於此時傾覆。由此推斷,《晉書·地道記》“樂陵國有新樂縣”的記載,當在建興元年之前。
綜而言之,從《宋書·州郡志》對《太康地志》《晉書·地道記》材料的運用來看,《晉書·地道記》的斷限當在《太康地志》之後,並非以太康三年爲斷。又據《晉書·地道記》中有東莞郡、樂陵國並述及永嘉二年所立碑的信息,其斷限當在西晉武帝以後。
結 語
學者對於王隱《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認識的分歧,實與王隱《晉書》輯本相關。清代學者出於廣泛搜集佚文的考慮,在輯録《晉書·地道記》時,往往將書名似是而非者一併收録。這使得《晉書·地道記》佚文所反映出的政區信息,在時間上衝突牴牾,令人莫衷一是。
基於此,在研究《晉書·地道記》斷限年代時,首先要嚴格史料標準,僅取明確出於王隱《晉書·地道記》者,以此確定可靠的、符合現代學術要求的研究起點。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佚文反映出的政區沿革信息,以及沈約撰寫《宋書·州郡志》的方法和對“王隱《地道》”的運用,可大致推斷出王隱《晉書·地道記》的斷限年代當在西晉武帝以後。
(本文作者爲河南大學黄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博士後)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招標項目“歷代國家治理的歷史底藴與當代價值”(號LSYZD21003)、中國博士後第71批面上項目“東晉南朝政治地理研究”(2022M711041)、河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兩晉政治地理研究”(2023-ZZJH-213)階段性成果;審稿專家提供了極富指導性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