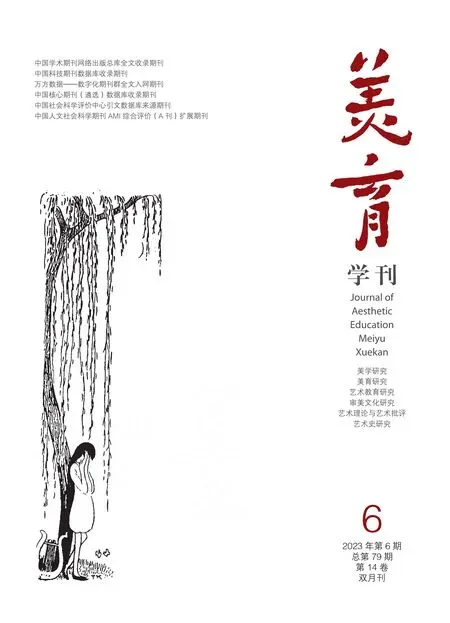苏联援华戏剧专家与中国话剧导表演人才培养体系
2023-12-16李贤年
李贤年
(云南艺术学院 戏剧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1949年以后,伴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话剧的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在道路选择上,它倾向于对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戏剧教育模式做进一步的推行和延展。但解放区戏剧教育模式在面对更高的时代要求(即正规化、专业化、体系化)时,则显得比较局促和单薄,亟需外力的支援与扶持。此外力便是苏联。事实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戏剧事业多受苏俄的影响,而解放区戏剧模式更是在“以俄为师”的政策指引下形成的。因而,继续延续这一政策仍然是积极有效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的“一边倒”政策。[1]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话剧此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路径在中苏同盟关系缔结的大背景中得以确立,即:“苏联的戏剧政策是中国话剧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苏联的戏剧体制是扶植中国话剧体制的典范,苏联的戏剧理论是中国话剧理论与实践的依据,苏联的演剧体系是中国话剧演剧专业化、正规化的手段与工具。”[2]
中国话剧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是薄弱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相对凌乱的。借此历史契机,在“走俄国人的路”的政策驱动下,话剧教育界力图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系统引进苏联戏剧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导表演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出符合中国社会实情的民族话剧演剧的人才培养体系。如田汉在1954年访问上海戏剧学院所说:“……继承中国优秀戏剧传统,学习苏联戏剧文化建设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戏剧创造成果,批判地研究其他国家古典的近代的作品与技术,正确运用并提炼中国语言,反映当代革命现实与历史真实,教育人民,为祖国伟大建设服务。”[3]而上述两个目标愿景的具体实现则迫切需要“请进来”一批苏联戏剧专家(以下简称专家)。
一、引进专家前的多重预热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次会议是国共内战后“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队伍“胜利会师”的政治仪式。这也预示着原本长期分隔的两支队伍要重新在共产主义的精神洗礼下,接受新政权的重组。中国话剧也因此进入一个全面“重组”的过渡期(1949—1953),其主要工作是领导机构、协会、院团、院校的重组。
其中,“重组”工作的一部分表现在共和国话剧高等教育机构(院校)的建设上。尤为突出的是:1949年至1950年,原华北大学第三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等机构合并组建成立中央戏剧学院;1952年至1953年,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戏剧科、上海行知艺术学校戏剧组等机构合并组建成立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更名为上海戏剧学院)。两所戏剧专门院校是共和国戏剧高等教育的“试验田”,旨在摸索可以全国推广的人才培养体系。随后几年陆续成立的几所综合艺术院校如南京艺术专科学校(今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今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专科学校(今吉林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专科学校(今广西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等的戏剧系(学科或专业),其教学体系便是以此为样板的。在“重组”中,中国话剧教育界顺利实现了一种“中央—地方垂直式培训”(1)即从各地方院校(机构)选拔戏剧干部(或人才)赴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接受各类理论与技能培训。的机制,为日后专家的教育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两所院校甫一成立,便移植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斯坦尼体系)为核心的苏联戏剧人才培养体系(尤其是导表演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赓续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戏剧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与专家们后续的教育教学形成内在的对接。
在师法苏联戏剧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最生动的部分要属对斯坦尼体系的学习接受。事实上,斯坦尼体系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话剧教育领域广泛传播了。如1938年8月23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隆重举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悼念大会。余上沅、金韵之等人借机将斯坦尼体系及其演员训练方法引入导表演训练课程,并不断深化和强化,一直持续至新中国成立前。与此同时,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更是将斯坦尼体系奉为圭臬,与国立剧专遥相呼应。除此而外,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校艺术教育系戏剧组、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科、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等院校机构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斯坦尼体系。历史地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话剧教育借斯坦尼体系着力培养了一批(一代)话剧导表演人才,成为共和国戏剧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早已认识到斯坦尼体系是“世界戏剧的结晶和成果”,是“正确的艺术要求”,是“中国未来演剧的正确路标”,是“民族形式的创造标尺”。[4]5因而,无论共和国的话剧教育事业是否直接求助于苏联,斯坦尼体系都会因其“科学性”而继续在中国广泛传播。
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也确实掀起了“(斯坦尼)体系热”。在教育领域,斯坦尼体系的轴心地位是高度明确的。如,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成立初便依托苏联当时的表演教学大纲授课,其核心就是斯坦尼体系。(2)据冉杰回忆,中央戏剧学院最初的表演教学大纲来自苏联戏剧教育界较早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表演大纲。见冉杰:《我的艺术生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4页。之外,以斯坦尼体系为主题的教学培训活动也层出不穷。如1951年,舒强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普通班”按照斯坦尼体系训练学生;同年,焦菊隐在中央戏剧学院讲授“导演如何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以教师身份开设“斯坦尼体系研究”课程,系统教授斯坦尼体系原理;1952年,东北中长铁路中央文化部文工团邀请三位业余从事戏剧工作的苏联专家(巴甫洛夫、马尔丁诺夫、契库拉也夫)向团员教授“演员自我修养”内、外部技术,其讲稿经整理编印,后由总政治部翻印,在部队文艺等团体中流传较广。(3)值得注意的是,此讲学活动是全国第一次对两部《演员自我修养》(此时第二部还未译介进来)的系统讲述,这对于戏剧家准确理解斯坦尼体系原理方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讲稿有多种编印版本,如东北中长铁路中央文化部文工团1952年编印的《演员自我修养内部技术》《演员自我修养外部技术》《角色的扮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1953年印行的《演员自我修养听讲笔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3年印行的《演员自我修养讲授笔记》。
“体系热”还体现在体系理论著作的广泛译介上。如,1951年召开的全国文工团长会议上,查哈瓦的《舞台动作》及阅读和研究《演员自我修养》的指导提纲等资料出现,进而在全国被广泛传阅。[5]1952年,根据英文版转译的全本《我的艺术生活》(瞿白音译)出版。在此前后,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著作,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伏尔科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苏联戏剧》(阿巴尔金)及《史达尼斯拉夫斯基论舞台艺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解说》(马加歇克)等也相继问世。大约同时,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三部作品(《奥赛罗》《海鸥》《在底层》)的导演计划”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著的翻译活动也在酝酿和进行之中。
此外还有研讨活动,如1953年6月,中国剧协在北京召开了主题为学习斯坦尼体系的座谈会;同年8月,中国剧协还联合中苏友好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举行斯坦尼逝世15周年的纪念会。
以上种种“体系热”的表现生动地反映出中国戏剧界对于苏联体系的热衷,这在戏剧教育政策、教学制度、教学计划等方面,为苏联戏剧专家在华的教育教学活动铺出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二、专家在华教育教学活动
共和国建立之初,全社会各领域的各项事业都面临着全面建设的重大难题。此时,苏联伸出援助之手,有计划派遣各类人才扶持百废待兴的中国。这些在当时被称为“苏联专家”的人才,总计约18000多人,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等诸多重要领域形成了全覆盖。[6]其中,中国戏剧界也于1953年至1957年间先后正式聘请了7位苏联专家前来“传经送宝”(4)此处的专家人数以正式聘请为准,不包括临时邀请讲学的人员。,分别是列斯里、库里涅夫、古里叶夫、雷科夫、费多谢耶娃、柯查金娜、列普科夫斯卡娅。他们都是活跃在苏联戏剧剧场和教育界的资深艺术家、教师。而如列斯里、库里涅夫、古里叶夫、列普科夫斯卡娅等人则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体系”有比较亲密的联系,在对“体系”的理论阐释和实践传播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他们分布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作为核心师资及教学督导(如院长顾问、系部教学指导等),开展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教育教学活动(如参与院系划分、专业设置、教学计划与教学内容的制定、实际教学与指导等),在当时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这些导表演专家最大的贡献便是在导表演教学体系的建设上引入了“体系”。正如首席专家列斯里在中央戏剧学院欢迎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他们“被派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带到这儿来”[7]。具体来说,导表演专家的“体系”传播分为教学培训和理论讲述两个部分。首先,其教学培训主要是通过“垂直式”训练(进修班)的形式,向从全国各地院团院校等机构抽调的青年骨干传授以“体系”为核心的导演原理方法、表演原理方法,旨在“为院校培养(第一批)师资,为院团培养可以‘带徒弟’的导表演干部”。[8]对此,两所院校对专家们委以众望,在教学上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可以说,中国戏剧界在当时是以一种巨大的虔诚面对这些“体系”的使者的。其结果是,数百人幸运地成为第一批被“体系”沐浴的戏剧家,成为第一批科班生,为“体系”在全国的更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整体情况见表1:

表1
专家的艰巨任务是要通过一年半时间将苏联导表演本科教学的所有内容作系统传授。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体系”也在此时刚刚实现了全国性的推广,取得了演剧上的正宗地位。在1950年至1951年间,苏联戏剧界展开了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作遗产的全国性大讨论。其中,官方对教育界未很好推行“体系”的现状作了尖锐的批评,如“导演系和戏剧学系的教学计划中,有关‘体系’的讲授还微不足道”,“国立戏剧艺术学员并没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遗产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苏联部长会议事业委员会的教学机构总管理局和国立戏剧艺术学院的教授团,直到现在还没有能编出一本真正科学的表演技巧教学大纲”等。[9]至此,苏联戏剧教育界开始积极响应号召,以极短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上述任务,而其最新的成果恰逢其时地被专家带入中国的课堂。比如,专家的教学充分吸收了新出版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演员创造角色”的其他著作,纠正了中国戏剧界关于“‘体系’重体验不重体现”的错误认识;同时,专家在教学中引入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重大发现——形体动作方法,以此建立起导表演创作的“行动分析学说”,使中国戏剧家把握到了“体系”的精神实质和演剧方法要领,受益至今。苏联专家“传经送宝”的使命客观上说实现了。
对“体系”进行系统化的理论阐释是专家教学培训工作中的又一重要任务。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古里叶夫于1957年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邀请之下为北京地区的千余名戏剧家讲述“体系”理论。在此之前,他也先后应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南京前线话剧团和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开设过类似的理论讲座,引起戏剧界广泛的兴趣和高度的关注。他在“千人讲座”上的讲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讲座》也被整理出版,形成了全国性影响。[10]而其他戏剧家也同样通过课堂形式不同程度传播“体系”理论,其讲义均以出版物形式得到推广,产生了积极意义。
几位苏联专家并没有辜负中国戏剧界的期望,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辛勤的努力实质性地参与到中国戏剧高等教育的建设事业中去。他们也确实是当时最好的老师、出色的舞台艺术家和戏剧理论家,其卓越业绩渗透在各项教学工作中。他们担任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等主干课程的艺术指导,既培养了学生,也为两所院校的教师提供了教学示范,还监督指导中国教师的课堂教学。与此同时,带有浓郁苏式戏剧教育气息的教学思想、教学制度、教学组织、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应运而生。其中,最能体现“体系”精神,对未来中国戏剧教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尤其是导演、表演、台词、形体(舞台动作)教学大纲。
三、导表演教学体系的建立
导表演教学大纲是对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1954版《“导演学与表演技巧”课大纲》《“表演”课教学大纲》的因袭。(5)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在苏联相当于中央戏剧学院在中国的地位。这两份大纲即前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作遗产大讨论”之后的最新成果,由苏联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学校管理处审定并在全国戏剧院校推行。两份大纲最大的特点是以“体系”为导表演教学体系的核心。“表演学”大纲中明确写着:
戏剧学校里的演员专业训练体系,应以……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以及他们的学生和继承者的教学经验和创造经验为基础。[11]
“导演学”大纲中也写着含义一致的话: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表演、导演艺术科学的基础。[12]
1954版教学大纲在以往大纲的基础上突出“行动”的核心,综合所有“元素”展开训练。同时,也兼顾到“体系”中“‘体现’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和“演员创作角色”两大板块内容。当然,大纲也存在对“体系”认识不全面的问题。
“表演学”大纲中的教学规划是这样的:
第一学年——使学生在他们自己创造的练习小品的规定情境中达到有机的、真正的,也就是合理的、合乎目的的、有效的动作。(即元素训练)
第二学年——使学生在作者——剧作家所建立的规定情境中达到有机的、真正的动作。用剧本的片断作材料完成任务。(即片断训练)
第三学年——开始创造角色。用剧本的各幕作材料完成任务。(即独幕剧创作)
第四学年——在一个剧里创造完整的舞台形象。(即大戏创作——括号内为编者加)
学生在学习内部表演技术的同时,应该在掌握外部表现手段上进行艰苦的锻炼(掌握台词的逻辑性的规律,正确地训练呼吸,练嗓子,松弛身体等等)。演员必须和掌握心理技术的同等程度地充分掌握自己的外形条件。[4]8-9
教学计划是将“‘体现’创作过程中的自我修养”分离出去,独立设计成“台词”“形体”的。此设计有两个问题,一是将“体验”和“表现”分立,割断了其互为表里的有机性;二是把“表现”训练简单看成外部技巧训练,如“训练呼吸”“练嗓子”“松弛身体”“身体训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体系”中关于“表现”训练的所指。斯坦尼在1935年拟定的两卷本《演员自我修养》的章节计划中就体现着“体验”“表现”的有机统一性。前14章是“体验”部分的训练,后11章则是“表现”部分的训练。分别是:
15.转到体现;16.形体训练;17.练声和吐字;18.言语;19.速度节奏;20.性格化;21.控制与修饰;22.外部舞台自我感受;23.总的舞台自我感受;24.体系原理;25.如何运用体系。[13]
从中不难看出,在“体系”中,“表现”并不仅是外部技巧,它同样是心理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有机的心理机制是当时的大纲制定者未认识到的。他们只是根据斯坦尼1933年的“戏剧学校教学计划及大纲”外部技能训练,结合以往的教学经验制定“台词”“形体”的教学大纲。这必然使得“体验”“表现”相脱离,当然也就给学生造成错误印象:“体系”重体验轻表现。
“导演学”教学大纲的训练思路和方法依然沿用从前,即在“案头分析”的基础上产生导演构思,进而制定排演计划,并完成排演。其训练进程和表演大纲相契合,即小品——片断——场/幕——大戏。总体上,培养导演的教学工作主要分为六步:
一、研究导演学的理论原理。
二、导演练习,处理导演小品,剧本中的片断、场、幕。
三、对剧本进行导演分析。
四、确定导演构思,拟定演出计划。
五、排剧。
六、实习和工作(编者总结)。[14]
两份教学大纲代表了苏联当时最新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恰逢其时地传入中国。两所院校将其直接移植,加之专家们紧密结合大纲授课,致使饱含“体系”基本精神的教学模式在中国生根发芽。直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戏剧教学机构的导表演教学依然沿用着“小品—片断—场/幕—大戏”的模式。
相对于导表演教学大纲的直接因袭,“台词”“形体”这类涉及外部体现训练的课程大纲必须要经过“民族化”的处理,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刚开始苏联专家是不加区分“一边倒”地沿袭苏联,不尊重汉语和俄语的差别,用俄罗斯舞台语言的训练习惯训练中国演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在形体训练课上暴露的问题也与台词课一致,其训练内容主要是芭蕾舞、俄罗斯民族舞,学员身上难见中国味道。针对此景象,时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敏锐感受到“大纲”在演员体现部分的问题,大声疾呼要建立中国话剧的台词、形体训练体系。他指出:语言和形体是话剧的两大支柱。[15]他大胆提出在传统戏曲及其他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中国话剧的台词、形体教学。这一主张引起强烈反响,也出乎意料地得到苏联专家的高度肯定,这也对当时话剧向戏曲学习的演剧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专家们都积极参与了台词形体课大纲的制定和实施。台词课大纲以“北京语系”作为中国话剧舞台语言的基础,根据汉语的语言规律,突出正音、呼吸、发声、读词等技巧,创造性地借鉴和运用戏曲念白、大鼓、单弦、相声等曲艺形式的发声吐字技术,同时兼顾歌剧的声乐训练方法,比较好地做到了话剧语言声音表达的规范化和艺术化。形体课开始注重话剧演员形体表现的民族气质,其教学目的为“培养学生具有灵活的身体,能够得心应手,动作准确,优美,简练,借以提高演员舞台动作的才能”,并且明确规定此课程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根据话剧专业的特点,充分地在戏曲、民族古典舞、民间舞、民族拳术、军事体育等领域中汲取养分。[16]应该说,台词、形体教学大纲既体现了苏联影响,又体现了中国智慧,为日后中国话剧演员在外部表现技能的培养方面起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苏联专家来华的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两所戏剧院校在教学思想、教学制度、教学组织、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上逐步达到了规范化和专业化,为全国陆续建立的其他戏剧教育机构树立了标杆。直到今天,几乎中国所有的戏剧教育机构的本科教学中依然可以看出苏联专家的影子,他们的贡献是必须要得到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