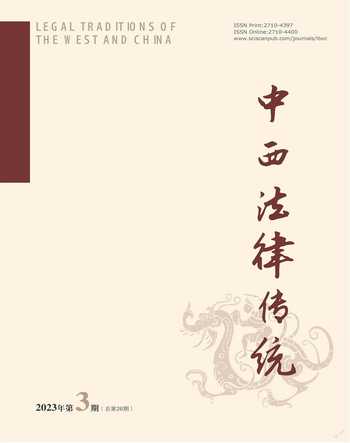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司法实践
2023-12-06冯雪菲
摘 要|清代著名的循吏良幕汪辉祖认为,官无成见、州县不直、讼师簧鼓、裁决过轻以及勘官过错均会导致州县细故缠讼。汪辉祖也为应对州县细故缠讼做出了积极努力,采用了体问风俗以求取实情、审讯中巧用钩锯之法、判决力图情法两尽、惩治讼师、劝谕教化等应对举措,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汪辉祖的做法能收获如此成效,也得益于其所处的时空。而其应对举措固然能收效一时,但依旧无法避免“人治”模式固有的局限性——存在“人亡政息”甚至是“人存政举”难以真正实现的风险。
关键词|汪辉祖;清代州县;细故;缠讼;司法实践
作者简介|冯雪菲,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清代的官箴书、基层诉讼档案等材料对“缠讼”多有记载[1],可见“缠讼”不仅为清代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现象,还是困扰清代官员的一大司法难题。
关于清代的缠讼现象,学术界已产出不少成果。徐忠明、胡震、龚汝富、李艷君等学者认为,缠讼是缠讼者争取有利判决的诉讼策略与手段[2]。海丹指出,缠讼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审判者并未回应当事人作出相应事实认定与道德判断的诉求,且承审考核制度未能对审判者作出有效引导[3]。滋贺秀三的研究表明,缠讼的存在是源于司法确定性以及相关观念的缺失[4]。尤陈俊指出,滋贺秀三的研究不能解释百姓在州县衙门反复缠讼且未能进展到上控的现象,而州县官实际任期较短是造成前述现象的制度性因素之一。陈会林则分析了清代官员对于缠讼等不同形式的“小事闹大”诉告的司法应对方式,他指出,清代官员应对“缠讼”的司法措施包括书面审查或讯问调查后的“不准”、警示化导、公堂调解、发审、官批民调。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缠讼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造成缠讼的因素的探讨。陈会林对缠讼的研究转换了视角,宏观梳理了清代官员应对缠讼的司法方式,但该研究并未具体展现不同层级的清代官员及其幕友的应对方式,且对缠讼的探讨是附带在“小事闹大”诉告这一主题下的,并非专门论述。因此,当前学术界有关清代州县官及幕友应对缠讼现象的司法实践的专门研究尚且较少。
州县细故缠讼,即州县细故中的两造在州县官作出裁决后仍旧继续控告,是造成词讼积案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览汪辉祖的生平,可以发现汪辉祖佐治任官多在州县一级,而他的司法观念又在清代被幕友和牧令“奉为楷模”,因此对汪辉祖的司法实践进行研究或许于清代州县政府司法实践的研究而言具有一定典范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学治臆说》(以及《学治续说》与《学治说赘》)、《佐治药言》(以及《续佐治药言》)、《病榻梦痕录》(以及《梦痕录余》)、《汪辉祖传述》为索引,试图探析汪辉祖对州县细故缠讼的认识、应对方式及其成效,进而探讨这一成效的背后所隐藏的局限性与汪辉祖的应对举措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一、汪辉祖对州县细故缠讼成因的认识
通过对汪辉祖的听讼故事及汪辉祖所撰写的官箴书进行梳理,可知在汪辉祖的眼中,官无成见、裁决不公、裁判过轻、讼师唆讼以及勘官过错都是造成州县细故缠讼的原因。
汪辉祖认为,“官无成见”会引起两造缠讼。汪辉祖在长洲县作幕友时,曾处理过一件两造缠讼的州县细故:孀妇周张氏的遗腹子继郎在将要成婚的前一月便因病去世了,族人以继郎尚未娶妻为由,主张给周张氏的丈夫立继;而周张氏想为儿子继郎立嗣,双方意见不合,便打起了官司。之前所有处理此案的知县都批“房族公议”,双方也是反复控告,该案历经十八年依旧未能完结。在汪辉祖的雇主郑知县上任后,周张氏又再次呈词。汪辉祖“吊查全卷”,发现卷宗“厚逾数尺,族继张词,张继族控”,于是指出此案“批妇房族,官无成见”。汪辉祖对“累批房族”的“无成见”做法十分反对,在他看来,“批房族不难也,为父母而令节妇抱憾以终,不可。”[4]汪辉祖对该案的描述表明,他认为此案缠讼不休、久拖未结是由于前任断案的州县官们未能形成成议从而作出了较为模糊的裁决。
“州县不直”或许亦为汪辉祖眼中州县细故缠讼产生的原因之一。汪辉祖就任宁远知县期间,审结过两起典型的缠讼案件——“匡学义假造产契与李氏争夺田产案”与“李氏与萧氏坟山争讼案”。前案中的匡学义是李氏去世的丈夫匡诚的乞养子。在匡诚有亲生子后,便给予匡学义八亩地,让其归宗。但在匡学义归宗后不久,匡诚就一病不起,于是又再次给予匡学义五亩地,嘱托他多加照拂家事。匡诚死后,妻子李氏勤俭持家,又得益于匡学义的帮助,在十七年间又增加了田产百余亩。而在一次田产交易中,李氏偶然发现所有的产契上都记载着田产均由李氏与匡学义同买,匡学义却坚称田产的确是合买,因此租金也是均分。由此李氏便控县控府控道,踏上了缠讼的道路。汪辉祖认为,此案中“前令不直,愬府发零陵,亦以产契租籍为凭”,因而李氏又“诉本道”[1]。他指出,匡学义“为李氏治家田,皆学义交易,李氏执契而不识字,契载自不可凭”,宁远前任知县与零陵知县以产契为凭据的判决自是属于错判[1]。可见在汪辉祖看来,李氏反复控告,是由于前令与零陵县县令的“不直”,他们所作出的审断并不公允。而另一个例子虽与匡学义案案情大不相同,但汪辉祖也做出了同样的评价。在坟山争讼案中,李氏将萧氏祖先墓削平后又为自家先祖立下墓碑。汪辉祖指出,萧氏反复控县,但前任县令们“皆以李碑有据,萧墓无凭,不直也”,萧氏听闻汪辉祖“勘山详审”,则又“呈图求勘”[2]。由此可知,在汪辉祖眼中,萧氏反复控县,自是由于前任州县官们武断地以李氏立下的墓碑为依据,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从汪辉祖对这两起案件的描述来看,可知汪辉祖认为,州县的错判、有失公允的裁决会导致负屈小民的缠讼。
在汪辉祖看来,“讼师簧鼓”也是两造缠讼的原因之一。对于讼师,清代官员的态度可谓是深恶痛绝。讼师通常会被官员们“视作教唆人们进行毫无必要的诉讼,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利用诉讼文书和花言巧语诱惑人们陷入诉讼,与盘踞官府的胥吏或差役相互勾结,从善良的人那里骗取金钱等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3]如曾任巴县知县的著名循吏刘衡就认为:“民间些小细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讼棍者暗地刁唆诱令告状。迨呈词既递,鱼肉万断,甚至家已全倾,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讼师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为害于民,莫此为甚。”[4]有学者指出,清代官方对于讼师的大肆批判、对讼师贪利无良形象的大力塑造,归根结底是由于当时司法体制中的“制度资源”无法应对社会情势变更,从而官方试图利用此类“话语资源”来弥补司法体制正当性的缺失[5]。汪辉祖作为清代较具典范意义的良幕循吏,对讼师的看法也与大部分清代官员如出一辙。他认为,“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6]而从汪辉祖在《梦痕录余》中记载的一起州县细故中可看出讼师唆讼与州县细故缠讼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联系。汪辉祖在平湖县作幕友时,平湖一富室嫡子陆腾与庶子陆煌因坟墓的建造而互相控告。陆腾在为庶母营造坟墓时欺负陆煌年幼,故意将庶母的坟墓往后退了四尺,又将其营造得十分狭小。庶子陆煌长大后便控县,汪辉祖作出了改造的判决。陆腾对此判决不服,便多次控府,而知府与汪辉祖作出的判决一致,陆腾便又再次上控至巡抚。对于这起缠讼案件,汪辉祖评价道:“方互讦时,腾受产本多,兼有私蓄,讼师簧鼓,志在必勝,”可见他认为陆腾反复缠讼与讼师唆讼密切相关[7]。汪辉祖指出,“再馆平湖,煌可自给,腾穷已久”,于是作出“天道响应,如之何勿惧”的感慨。在他看来,陆腾的反复缠讼也最终产生了自己家道中落的恶果,这也使得他坚信因果报应的观念。
前文以《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中记录的缠讼纠纷为材料,分析了汪辉祖眼中造成州县细故缠讼的成因。而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也表明了自己对于缠讼成因的看法。他指出,若不知犯罪真情,则可能“从末减矣”,从而“彼以为官固可欺,必图翻异”[8]。由此可见,汪辉祖认为官员因不知犯罪实情而对犯人作出过轻的裁判,也会使得犯人再次翻案,从而演变为缠讼(州县细故中的当事人行为包括斗殴、赌博、盗窃等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州县细故纠纷中亦可能会存在犯人)。而对于勘丈案件所引发的缠讼,汪辉祖认为这是勘丈官员的过错所酿成的后果,“唯风水山场有影射,有牵扯,诈伪百出,稍不得实,张断李翻,甚至两造毁家,案犹未定,皆勘官酿之祸也。”有学者指出,清代田土案件之勘丈,通常由州县官、县丞、巡检、典史等官为之。可见,勘丈的实施主体既包括正印官,也包括佐杂官员。因此,汪辉祖所指的“勘官”可以被统称为“官员”。
综上可见,汪辉祖认为州县官、讼师、勘丈官员都会导致州县细故缠讼的产生。换而言之,汪辉祖将州县细故缠讼产生的成因归结于人,无论是官员(州县官、勘官)还是讼师,都是诉讼环节中的参与者。但汪辉祖的认识依旧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州县细故缠讼的出现,除去汪辉祖所认识到的人的因素,关键还在于制度与体制层面的缺陷——诉讼时效制度的缺失、限制诉讼次数的制度尚不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过分简约以及司法体制所带来的有效监督机制的匮乏。而汪辉祖却并未将州县细故缠讼与整个诉讼环节乃至于司法行政制度、体制的设计联系起来,这或许是囿于其所处的时代吧。
二、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举措
汪辉祖在其司法实践中,采取了体问风俗以求取实情、审讯中巧用钩锯之法、裁判力图情法两尽、亲自踏勘、往复履勘、勘丈时念及子孙、惩治讼师、劝谕教化的措施,审结了不少缠讼纠纷,减少了缠讼纠纷的产生。
对于真相不明的州县细故纠纷,汪辉祖坚持求取实情。汪辉祖十分注重体问风俗,他认为“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而透过汪辉祖所处理的州县细故缠讼个案,可以发现汪辉祖在司法实践中也通过体问风俗的做法来求取实情。汪辉祖在审理萧氏与李氏的坟山争讼案时,尚且不明李氏冢地中是否有萧氏祖墓,由于“萧力言下有尸棺,具结求开掘”,因而汪辉祖进行掘墓,但起初勘丈并不顺利,“掘至五尺余,尚无迹”,汪辉祖本意欲辍工,但在萧氏的“再三哀吁”下对此案又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便“召观勘之临武县耆老”,体问此地“乡俗葬法”,这才得知根据此地风俗,墓可深至八尺。尔后再掘到八尺深时,发现两胫骨,这才证实此地应为萧氏祖先墓。据此,汪辉祖便酌情作出了“原碑移置小峰之下,李墓之上,其自峰而上地,尽归萧”的裁决,这才将该起缠讼不休的州县细故纠纷完结定案[5]。此案中,李氏与萧氏的供词均真伪不明,前任知县们的“不直”也导致了萧氏的反复缠讼,而汪辉祖也正是通过向堂下耆老们体问风俗,从而找到真相、作出较为平允的裁决,彻底平息了这场缠讼纠纷。
部分州县细故纠纷依据逻辑可以推断出现有凭据与事实并不一致,舍弃现有凭据仅依靠推断的事实作出裁决固然较为公正,但亦会引起现有凭据所偏向一方的不服;若依照现有凭据作出裁断,则会使得负屈缠讼的原告冤屈未伸,从而继续缠讼不休。针对这种疑难案件,汪辉祖在审讯中巧用钩锯之法,既让负屈缠讼的原告得到平允的裁断,又能让另一方输服,从而定止纷争,不至于继续缠讼。汪辉祖在审理匡学义案时,从常理推断出匡诚死后新置的百余亩田地并非匡学义与李氏共同出资购买,但产契上又记载为双方共同购置,这便是现有凭据与事实不一致的典型情况。倘若如前任知县一般以产契为依据,李氏仍会继续缠讼;但只是追求公正,“舍契以断,不足以关学义之口”。汪辉祖“据《汉书·赵广汉传》钩锯法”审结了此案,打破了这一两难困境。所谓钩锯法,即从事物关系中找寻线索,间接获取真相,如“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本案中的汪辉祖假意与匡学义攀谈,从询问其家产、家口、生业入手,使匡学义放松警惕,露出破绽,又“命吏检历年报窃档案,佯为究鞫”,从而促使匡学义自己交代出实情。汪辉祖在本案中便运用钩锯法,诱导匡学义亲自交代真相,既作出了让缠讼的李氏较为满意的裁决,又足以让败诉的匡学义心服口服,不会因心有不甘而开始缠讼,可谓是一举两得,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缠讼案件。
面对实情明朗,但难以折衷裁断,却又缠讼不休的州县细故纠纷,汪辉祖力图做到情法两尽。汪辉祖佐幕于平湖县时,审结过一起争产缠讼案件。寡妇黄俞氏无子,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族长向刘知县呈请将黄俞氏的夫产附于宗祠作为祭产,由族长收租,每年给黄俞氏三十石租米,剩余归宗祠管理,黄俞氏不可私卖田产,亦不可私下收取各佃户的租金。刘知县裁决批准族长请求后,黄俞氏对此裁决不满,便选择控县。汪辉祖经手此案时,并未直接援引与之相似的殳球案,而是努力做到情与法的平衡,既引用律例“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例得亲女承受”,又从情理上分析“祔食”的不合情理,“转以无干之族长,为之制其肘,而攘其财,不惟嫠妇含冤,并使幽魂饮泣,无此政体,亦无此风俗”,从而改变原先刘知县作出的裁决,作出“以五亩立黄祠祭户,俟俞氏女嫁、身故,归祠收息,为伊夫妇祔祭,其三十七亩听俞经营,膳养、嫁葬、或存、或发,总不必房族过问,以断葛藤”的裁决。如此,既合律例又合情理,因对原先裁决不满而缠讼的黄俞氏不再缠讼,败诉的族长也未继续呈控,该案便就此涂销完结了。有学者指出,汪辉祖在没有相关律例的情况下,会试图在律例设定的底线下援引礼经、情理和道义;在有可供援引的律例时,汪辉祖会参照律例进行裁判的同时又援引礼、道义、情理,汪辉祖既不追求“依法裁判”,也并无“情理裁判”的取向,而是追求“律例上有依据,情理上无窒碍”。综上可见,汪辉祖在处理州县细故的司法实践中,也是尽可能地做到情与法之间的协调,进而做出两造较为信服的、比较折中平允的裁决,这也使得他成功审结了一些较难裁决的缠讼纠纷。
由上可见,汪辉祖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面对缠讼纠纷,采取了体问风俗以求取实情、审讯时巧用钩锯之法、裁判追求情法平衡的措施,力求做到裁决明确且平允,尽可能地避免“无成见”、裁决“不直”、裁判“从末减矣”的出现。
由于宁远县多争界之讼,勘丈案件自然较多,因而汪辉祖对勘丈案件也较为重视。如前所述,汪辉祖认为,勘丈官员的过错与州县细故缠讼的产生有着密切关系。对此,汪辉祖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得在其任内,宁远县的勘丈案件从无翻异。一方面,汪辉祖尽可能地减少勘案中差谬的出现。为了做到“一勘无翻”、避免“张断李翻,甚至两造毁家,案犹未定”,汪辉祖遇到勘丈案件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委托佐杂官员,他认为“转委托佐杂,徒费民财,不惟不公,即公亦不足以服人,至于人不能服,仍归亲勘”;在勘丈时也会就两造绘图认清山名方向,再“往复履勘,凡所争之处,及出入路径,一一亲历,毋惮劳琐”,也尤其注意“不许两造随舆哗辨,以淆耳目”;勘丈结束后,“将两图是非,逐细指出,为之明白讲谕”,然后“再行剖断”,从而两造“自然心平忿释,不致争竞”。另一方面,汪辉祖认为,勘丈难以做到毫无差谬。因此汪辉祖在两造面前时常念及子孙,既向两造表明“尽心”的态度,又保证自己毫不偏私,以获取两造的谅解,从而使得勘案不至于因为不可避免的错误而翻异。汪辉祖就任宁远知县之前,宁远县勘丈案件“多反复”,汪辉祖在上任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便对勘案中的两造发誓“吾才势不能周,如有袒私,他日尔子孙斗争,吾子孙亦斗争;尔子孙以斗争酿命,吾子孙亦以斗争酿命,愿尔子孙自吾此勘,永杜争端,即吾子孙幸也”,从此,“四年间,本境勘案及委勘邻境之案,从无翻异”。
前文还指出,汪辉祖将讼师唆讼作为州县细故缠讼产生的原因之一。汪辉祖也在其司法实践中对讼师严加打击。一方面,汪辉祖从吏役入手,间接地敲打讼师。在他看来,讼师与吏役往往相互勾结。因此,他遇到“讼师播弄之案”,便“澈地根究一二,使吏役畏法”,从而“若辈自知敛迹。”另一方面,汪辉祖采用了非司法的手段惩罚讼师,以儆效尤。汪辉祖任宁远知县时,将一名“更名具辞”的讼师当堂锁系,一边检查并分别审理该讼师所引起的讼案,一边将其系在公堂的柱子上令其观看自己审理其他案件。汪辉祖每隔一日,就审理一起该讼师唆使的讼案并对其予以轻微的杖刑,不过半月该讼师便疲惫不堪,“哀吁悔罪”。汪辉祖将其“从宽”保释后,这名讼师便“挈家他徙”,此后“无更犯者,讼牍日减矣。”[1]汪辉祖采取上述两种做法,成功做到让讼师“敛迹”“无更犯者”,如此,“讼师簧鼓”所导致的州县细故缠讼现象也大大减少甚至可能会暂时地消失。
此外,汪辉祖是位十分合格的传统中国制度下的儒家执法者,他的司法观念也带有十分典型的保守主义特征[2]。儒家重教化,汪辉祖作为儒家执法者中的典范,自然也将劝谕教化作为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重要举措。在汪辉祖的司法实践中,劝谕教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汪辉祖坚持公堂理讼。他指出,州县官如若在内衙听讼,虽然能够平息两造的争端,但无法教化旁观的其他民众。而在公堂理讼,堂下旁观者数百人,因为引起词讼的事由总有相似之处,可以引申,故而审断一起细故,既能够警示未讼者不要开启讼端,又能间接教育已讼的两造息讼。汪辉祖认为,公堂理讼是他任职宁远知县时宁远县从未出现一例上控的重要原因,“余唯行此法,窃禄四年府道未受一辞,各宪因为余功,乃知大堂理事,其利甚溥也”。[3]可见,公堂理讼也是一种教化的方式,既可以教化缠讼之人息讼,又能从源头预防诉讼的开始、缠讼之门的开启。另一方面,汪辉祖也在审理州县细故纠纷时对缠讼不休的两造进行劝谕。宁远富民杨继时无子,在其死后,其妻子立了杨逢年的儿子为嗣子,這使得杨逢星欲将自己兄长的儿子过继的想法落空。杨逢星便以其他事情诬陷杨继时之妻,双方互相控告了十八年,即使经过一州八县的审判,也未能将此案彻底完结。汪辉祖接手此案后,对两造进行劝导:“匪惟本县有所不忍,尔祖宗有知,必当悯恻。本县以父母斯民之心,体尔祖宗保世之念,谊联一本,筹出万全。尔等俱当感发天良,无欺无隐,以体本县曲予矜全之意。”[4]而正是由于汪辉祖言辞恳切地谆谆劝谕,让两造为过去仇讼不休导致伤及族人之谊的行为而悔悟不已,之后,两造间缠讼已久的纠纷也很快就了结了[5]。
三、汪辉祖的应对举措之成效、局限性及意义
汪辉祖任幕友34年,前后佐治元和、长洲、无锡、仁和、钱塘、海宁等州县,又在宁远县任职州县官4年[6]。汪辉祖佐治任官的近四十年间,面临并解决了不少缠讼纠纷。且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缠讼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向同一衙门反复控告,一种则是向不同衙门反复控告,而后者通常表现为上控[7]。宁远县之前民风好上控,而在汪輝祖任宁远知县的四年内,所审结的词讼无一上控[3]。可以说,经过汪辉祖的治理,宁远县民缠讼的手段也变少了。可见汪辉祖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缠讼之策。
尽管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一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这成效的背后,依旧隐藏着局限性——时空局限性与“人治”模式固有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在汪辉祖就任宁远知县时,宁远县民缠讼的常用手段——上控消失了。汪辉祖作为宁远县知县时的应对举措能取得这一不错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其所处的时空。换而言之,这一成效具有时空局限性。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会结构较为单一的地区,大多数州县细故仅仅只作出一次判决即可完案,只有少数细故纠纷会继续纠缠不休;而在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结构较复杂的地方,不少讼民是有钱有势的人,或是宗族、地主集团等团伙,他们有见识,不轻易屈从,甚至会为打赢官司编造情节,从而使得许多词讼的裁判会受到讼民们的反复辩驳[1]。宁远县属于较为偏僻的小县,“宁远僻处万山之内”“县境无著名殷户,俗又不谙经济”,因此宁远知县在当时属于简缺[2]。汪辉祖就任宁远知县的时间节点为乾隆时期,此时正处于清代中期,也即是商品经济尚未蓬勃发展、小农经济仍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由此可以推断,无论是从横向的地域来看,还是从纵向的时代来看,当时的宁远县商品化程度和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社会结构还相对而言较为单一。彼时宁远县还依旧属于典型的小农社会,县内就州县细故纠纷进行缠讼的富民和诉讼集团较少,因此县内州县细故缠讼发生的概率相较于经济发达、商品化程度高的地区而言会低很多,且县内的大部分缠讼纠纷也不会过分复杂,作为有能力的州县长官,汪辉祖尚有余力应对宁远县的州县细故缠讼。而同是处于清代中期,在经济发达、商品化程度较高、社会结构较为复杂的江浙一带的州县,即使有能力如汪辉祖,也终究会有许多应付不了的缠讼纠纷,甚至还有不少缠讼纠纷是由汪辉祖未能解决的州县细故演变而成。这些纠纷中有不少属于富室争讼案,如殳球案中汪辉祖的批词并不能让殳球信服从而殳球开始缠讼、周张氏案中汪辉祖的裁决也并未能阻挡败诉一方的缠讼、陆腾案中的陆腾也因不服汪辉祖的裁断而反复缠讼。以上横向地域的对比无疑也是印证了前述作为宁远知县的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一些举措所获得的成效具有时空局限性的观点。
前一部分探讨了作为宁远知县的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成效所反映的局限性,这一部分将试图对汪辉祖整个佐治任官生涯中的应对举措之成效背后所隐藏的局限性进行分析。汪辉祖无论是作为州县官,还是作为州县官的幕友,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所取得的成效终究还是无法摆脱“人治”模式的局限性。一方面,即使汪辉祖积极应对州县细故缠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非每位州县官及其幕友均能如汪辉祖一般勤政爱民、精通礼法、耐心教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自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州县细故缠讼纠纷在汪辉祖审理之前亦经过了一些州县官及其幕友的审理,但最终定止纷争的依旧只有汪辉祖。或许在汪辉祖离开后,一些新的州县细故纠纷也会因为未得到妥善解决而演变为缠讼。在“人治”模式下,只有当有能之人在职之时,才能暂时地解决一些司法难题。另一方面,所谓的“人存政举”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清代采用“同级集权,层层监督”的简约型司法体制。清代州县政府为“一人政府”,州县官既是法官、税收官,又是无所不管的行政官员,集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于一身[3]。可以说,州县官在其任职的州县中拥有至上的权力。而清代司法体制中的“纵向监督”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同级过分集权所带来的腐败,但有学者表明,这种层级监督会使得州县官与能够直接决定其升迁与否的地方上级官员进行利益合谋,共同规避监督要求,因此清代的司法体制并不能实际有效地监督州县官[4]。且到了清代后期,地方上级官员对审理两造上控案件的承审官进行考核时,更注重量化标准(审结数)是否完成,质(处断是否妥当、妥当的处断是否得到执行)并不纳入考核范围,承审考核制度也未发挥应有的引导和监督作用[5]。可以看出,承审考核也不能从根本上限制州县官自由甚至是随意裁断州县细故的权力,即使州县官作出“不直”的枉断,只要暂时审结完毕,地方上级官员不会过度追究。由此可见,“层层监督”的司法体制与承审考核等专门的监督制度并不能完全中和“同级集权”为州县官所带来的过大的权力,而过大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简而言之,即使一位州县官在刚上任时如汪辉祖一般积极采取各种举措来应对州县细故缠讼并收获了不错的成效,但由于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很难保证其一直不会“懒政”与“怠政”,也无法保证其能在任内坚持采用甚至不断改进这些应对举措。此外,州县幕友是由州县官自掏腰包雇佣来的,即使在州县官的允许下可以对缠讼纠纷进行审判,但州县官作为雇主也可以直接驳回幕友的裁决。幕友提议的一些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举措也未必能全部施行。由此可见,就算有能之士在任,其应对举措的效果也可能会因为无人监督所带来的腐败或作为幕友所受到的州县官的牵制而大打折扣,甚至还可能会因上述原因导致原本采用的应对举措所取得的成效“昙花一现”。
由此可见,汪辉祖的应对举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州县细故缠讼这一司法难题。这归根结底是由于制度与体制的设计难以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清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也愈来愈高,有钱有势且法律意识较强的富民及老练的诉讼集团会随之增加,如此,相当复杂的、难以解决的缠讼纠纷也会越来越多。对于这种变化,清代本就存在缺陷的体制与制度更是难以应对,甚至这些体制与制度本身也是导致缠讼纠纷产生的关键因素。“一人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本就让州县官们疲于应对所辖州县内的繁杂的事务,这会使得他们较为忽视和考成关系不大的事项——州县细故的审理。而司法体制中“层层监督”也并不能有效地限制“同级集权”带来的过大权力。行政管理体制与司法体制的缺陷、考成制度的引导,促使州县官们更加自由甚至随意地审理州县细故纠纷。如此,州县官在不少情况下难以作出令两造信服的裁决,州县细故缠讼的现象也会随之产生。同时,诉讼时效制度的缺失与限制诉讼次数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也给了百姓不断缠讼的机会。总而言之,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缠讼纠纷走向复杂化,而清代的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考成制度、诉讼制度不仅不能很好地作出应对,其本身也会引发缠讼纠纷的发生。汪辉祖作为个人,既无法阻拦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也无法改变整个制度与体制,因此,他的应对举措只能起到暂时、局部的作用。
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司法实践虽存在局限性,但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首先,汪辉祖在审理缠讼纠纷时会求取实情、力图作出明确公允且情法两尽的裁决,尽可能地避免“不直”,如此,许多负屈小民的正当利益也受到了保护,如前述的匡学义案中汪辉祖所作出的裁决保护了李氏的利益。其次,汪辉祖彻底审结了不少纠缠已久的州县细故纠纷并减少了缠讼纠纷的发生,这也有助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最后,汪辉祖所撰写的官箴书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被誉为幕友和牧令遵奉的“科律”,其在官箴书中所提及的实现“一勘无翻”的做法及惩治讼师的举措或许也能为当时的幕友及州县官们所借鉴。
四、结语
汪辉祖应对州县细故缠讼的举措虽然存在局限性,但对当今的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当前,缠讼依旧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司法难题,民事缠讼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汪辉祖的应对举措充分展现了个人在应对缠讼上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也能启发当今司法机关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道德素养,充分发挥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且司法工作人员在应对民事缠讼时,可以将汪辉祖的应对举措作为本土资源予以变通地利用,例如遇到需要勘丈的案件时,借鉴汪辉祖“念及子孙”的做法,在原被告面前宣誓;参考汪辉祖“劝谕教化”的做法,善用“调解”化解矛盾,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在做到依法裁判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兼顾到情理。由此可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有必要的,优秀传统文化能为化解当前司法困境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不仅要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可取之处灵活地运用于司法实践,还要看到优秀传统文化的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与局限性。汪辉祖的应对举措虽能取得不错的成效,但终究因未在制度与体制层面做出改变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州县细故缠讼。因此,当今应对民事缠讼,不仅要从司法工作人员这一微观个体入手,更要在制度与体制层面发力,不断完善司法体制与法律制度,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司法监督机制。
[1]唐仕春:《北洋时期基层社会的缠讼》,载《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2]参见徐忠明:《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0期;胡震《清代京控中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和官方的结案技术——以光绪朝为例的一个分析》,载《法学》2008年第1期;龚汝富:《清代江西赋税讼案浅探——以<名花堂录>为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李艳君:《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以<冕宁县档案>吴华诉谢昌达为例》,载《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海丹:《“缠讼”与“清讼”——清代后期地方官的上控审判与承审考核》,载《法律史评论》2019年第1卷。
[4][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5]尤陈俊:《聚讼纷纭》,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81-318页。
[1]陈会林:《论传统诉告中“小事闹大”的司法应对方式——以清代司法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汪辉祖任官时官职均为属于州县一级,而在他佐治的34年间,除去早年(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担任知府胡文伯的幕友6年,以及在乾隆三十五年的九月至十二月短暂地佐幕于宁波道之外,他在其余时间均游幕于江浙一带的州县,可见汪辉祖绝大部分的司法实践都在州县一级。汪辉祖在府、道担任幕友时的司法实践的相关材料较少,“州县细故”也将本文研究对象限制在了州县一级,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材料并不包括这一部分。
[3][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载《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17页。
[4][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载《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17页。
[1][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64页。
[2][清]汪輝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64页。
[3][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69页。
[4][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5][清]刘衡:《庸吏庸言·理讼十条》,载《官箴书集成》(第6册),清同治七年(1868年)楚北崇文书局刊本,第197页。
[6]尤陈俊:《聚讼纷纭》,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55页。
[7][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地棍讼师当治其根本》,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46页。
[1][清]汪辉祖:《梦痕录余》,载《汪辉祖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661页。
[2][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未得犯罪真情难成信谳》,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33页。
[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勘丈宜确》,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37页。
[4]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5][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初任需体问风俗》,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29页。
[1][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69页。
[2][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70页。
[3][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70页。
[4][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64页。
[5][清]洪亮吉:《皇清敕授文林郎湖南永州府宁远县知县晋封奉直大夫汪君墓志铭》,载《汪辉祖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778页。
[6][汉]班固:《汉书》卷76,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02页。
[1][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25页。
[2]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勘丈宜确》,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37页。
[4][清]汪辉祖:《学治臆说·为治当念子孙》,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70页。
[5][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地棍讼师当治其根本》,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46页。
[1][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治地棍讼师之法》,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46页。
[2]康建胜:《汪辉祖的司法实践及“情理观”》,载《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
[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亲民在听讼》,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31页。
[4][清]佚名:《汪辉祖行述·遗事中》,载《汪辉祖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804-805页。
[5]此案由于两造之一的杨逢星曾经上控到臬司,故而即使是州县细故纠纷,汪辉祖也需要将此案的裁决结果上报臬司。汪辉祖审结此案过于迅速和顺利,也使得臬司产生了怀疑。臬司驳回五次后又过访杨家,发现杨家早已欣然接受汪辉祖的裁决,这才不再驳回。由于臬司驳回的这一小插曲稍稍延缓了销案的进程,此处便使用“之后”一词。
[6][清]王宗炎:《皇清敕授文林郎湖南永州府宁远县知县晋封奉直大夫汪君行状》,载《汪辉祖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762页。
[1]海丹:《“纏讼”与“清讼”——清代后期地方官的上控审判与承审考核》,载《法律史评论》2019年第1卷。
[2][清]汪辉祖:《学治臆说·亲民在听讼》,载《汪辉祖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版,第231页。
[3][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4][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载梁文生、李雅旺(点校),《病榻梦痕录 双节堂庸训 吴中判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77页。
[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第27、285页。
[2]邓建鹏:《清代州县词讼积案与上级的监督》,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3]海丹:《“缠讼”与“清讼”——清代后期地方官的上控审判与承审考核》,载《法律史评论》2019年第1卷。
[1]徐忠明:《清代中国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以汪辉祖<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例》,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