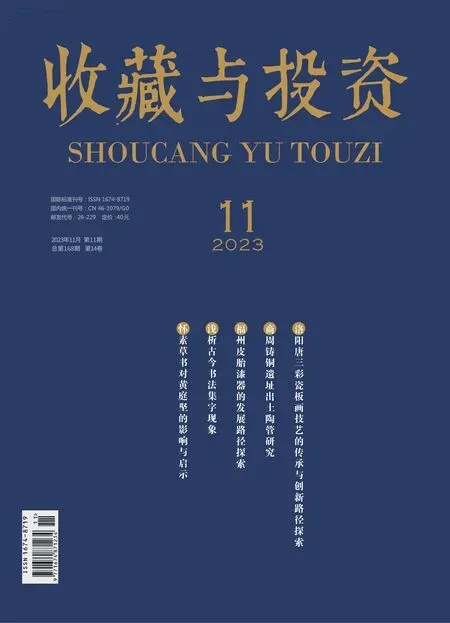北周须弥山石窟艺术与地区信仰
2023-11-24谢千帆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重庆400700
谢千帆,叶 原(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0700)
始修筑于北朝时期的须弥山石窟自中古以来便是僧人信徒参拜修行之所,石窟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的六盘山脉,《万历固原州志》载:“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元封圆光寺。”①固原古称原州,随着佛教传播及信众规模的扩大,形成了浓厚的佛教信仰氛围,并开凿了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须弥山石窟。北周时期是须弥山石窟开凿的高峰,其窟龛形态的袭承与变化,对理解当时原州佛教徒的信仰情况和文化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原审美在石窟艺术中的显现
古代中国修筑的石窟,往往带有本土审美文化特征。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特点,比较典型的是北朝佛像中褒衣博带式袈裟的流行。对此,《历代名画记》的描述是:“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②之所以出现“秀骨清像”的艺术特征,是由于佛教传入之时受到北魏时期汉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风土以及信仰发生碰撞,二者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与传入地相异的信仰形式与文化样貌。
北周时期,承袭自北魏的佛教造像,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相较于前代“秀骨清像”式的艺术特征,北周须弥山石窟造像则变清瘦为丰腴。如须弥山北周第51窟右壁佛龛,头大、脸圆,身形圆润健硕,呈现了萧梁新风(图1)。“像人之妙,张得其肉”,对萧梁佛教造像风格的吸收和借鉴,使得北周时期的造像艺术向南朝以张僧繇为代表的造像审美靠拢。值得注意的是,北周时期须弥山石窟造像风格仍然受到汉文化审美模式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北朝佛教造型艺术受到了南朝迁入工匠的影响,而随着萧梁政权更迭,荆、蜀两地被并入北周领土,北周时期的造像风格则更多展示了对萧梁主流造像风格的吸收和借鉴。萧梁因裁革齐制,张僧繇画派占据主流,因此北周造像虽略有北魏“秀骨清像”的余韵,但更突出丰满圆润的特征。二者的差别体现了时代变化中主流审美取向的不同。可见,北周须弥山石窟的中原审美特征不仅继承了北魏晚期造像传统,也因朝代更替随萧梁主流审美变化而变化,显示了南方政权主流文化对北周石窟艺术的影响。

图1 须弥山第51 窟佛龛
此外,中原汉族的生活方式和起居文化也深刻融入了石窟艺术的外在特质。如北周须弥山第45、46窟造像出现大量帐形龛,其龛口多呈方形或帐形,横枋饰以不同纹样,显得富丽堂皇。古代中国的“帐”泛指床上的帷幔,“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③,作为家居陈设的一种样式,使用帷帐能够突出人物的显耀和华贵,具有鲜明的等级意涵。作为中国传统风俗习惯,将佛像置于帷帐之内,是当时佛教徒们展现心中尊贵神明形象的方式。家具陈设与佛龛样式的结合,不仅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表现,也揭示了原州信众在窟龛开凿过程中,基于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所建构的佛国幻想。
二、北周窟龛与原州佛教信仰表达
北周佛教石窟艺术的变化只是佛教中国化的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信徒对佛教理念的理解逐步演变。在探讨云冈石窟早期佛教艺术与中华文化关系时,巫鸿曾指出二者相互混合的构成模式:“偶像的形式与艺术风格基本上是外来的,但其宗教功能与象征性则是‘中国的’。”④2—6世纪,佛教融入古代中国的生活和民众信仰后,与本土固有的信仰、道德、文化相结合,从而呈现了具有本土特征的信仰形式。
须弥山北周第46窟中心柱下层基柱所刻神王就属于原州地区佛教信仰本土化的一个例证。神王是佛陀的护法神,源于印度民间信仰与婆罗门教,在经文中,神王能够“护今现在及未来世诸比丘辈,不令五瘟疫毒之所侵害。若为虐鬼所持,呼十神王名号之时,虐鬼退散,自护汝身,亦当为他说,使获吉祥之福”⑤。可见须弥山第46窟中所刻神王,目的在于供养、护持佛法以及保佑吉祥。祈福禳灾透露着道教“贵生”的想法,而佛家强调“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⑥,结合第46窟内七佛“七世父母”的内涵,可见窟内所刻神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的是人们禳灾祈福的世俗思想。
此外,北朝后期的北方地区,弥勒菩萨信仰相当流行,在北周须弥山石窟中亦可见单身立佛、佛装和菩萨装的弥勒形象。关于信众对弥勒信仰的指向,北周天和四年(569年)王迎男造像碑所刻发愿文颇具代表性,节录如下:“……今有邑师/比丘道先合邑子五百廿人/等,自慨上不值释迦初兴,下/不睹弥勒三会,二宜中间,莫/然□(兴)□□。遂相率化,割削名珍,敬造石像一区,崇功已就,仰/愿皇帝圣祚长延,明齐日月/。良相永□,忠臣孝友,及历劫诸师,七世父母,因缘眷属,法/界众生,有形先亡,神杲九□/,现在大寿,恒修功德,神造□/无上至菩提,一时成佛/。天和四年岁次己丑八月戊午朔廿二□(日)乙卯造讫。檀越主王迎男。”⑦就碑文所示,有多达五百二十人参与了造像活动,文中“皇帝圣祚长延”“忠臣孝友”“历劫诸师”“七世父母”“法界众生”等称谓,其背后既隐含着对自身命运、父母来世的关心,也包括对众生、国家的希望。北周须弥山石窟弥勒造像多在中心柱窟内,供信徒礼拜之用。由造像题记体现的儒家伦理规范与佛教信仰交融的福报体系,则从侧面反映出北周时期原州地区宗教行为融入社会秩序建立、社会道德维护的过程。
三、地方治理与须弥山石窟面貌的营造
“宇文泰军于高平,因而规定关陇”⑧,原州是宇文泰的起家地,永安三年至永熙三年间(530—534年),宇文泰“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⑨,管理原州四年之久。永熙三年宇文泰平侯莫陈悦,出兵洛阳,两次皆从原州发兵,足见原州对于宇文氏政权稳定的重要意义。也因此,北周时原州地方长官长期由宇文泰心腹原州李氏家族的李贤兄弟担任。北周时期,原州是边城胡族与汉族的杂居之所。自北魏以来原州就居住着一定数量的游牧民族部众:“初,显祖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有一千余家。”⑩由于部落间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原州长期维持着“夷汉杂居,风土劲悍”的地域特征。可想而知,至须弥山礼拜的佛教信众也多为混居杂糅的汉人与边地胡族,因而对于地方治理而言,北周政权所提倡的伦理规则与教化在须弥山石窟中的显现,相比汉族聚居区具有更为鲜明的现实意义。
北朝以来,佛教不仅在宗教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在政治、社会层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⑪,借助沙门教化信众,意味着佛教信仰脱离了纯粹的个人性,个体的宗教行为则被置于家族、社会、国家的道德规范之下。
在此语境下,北周时期具有官方性质的窟龛造像显然具有教化信众、传播儒家价值标准的功能。以须弥山北周第46窟为例,虽然窟龛人物皆着圆领窄袖胡服,但在姿势上,维摩诘居士、文殊菩萨及一位侍者采用的却是中原汉族文化中的跪坐礼俗(图2)。宇文氏原属鲜卑后裔,由于得到汉族世家的支持势力逐渐壮大,王朝遵奉周礼。因此,北周须弥山石窟出现“胡服跪坐”的造像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个背景,其内核是北周统治者意志的体现,与调和胡汉差异的策略有关。借助宗教意象,以儒家文化作为立国基础的国家意志得以在原州佛教信众间得到强化和传播,这也为“胡服跪坐”的出现提供了合理解释。
此外,将象征官职及身份的车马图像用于供养人像,则更明确地展示了地方权力与石窟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莫高窟第290窟窟主是河西公李贤⑫,在290窟供养人像中就出现了颇具礼仪性的车马图像。舆服志中详细规定了从天子到公卿大夫各阶层的车马使用制度,石窟中车马形象通过礼制化的图像秩序向信众传达了政治权威和等级规范,强化了供养人与普通佛教信众的社会等级和尊卑差别。在此意义上,莫高窟第290窟的车马图通过描绘富贵的生活方式和场景,强化了观者对其背后所代表的世俗权力的崇拜意识,反映了北周时期原州李氏家族试图在超越性的信仰环境中凸显世俗等级观念,维持显赫地位的期望和努力。
四、结语
北周时期须弥山石窟所呈现的艺术形式,深受北周立国的文化倾向和原州地区佛教信仰表达的影响。得益于汉族世家的支持,北周宇文氏更倾向于汉化发展方向,反映在须弥山石窟艺术中,便是中原汉族主流审美模式在造像、窟龛形制上的显现。本土化、世俗化的信仰形式是佛教艺术能够如此契合古代中国伦理信条、道德规范的内在原因。当宗教信仰与儒家伦理规范相互交融后,北周须弥山石窟的建造与社会秩序建立和社会道德维护有所交集。可见在古代中国,人们所追求的终极境界并不是原始佛教信仰所强调的绝对与超越,而是在有限的俗世中实现人生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