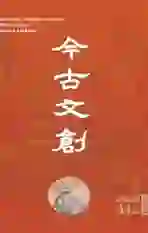明代北疆边界贸易的转型
2023-11-20高娜
【摘要】大同镇商业贸易是明代北疆边界贸易的一件大事,但有关大同镇商业贸易的文献记载材料较少,以致于现有研究存在一些基本的史实错误。基于此,考察明代洪武至景泰年间的蒙汉贸易,天顺至嘉靖年间的蒙汉贸易,隆庆至崇祯年间的蒙汉贸易,研究明朝与蒙古贸易发展的轨迹,对明蒙互市的情况及互市贸易的主要商品分别进行详细的考证与分析,探索边界贸易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北疆;商业贸易;互市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4-009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30
一、洪武至景泰年间的蒙汉贸易
明朝初年,元順帝向北迁移后与明对峙,双方时战时和。明处于强盛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处于发展的趋势,而此时的元虽然北迁,但还是心怀复兴之志,洪武年间双方关系以战争为主。
建文三年,鬼力赤杀大元的大汗坤帖木儿,并且自称可汗,废了北元国号,称回鞑靼。从此蒙古分裂成为了三个部,分别为:兀良哈部、瓦剌部、鞑靼部。兀良哈部势力在这三个部里最弱,所以在漠北蒙古势力里主要是东蒙古势力鞑靼和西蒙古势力瓦剌对抗。明廷对待愿意臣服的部落则允许朝贡,敌对部则用军事手段打压。永乐年间,明与漠北蒙古部落的经济往来开始走向恢复。明蒙之间的朝贡贸易在正统至景泰年间发展到了高峰,朝贡贸易制度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完整的机制。在朝贡贸易的发展中衍生出了马市。
(一)洪武至宣德年间的蒙汉贸易
对于那些向明朝臣服的蒙古部落,明则会通过“发布诏谕,允许蒙古各部在与明通好的前提下,可以前来朝贡,明朝则会给予赏赐并与之互市。”这是明用政治和经济双重手段对蒙古各部进行的招抚——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实现了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产品交换。
建元三年,漠北蒙古分为东蒙古鞑靼和西蒙古瓦剌两大势力,他们之间相互厮杀。而明朝在明仁宗明宣宗的统治下国家安定、政治清明,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仁宣之治”。蒙古势力明显弱于明方,明蒙关系上,明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办法。针对蒙古不同的部落分别采用军事和经济两种手段,从而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首先,对于那些没有向明朝臣服的蒙古部落,明成祖亲自率领军队打击,以此来削弱他们的势力,比如在永乐年间明利用军事手段来打击漠北蒙古势力。在明朝用军事手段沉重打击后,鞑靼的太师阿鲁台在永乐八年派遣使者朝贡,明朝赏赐了袭衣和彩币,随后明朝册封了鞑靼的太师阿鲁台为和宁王,封其母亲为和宁王太夫人,明朝与瓦剌恢复朝贡关系。
另一方面,明成祖多次向蒙古两大势力遣使以求通好。永乐年间瓦剌的马哈木派遣使臣随着明朝使臣亦剌斯等至明朝贡马,后来马哈木被册封为顺宁王,秃孛罗被册封为安乐王,太平为贤义王,明朝与瓦剌正式恢复朝贡。
瓦剌自永乐八年后,每年一贡,有时是两贡,贡道常走宁夏、甘肃。贡物主要有马、驼、貂鼠皮等。东蒙古鞑靼从永乐八年开始朝贡,每年一或两贡,有些年份会三次或者五次。朝贡时间不固定,每年正月、十一月或者十二月。永乐十三年贡使最少,为三十二人,宣德十三年最多,为六百六十人。永乐十三年十一月贡马数量最少,为七十五匹,宣德五年正月贡马数量达到最大,为一千二百八十匹。朝贡物品与瓦剌的贡品差不多,也主要是驼、马、青鼠皮、貂鼠皮等。明朝赏赐的物品主要是鞍马、金盔、绒锦、织金文绮、彩币、彩绢、袭衣、纻丝。这些物品都是供给蒙古部落的酋长和贵族消费的奢侈品。
(二)正统至景泰年间的蒙汉贸易
蒙古方面,西蒙古瓦剌部在脱欢、也先父子的苦心经营扩大下日益壮大,最终在正统年间统一了蒙古。蒙古的政局稳定,军事力量也很强大,明朝在军事上采取全面防御。蒙古统一后,便不再接受册封,但积极向明朝派遣使者进行朝贡,以此获得更大的积极利益,但明朝因为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在外交上被动且保守。所以明蒙的朝贡关系逐渐转变成朝贡贸易关系,也就是朝贡沿途贸易。
1.由朝贡衍生的朝贡沿途贸易
明朝边防到仁宣宗时期荒废,频繁发动战争对于明的实力来说已经不现实,而且仅依靠武力也不能解决明蒙关系,经济上加强贸易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再加上瓦剌在统一漠北蒙古诸部后,实力大大增强,对明的态度颇为积极,不仅向明朝遣使入贡、通好,连派遣的使臣人数和贡马也日益增多,据明史记载,这一时期的蒙古朝贡使团人数增加至三千多人。明朝给予蒙古的赏赐往往是不对等的,这给了明朝无法承担的财政压力,比如蒙方三千余人进京朝贡马匹貂鼠皮,明方需要赏织金彩表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绢九万一百二十七,衣靴帽万”。
正统三年,明廷规定,蒙古的正使三、五人至京,所贡的马驼让人代为上贡,其余的使臣和从人,都在大同留下来,可以将剩下的物品在大同进行交易,这就是朝贡沿途贸易。并且在此时确定了瓦剌向明朝朝贡的时间和路线。时间和路线大体是:每年十月从大同进入边境,参加正旦的朝贡,然后赏赐宴席,二月离开大同,明方派遣使臣送瓦剌使臣返回,等到下一个使团进京时再返回京城。
正统十四年,蒙古军队在瓦剌首领的率领下大举南下,王振撺掇明英宗仓促亲征,最终明军大败,明英宗则在土木堡被俘。自此明蒙的沿途贸易禁了一段时间,直到蒙双方迎来和解并签订了景泰和议。明蒙关系在此时到达了第一次高潮。李秉在景泰五年向明景帝上奏道“昔尝待之以宽,今遽太严……乞驰其禁”,明景帝最终放松了禁令,所以大同的朝贡沿途贸易逐渐正常化。
2.私市开始出现并且活跃
私市是在蒙汉毗邻的区域,蒙汉人民自发地进行互市,私市因为常常包含明朝的违禁物,所以一直被禁止。明方人民常常以斧、铁、细耳坠、火石来换取蒙方的裘、羊肘、马尾、羔皮。一些人为了获得利益,便铤而走险用违禁物品来贸易。正统八年,“今岁瓦剌使臣行李内多有盔甲、刀箭及诸违禁铁器,皆大同、宣府贪利之徒私与贸易者”这些人里并不缺乏官吏。
明朝政府面对私市并非置之不理,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打击私市,比如命令锦衣卫到居庸关至宣府、大同,使臣经过的地方以及去处侦查缉拿,如果有将军器走私给蒙方则押送到京城;明朝政府还一再向大同和宣府总兵等官下禁令,凡是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成批的缎子、绸绢、丝绵卖给境外的人,杖责一百,负责挑担运输的人罪减一等。私自贩卖硫黄五十斤或者焰硝一百斤以上的,也要治罪;明廷对参加私市的官员也做出了严厉的禁令“凡官员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于进贡夷人图利……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斩,为从者,问发边卫充军”。
这些措施并没有使走私贸易消失,我们可以从明景帝在景泰三年(1452年)在敕书中提到的一段话看出来,“近访得瓦剌使臣察占等带来在馆盔甲、腰刀、弓箭、把铳等物,每件有至二三百以上者,此必初入境时沿途军民贪图微利潜卖与之”,民间的走私贸易依然很活跃。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常常会令人多制造一些钢铁箭,偷偷用瓮盛着这些违禁物送给瓦剌使臣,作为回報也先每年则用良马等物贿赂郭敬。
二、天顺至嘉靖年间的蒙汉贸易
景泰年间,蒙古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天顺至嘉靖年间蒙汉处于长期战争的状态。天顺至弘治年间,蒙汉的朝贡贸易时断时续,弘治末年到嘉靖中期,蒙汉的战争持续了将近四十年。所以在弘治十一年后,蒙汉的朝贡贸易中断。正常的贸易不能进行,这时私市开始泛滥。蒙汉贸易地中断,在多次求贡没有结果后,蒙方兵临城下,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被迫对蒙开设马市,但这种在胁迫下开设的马市很快就关闭了。
(一)天顺至弘治年间的蒙汉贸易
天顺六年二月,明英宗在给孛来的敕谕中,让他在朝贡时照旧从大同经过,蒙汉朝贡贸易在此时恢复。至五月时,明英宗在给使团正使察占的敕谕中,让他只带三百人进京,“其余从人俱留大同安歇,给与口粮,下程有货物交易者,听其就彼交易”,从此,大同地区的朝贡沿途贸易正式恢复正常。但从天顺末年一直往后,蒙古地区各部落之间相互争夺,对明朝也是掠夺和朝贡同时进行,但双方的朝贡关系却一直延续着。
(二)弘治末年至嘉靖年间的蒙汉贸易
1.走私贸易泛滥
朝贡贸易中断并不意味着明朝与蒙古之间的经济往来停止,蒙古的牧民缺少斧,衣帛;而内地的军民也因朝贡贸易的中断缺少军马、农耕、畜力、皮货一些生活用品,因此双方的贸易往来并不可能因此而中止,当正常途径受到阻碍时,蒙汉军民就会以贸易走私的形式来代替原来的朝贡贸易。这样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困境,也更好地继续维系双方的经济交流,在这种情况下走私贸易出现并开始代替朝贡贸易成为双方经济交往的主要贸易形式。
私市参与人员很广泛。上至中高级将领等“势家”,下达军民都积极参与其中,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总兵神英、巡抚刘瓛、镇守孙振等官员带头交易。对于私市的进行,官员们有意放纵,双方军民相互勾结,甚至“虏代墩军瞭望,军代达虏牧马”,长城沿线的墩哨军士不顾禁令帮助达虏进行交易。
私市主要的交易物是铁器、兵器。明朝担心蒙方交易换回兵器来和自己一方作对,正统三年下令“庶远人驼马军民得与平价交易,且遣达官指挥李源等通其译语,禁货兵器铜铁”;明廷主要是担心蒙方换取铁锅、铜汤瓶、剪子等金属物品后打造成兵器来攻打自己,所以在弘治十六年下禁令,军民和监管市场的官员在开市的时候不能携带铁锅铁器。但这些禁铁令并没有生效。反而铁器作为私市的主要交易物存在。“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边境官民常常私造兵器等瓦剌使臣返回时在闲僻的地方交换或者将官用军器也卖给蒙古。交换手段也是相当奇妙,以送礼为借口藏在酒坛里。
2.独立的贸易形式——马市
蒙方多次求贡未果,俺答发动了“庚戌之变”,战争攻打至京城的东直门,并说“予我市,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虏而郭”俺答汗在此时再次提出通贡互市。在边臣仇鸾、苏佑、翁万达的努力下,明廷方面则表示支持互市,但拒绝建立朝贡关系。加上仇鸾趁机撺掇仇鸾与明朝开设马市,蒙古方面最终将原来请求由通贡改为了开设马市。最终促成了嘉靖三十年四月的大同马市。
马市设立后,朝廷派侍郎史道来掌管相关事宜,这次马市最终交易马匹约2700匹。
首先,马市开设地点确定但市口少。这次马市共有四处地方——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堡、延绥宁夏花马池、大沙沟。
其次,马市开设时间短暂。蒙方对于这次马市并没有珍惜,“大同市则寇宣,宣市则寇同,甚者朝市暮寇,并掠羸马去”。在进行大同如果开市就去宣府掠夺,反之则掠夺大同,一边与明朝进行马市贸易一边掠夺,蒙古一族甚至还用体质羸弱的马换取丰厚的物品,如果不允许,就大声喧哗,并且马市是蒙方兵临城下胁迫明方开市,这些原因都决定了这次马市不能长久,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关闭马市。
嘉靖三十一年,明世宗表示,各个边境的马市全部禁止,但凡有建议开马市的人,则斩首。最后,马市开始以一种独立的贸易形式出现,不再是朝贡沿途贸易的附属形式,它有着固定的市期和地点,并且规划了蒙方互市的部落顺序,在管理规则上也是相对明确,这些说明了大同地区的马市已经由随意性的贸易向正规性的贸易转变。因此,这时的大同地区蒙贸易的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三、隆庆至崇祯年间的蒙汉贸易
明朝隆庆和议后,结束了明蒙将近七十年的战争对抗局面,在明廷意识到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大量边防所用的兵马后,蒙汉贸易便走向了繁荣。此时的朝贡贸易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所以此处不再详细论述。
(一)繁荣的马市
明朝隆庆五年,明朝在妥善处理把那汉吉事件后,蒙古土默特部抓住了和明朝重修于好的机会和明签订了合约,史称隆庆和议。和议规定:明朝封蒙古土默特部落的首领俺答为“顺义王”,封部落的贵族为都督同知、指挥使等官;俺答一年必须向明朝朝贡一次,明朝厚赏部落;在两族交界处开设马市。马市这一时期在蒙汉贸易形式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次和议后大同地区的蒙汉贸易已经达到了明代的鼎盛时期。之后一直到崇祯年间,在大同地区马市都是蒙汉贸易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的马市极大地促进了大同经济的发展。大同繁华富庶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地区,物品的精美是所有的边陲之最。
1.馬市市期与货源地域的变化
嘉靖时期则规定马市的市期是一年两次,而隆庆时期的官市,由最初的不到半个月一次到后来的一个月一次。嘉靖三十年马市四月开市,十二月闭市,共开设八个月。而隆庆和议后,马市基本上维持到明末。大同镇在隆庆五年共购马2941匹,隆庆六年共购马2378匹,万历元年共购马3788匹,万历二年共购马5000匹。对比嘉靖三十年马市的易马量,隆庆和议后马市的易马量大大增加,并逐年递增。
此时明朝商人运送外地的商品进行市场贸易,以丝织品为例,丝织品作为蒙汉贸易市场主要的交易物主要是因为蒙方的需要,蒙方人民不进行耕织,纺织品全仰仗明廷供给。此时的纺织品主要来自湖广、苏杭等江南地区以及山东。据史料记载“工部覆浙江巡抚萧廪言,岁造段疋、金素,本有旧额,迩因赏赉虏王新增改织二千,独行浙江,然岁造原分各府,则改织不当独派一方,宜分浙江、福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扬州等府及广德州,庶众轻易举”“兵部题赏夷布,查历年买一十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三疋,今改买山东粗布,加一万三千二百九十二疋,每布三千疋为一车,计步填车”。
2.马市由官方主导转为市场主导
明廷批准了王崇古对马价的建议,上等的马匹十二两;中等的马匹十两;下等的马匹八两,但在马市中实际情况却是上等的马匹九两;中等的马匹七两五钱;下等的马匹六两四钱。隆庆年间大同马市的平均马价是白银七两多,价格逐渐下降。官方虽然有固定的价,但实际价钱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马匹的定价已经由官方控制转移到市场控制。
3.市口分布独具特色
宣大山西是拱卫京师的非常重要的防线,一旦被攻破,王朝岌岌可危,所以这一线市口的布局设置上还要考虑防卫问题。在靠近京师的一侧,市口设置的密度偏低,而远离京师的那侧,市口设置的密度偏高。所以,大同市口沿着长城边城墙分布,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都集中在东北侧,间距比较大,开市的周期也比较长;六个小市主要集中在西南侧,间距比较小,开市周期也比较短,市场大多都分布在长城边城墙的外侧,以此来防御蒙古势力的入侵。
(二)民市开始出现
为了弥补马市的不足,开设了民市,允许民众自相交易。民市开设时间短,市场少,常设在沿边墩堡,在万历元年,大同又设立了“月市”,顾名思义,这种互市市场一月一开由蒙古部落人民和以山西商人为主要成分的商人进行交换。月市其实是民市的进一步发展。在民市和月市里粮食、生产工具以及生活用品都是主要交易物。蒙古位于漠北,其气候、环境决定了大多数的地区都不适合耕种。蒙古人民常常会“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这种需要使粮食成为重要的交易物品。蒙古人虽然有大量的牧马牧牛但却缺少耕牛和耕作工具,蒙方的冶金技术和耕种技术大大不如明方,所以需要从明方换取大量的生产工具;蒙古人也会用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等来换取明方的生活用品。
在嘉靖三十年和议前泛滥的私市,使明蒙双方高层意识到必须要将这种涣散的市场纳入到官方的控制下,才能使双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所以在隆庆六年将这种私市转变为官方的民市。
四、结语
明蒙贸易是从朝贡贸易开始,而马市、私市也是由朝贡贸易开始。朝贡贸易双方上层之间的交易,并不能满足边境下层人民的需要,于是马市、私市出现。明朝初期,洪武年间到景泰年间,朝贡贸易恢复并且占主导,马市作为朝贡贸易的附属品存在,私市萌芽;中期,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朝贡贸易时断时续,马市在蒙方兵临城下被迫设立,但已经成为独立的贸易形式,私市在此时蓬勃发展;后期,隆庆和议至明朝末年,双方在政治协议下维持和平,马市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马市已经有完整的机制,私市转化为民市。
蒙汉双方冲破了重重阻挠,最终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商业贸易关系。通过互市贸易,蒙古族人民获得了游牧经济无法生产出的商品,这促进了蒙古经济的发展。蒙古各部将大量的牛、羊、马等牲畜和皮毛、马尾等畜产品输入内地,这不仅仅满足了汉族人民对畜产品的需要,也打开了自己产品的市场,推动经济的发展。
隆庆时期的马市形成蒙古族人民与江南人民进行交易的平台,蒙古族人民大量畜产品流入到江南地区人民的生活中,改善了江南地区汉族人民的生活,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蒙汉互市贸易满足了蒙汉两族人民的需要,拉近了蒙汉两族的距离,促进了民族融合。
参考文献:
[1]田靖.明代大同地区蒙汉贸易形式演变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5.
[2]金星.明朝与蒙古的贸易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2.
[3]王苗苗.明蒙互市贸易论述[D].中央民族大学,2011.
[4]李东阳.大明会典[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5]李峰,张焯.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6]叶向高.四夷考[M].北平:文殿阁书庄,1934.
[7]方孔炤.全边略记[M].台北:台北广文书局,1974.
[8]王苗苗.明蒙互市贸易论述[D].中央民族大学,2011.
[9]顾秉谦.明神宗实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10]方孔炤.全边略记[M].台北:台北广文书局,1974.
作者简介:
高娜,女,汉族,广州华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