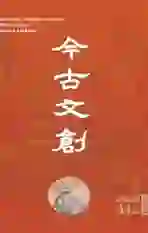《微物之神》中服饰下的绝对他者
2023-11-20王秀秀
王秀秀
【摘要】在阿兰德蒂·罗伊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中,服饰主要反映了两种充满矛盾的他者形象。其一源于近代的被殖民历史,即使解放之后,印度社会依旧以“异域情调”(Exoticism)之名被西方社会他者化,臣服于英国殖民者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其二则是由于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印度社会内部,相对于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低种姓阶层,尤其是“不可触摸者”(The Untouchable)仍然处于一个“绝对他者”的地位。而通过分析这两种不同他者形象的构建过程,作者也揭示了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和种姓制度对权力的操纵,进而导致的一个层层分级充满矛盾的印度社会。
【关键词】《微物之神》;服饰;他者;帝国主义;种姓制度
【中图分类号】I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44-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05
文学中关于服饰的研究最早始于女性主义文本。乔·保莱蒂(Jo B.Paoletti)曾提出,男权社会通过规定女性服饰的色彩、剪裁方式以及配饰,实现对“女性气质”的定义,从而进一步维护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实现对女性的生理及心理的压迫与束缚。比如,因紧身装束对女性行动力和活力的限制与剥夺而引起的气喘甚至晕厥,曾被视为是女性柔弱美最精妙的体现。珍妮·巴特勒(Jennie Batchelor)研究了包括小说、行为书籍(conduct books)和女性杂志在内的正统和非正统文本,调查时尚市场的发展对女性美德之标准带来的影响。国内学者王卫新从服饰入手,指出在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如何掩盖达林顿府不光彩的历史,压抑真实的自我,从而揭示其服饰政治背后潜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正如巴特勒(Batchelor)所说:“服装是一门语言,它的内涵是互通的,并有着无穷无尽的解读方式。”[1]11印度裔女作家阿兰德蒂·罗伊的处女座《微物之神》问世以来好评不断,罗伊也成为第一位获得英国布克獎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印度裔作家。在小说中,人物的服装这一因素巧妙地暴露了种姓制度以及殖民压迫之下,低种姓人群极度低下的社会地位与极端边缘化的社会生存状况,以及底层人物徒劳的反抗与挣扎。印度自1947年便宣布独立且废除了有千年历史的种姓制度,然而政治和法律上低种姓人民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矛盾与冲突的解决。服饰作为《微物之神》中文化以及社会编码的最直观载体,深刻反映了各阶层之间的不对等地位所导致的绝对他者形象的构建过程,以及帝国主义和印度种姓制度双重枷锁下的权力失衡。
一、被他者化的印度传统
《微物之神》从一对异卵双胞胎——艾斯沙和瑞海儿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小镇阿耶门连的故事。小说开头从成年之后二人在阿耶门连的相遇开始,同时又通过闪回的叙述手法,讲述了在1969年,他们的母亲阿慕——一个印度离异的高种姓女子和一个来自帕拉凡阶层(也被称为贱民阶层)的木工维鲁沙二人之间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悲剧。个人悲剧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层的社会原因,而服饰也成了界定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以及不同种姓之间身份的标志性记号。
《微物之神》中的服饰背后隐藏了两种冲突。首先是西方殖民文化与印度本土文化的失衡。印度在独立之后, 依旧无法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因为殖民主义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新面孔,继续操控这个国家。面对这种殖民主义的残留,大部分印度本土人民欣然接受。一方面,对于一部分印度本土人民来说,英国殖民者的文化是先进文化的象征,所以他们选择模仿殖民者的文化,企图从外观上向这种中心文化靠拢,以便抹掉自己边缘的地位。然而在这种模仿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反差愈加深刻,模仿者对于本土的文化嫌弃之心愈发严重,因此两种文化愈加失衡,最终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主导与压迫。《微物之神》中,恰克代表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回国的时候,总会“穿着免烫的套服,戴着红色的太阳眼镜,充满贵族气派的行李箱……他们带来马克西斯和高跟鞋,带来蓬蓬袖和唇膏,带来密克西牌研磨机和相机的自动闪光装置……”在服饰上,他们选择向西方文化靠拢,渴望被“中心文化”所接纳,他们“心中涌起一股爱,以及些许羞耻,因为他们看到来接他们的家人竟然如此……如此……粗俗笨拙”[7]127。对殖民者的爱和对自己植根的土壤的羞耻,这两种感情在他们心中激荡,使他们自动对西方文化俯首膜拜,并臣服于他们殖民者的文化。
在去机场迎接妻子玛格丽特和女儿苏菲时,恰克便努力从服装上去避免这种被嫌弃的窘状,向西方代表的中心文化靠拢。他“把自己的发福的身躯塞入西装,打上领结”。艾斯沙被穿上尖头皮鞋,梳着猫王的飞机头。瑞海儿穿上花边连衣裙,“被打扮得像品味极差的机场仙女。”[7]126他努力擦掉自己以及他的家庭身为印度人的印记,使之配得上身为白人的妻女。因为在恰克与妻子玛格丽特的婚姻之中,与“他的征服者结婚”[7]45使恰克获得一种自己与西方人同等地位的错觉。所以为了维持这种地位,恰克所代表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intelligentsia)模仿西方的穿着,学习他们的语言,从日常习惯上磨灭自己的印度性,努力在印度的身躯上裹上一层白面罩。而这种穿着上的模仿也卓有成效,西装领带成为西方权力的象征,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所以在拿行李的时候,“戴着帽子佩戴肩章的看守员,受到恰克的西装和歪着的领带的威胁”,匍匐在地,臣服于代表着西方文化的服装符号中。[7]126
印度人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来自早期自身被殖民的历史。1835年,殖民政府曾颁布《英语教育法案》(English Education Act),旨在“推广印度人对英语文学与科学的学习。”[4]798这便是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形成的原因。《微物之神》中恰克的父亲帕帕奇便是这项法案的受惠者之一,他接受过西式教育,印度独立之前,他是一位大英帝国昆虫学家;独立之后,它变成了动物研究院的副院长。对于英国文化,他顶礼膜拜,因为对帕帕奇来说,正是因为来自殖民者的馈赠才使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可以高高地凌驾于印度本土人之上,享受作为特权阶层的优势。所以在他的女儿阿慕因为自己的丈夫准备把她献给自己的英国长官而离婚时,他拒绝接受她。因为在帕帕奇心中“没有一个英国人会觊觎别人的老婆”[7]39,尤其是一个有着印度面孔的女人。帕帕奇之流,便是殖民者要培养的阶层,他们把西方文化奉为瑰宝的同时鄙视自己的本土文化。但是殖民者颁布法令的本意是要培养出自己的代言人,培养一个帮西方人统治千千万万印度普通群众的阶级,一个“虽然有着印度人的血液和面孔,但品位,生活习惯或者学术追求都和西方如出一辙的阶级”[4]798。
那些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阶层们对于西方人模仿和崇拜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法侬曾经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写道:“黑人为了得到白人的尊重,努力脱离自己低劣的种族,进入白人社会。他们努力抹去自己黑人身份所带来的耻辱,他们憎恶自己,然后生理和心理都进入一种自我贬低,自我毁灭的状态。”[9]56把社会语境转换到印度,这种自卑情结在帕帕奇身上得以体现,他退休后日日穿着剪裁得体的“羊毛西装”,戴着怀表,坐在蓝色的普利茅斯里[7]46,这些西式服饰代表着他创造的白人身份。而玛玛奇穿着的“沙丽”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代表。帕帕奇对玛玛奇的殴打,则是两种服饰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压迫,结果便是帕帕奇代表着他的殖民者对自己的文化实施了殖民行为。
二、帕拉凡的绝对他者形象
除了帝国主义和印度传统的矛盾,《微物之神》中印度社会的内部冲突依旧存在且愈演愈烈。这种内部冲突来自印度的种族制度。在印度独立之后,这种制度虽然表面上被废除,但依旧在印度社会发挥着自己的影响,控制着一代又一代的印度人。如陈峰君在《印度社会述论》中所说:“即使在大城市的公共场合大家按照现代观念行事,但私下里,老旧观念依旧盛行,而在农村,许多地区依旧奉行严格的种姓制度。”[8]167在《微物之神》中,种姓制度和资本主义相结合,使得各个种姓又被糅杂成新的阶层,继续延续着印度这一古老制度。
首先文中女性这一群体的服装呈现鲜明的对比。文中高种姓女性的服饰总是各种昂贵的莎丽与各种华丽的首饰。不同于西方的玛格丽特的洋装,《微物之神》中印度高种姓女性如宝宝克加玛、阿慕或者是玛玛奇的服饰,总是“柔软,干爽,被烫过,被熏过香”的莎丽。[7]152-256玛玛奇耳朵上戴着钻石耳环,手上佩戴着红宝石戒指,二十三年后的宝宝克加玛戴着她所继承的全部珠宝。与伊普家族女性华丽的装扮相对比的是文中出现的女工。在迎接恰克的女儿苏菲默尔时,她们排成一排,名字按照首字母顺序列出。(阿竹,荷西,阿尼安……)她们的“蓝色的围裙,白色的帽子,像一团别致的蓝白裙子”[7]157,在这里,这些女工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化身為一种符号,她们不仅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更要服务于老板妻女所代表的外来文化。她们所穿着的围裙则是他们身份的代表,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御寒,因此穿大衣是合时宜的,但围裙不一样,它意味着不体面的活动……从事需要防止尘土污染的劳动是一种侮辱”[3]14。种姓制度下的地位不平等,在殖民主义的入侵下,形成了新的形式。伊普家族腌菜厂的发展与壮大,以及恰克之流与西方文化的靠拢,使得高种姓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形成了高种姓资产阶级。与之相对应的工厂的工人们除了在古老的种姓制度下挣扎,又化身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成为“他者”,屈身于资本主义与种姓制度的双重剥削。
在这一群“他者”中,处于最边缘的则是以维鲁沙为代表的帕拉凡(Paravan)——不可触摸者(The Untouchable), 也被称为贱民阶层。在印度社会中,“贱民阶层(帕拉凡)被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禁止用衣物遮盖上半身……”[7]65除了芒杜,他后背那片“来自胎记之树的叶子”[7]158是他唯一可以遮身庇体的东西。从服饰上,他的身份被绝对地限制甚至否定。他在这个以恰克一家为中心的小世界里,是低于其他工人的存在。从服饰所代表的表层身份上来说,帕拉凡的存在不被认可,他们的身份受到了否定。因此在整个印度社会中,他们没有话语权,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处于边缘,是绝对的他者。
三、觉醒者的徒劳反抗
在小说中,维鲁沙是作为一个勇于反抗印度社会不公制度的普通民众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是微物之神,是能够“讲述自己故事”努力摆脱被代表的命运的先行者。维鲁沙的反抗,首先体现在他的政治追求。工人阶级斗争爆发时,他穿上白衬衫,拿着红旗,参加了著名的“科钦游行”。从被禁止用衣服遮盖上身到白衬衫和红旗,是从一种身份缺失到新身份的获得,也是维鲁沙身份从帕拉凡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短暂的转变,更是他对印度传统种姓制度的挑战,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颠覆。然而以皮莱为代表的活动负责人,只把政党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的、改善自身生活的工具,而并不真正在乎帕拉凡的社会地位;而其他参与活动的普通工人,虽然或多或少地也参加了活动,但并未将之放于心上。所以,维鲁沙以一己之力对古老制度的反抗最终以流产的结果告终。
帕拉凡阶层的维鲁沙与来自婆罗门的阿慕本不为他人所容的爱情,也是另一种对古老制度的蔑视。按照《摩奴法论》的规定,髙种姓男子勉强可以娶低种姓女子,而低种姓男子和高种姓女子则绝无婚配的可能。从服饰上来说,它留给人的是表层身份(surface identity),穿上服饰之后,“许多可能的身份就被隐藏在下面”[6]149。二人的跨越种族阶层的相恋说明了他们意识到服饰所代表的身份之下,二者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拥有平等爱人以及被爱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对服饰所代表的身份的一种否认,更是对既定习俗的反抗。在现代文化中,“服饰变成了旧有的、虚幻的生活方式的象征;裸露开始指示新发现的以及新经历的真理;脱衣的举动变成了精神自由、追求纯真的举动”[2]106。阿慕的彻底觉醒便在她脱掉衣服,在浴室里省视自己的身体时最终达成。她以这种自我内省的方式,试图剥离服饰给定的表层身份,直面原始的自己。然而这种大胆地去伪求真的举动之后,等待她的并非自由,而是“一缕疯狂,从装它的瓶子里逃了出来”[7]212。这种疯狂在他们的家族内部流传着,恰克称之为近亲结婚的后果,而玛玛奇不同意。在女性视角来看,这种疯狂是一种清醒之后无力反抗既定现实的逃避之举。而阿慕,作为新一代的清醒者,剥离虚假外衣之后看到的只有深深的绝望,只能把自己藏在“沉重的头发”之后,然后“从分开的发缕之间凝视通往衰老和死亡的道路”[7]213。
维鲁沙对平等爱情的追求,阿慕对自己不幸婚姻的抗争,都是一种对强压在小人物身上强权的反抗。然而种姓制度植根于印度人的血液之中,禁锢各种姓各阶层印度人的思想,维鲁沙的父亲,因为自己儿子的与众不同而恐慌;克加玛为了掩饰维鲁沙与阿慕的恋情,谎称他挟持了阿慕的孩子;本该执法的警察即使知道真相,却因维鲁沙的帕拉凡兼共产党员身份可能给他们带来政治麻烦,依旧坐实他的罪名。种姓制度从上至下像一层枷锁,使人们在这个金字塔般层层分级的社会里,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使之代代流传。
四、结语
在《微物之神》中,服饰化身为一种符号,和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无形中代表着各种社会、阶层以及不同文化的冲突与失衡。这种符号的背后隐藏着的两种他者形象的构建,正是不同权力关系的失衡所导致的后果,也就是殖民者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失衡以及不同种姓之间的层层压迫。文中不同人物悲惨命运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种姓制度对权力的操控。而在操控权力的过程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得当代印度社会形成以西方文化为首的层层分级的状况,同时也构建出帕拉凡阶层的“绝对他者”的形象。
參考文献:
[1]Batchelor,Jennie.Dress,Distress and Desire:Clothing and the Female Body in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2]Berman,Marshall.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
[3]Cunnington,Phillis.Costume of Household Servant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900[M].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74.
[4]Muir,Ramsay.“The Making of British India 1756-1858”[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16:798-799.
[5]Paoletti,Jo B.Sex and Unisex:Fashion,Feminism,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5.
[6]Trimm,Ryan.“Inside Job:Professionalism and
Postimperial Communities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J].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2005:149.
[7]阿兰德蒂·罗伊.微物之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8]陈锋君.印度社会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9]法侬.黑皮肤,白面具[M].上海:东方出版社中心, 2022.
[10]王卫新.试论《长日留痕》中的服饰政治[J].外国文学评论,2010,(01):216-223.
[11]黄芝.“天堂与地狱之间”:《卑微的神灵》中的卡塔卡利舞者[J].外国文学评论,2014,(01):133-142.
[12]赵建红.全球化与后殖民状况:《微物之神》之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7,38(02):13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