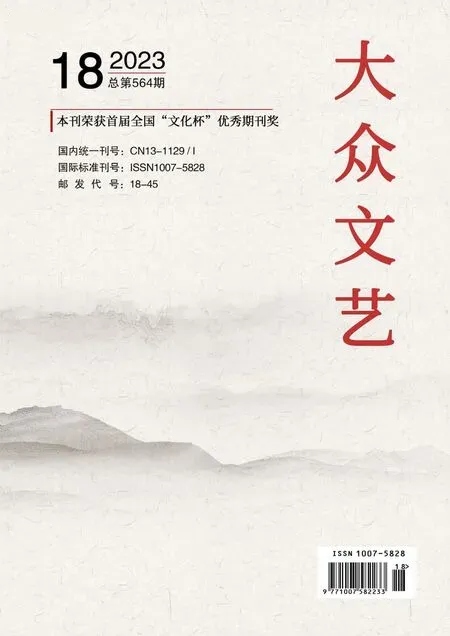《玩偶之家》与《朱丽小姐》的主题选择与中国接受之比较*
2023-11-15李子轶
李子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106)
作为对二十世纪西方戏剧发展影响深远的两位剧作家,易卜生与斯特林堡在欧洲戏剧史上的地位可谓不分伯仲,两人在戏剧观念上针锋相对,在艺术手法上各具特色。易卜生的《玩偶之家》(1879)与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1888)这两部分属“现实主义戏剧”与“自然主义戏剧”的同时期代表作,都聚焦女性角色来探讨两性关系问题,但二者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却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前者于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的192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掀起波澜,而后者则是到了“戏剧观”论争激烈的1980年代才被国人所知晓,更多是在戏剧界产生影响。这并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两部作品的主题差异以及时代选择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一、娜拉之走与人格独立之声
19世纪中叶,在欧洲诞生的“社会问题剧”注重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相关问题的发现与观照,进而呼唤人们关注和讨论,寻求解决之道。受其影响,易卜生的创作在1864年以后也发生了转向,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代表作《青年同盟》(1869)、《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3)等都从不同角度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这些剧作都具有很强的主观上“提出问题、表达主张”的意识,对剧作引发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恋爱婚姻与妇女解放往往是易卜生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重点之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家庭生活中,爱情常常不敌金钱,女人也难以摆脱男人的支配。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一经面世,随即引起巨大轰动与激烈争论。家庭主妇抛夫弃子、离家出走,这是当时的社会观念所无法认同的。由于题材的爆炸性,这部剧作的艺术成就在当时反而被忽略了,剧中所反映出来的女性“出走”问题则成为人们兴趣的焦点。《玩偶之家》在题材上所带有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叛逆”特质,为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中国接受”奠定了先天的心理基础。
民国初年,中国的思想解放与女权运动风起云涌,旧的观念得以破除,新的观念在尝试与碰撞中逐渐形成,这一切都使得女性独立意识变得愈发强烈,女性开始由“闺阁”迈向社会,在对待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别于往昔的态度。“五四”时期至1920年代末,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更是成为整个文学艺术界所聚焦的核心主题。1918年6月,《玩偶之家》经由《新青年》的“易卜生号”介绍给国内公众,翻译忠实地保留了原作的“出走”结局,其所提出的女性觉醒意识与人格独立之声,恰恰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随即在知识界和思想界引发热议。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启发和教化民众的考量,首先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思想观念上的传播,他们更为看重的是剧作直面人生与现实的深刻主题,进而将其引向“为女权发声”的一面旗帜,引发巨大反响。伴随着向西方戏剧思潮学习、“去旧革新”的潮流,国内戏剧界也掀起了一波推崇与效仿的“易卜生热”,应运而生了以胡适的《终身大事》(1919)、田汉的《获虎之夜》(1921)、欧阳予倩的《泼妇》(1922)等为代表的一批“易卜生式”社会问题剧。
易卜生曾谈到,《玩偶之家》关乎的是“人”的自由和独立,并不局限于“女性”。如果仅仅把《玩偶之家》视为女权主义者的“宣言书”,把娜拉看作争取妇女解放与自由的斗士,是对易卜生思想及其剧作本身思想的片面曲解。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需求下,该剧所传达出的女性觉醒与独立自由之声可谓振聋发聩,“娜拉”这一女性角色的成功塑造,使其几乎被奉为女性解放的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由这部戏本身所带来的关于现代公民社会中的人的独立人格,以及对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追求等内容,在当时也就自然超越其艺术价值而成为一种至高精神。
当时的人们更多从“问题”的角度而非“艺术”的角度去探讨该剧也是情理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易卜生在剧中借娜拉之口直抒观点、表达立场时确实带有着墨过重的“人为”痕迹。剧作结尾处,海尔茂在收到柯洛克斯泰的借据后“转危为安”,随即“宽恕”娜拉,而此刻的娜拉却如梦初醒,毅然决然地选择抛夫弃子而离家出走。她在临别前义正词严所道出的告别“玩偶生活”的长篇大论,尤其是那句“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1],则更像是一篇直白、犀利的女性独立宣言。这与1919年《新潮》中叶圣陶先生的倡导近乎一致:“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2]然而,如果根据事件的发展脉络和人物的个性特点等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娜拉这些立场鲜明的独白内容,似乎缺乏“铺垫”,带有略显突兀的“设计”色彩,更像是易卜生对其个人观点的摇旗呐喊。
对于这种借角色之口抒发剧作家个人主张的做法,斯特林堡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他在讽刺当时法国盛行的过分强调精巧结构的“佳构剧”(易卜生的创作便受到这种剧作结构的影响)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在《朱丽小姐》的序言中,他如是说到:“在对话方面我打破了一点常规,没有把我的人物塑造成了引出一个巧妙的回答而坐着提出愚蠢问题的传教士”[3],而是回避了法国剧作中那种数学公式一般的对称式对话结构,不允许人们的思维进行规律性的思辨。这一点是与他一直所追求的“自然的真实”原则相吻合的。毕竟,作为现实主义戏剧的一种极端化发展,自然主义戏剧更加强调要在舞台上做到尽量绝对的真实,不留下人为创作的痕迹。
两位剧作家在戏剧观念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创作表达上的不同,而这也使得“五四”前后的中国选择“娜拉”而非“朱丽”成了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结果。《玩偶之家》与生俱来的更加直接的社会性意义和实用性功能,恰好迎合了彼时中国知识青年们渴望打造具有个人独立意识的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求。从女性觉醒到人格的自由独立,易卜生的呐喊自此响彻中国大地。忠实呈现《娜拉》“出走”的意义,“在于彰显五四时代反传统意识的激烈性”[4]。虽然易卜生的后期创作转向了象征主义,但其观照社会、提出问题的“批判现实主义”在1920年代前后的中国却受到了绝对推崇,并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正是易卜生及其《玩偶之家》所带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多重色彩为当时国人的接纳铺垫了丰沃的土壤。这种“接纳”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它被直接视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一剂“良药”。而反观《朱丽小姐》,那更为细腻缜密、讲求科学的关乎精神与心理层面的两性争斗与头脑博弈,则似乎与当时的中国社会需求不相兼容,“擦肩而过”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种历史必然。
二、朱丽之死与人性博弈之争
有学者指出,斯特林堡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是在1930年代,不但晚于易卜生,在影响力方面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斯特林堡的名字基本上只局限于外国文学专家学者圈内,而易卜生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尊崇的偶像。”[5]实际上,早在1918年,周作人就已经对这位剧作家进行了介绍:“A.Strindberg著作中,戏曲尤为世间所知,与诺威之H.Ibsen并称,如《Julie姬》(Fröken Julie)、《父》(Fadren)、《伴侣》(Kamraterna)皆是。”[6]同年10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发表了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在这份较早较为完备的西方名剧精选目录中就介绍了《朱丽小姐》。然而,较之于易卜生的烜赫一时,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对斯特林堡的学习与效仿者却寥寥可数,这是与其戏剧成就极不相称的。造成这种“错位”的缘由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
斯特林堡笔下的女性角色,通常都带有令人憎恶的负面色彩,在“朱丽”这一人物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斯特林堡的剧作不仅与易卜生差别明显,甚至还是“反易卜生主义”的,“他把妇女解放的问题仅看做是一小部分无所事事的上层妇女的问题,并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百般挑剔、挖苦。”[7]《朱丽小姐》中的某些部分就是反易卜生的女权观点而写的,而斯特林堡本人也常被贴上“厌恶女性者”的标签。无论是他的价值观念或是剧作表达,皆透露着对女性的不善态度,而这一切却都是与1920年代中国社会所追求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尤其是强调女性独立与自由的社会主题氛围全然相悖的。
斯特林堡受“自然主义”创作原则影响较大,他警惕并反对记录烦琐小事的表面的“现实主义”,强调应忠实于自然的真。但是,他“不满意对‘生活的片段’作简单的客观反映,他所要求是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刻的透彻的描绘……他的兴趣主要不在于事件的描写,而在于内在的心理分析……斯特林堡的心理的自然主义重在表现人物的变态心理和精神分裂状态”[8],往往透过剧作“描写根本性的真实,如性关系,意志的心理冲突及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等。”[9]其中还涉及了遗传学、进化论等内容。因此,《朱丽小姐》的主题所关联的两性、阶级等内容具有一定的精神内涵与认知厚度,它并不像《玩偶之家》那样针对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或问题,而是聚焦表象背后的人性话题。他在为《朱丽小姐》的《序》中说道:“我选择了一个可以说是位于当今争执的题目之外的主题,或者说被这个主题吸引住了,因为社会上的升降,地位的高低,好与坏、男与女的问题,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人们所关注的。”[10]这一主题从两性的争斗,继而发展出关于人的思想的博弈,其中更隐含了强者与弱者的微妙对峙,即强者可以通过思想传导,以此为武器进而控制弱者。朱丽小姐从失身、私逃,任由其摆布的堕落直至最终走向自杀,便是男仆让以强者身份在两性之争中获得的一种胜利。然而,这种具有人性永恒价值但却缺乏时代性的主题,无法满足彼时中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迫切需求。
在“五四”前后日渐高涨的社会改革热潮与独立自由的呐喊声中,人们更多是从改良社会与启迪民智的视角去看待戏剧功用,认为戏剧应当直接为现实服务,其社会性应重于艺术性。而斯特林堡在创作的艺术风格与技巧手法上复杂多变,并不直接描写社会问题,缺乏时代感,往往透过更深层次的心理剖析来探讨人性的复杂,这不仅不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其深奥晦涩也让人们难以理解。由此,《朱丽小姐》这部带有浓厚的心理分析色彩的自然主义悲剧,也就不可能如《玩偶之家》那样引起当时国人的认同和追捧。两部剧作所表现出来的对待女性的不同态度以及结尾呈现的人物的不同命运,自然将《朱丽小姐》排除在了国人“主题先行”的视野之外。
真正让斯特林堡及其作品为国人所熟悉,是在1980年代的“新时期”阶段,彼时发生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影响深远的大规模“西潮”。这一阶段的戏剧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验探索、追求创新。一方面,自“五四”以来于文本创作与舞台实践两个维度逐渐形成的“易卜生—斯坦尼”独尊的模式第一次成了需要被打破的对象,人们开始反思过往戏剧创作中那种公式化、概念化、主题先行的倾向,要求“推翻所谓易卜生写实主义戏剧模式,探索新的戏剧叙事形式”[11],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观”的论争也由此展开。在思考中国戏剧未来出路的过程中,戏剧观念开始由单一、僵化转向多元、开放,“现实主义戏剧遭到前所未有的冷落”[12],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追求。作为现代派戏剧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斯特林堡也就自然地进入了国人视野。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译介以及这一潮流在中国哲学界的兴起,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异化等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具体表现在戏剧方面,则是戏剧家们开始关注对人的考查,书写人的存在遭际、生命体验以及人本体的迷惘等等,展现人类精神世界丰富而复杂的面貌。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人学”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得以深化,西方社会对于意识流、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始影响中国戏剧人。于是,新时期戏剧开始从过往的揭露和批判社会政治,转向更为深层次的对于人的内在心理层面的探究。换言之,即从反映现实生活转向了挖掘、拓展人的精神世界。而糅杂着丰富的现代心理学内容的《朱丽小姐》,则契合了国人的这种内在需求转向,成为学习和讨论的对象。时至今日,《朱丽小姐》仍在世界各地长期热演,斯特林堡所留下的关于人性博弈的永恒主题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较之于易卜生,斯特林堡的作品或许没有那么鲜明的典型性与社会性,但是,他始终没有忽视人性深处那些始终叩击心灵的本质问题。
结语
《玩偶之家》与《朱丽小姐》这两部同时期剧作借由两位女性人物的觉醒与毁灭,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不同可能与人性的复杂样貌。两位观念迥异的剧作家通过各自不同的主题与视角,探讨了困扰现代社会的两性关系问题。但历史却对他们开了一个“玩笑”,让娜拉与朱丽在中国接受的“命运”呈现出一种戏剧性的反转之别。然而,较之于《玩偶之家》结构精巧、细节考究的“问题”批判,《朱丽小姐》剥离表象、追求本相的“人性”拷问,似乎更显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与恒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