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的石头
2022-10-13李国彬
李国彬
一
今天,石头很高兴,给雅雅办的事相当顺利,对方看过材料后,没说什么,估计是介绍人把好话都讲到前面了,接着,他把雅雅直接带到了人事科,雅雅就算正式上班了。
雅雅上班那天,作为大哥,石头又一脸严肃地向雅雅交代了一番,无非是如何跟上面和下面搞好关系,不能迟到不能早退,把工作干好,等等。他一本正经地交代时,雅雅笑着点头,一副喜不胜收的样子,直到他离开。
离开了妹妹,石头开着出租车去拉客。一上车,他就把音响打开,大声地放着歌曲。好像是姜京佐的(《野兽》),“轰轰轰”的,唱得非常开心和快乐。他也跟着哼,不时地摇着脑袋,晃着身子,前摆后摇。
车子开到苦瓜路1号时,行人多起来,他的车速减慢了许多。他看到一个老头,六七十岁的样子,提着灰布包,一边擦汗一边左顾右盼,显然在等出租车。同时他又看见一个女子,正低着头,从巷子里往外走,手里拉着一个大箱子,蓝色的。女子个子很高,长发,穿长裙,戴着墨镜,身材是那么苗条,充满了活力。他把车子向那女子开了过去。
Hello(你好)!他把车子开到女子身边后用英文喊话,并把自己的墨镜摘下来,给对方一个满满的笑容。他很黑,在阳光下显得跟木炭一般。
女子冷峻地看了看他,又向车内看了看,然后准备上车。他忙走下车来,帮女子提箱子,塞进后备厢,嘴里还说着,呵,真沉啊!女子笑了笑。见箱子落实了,女子把头发向上一捋,弯腰钻进了车。
女子准备到动车站去,要在六道口上地铁。他算了算,不远。他笑着问,是不是出差呀?女子说,不是。他听出来了,女子不是本地人,便等女子再说,但女子不说了,就那一句话。
他想,如果沿着西门店向前走,只能苦一个出车的费用,而且遇上这么漂亮的女子也失去了说话的机会,于是他把车子掉了一个头,“刺刺”地向翠花乌方向开去。
天很热,走路的人都低着头,或者用手挡着脸。沿河一线,树叶子蔫蔫的,有的都黄了,散发着旱气。一棵棵树,无精打采地站立着,眼看着要垮塌了一般。但是他很开心,空调开着,音乐放着,口哨吹着。车子拐过道口,他放低速度。他在琢磨怎么才能和女子搭讪,这时女子伸着头,看着外面说话了。
变化真大。
你说什么?他问。
我是说你们这座城市变化真快。
他忙“嗯”了一声。
女子接着说,我前两次来好像走的不是这条路,功名道在维修吗?
他又一惊,忙说是的……在修地铁。
这么说着,他赶紧把路线变了。车子鬼鬼祟祟地转了个身,向南开去。那女子感觉到了,也不说这个了,只是说城市建设得真好。
说到城市建设,他来劲了。他是十五年前来到这座城市的,到今天,也算是地道的老居民了。来时,这里还没有地铁,到处都是农田,一到该生长的时候,四处绿油油的,挤挤呛呛的。如今这一片都盖上了楼房,到处高一阵低一阵的,堆山一般。于是,他就以这个城市人的口气,大吹这里的变化,从地铁到高铁,从过河通道到飞机场,嘴“呱呱”地说个不停,一边说,一边还从后视镜里看女子。女子对他的话也感兴趣,不时地和他对话。还别说,女子的声音真好听,跟脆铃一般,是那种嫩嫩的脆,好像冒着水汽。
很快,出租车开到了地铁站,他觉得自己的兴奋劲还没结束,暗自叹了口气,在那儿愣了一下,然后说,到了。
女子打开手机扫码,把钱转给了他,然后下车取东西。他也跟着下去,把女子的箱子提溜出来。他有些渴望地看着女子,但女子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神,只顾看了看四周,然后拖着箱子,飘飘荡荡地向地铁站走去。
回到车上,他闻到车子里有一种独特的清香味,忽淡忽浓,让人陶醉。
二
今天是礼拜三,六道口地铁站门口的人很多,车子沿着绿化带旁的行车线缓慢地向前滑行。他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情不自禁地向地铁口观望。那女子的形象依然那么鲜活,他真希望她能转身回来,问他些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他能解决的。接着他又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走吧走吧。
他正准备加速,忽然有人敲他的车窗,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种人他见得多了。那男人也不说话,只是往前面的空地上指了指。他觉得这个男人可能想在空地上搭车,就把车子向那里开了过去,并从倒车镜里看到那个男人快步跟了过来,然后再次敲他的车窗,“嘭嘭嘭”。他感到奇怪,因为这个时候,客人上车就可以了,没有这种不着调的。他看了看这个男人,眯着眼睛问,有事?那男人点了点头。他把车窗摇下来,一股热风立刻跟了进来。
那男人也不说话,只是把一个黑皮本子展开,轻轻地推在他面前。他看了看,本子很干净,上面有文字:出租车管理处的车管员朱丽。他立刻慌了,把口罩向上扯了扯,身子下意识地动了下,满脸带笑地说,你好,请问……
朱丽向他行了个礼,又做了一个让他把车辆丢开的手势。
他忙把车子熄火,有些慌乱地走下车。他满脸堆笑。说实在的,他怕这种人。去年,他的一个出租车朋友跟这种人斗硬,结果车子被“斗”走了。
朱丽并不看他,说,可知道犯了什么错吗?他摇摇头,脸上的笑堆得更满了,向外溢着,而且越来越不自然。
朱丽敲着他的车窗问,对方要发票了吗?
你说什么?他抹了下口罩,知道不是因为自己没戴口罩的事。
朱丽不说话,看着他,等他说话。
他略做思考,便明白了,是刚才那个坐自己出租车的女人的事,那个女人的美好形象在他心里顿时熄灭了。他只是干笑着不说话,也不看对方,估计在想着什么。他心里有数,大多数客人都不要发票,司机也懒得给,在这方面,或者说自己是没有错的。然后他说,我问她了,也给她了,她不要……
朱丽点了点头说,好,她不要。说着,拿出一沓票据,撕下几张来,然后递给他说,看看吧,她不要发票没有错,你不给就不对了,来,一共360元。
他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坠。现在,出租车的生意非常难做,加上各类网约车抢生意,赚点钱非常难,360元就等于是自己一天的活计。他看着朱丽递给他的那沓票据,苦着脸说,这个……他们都不给……
朱丽说,但你不给,我看见了,不管就是我失职,快点拿着。
他头上的汗出来了,自己留的那个毛寸发型也变形了,脸上也有了汗。再过一会儿,那些汗水汇在一起,一个劲地往下流,花衬衫很快就贴在了后背上。他苦着脸,极不情愿地接过朱丽递过来的票据,又回到车上。他从票夹子里拿出钱来,心疼地抽了几下,这时,他看了一眼票据,愣了愣,又下车回到朱丽身旁,笑着说,我……我只有一个错啊,哪来的六个?什么超速、鸣笛、越界……
朱丽打断他的话,瞪着眼说,六个就是六个,废什么话,否则连人带车去局里。
他举着手,连连认输,把钱给了朱丽。
朱丽并不看他,说转账吧,这样你我都利索。
转账转账。他又连连说,连忙把钱装起来,打开手机,在上面嘀嘀嗒嗒地点了一番,然后又“嘀”的一声把钱转了过去。
好的。朱丽板着脸,看着对面的楼顶说,祝你顺利。
他也不说话,钻进了自己的车。
不知什么时候下雨了,天昏地暗的。雨是突然下的,先是一滴两滴,接着就变大了,一大片一大片的。四处都是树叶子拍打树干的声音,噼里啪啦的。他叹了口气,接着又叹了口气,把车子向雨幕深处开去。
三
车子开出三四公里,也没见到一个招手的人,可是那件事却顶在他的心头,越来越难受。他打开对讲机,把自己刚才的遭遇跟几个出租车朋友说了。几个朋友听后,都气得直摔面前的东西,对讲机里传来乱哄哄的声音。一个叫胡老九的说,告诉你一个绝招,保证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其他几个司机都催着胡老九快说。胡老九就说,他那六个罚单至少有五个是违法的,你跟他说,要么放弃,要么去见你们领导,你试试,看他还敢胡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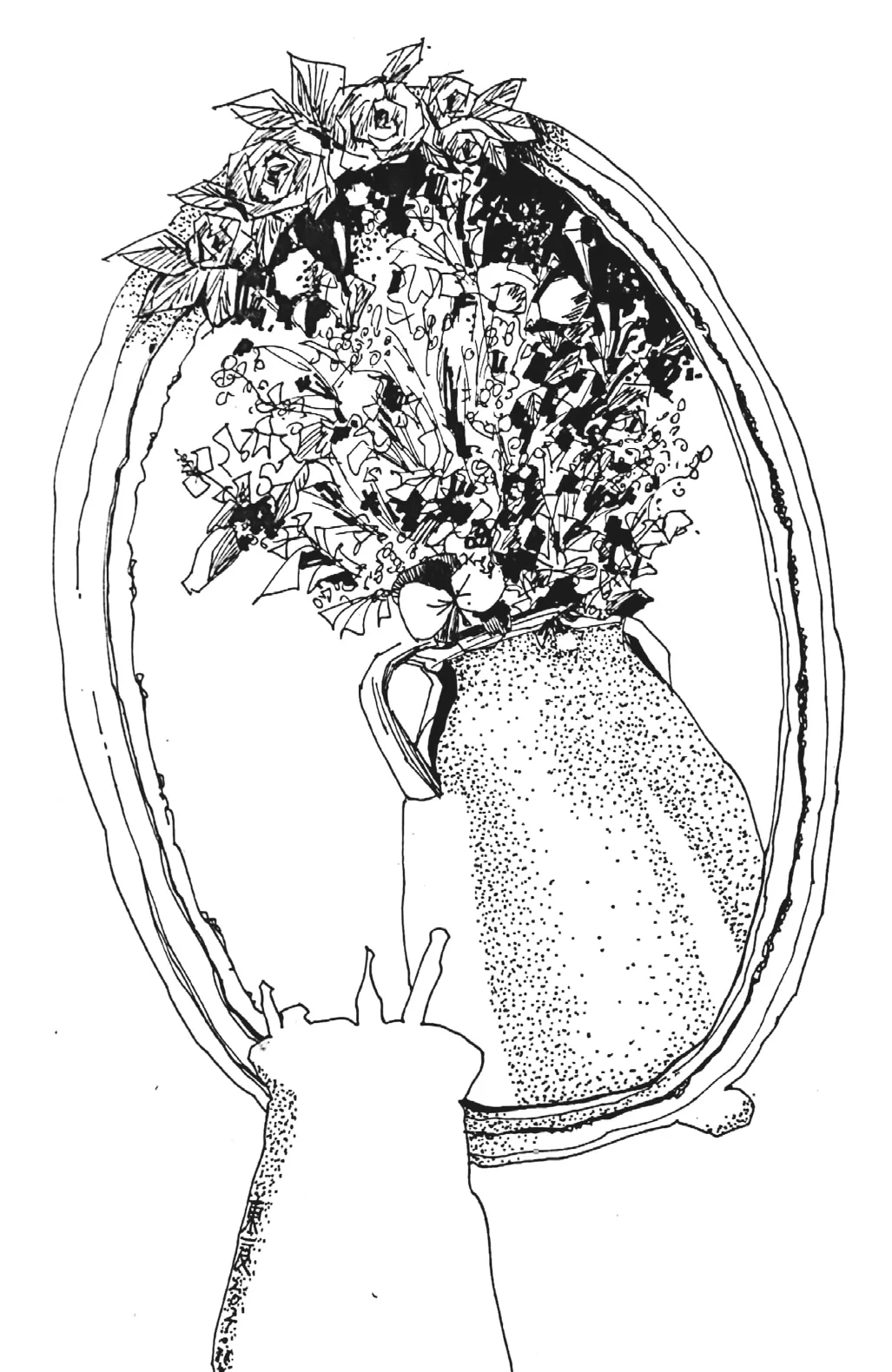
《镜中花》(东良 绘)
哎!对。
就这样。
这时,又一个声音传了过来,你不是能耐得住吗?你也知道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帽大一尺,算了,收收吧,看这跤摔在哪个脚下。
……
面对大家七嘴八舌的意见,他也不吭声,只是表情越来越严肃,脸色憋得越来越难看。
车子又绕了几圈,在一家叫大绒花的美容店前停了下来。一个小伙子刚理完发,急忙跑过来,撅着屁股往车里钻,说要往烟厂赶。石头说,对不起,我……我交班了。
那小伙子不相信地看看他。
他说,真的。
小伙子嘟囔着,只好从车里退出去。
他根本就不是交班,下班也不是这个时候。他肚子里拱满了那几个朋友的话,像虫子一样,在里面东戳西捣的。他觉得没给那个女人发票,就算是自己的错,自己也接受了,并且受罚了,但是自己又被罚了五个错,而且都是虚的,这确实太吃亏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将来还会吃大亏。
这么想着,他的车子扭扭捏捏地转身了,然后突然加速,向北开去。
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六道口地铁站,他抬头一看,朱丽还在那里。他正站在地铁口,一脸的严肃,两手抱在怀中,像鹰一般地四处巡视着,眼珠子在飞驰的出租车上滚来滚去。
他把车子缓缓停靠在报亭左边,然后紧张地叹了口气,下车向朱丽走去。
朱丽好像不认识他了。他笑了笑说,那个……我找你。
朱丽用陌生的眼神看了看他,指着自己问,你找我?
是的,我是你才罚过款的那个。他带着勉强的笑。
朱丽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漠然点了点头说,哦,还是你家车子的事吧?红色的?
不是不是。他觉得朱丽把他认错了,连连摇手,然后把身上的罚款票据掏了出来,递给了朱丽。
朱丽并不接,他斜着眼睛看了看单子,好像意会过来了,他问,怎么讲?
他拿着票据的手还举在空中,哭笑不得地说,我……我感到你罚多了。朱丽恶狠狠地看了看他,嘴里“哼”了一声,转身要走。他上前一步拦住他说,我觉得你惩罚过重,就算我不提醒顾客要发票,那么……那些理由……也不是我的,不能罚我。他故意不提其他“罪名”,不把“那些理由”说明白,算是给朱丽一个面子。朱丽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你想干什么?
他不吭声,嘴里“嗯嗯”着,表情难看死了。
朱丽用手指了一下他的胸口说,我跟你说,事情已经处理完毕,单子也开出去了,这件事情已经得到妥善处理,结案了,有什么事可以向上反映。说着,朱丽向另一个站台走去。
见朱丽走开了,他也只好快步走开,来到自己的车旁。他把车子开到一个拐角,停好车后,又走了回来。转头见朱丽到另外一个站台去了,于是他越过人群,也到了那边。
朱丽看他走过来,低头点上一支烟。朱丽的烟瘾不小,一口下去,烟雾浓浓的,把一张脸分成好几块。他走到朱丽面前,咽了口唾沫,脸色很不好看地说,我生意也不做了,这个车子如果一个小时不动,就算自动放弃下午的业务,我一点都不怕,你不把罚款的事情说清,我情愿倒贴。说着,他腰往下一弓,就在朱丽旁边坐了下来。
天神奇地晴了,原先堆积在一起的乌云如同被谁吹了一口气,不知散哪儿去了。太阳也出来了,那阳光如同在脸上或深或浅地下针一般,刺茫茫的。他故意披着阳光,由它晒去。同时,汗水在他脸上滚着,他也不擦,任凭那些汗水在脸上滚动。地上还有积水,他坐的那个地方,很快就把裤子弄湿了。
朱丽耷拉着眼,快速地吸了几口烟,然后把烟蒂扔到旁边的垃圾箱里。你起来。他对石头说。此时,他有点无奈了,口气也比先前软了。地下的温度很高,地皮发烫。石头说,谢谢,没事。说着,他抹了一下脑门上的汗。手上立刻油乎乎、湿漉漉的。朱丽叹了口气,说你要学会配合我,懂吧?将来,你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的,难免会碰到这个事那个事的,我也会帮助你的。
他不说话,半句话也没有,只顾看着街上的行人。这些行人都戴着口罩,慌忙地走着,对他们两人的事毫不关心。
这时,朱丽挪了一下腿,沉默了一会儿说,唉,干哪行有哪行的难处。他看了看朱丽,爬了起来。两人来到了一棵树下,那么大一块荫凉,立刻把他俩罩住了。他不说话,狠狠地擦了一把汗,把挂在下巴上的口罩撸下来,坐到旁边的石凳上。朱丽也坐下来,先是叹了口气,然后说,唉,哪家都有哪家的难处,我也是大难处、小难处淹了半个身子的人,孩子没有,老婆又生病,自己对工作也不是太满意,上午,我们公司的那个“笑面虎”,见了我的面,什么都不问,就拐弯抹角地说我不上班,哎呀,这个“笑面虎”……
他打断对方说,你说的这些,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有一个目的,按章办事,一把铲子掘一个坑。你看看你的罚单,说着,他把窝在一起的罚单又拿了出来,递给朱丽看,后面的那几项,哪个是我的?
朱丽站起来,显得有点急躁,口气很不好地问,那你的意思呢?
什么都不说,按章办事,该罚的,我接受,不该罚的,收回去,我多出的钱,该……该退就退……
朱丽有点火了,他向后退了两步,脸色很不好看地说,你还要得寸进尺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对你的车子施行长期监控。
我不怕。他头一歪说,我现在报案。
请!请请请!
他“哼”了一声,声音里有犹豫。朱丽来劲了,挥着手说,你要去报案,我才不会拦着你!见他还是不动,朱丽声音更大了,几乎是喊道,你去呀,去!他站了起来,也不说话,拿起手机打起了电话。在手机里,他问到出租车管理处办公室的电话,对方跟他说了。
朱丽不断地挥着手说,他说的不对,是71XXXXX。
他不理朱丽,站起来,转身走了。
去吧去吧,快!朱丽在他身后喊道。
他不理朱丽,一个劲地往前走。跨过了街道,眼看就要走到福华楼的前头,朱丽喊,哎,那个人你回来。
他不理朱丽,继续大步地向前走。
朱丽见他一个劲地向前走,犹豫了一下,便跑了起来,很快撵上他,拽住他的衣袖。
你想干什么?他问,眉毛倒竖着。
朱丽喘着粗气说,不就这么大点事吗?可有必要?
他停了下来,把脸转向一边。
好吧。朱丽见他老实了,又喘着粗气说,首先,你不提醒那个女顾客要发票是不对的,是不是?当然,在这个城市,许多司机都不提醒,这都是不对的,我看到了必须罚款,并且提醒其要注意这里的规矩,我罚你的款,对不对?
对。他说,不过,罚多了。
朱丽赶紧把手向下盖了一下,好像要把他罚的那几个莫名款项的事都盖住似的。好,这样。朱丽又说,你没有提醒女乘客向你要发票是不对的,我罚你50元,可对?
他看着朱丽,没说话。
朱丽说,好,对,是吧?其他的……好,你看着。
说着,他拿出本子,翻了几下,找到了罚款项,然后用笔把后面的五大款项划掉,又掏出310元来。好了,我们账目清了,他说着把钱递给石头,你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好了,我们这个事就这样了。他义正词严地说。
石头接过钱,吐点唾沫在手指上,开始点钱,点了几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又迎着阳光看了看那些票子,都是真的,然后把钱往身上一装,准备离开。
你等一下。就在他要走时,朱丽喊住他,并点着手指说,你把那个票给我。他想了想,便掏出那些票来。他在那几张票里找了一下,然后把那一张因为没有提醒女顾客要发票的罚款单挑出来,其他的都给了朱丽。朱丽接过去,认真看了看,问道,不是还有一张误闯红灯的票吗?石头身子一挺说,我没闯红灯。
是的是的,你没闯。朱丽说话时并不看对方。
他明白了,说,哦!加上没提醒对方索要发票,一共六张。
朱丽点点头,接着无事人一般,把票据装了起来,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见朱丽走远了,石头向自己的车走去。刚走到车前,又听朱丽在远处喊他。他转过头看着朱丽。朱丽快步走过来,并不看他,嘴上问,你没复印吧?他摇了摇头。
四
战胜了朱丽,石头感到非常惬意。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还是要争取,只有争取了,才能甘心,才能找回它本来的样子。今天,自己就是发狠了,什么都不顾了,结果就成了——赢了!
他开着车子出了彩信门,越想越开心,浑身像卸下了一副重担,同时感到车子也轻快了许多。过去开起来时“啪啦啪啦”的声音也小多了。接下来,他又用车载对讲机把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给几个开出租车的朋友说了一遍。他说得十分夸张,十分传神。几个朋友听后,“砰砰”地拍着方向盘,敲着驾驶台,一起喊赞,声称这是一次胜利,非常值得祝贺。
高兴就唱吧。他摇头晃脑地唱着京剧《清官册》,满脸是笑。这期间,有人要车,他停了下来,见顾客带着东西,他满脸带笑地下车去,帮着客人放东西。他麻利的动作让客人很开心。
到了晚上,他把车子收回车库,哼着小调往家走。走着走着,不知为什么,哼着的小调弱了下来,最后,一点声响都没有了。他的心情忽然黯淡下来,朱丽那张毫不在乎的脸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这让他很不舒服。他不断地揉着自己的鼻子。他感到自己的胜利实属侥幸,如果不是亲自找上门,摊上个胆小怕事的,可能就栽了。再说,朱丽走时并没有跟自己道歉,还和没事人一样,这什么意思?
他越想越感到不对,越想脸上的表情越阴沉,最后,他认为这次的胜利者不是自己,而是朱丽。他叹了口气。此时,天已经快黑了,麻雀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鸟们“扑啦啦”地往树上飞。他想了想,决定明天去出租车管理处。
第二天,他早早地就出了车。跑了十几趟后,已经是上午十点多,此时高峰期已过,路上客人特别难带,有时,几部出租车挤在一起,面前的提示牌都亮着“空”。他决定不带人了,于是让车子拐了一个弯,向出租车管理处开去。
进了出租车管理处大院,他把车子停靠在院墙外的那几根装饰柱下,然后往里面走。走到一组“先进工作者”的公布栏旁,他站了一会儿。在第三排,他认出了出租车管理处的处长——姓左,叫左右。
左右处长是个40多岁的人,头发却白了,见到他,石头笑着问好,左右处长也谦和地问,您好,您找谁?左处长的语气让他舒服,他一下子就不害怕了。您是左处长吧?他问。
是的是的。左处长笑着说。
我来反映一个问题。他说。
左处长马上严肃起来,连连说,哦哦。接着,他倒来一杯水,一边让石头坐下,一边把那杯水小心地放在石头面前。等这些做完了,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笔,又从旁边拿出一个本子,然后说,您请讲。
石头端起水杯,想喝又没喝。他把水杯放下,问,你们这儿可有一个叫朱丽的人。左处长没有回答,只是“嗯嗯”了两声。这就等于承认了。他接着说,我想反映他的问题。说到这,他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票据来,是复印件,先前是朋友提醒他去复印的,他原以为没有用,现在带来了,才感到挡大事了。
他没有把复印件给左处长,而是把自己的遭遇先说了一遍。左处长一直在记,脸上表情十分严肃。左处长记东西时歪着头,手里的本子也歪歪的,笔往怀里带。等记完了,他笑着问,还有吗?
他笑着说,还有就是下一次了。
什么意思?左处长问,也笑着。
他说,这一次不把这位同志教育好,下次,他就会依然如此,也可能还会有什么更大的问题。
左处长点了两下头,又点了一下头。这时候,他把那些票据拿出来,先看了看,然后给了左处长。左处长认真地看了一遍他递过来的票据,放在一边,想了想,笑着说,您先回去,我们一定会找他谈话的,对了,您可有什么想法?
他笑了笑说,我们就是老百姓,能有什么想法,你们能保证批评他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也承认错误,客人不要发票我就忘记给了……
左处长笑着向他摇了摇手。他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忙打住了话头。他要走了,左处长站起来,笑着和他握手,感谢他对处里的工作提出批评,说这是最大的支持,又送他到大门口,客气得跟兄弟一般,让人很舒服。另外,他的感觉也非常好,左处长的手软软的,像刚出炉的面包。接着,他和左处长打了声招呼,就向外走。
刚走到大门口,左处长又喊住他,请您来一下,左处长笑着说。
他以为自己丢了什么东西,伸手在自己身上摸了摸,便走了回去。
请您在这上面签个字。左处长说。
这个他很乐意。而且,这样的话,他觉得问题反而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他在签字时,左处长又笑着问,您看,要不要我们到您门上道歉。
他连忙摆手,一再说自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这个朱丽能自我反省一下就可以了。最后,他说,不要,不要,那不需要。
左处长呵呵地笑着,接受了他的意见。
左处长的态度再次让他感受到了尊重,整个身体都软软的,暖暖的。
事情协商到这种地步,左处长把两个拳头抱起来,上下摇了摇,满脸带笑地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件事上,怎么说呢,我们感谢您,也等到了您。左处长最后笑着说。
他不是太理解左处长的话,但是,自己来反映情况,看来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五
从左处长办公室出来,他感觉自己总算出了口气,而且很爽。他很高兴,并决定把这份喜悦之情也传达给别人。这时,一个男孩上车。男孩是大学生,十八九岁的样子,背着乐器,戴着眼镜,一脸的汗,上车后就问到财政局需要多少钱,说自己只有35元,怕不够。大学生说完,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他一挥手,笑了笑,大声地撇着南不南北不北的口音说,不要了,你坐好吧。大学生扶了扶自己的眼镜,愣愣地看着他。他感觉到了,笑着说,是的,我高兴,不要钱了。大学生想了想,说,哦,我……我忘了拿一件东西,说着,慌忙地下了车,然后转身向不远处的一辆车快步走去。他看着大学生慌忙离开的样子,又看着他慌忙地钻进了另外一辆车,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觉得这个大学生真是奇怪。
但这并没影响他的情绪,他把车子向南门街开去。开车时,他唱着歌,打着节拍。唱了一会儿,他想了想,又把车载对讲机打开,和朋友聊了起来。他把刚才的事跟车友们说了。他说,我感觉这个管理处没有问题,好得让人感觉像喝蜜一样。
你占了理。这个事,本身就是那个家伙的问题。
你能耐!哈哈哈……
车友们三言两语地恭维他,他很高兴,车子开得“呜呜”的,同时,又觉得自己终于把心里的气发完了,为此,他笑了,哼着小调向前飞奔。
开了很长一段路,也没碰上一个客人,他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表情也渐渐地严肃起来。
在这件事上,朱丽是有错的,尤其是乱加的那些名头,乱罚款,高达几百元,但是,人家先前毕竟认过错了,就算态度有点模糊不明,但人总归要给自己留点面子嘛!何况最后又没多收自己一分钱,自己又何必那样不依不饶呢?到时候,为了对证,办公室再把自己喊去,要自己把遭遇讲讲,把那些收取费用的收据拿出来……他忽然感到了无聊。
他思来想去,一直到中午。这时,他把车子停下来,找地方买点吃的。
等吃完盒饭,他的心情好多了,那些事也忘了。他上了车,开始冲街上的行人大喊大叫,上车上车,我的车消毒了!其实,他喊的是废话,早晨开出来的每部车都必须消毒。不过,他喊得有效果,很快就有人拦住他的车,还伸头问,真消毒了?嗯嗯。他连声说。他觉得这些人好奇怪,自己不说消毒,也不会有人问。
把最后一个客人送到地方,他舒了口气,正准备驶走,驾驶台上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眼号码,手又缩了回来。手机的尾号是2471。他记得清楚,这是朱丽的手机号,他在票据上见过。他为什么打我电话?他在心里想,肯定是自己告状的事。他脸红了,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任手机在那不停地响着。
但是,总不能老让它响啊!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手机不响了,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好像看到朱丽转身走了。可是,车子没开多远,手机又响了。他看了看,是另一个号码,便去抓,转而又想到,这会不会又是朱丽呢?他用另外的手机联系自己?如果不接,假若是客户的手机,不就失去一次机会吗?思来想去,他还是拿起了电话。喂……他试探地说。
是我,朱丽。对方的声音干脆、自信、低沉。
哦!他叹了口气,身子歪了歪,越是怕鬼,鬼越是来了。他勉强地笑着问,什么事?他脸上红了。因为黑,整张脸显得更黑。朱丽说,阮师傅,我正在溪口值班,我们有话跟你谈,你下班就过来,说完把手机挂了。
听到是“我们”有话跟你谈,他的手颤抖起来。他把车子停在路边,想了一会,最后觉得不去不好,就开着车子向前走了。车子向前晃晃悠悠地开了几十米,他又自信起来:自己没错,该罚的钱也罚了,错的是朱丽。想到这儿,他脚上一用力,车子向溪口开去。
六
溪口是本市最繁华的地方,每天均有大量的客人往来这里。它也是贩卖鱼虾的市口,离很远就能闻到一股股浓厚的鱼虾味。
由于来往的人较多,石头把车速减到最慢,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子开到烟盏牌坊后,他把车子停了下来。他向左右看了看,并没有看见朱丽。尽管车内开着空调,他还是流汗了,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这会儿,他看到了,朱丽正在前面的报亭和一个男人说着话。那男人说话时,脸上带着一大把的笑,朱丽也淡淡地笑着。他舒了口气,然后下了车,向前走去。朱丽身边的那个男人和朱丽挥了下手,走开了。朱丽抬起头,转眼看见他,便冷着脸,向他举了举手。他笑了笑,多少带有点讨好的意思走向朱丽。朱丽板着脸说,我们到里面谈吧。
他估计里面还有几个人,心里一沉,脚步又迟缓了一下,跟着朱丽往前走。朱丽走在前面,还点了根烟,大口大口的烟雾在朱丽身边缭绕。很快,他们来到金砂大酒店的门口。他很奇怪,怎么还有在大酒店办公的?又一想,也许这里有饭局,朱丽正巧碰到这件事,顺便喊他过来谈谈。
他们走进一间屋子,装潢得很漂亮,一位女服务员站在那里,见到朱丽便问,先生,其他的菜可以烧了吧?朱丽“嗯”了一声,服务员退了出去。
坐。朱丽说。
他没有坐,红着脸,慌里慌张地说,这个事情是这样,你先听我说……
朱丽挥着手说,不急。
是这样。他坚持说,我只是觉得那几张票据与我没有关系,所以我昨天去你们单位了,找到你们的领导,首先承认了我犯的错误,也说明了那几张票据开得……开得不对……
朱丽想了想,摇了摇手,说,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今天,我在这里请客,只请你一个,向你道歉。
他心里一惊,然后明白了,忙从屋子里走出来,一边摇着手一边说,这个不行,真不行。
朱丽勉强地笑着说,我是诚心的,你看到了。
他是第一次看到朱丽对自己笑,于是也笑着说,我什么都没看到,真的。
你看……朱丽喊道,姑娘。
刚才那位女服务员来了,说,先生,快了,都下锅了。
等一下。朱丽对服务员说,转而又对他说,你看,菜都烧了,我总不能一个人吃。
他不断地摇着手,苦着脸说,你有什么事谈什么事,这个……我真没时间。
菜我已经点了。朱丽忽然严肃地说,为你点的。
是的。他也严肃地说,不过,我没答应啊。
朱丽苦着脸说,那是为你点的啊!
他说,有事谈事好不好?
朱丽的脸阴沉着,转向服务员,半天才问,我的菜怎么样了?
服务员笑着说,先生,刚才跟你说过了,现在应该好了,上菜吗?
朱丽搓着手,看着石头,又说,你看……都好了。石头向外又退了一步说,你找我什么事?看朱丽在犹豫,他又说,我绝对不在这吃饭,我吃过了。朱丽叹了口气,说,好吧,我们到里面谈吧。石头向旁边看了看,说,就在这谈吧,然后带头钻进一间空着的客厅。
朱丽答应了,然后走进客厅坐下。朱丽坐下时,他没坐,只是站在那儿。朱丽看了他一眼说,我认倒霉,你坐下行不行。
他想了想,在旁边坐了下来,离朱丽远远的。朱丽抽出一支烟,向他晃了晃。他确实想抽烟,他是有烟瘾的。不用不用。他说。朱丽把烟放进自己嘴里,叹了口气说,这次,你把我害苦了,比黄连还苦。说着,他打着了火机,把烟点上。
听朱丽这么说,他有点过意不去,很不自然地看了朱丽一眼。朱丽瘦了不少,眼圈四周青青的,上了一道箍似的。他心里一软。
朱丽把刚叹出来的气向回压了压说,上午,领导找我过去,把你反映的事跟我说了……朱丽说到这儿,突然不说了。石头感到面颊发热。
唉!现在,领导在追究我的责任,主要是针对你的事情,其他……其他罚款,真对不起你,我不该给你开那些票据,其实都是……唉……
听朱丽这么说,他心里彻底软了,平平地堆在那里。平时,他就是这样的人,谁跟他硬来,他照死不服,就怕人跟他软。于是他声音低低地说,没什么……
朱丽说,是的,我毕竟没有向你多收钱……
他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朱丽又说,我找你,是想让你为我说明一件事,不知道……
他看了朱丽一眼,心想,让我说明什么事呢?让我说那些票据不是他开的?呵呵……
朱丽说,不错,那些票据是我开的,但是,我没收你的钱,都退了回去,是不是?我想……我想请你说明一下,就这个事,说明一下,你这样说,我或许还能保住工作……说到这儿,他好像说不下去了,一副要哭的样子,脸色也暗暗的,烟都快烧到手了。朱丽的样子让他有点难堪。他忽然又想,因为这种事,挨批评是肯定的,甚至罚款也可以,但是,说把工作丢了,可能是瞎扯的。
真的,他们一直想把我搞走,一直在找机会。说到这儿,朱丽又不说话了,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
他真的头大了。他挠了挠自己的脖子。脖子上先是有几道灰白色的痕迹,随即,那些痕迹就变红了,殷红的。
朱丽把手里的烟蒂放在烟灰缸里,说,唉!我也不容易,老婆在住院,真的,住一年多了,身边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整天心情不好,苦得钻心。唉!他摇着头。朱丽的话把他压得低低的。他心想,怎么办呢?去说明那票据是朱丽开着玩的,领导会相信吗?自己已经出示证据,怎么可能再重新编造呢?再说,这种公然推翻证据的做法,明明有撒谎之嫌啊!可能还是犯罪……
你看呢?这时,朱丽苦苦地问,声音很小。
他叹了口气说,唉!这件事……这件事……
朱丽不再看他,又抽出一支烟来,点上,默默地抽,很烦恼的样子。
我回去想想吧。他说,头上出汗了。
朱丽头低着,嘴里小声地骂着什么。从表情上看,估计是骂那个左处长的。石头站起来,顿了顿,声音不高地说,好的,你在这,我先走了,说完,没等朱丽说话,就抬脚离开了酒店。
天上,乌云一层压着一层,厚厚的。
七
石头把车子晃晃悠悠地开到家,天已经黑了。妹妹已经把饭烧好,石头简单吃了几口,就去洗澡,上床,抽烟,想这个事。那个叫朱丽的人,在他脑海里是那么可怜。朱丽那种伤心无奈的神情让他看着难受。但是,现在让他出面,重新换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去“拯救”他,他又觉得太难了。如果不去说,朱丽的工作可能就难保,可自己又在现场表过态,说回去“想想”。唉!他叹了口气。
抽完第四根烟,嘴都麻了,他什么办法都没想出来。妹妹在那边看手机视频,一边看一边叹息,让他更烦。最近,妹妹总是叹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他真想过去,让她别叹息,别弄这么大声响,但最终还是没过去,只是歪着身子睡了。
转眼三天就过去了。这三天,他没有想到任何办法。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说那些话。好在,这三天,朱丽也没有打他电话。又一天过去了,他的心情好了些,因为这两天朱丽仍然没来电话,这说明事情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回家后,妹妹还没有回来。他到处摸了摸,翻了翻,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冰箱里还有半块大饼,时间太长了,都有了霉点。他想了想,便打电话给车友顾秃子,叫他出来喝酒。顾秃子刚把车子停下来,听说他请客,说,把孩子弄好了就过来。
半个小时后,顾秃子趿拉着拖鞋来了。他穿着中裤,肚皮秃噜在外,一走一晃的。他们在今朝饭店要了桌位,点了一盘酱牛肉,一碗凉拌苦菜,一碟花生米,一条鱼,要了一瓶酒,两人各捏着一个酒盅喝了起来。
喝到二八盅,他又说起自己战胜朱丽的事,他兴致勃勃地说了半天,这秃子的脸都板着,怎么都打不开的样子,只顾一个劲地吃菜。他有点无趣,就不说了,同时又觉得有点问题,就情不自禁地看了看秃子。顾秃子喝了一口酒,低着头说,那个人叫朱丽,被辞了。
辞了?他惊讶地叫,拿着筷子的手停在那里。
顾秃子又喝了一口酒说,我家老表在那个局里,跟这个朱丽坐对面,又说,你去找他家领导,真算是找对了人。
石头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张着。他在琢磨顾秃子的这句话。他的精气神一下子就弱下来,酒杯落在桌面上时,发出的声响也弱弱的。接着,秃子把这个人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最后说,说实在的,他被辞退确实是有点重了,但是……他平时也太不注意。秃子说完,摇着脑袋。
他知道秃子的这几句话是说给他听的,是一种安慰,但是,他听后很不是滋味。他“唉”了一声,又把一大杯酒灌了下去。秃子见他仍无法释怀的样子,又把自己听到的事说了出来。
八
那天,石头刚离开出租车管理处,左处长就把所里的几个领导喊进了自己办公室。左处长每人散了根烟,然后把桌上的那沓材料往前一推,说,看看吧,出事了。
几个人一愣,七手八脚把那些材料翻了一遍。一个人看着那些罚单说,这……没有什么啊,不就是罚款吗?
另一个说,不对,一个人同时期内哪能罚这么多。
对啦!左处长拖着嗓音说,是同时。
几个人见处长这么认真,都严肃下来,把那些材料又反复看着,有的人还嘀咕出了朱丽的名字。上午,受害人找上门了。左处长说,意见很大,这叫什么?叫拿着集体的权力谋取私利,不是吗?叫他管理市场,他倒好,把我们处里的荣誉和尊严都拿去典当个人利益,平时工作三心二意,不给说,不给讲,这种人非要被人抖搂出来才行。说完,左处长在原地转着。
其他几个人心里就有数了。左处长走到桌前,拿起了电话。他的电话是打给交通局客运管理部门的,想请他们帮助调取现场录像。不一会录像调出来了,很清楚。录像详细记录了石头的系列行为:怎么下车的,怎么和朱丽接触的,怎么走的。尤其是朱丽,好像录像就是为他设立的,跟着他转,一举手、一投足都有,直到他离开。把录像翻录下来后,左处长说,可以叫他过来了。
朱丽来了,进门后,看一屋子人,忙问,什么事?左处长让他坐,朱丽没坐,警觉地盯着处长。他从处长的表情里看出了一些什么。左处长说,那好,我们开门见山吧,昨儿你执行任务时……犯了什么错?
错?我能犯什么错?朱丽睁大眼睛。左处长不看他,也不吭声,脸板着。朱丽好像想起来了,他说,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违反行车纪律的出租车。他想了想,又抬起头说,他没有提醒客户要发票,我罚了他。说到这儿,朱丽看了看处长。由于紧张,他嘴唇干干的。左处长仍然没吭声。朱丽继续说,我是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
你说得好。左处长说,你罚他,是因为他没有提醒客户要发票,或者没有把发票给客户,都对,但是,你看看这个。说着,他把那六个违反出车纪律的复印件拿了出来。朱丽愣了,头上有了汗。他翻着那些票据说,是的……这个是的……可是,我并没有罚他,只是跟他开个玩笑。
玩笑!左处长说,需要看看录像吗?
朱丽眼睛睁得很大,愣愣地看着处长。左处长打开录像机。按键按下去后,录像机像是被吓了一跳,立刻在旁边的电视机上投出了朱丽和石头的影像:朱丽和石头在对话,至于说了什么,一点也听不到。
朱丽哈哈一笑,这能说明什么?他问,脸却是红的。
这能说明人家是对的。
他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不向顾客提供发票也对?
但是,你拿出了那么多假票就是你的不对。左处长说着,把那些复印件放到朱丽面前。朱丽愣了下,但他马上说,我说过了……虽然这个……但是,这几张票据没有收钱,再说,我也撕了。左处长抓起桌子上的一沓文件,往桌子上一摔说,还狡辩,你是怕人家告你才撤回的。
朱丽不吭声了,只是歪着头,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左处长声音更大地说,事情非常严重,你作为我们站内的管理人员,做出这样的事,就等于渎职,是在为大家抹黑你知道不?
朱丽瞟了左处长一眼,冷冷地说,这下找到理由了。
左处长端起茶杯,低着头,连喝了几口茶水说,等候处理吧。
朱丽“哼”了一声,我反正没收钱,那些票据都撕掉了,你们看得到!
九
尿毒症患者厌食、肚子不适,另有恶心、呕吐、腹泻、舌炎、口腔溃疡等症状,另外,体内循环的动脉血压降低,心律异常,酸中毒时呼吸深长……朱丽的老婆患的就是这种病,而且以上症状都有,脸上长满了老年斑。两年了,人越来越虚,越来越瘦,朱丽每天都要陪她去换血,结束后再去上班。有时,老婆哭哭啼啼的,他又不忍心离开,就在那儿陪她。由于请假的次数过多,加上自己的心情和性格都变得不好,和大家以及上司的关系越来越差。
这一次,朱丽犯的错误太大了,自己还不愿意承认。另一方面,石头找他们领导,是有“报仇”的意思,但是,那不过是想让领导对朱丽狠狠地批评教育一番,没想到自己这一枪,把人家的工作打得稀巴烂,这让石头很不安。
第二天,石头把车子开到新华路时,又感到这事处理得有点玄,怎么会因为这个原因让朱丽走人?于是,他把车子停到车辆管理处门口,向院子里走去。院子很大,他绕了几个弯,终于找到朱丽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龄大的男人在贴宣传画,见有人进来,便看了看他,扶了扶眼镜,没吭声,继续干着手中的活。石头向里面望了望,空间很大,有七八张桌子,上面很乱。其中,有三张桌子上有电脑。
石头说要找朱丽,贴画的人冷冷地问,找他有什么事?又调换了一下手上的画说,他不在。
他问,他是不是不在这上班了?贴画的人又看了看他,继续贴他的画,没回答。他感到无趣,同时也不想再问了。他希望听到“他出去了”,这样,也还有个盼头。他正准备离开,贴画的人说话了,不在这儿上班了。
他愣了下,心里顿时空空的:这证明了顾秃子的话。他说了声谢谢,对方也不回他,他独自走了出来。
车子发动后,他没有马上走,而是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才拐上马路。他去了医院,希望能在那里看到朱丽。
很快到了医院,他转了几圈,未见朱丽,只好往回开。路过大市场门口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了,他考虑中午在哪里吃个盒饭时,就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穿得很干净,梳了头发,还喷了水,头发上湿漉漉的。他手里提着一兜盒饭,正向自己快步走来。等再走近些,他一眼便认出,正是朱丽。
朱丽低头上车,说,去第三人民医院。朱丽瘦了,手颈看上去很细,乱哄哄地长着很多毛。他说,好。这时,他回头看了一下,正好和朱丽的目光相遇。朱丽一下子认出他,把脸转到一边。转脸时可以看到,朱丽的嘴唇开了许多小裂口。他心里有数,这是火气大的缘故。
他非常想和朱丽说几句话,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很快就到了医院,朱丽把手里的东西放下,给他付钱。
就十元吧。石头说。
朱丽看了眼计价器,忙说,哦我有我有。说着,他用手机扫码,把二十一元钱汇了出来。
十
石头浑身不舒服,把车开出来后,不是看不见客人,就是客人向他招手,他车子又开过去了,好不容易拉到一个,还把人送错了地方。客人跟他吵,说怨气话,说他故意绕路。他也不辩解,只是说,你走吧,算我的。客人也很认真,说这没有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我给。
石头叹了口气,把车停在那儿,只感觉不对,好像是什么附了身,让他稀里糊涂的。他把车子向第三人民医院开去。
医院门口,巨大的公益广告牌十分显眼,所有人进医院,都必须用手机扫码。他缓缓地开着车往前走。当他的车子即将从医院东边开向医院西边时,一部奥迪车从他旁边飞驰而过,然后在他身后发出刺耳的刹车声。他从倒车镜中看到,奥迪车停下了,一个留着小辫子,穿着花衬衫,戴着大项链,肚子完全拱了出来的小伙子满脸通红地从车里钻了出来。接着,他看到小伙子左手揪着一个人的胸襟,右手指着这个人的鼻子叫嚷着什么。
他的车子还在移动,于是,这个场景越来越小。他忽然觉得不对,小伙子揪着的那个人他怎么这么熟悉。对,是朱丽,绝对是他。他沿着布泥东路绕了一个大弯,又飞快地转了回去,回到刚才事发的地点。那里围满了人,奥迪车还停在那里,后面的车辆堵成了一条长队,有着急的,嘀嘀地鸣笛。他把车子停在岗亭旁边,向围观的人群快步走过去。
小伙子正被一个人抱着腿,站在那儿大喊大叫着。抱着他腿的人满脸是血,身边撒满了饭菜,正是朱丽。他冲上去,猛地推了一把小伙子,瞪眼问,你怎么打人?小伙子不乐意了,也瞪着眼说,他明明看到我的车了,也不让,他有没有问题?说着,就要走。石头一把抓住小伙子的衣服说,不行,你撞了人就不能走。那小伙子猛地甩掉他的手,再拔腿甩掉搂着他腿的朱丽,大步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石头跑到奥迪面前,拦住车门说,你走不掉。
小伙子挥拳打在他鼻子上。一阵火辣味蹿上来,鼻子立刻出血了,刺刺的痛。他一边擦着鼻血,一边拔掉小伙子的车钥匙。那小伙子立刻和他搅打在一起。几个回合,他就败了,任小伙子对自己拳打脚踢,身上发出“砰砰”的声音。就在这时,一位民警骑着摩托过来了,小伙子才停下来。民警问了问现场情况,又见不远处还有一个人半躺在地上,便后退一步,举着自己的证件对小伙子说,你严重违章,而且有打人行为,跟我走吧。小伙子还想解释什么,民警瞪着眼,大声地命令,跟我走!
事情很快得到处理。那小伙子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姓路,因为中午去接女老板赴宴,本来就迟到了,着急赶路,在医院门口加速时,才出现了以上情况。但是,车祸发生,又殴打行人,小路要被拘留。朱丽小腿被撞,骨头开了一个很小的裂缝,要住院治疗。石头因为劝阻,眼睛被打,肿得跟小山包似的。两人的医药费自然都由小路负责。石头亲眼看见小路在交警队掉眼泪了,也知道了他撞人的原因,忽然同情起小路来,于是对交警说,自己的眼睛没问题,至于小路,放了算了,这个事情就这么结了。交警瞪着眼问,你能代替他呀?交警的眼睛本来就大,瞪他时,眼珠子都快要出来了。
石头不敢说话了。
他去了14号病房,朱丽住在那里。看到他进来,朱丽连声感谢他,身子动了动,说话时脸上有了笑容。提到自己老婆,朱丽觉得自己躺在这儿可不行,他的父亲七年前就去世了,母亲腿不行,去了新疆,跟女儿生活。老婆是婺源人,是打工时和朱丽认识的,原来在纺织厂上班,两人一直没要孩子……
十一
石头丢下自己的生意,经常来回地跑,遇到了许多麻烦事,可是他没觉得累。朱丽被单位除名后,他一直希望能有个什么机会深入接触一下朱丽,给自己一个补偿的机会。
他对朱丽说,你安心养病,我来接送你老婆,咱有车,方便。朱丽有点不忍心,但也确实没办法。他说谢谢你,兄弟。这个“兄弟”是朱丽第一次说出来,很真诚。
就这样,他一边接送朱丽的妻子,一边照看朱丽,几头跑,渐渐地就受不住了。晚上他开车刚到家,妹妹雅雅也回来了,脸上汗津津的,脑门上沾满了头发,胳膊上搭着脱下来的衣服,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他这些天很少问妹妹的工作情况,就问,你怎么回事?
妹妹也不说话,往床上一躺,缩成了一团。
他觉得女孩的事多,也不好瞎问,就准备做饭。这时,妹妹说话了,哥,我不想干了。她说着坐了起来。他急了,问怎么回事?哪个惹你了?妹妹也不说话。到底怎么回事?他走过去问。妹妹叹了口气说,你不说工作多好吗?其实很烦人!
他笑着劝说,哪有那么好干的工作,你才干就这么计较,你是累的,歇歇就好了。妹妹又叹了口气。他问,工资怎么样啊?
三千多。妹妹说,去掉保险什么的,才两千多一点。
他感到纳闷,开始不是说工资挺高的吗?他还没问出口,妹妹就说,开始以为工资还会涨的,哪知不仅不涨,而且还扣得更多了,迟到了扣点,讲话了扣点,这个扣点,那个扣点,到了月底才……
他笑了,说,你自己爱说话,又喜欢迟到,在家懒散惯了,以后克服了就行了。说着,他走开了。电热炉上的水咕嘟嘟地开了,他得去灌水。
他忽然想到朱丽的妻子,想到一个可以替自己照顾她的人。
第二天早晨,石头先到朱丽那里,和朱丽聊了聊。这时,正赶上医生会诊,他向一个秃顶的老医师问了问情况。还好,朱丽是轻度撞伤,没触及要害,大约再恢复一段时间就能好了。他帮朱丽拿了药,又买了早餐,然后再开车去接朱丽的爱人。
朱丽的爱人虽然不到30岁,看上去却有四五十岁的样子,骨瘦如柴,锁骨高悬在外。她早就知道朱丽的事情,对石头有气无力地说,谢谢你……我们……我们全家都多亏了……她脸色灰暗,一点力气也没有,话没说完,就只顾在那喘着,眼里流着泪。石头最怕看别人流泪,便连连摆手,表示没关系。
把朱丽的爱人安排好后,石头又去医院照顾朱丽。
晚上回到家,他坐在板凳上等妹妹。不一会儿,妹妹回来了,背着沉重的包,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先站了起来,待妹妹走进屋子,便说,我给你找了份新的工作。妹妹脸上一阵欣喜,啊,在哪儿?
他做了一个让妹妹坐下的动作。妹妹两眼闪着光,慢慢坐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也坐下了,清了清嗓子说,医院的。
妹妹高兴地拍着手。他说,不过,你要先学会护理,我可以给你找个人练练手。妹妹高兴地说,行,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不再去那个破单位。
他低头想了想,装出一脸焦虑地说,还不能高兴过早,因为……想干这个事的人不少。妹妹的脸色立刻变了,紧张地看着哥哥,双手抱在一起。
他点了点头,说,工作是这样……妹妹立刻打断他,说只要能去医院,干什么都行。他又点了点头。
妹妹就辞去了厂里的工作。他先把妹妹安排在了朱丽老婆的身旁,工资由自己偷偷垫付。一个月后,朱丽感到不对,坚决不答应石头为自己出工资,贴了南墙还要你贴北墙吗?我付。
他见朱丽一脸的真诚,想了想,就不争了。
转眼到了秋天,满城都飘着发黄的树叶,尤其是那种银杏树,不敢招惹似的,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落叶,看上去让人忽然欣喜,又忽然伤心。此时,朱丽的老婆已经病逝,他跟朱丽也不再见面了。
石头还真在医院里给妹妹找了份工作——清洁工,专门收拾、清洗床单,工作时间不长,正常上下班。他问过妹妹,怎么样?妹妹低着头,撸着自己红肿的指头说,嗯,比在家里刨地强。
他没说话,怪心疼的。
又干了一段时间,妹妹说,哥哥,我离医院蛮远的,想在医院附近租一间房子。他想了想,妹妹也大了,特别是夏天,跟自己住在一起总不是个事儿,就答应了。妹妹说,那我明天就搬了。他说,这么快。
大概是一年后,秋天,晚上,石头把出租车收好,沿着湖边散步。天上,月亮好大,真亮,四周都白沙沙的,像点了多少盏灯的样子。湖边有很多人,有独自散步的,有谈恋爱的,还有吵架的,闹兮兮的。这时,他看见了一个人,齐耳短发,说话时喜欢把手放在脸的一侧,很像自己的妹妹。她正和一个男人边走边聊,过了一会儿,又见那个女孩抱住男人的胳膊,头歪着,靠在上面。石头感觉女孩旁边那个男人的身影,也非常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