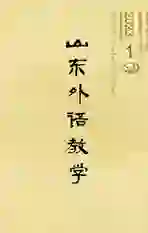论科尔森?怀特黑德小说《地下铁道》中的棉花叙事
2023-10-24张琳
[摘要] 在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历史推想小说《地下铁道》中,棉花叙事贯穿其中,成为尤为凸显的文学现象。小说中的棉花叙事资源涉及内战前美国南方棉花王国的形成、黑人棉奴的命运,以及种族极权主义等问题,全面再现了由棉花经济和奴隶制双重主导的南方地域图景。怀特黑德将棉花叙事嵌入逃奴叙事,一方面使奴隶个人叙事和由棉花驱动的国家话语勾连,为奴隶叙事添加了豐富的经济学和历史学注释;另一方面以棉花引发的社会问题为纽带,使黑人逃奴成为若干种族主义历史事件的观察者和叙述者,由此实现对白人种族主义历史编撰的“反凝视”和“反书写”。
[关键词] 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棉花叙事;奴隶制
[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文献编号] 1002-2643(2023)01-0095-08
The Cotton Narrative in Colson Whiteheads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JZ)]
ZHANG 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In Colson Whiteheads speculative historical fiction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the cotton narrative runs throughout the text and is especially noteworthy. It covers the formation of the Kingdom of Cotton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the fate of black cotton slaves, and the issue of ethnic totalitarianism. In this way, the landscape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simultaneously dominated by cotton and slavery, is fully presented. By embedding the cotton narrative into the fate of the fugitive-slave, Whitehead relat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gitive to the national discourse driven by cotton, which mediates the individualized slave narrative with abundant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notes. Meanwhile, Whitehead locates the fugitive slave in the cotton-related racist events, who serves as the observer and narrator of the events, exercises the oppositional gaze and rewrites history against white racialists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cotton narrative; slavery
1.引言
尽管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 1969-)的历史推想小说《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充斥着历史事件的年代错置(anachronism)(翟乃海,2019:72-73),但这部奴隶逃亡小说的时间主线设置在19世纪上半叶,与美国南方“棉花王国”的兴起(1790-1840)同步。伴随黑奴女孩科拉从佐治亚出发、经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印第安纳,最终到达北方的逃亡旅程,棉花叙事贯穿其中,成为该小说尤为凸显的文学现象。
根据AntConc软件对《地下铁道》中高频词的分析结果①,作为主题词之一的“cotton(棉花)”出现57次;加上其他相关词汇,如“field(棉田)”、“boll(棉铃)”等,棉花词汇共计出现90余次。需要指出,小说中的棉花并非简单用以充当故事背景,而是被赋予了更深层的主题意义和叙事功能。怀特黑德将棉花嵌入奴隶叙事,试图向读者传递何种信息?目前学界尚未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本文通过对文本中的棉花共现语境进行提取和梳理后发现:小说中的棉花叙事资源涉及内战前美国南方棉花王国的形成、南方黑人棉奴的命运和记忆,以及南方种族极权主义问题,全面再现了棉花利润驱动下内战前美国南方的地域图景。
2.“棉花为王”:棉花王国的形成
尽管美国的植棉史与英国在北美的拓殖史一样久远,但棉花成为“白色黄金”则发生在18、19世纪之交。除南方适宜棉花栽培的气候条件外,肇始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对棉花的巨大需求,促成了美国南方棉花经济的转向。“……欧洲求棉若渴,急需大量棉花供应”;“为了满足全世界对棉花的贪婪需求”(怀特黑德,2017:13,48)②。这两处形象地指出了棉花是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命脉。欧洲市场的棉花供应缺口使美国南方农场主看到了商机,他们中许多人转向植棉业。植棉业的兴起遏制了当时国内反奴隶制思潮的强劲势头③,给当时日渐式微的奴隶制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之重焕生机,并将其推向巅峰。只有奴隶制才能保障棉花产量,对此,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马克思、恩格斯,1976:21)。
奴隶劳动力的持续供应是不断扩大棉花生产的前提。特别是1793年惠特尼轧棉机(Whitney cotton gin)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后,种植园主们更是野心勃勃,想方设法获取更多奴隶。1808年之前,种植园主要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购买奴隶,正如小说所述,“棉花无情的发动机需要非洲的躯体做燃料。轮船在海洋上奔波往复,带来血肉之躯,耕种土地,繁殖更多的躯体。这发动机的活塞不留情面地做着运动。更多的奴隶带来更多的棉花,更多的金钱,用以购买更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棉田”(145)。1808年国际奴隶贸易被取缔后,种植园主要依靠国内奴隶贸易获取劳力。据史料记载,在轧花机发明后的30年中,国内奴隶贸易将约100万奴隶输送到美国深南部,大部分都去种棉花(Beckert, 2014: 109)。
除劳动力的补给外,土地是制约植棉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对以扩张主义为立国之本的美国来说,开疆拓土和土地征用是其昭昭天命;对此,小说中的猎奴者里奇韦深有感悟:“这才是真正的大神明,是连接一切人类宏图的天赐之线——你有本事把它留住,它就是你的。你的财产,你的奴隶,你的大陆。这就是美国的天命”(76)。无论是个人或国家层面,种植园主和联邦政府都穷尽一切手段、设法将土地据为己有。从个人层面看,以小说中的兰德尔种植园为例,颇具经济眼光的老兰德尔率先将棉花取代靛蓝和粮食,同时以帮助偿还债务的名义吞并破产农民的土地,随后购买邻近种植园,并不断向外拓展,最终发展成坐拥南、北两个棉区的大型棉花种植园。从国家层面看,联邦政府通过购买、战争和抢夺等手段,从外国政府和印第安人手中擭取土地,掀起了一股土地热。小说中提到的新兴植棉州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都是国外购地的成果。对于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国政府更是觊觎已久。1830年,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推出了《印第安人驱逐法》(Indian Removal Act),命令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划定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大批印第安人被迫踏上漫长的迁移之路,他们中的切克基人(Cherokee)更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磨难。当猎奴者带着被捕的科拉横穿田纳西时,他向后者讲述了曾经栖居在此的切克基人的“泪水之路”(Trail of Tears),科拉也由此参透了美国财富积聚的秘密,即“用偷来的身体耕作着偷来的土地”(109)。正是通过以上投机或暴力手段,美国征用了大片土地,在其中富庶的土地上种植了棉花。南方的棉花种植区域因此得以迅速扩大,最终发展成35万平方英里的棉花王国。
棉花王国的棉花经济并非只是区域经济,它还通过海外资本的连接,与欧洲市场、金融等行业形成了棉花经济共同体。小说描述了老兰德尔把农场变成棉田后的举措:“他在新奥尔良签下新的合同,跟代理商握了手,这些人背后有英格兰银行鼎力相助。钱来了,数量空前”(17)。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这一跨国交易的运作轨迹: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运营资金由伦敦货币市场(London Money Market,英格兰银行是其运用货币政策的主要场所)支持;资金具体由聚集在美国港口城市(如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新奥尔良)的代理商提供给种植园,而种植园需按时供应棉花。从环环相扣的交易过程中,可以窥见这个棉花经济体的本质:这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中心、以棉花为载体,以代理商为中介、资本和棉花双向流动的经济共同体。
正是在棉花经济共同体、奴隶制、国家力量等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内战前美国南方完成了以植棉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仅1800年到1820年二十年间,棉花占美国出口商品的比例增长了近五倍,1840年,棉花的价值占了出口商品总价值的一半”(Schermerhorn, 2018:I)。棉花业的发展使南方积累了巨额财富,重塑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棉花经济的壮大使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的政治辩论愈加激烈,但棉花带来的超高利润及其对美国经济的托举使南方始终占据优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内战前南方脱离派总是拿棉花当护甲向北方叫板;典型的例子当属南卡参议员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的公然叫嚣:“普天之下没有哪股力量敢对棉花开战,棉花就是王。” (Schoen, 2009: 322)
3.“棉花兽奴”:南方黑人棉奴的命运和记忆
随着棉花经济的快速膨胀,南方棉花种植园不断进行改进,以期供应更多的优质棉花。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对黑人棉奴进行压榨。小说中,兰德尔种植园南北两个棉区都采用了“种植园主-监工-工头”管理模式,但由于两个棉区分属老兰德尔的两个儿子,因此具体管理策略略有不同。北区由兄长詹姆斯掌管,在强迫棉奴劳动之余,给予他们微薄福利,如获准外出打额外零工、星期日半天休息等。但当詹姆斯猝死后,北区被生性残暴的弟弟特伦斯接管;他将棉区合二为一,统一采用铁腕管理,取缔北区的节日活动,亲自安排奴隶的婚配和生育,还要求额外打零工者交稅等。
在对劳动量的要求方面,特伦斯采用动态增长的采摘配额制度,“每一个采摘工每天的定量,都要根据他们上一年收获时录入的数字,按一定的比例加以提高”(48)。在特伦斯看来,奴隶的使用价值体现在每日杆秤上棉花称重的数字和记录簿上每个奴隶对应的采摘数量。他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要千方百计增加运往新奥尔良的数量,他要榨干每一块钱的潜力;当黑色的血就是金钱,这个精明的商人知道如何把血管切开”(26)。在兰德尔种植园,棉花计量工具和数字决定了棉奴食物份额的大小、体罚的轻重、甚至生死。
对奴隶的暴力惩治是确保棉花产量的基础,种植园主更相信“暴力会带来更多效益”(Schermerhorn, 2018: 40)。劳伦斯从父亲处继承的狼头手杖、监工手中的九尾鞭、为惩罚逃奴专门定制的各式刑具,以及园主和监工的每日巡视,都在无时不刻地威吓奴隶去除杂念、卖力干活。每日的高强度劳作,加上花样翻新的惩罚手段,使棉奴们身体受虐、精神受损。兰德尔种植园有个被称为“伶仃屋”的木屋,专门用来安置“非正常”的奴隶,包括“被监工的惩罚弄成跛子的人”、“被可见的及不可见的方式累断了脊梁骨的人”、“神志错乱了的人”和“孤立无依的人”(20)。而住在普通房舍的奴隶,情形同样悲惨;他们白天受尽折磨,“午夜之后常常暗自哭泣,或因噩梦和悲惨的记忆发出尖叫”(207)。总之,种植园里的黑奴无人能够逃脱棉花带来的厄运。他们要么像科拉的外婆一样终生沦为“棉花兽奴”(147),在棉田里耗尽生命;要么像老乔基一样,拖着残躯苟延残喘,“不过是残虐恶行的最后一块活化石罢了”(28)。更可悲的是,这些被棉花榨干生命的棉奴几乎没有见过棉花的终端产品。当科拉在逃亡路上第一次触摸棉布裙时,才明白“棉花进去一个样,出来是另一个样”(104),这一切正如学者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 1955-)所说,“黑人生产的棉花几乎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受益,几乎所有人,唯独他们自己除外”(2014: 504)。
对于侥幸逃跑的棉奴,比如黑人女孩科拉,即使她成功逃离种植园、并乘地下火车越逃越远,棉花仍是她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关于创伤,学界普遍认同创伤理论家卡鲁思(Cathy Caruth, 1955-)的观点,即创伤源自“突发性、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超出普通人的经验范畴”(Caruth, 1996:11)。然而该观点却不适用于考察奴隶制黑奴的创伤症候,因为他们的创伤源自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灾难和恐怖。相较特殊事件引发的创伤,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创伤更容易沉淀为受害者的生命意识和情感体验,并在日后以记忆的形式不断复现、侵扰受害者。小说中,无论当科拉身陷囹圄之时,还是开启新生活之际,身为棉奴的记忆总是自动涌现、如同鬼魅。当猎奴者追踪到南卡罗来纳、科拉被迫藏身地下车站时,饥饿感勾连起她在兰德尔家因棉花采摘量不足而挨饿受罚的记忆。在此之前,当她舒适地坐在黑人教室、为自己的学习进步感到自豪时,竟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植棉生活的苦难。反复经历棉花记忆的侵扰后,科拉意识到“……不管走了多少里路,人们还是把种植园带到这儿来了。它就住在他们心里,住在所有人心里。一旦有机会,它便显现,折磨他们,嘲笑他们”(99)。
对科拉而言,棉花不仅是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更是难以消除的认知习惯和语言身份。科拉逃亡前,棉花是她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体认对象。她熟谙有关棉花的一切常识,更是亲身感受并深刻理解了棉花意象喻指的“劳作”“奴役”“暴力”和“剥削”。棉花作为一种现实表征的意象图示,悄然嵌入科拉的语言表述和思维方式中,成为她描述和理解种植园外世界的修辞符号和认识参照。当科拉初次见到地下车站庞大的入站洞口、满是雕刻图案的石墙、以及通往神秘远方的铁轨时,她潜意识地调用棉花修辞开启对地下铁道这一新事物的认知:
隧道强烈地吸引着她。建造这样一个地方需要多少人手呢?还有隧道那一端,它通往哪里?路程又有多长?她想到了采收,想到怎样在收获时沿着垄沟奋力向前,一具具非洲躯体投入劳动,像一个人似的整齐划一,拼尽力气,全速采摘。广阔的棉田上,遍地都是白色的棉铃,数量何止千万,宛如星海,在最晴朗的夜空里光芒四射。等到奴隶们完工,他们仿佛剥去了棉田的颜色。这是一项壮丽的工程,从棉种到棉包,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付出的劳动感到自豪。那是从他们身上窃取的劳动,他们的血汗。而这隧道,铁轨,连同车站和时刻表,还有那些从中发现得救之道的苦命人——这才是让人为之自豪的奇迹。(67)(黑体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在科拉的认知过程中,棉花词汇的运用激活了她对棉奴劳动的记忆储备,为她理解地下铁道提供了心理通道和认知基础(集体劳动和令人惊叹的劳动成果是两者的共同特征),实现了认知的可及性。事实上,科拉的棉花修辞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包括棉花词汇和各类棉花比喻。高频率的棉花修辞构成科拉的语言身份,反复强化她的棉奴生活背景。尽管科拉在逃亡旅途中不断吸纳新事物,并积极构建新的社会身份(如博物馆员工、黑人社区居民),但她的棉花叙事始终把她与棉奴身份捆绑一起,成为特殊的身份标识。仅从这一点看,棉花对棉奴的心理影响根深蒂固、无法消除。
4.“一切要从棉花说起”:南方种族极权主义
小说中科拉的站点式旅程不仅呈现了南方各州的不同景观,而且绘制了一幅种族极权主义统治地图。正如阿伦特 (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8)中所描述的极权主义社会形态,内战前美国南方完全由种族主义控制,其统治覆盖一切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探究南方种族极权主义形成的根源,借用小说人物马丁的话说,“一切要从棉花说起”(145)。根据马丁的解释,“更多的奴隶带来更多的棉花”这一利润增值逻辑使大批黑奴涌向植棉州,黑人数量在短时间内呈爆炸式增长,部分州黑人的数量甚至远超白人。不时发生的奴隶暴力反抗使白人心生恐惧,“他们恐惧的程度如此之巨,甚至大过了棉花的利润”(156)。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黑白混血儿的出现使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种族危机。在他们眼中,种族交混的州是“令人厌恶的杂种州,白人掺杂了黑人的血,被弄得肮脏不堪,不清不白,一塌糊涂”(149)。正是白人构建的种族威胁论和种族污染论触发了种族极权主义机制。
小说中,南方的种族极权主义体现在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联手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在北卡罗来纳,法律、暴徒、私刑和死亡景观交织成一张极权主义大网,对黑人赶尽杀绝,对白人严加管控。法律向来是种族主义的同谋;南方的极权主义者以立法形式将种族主义合法化,并以法律之名实施极权统治。州政府颁布了新的种族法,禁止有色人種进入,同时对现居的自由黑人进行驱逐或杀戮。在法律的赋权下,一批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徒组成巡逻队,成为种族歧视法的拥趸。值得注意的是,巡逻队在执法过程中对同情黑人的白人采取无差别对待,将他们也送上绞刑架。由此可见,种族极权主义的统治逻辑并非基于黑白肤色的对立,而是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绝对对立。极权主义者不断煽动民众制造想象中的敌人,持续强化其非此即彼的敌对意识,并对白人内部的异己声音进行清算。在此语境下,萨勒姆猎巫运动的鬼魂重现,当地民众卷入检举“白奸”的风潮:“人们检举商业上的竞争对手,陈年的世仇,还有邻居,详述昔日的交谈,回忆叛徒们如何表露过不该有的同情;孩子们告发自己父母,将女教师讲授的煽动性言论的种种特点对号入座”(150)。普通白人的日常生活被监控,私人空间被挤压,人人都为不可预知的厄运提心吊胆。对此,科拉向马丁发出诘问:“你感觉自己像不像奴隶?”(152)
除精神控制外,私刑和死亡景观是种族极权主义摧毁人性的惯用手段。私刑强调公开刑罚,极具仪式感和表演性。典型的私刑“表演”不仅展示白人对黑人施加的残酷刑罚,还展演民众的集体围观和共同参与。科拉通过马丁家阁楼墙壁上的孔洞,目睹了对面公园“周五晚会”上演的私刑全过程。她发现白人民众不分年龄、性别,个个歇斯底里,全部被挟裹在狂热的种族仇恨中。在科拉的视野中,白人在私刑场景下形成了“理想化的南方白人共同体”(Wood, 2009: 9)。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体意识不复存在,所有人都受控于共有的种族敌对意识,成为整齐划一的加害者。私刑过后,黑人的尸体被悬挂在通往各城镇的“自由小道”上,与之前挂在树上的尸体一起,组成令人惊悚的死亡景观;“死尸有多少,道路就有多长”(166)。这些遗骸作为私刑的转喻表征,不仅直观地展现了种族极权主义的暴力手段,而且通过观看者的凝视转化成威慑力,对观看者形成规训和警示。
与北卡罗来纳肉眼可见的恐怖景观相比较,南卡罗来纳则打着种族融合的幌子,秘密地通过生育控制和梅毒实验对黑人种族进行改造和控制。同法律一样,医学也往往被种族主义者利用,充当其极权统治的依据和手段。小说借两位白人医生之口表达了政府对黑人人口激增问题及黑人恶劣品行的担忧,并阐明了为解决以上问题而实施的医学战略的必要性。医生声称他们依照种族基因特征对黑人施行绝育手术,旨在遏制黑人生育率和其低劣的基因,以成就“史上最具胆识的科学工程”(113)。而关于梅毒实验,医生则轻描淡写地讲述他们如何放任已感染梅毒、但毫不知情的黑人进行性活动,致使梅毒在黑人内部快速传播,却不提供任何医疗救助,任其自生自灭。
事实上,白人医生谈论的战略绝育和梅毒实验均发生在二十世纪美国的其他州(史鹏路,2020:233-235)。然而,小说通过时空错置手法,将以上典型科学种族主义事件放置在内战前的南卡罗来纳,意在凸显南方种族极权主义者的统治假想,即他们以掌握自然规律(种族基因差异)为名,“认为自己从事的乃是一项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大事业,对一部分人的肉体的消灭,不过是历史进程中必要的最终的解决”(陈伟,2004: 45)。此外,两个事件发生地的错位安排也反映了作家对美国科学种族主义的“源”与“流”的考量,毕竟南卡罗来纳不仅是诸多科学种族主义先驱者的摇篮,还是多基因论和人类多重起源研究的发轫地(参见史鹏路,2020: 237)。
作为内战前美国南方的缩影,小说中的南、北卡罗来纳分别以隐性和显性的恐怖手段,对自由黑人或僭越奴隶制的黑奴进行惩治或清除,剥夺了黑人作为“人”的权力、强化其作为“奴”的合法性。同时,种族极权主义社会大环境向黑人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即“逃离种植园的地界,就是逃离基本的生存原则”(14)。这也是科拉的外婆终生奉为圭臬的生存哲学。而科拉在亲历了南方各州种族极权主义统治后,也终于认识到“无论是在棉田、在地下,还是在阁楼的一间斗室,美国都是她的监牢”(156)。
5.结语
《地下铁道》中,怀特黑德巧妙地将棉花叙事嵌入逃奴小说,使棉花充当调用多元历史文本的牵引绳,全面再现了内战前美国南方的地域图景。这为颇具个人化的奴隶叙事添加了丰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注释,使其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雪白的棉花剥夺了黑人棉奴作为自然人的全部权利,浸染了黑奴的血泪和生命,见证了奴隶制和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这在主题上既是对经典奴隶叙事的继承,又是深化和拓展。棉花将黑人逃奴的个人叙事和由棉花驱动的国家话语交织一起,使二者互为注脚,对勘映射,凸显了黑人奴隶在美国国家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此外,怀特黑德还以棉花引发的社会问题为纽带,将科拉与若干种族主义历史事件关联,使其成为美国历史的观察者和讲述者。“文学成为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发生交会之地”(王卓,2022:280)。无论亲历南卡罗来纳的医学丑闻,还是目睹北卡罗来纳的种族极权主义恐怖活动,科拉习惯性地将自己与历史事件拉开一定距离,始终保持冷静的观察态度、克制的叙述风格和思辨性的批评立场,并不断对美国历史的本质、自由的真谛等重要命题提出犀利的观点。不难看出,作家从黑人的目光审视、评判美国历史,由此实现了对白人种族主义历史编撰的“反凝视”和“反书写”。
注释:
① 本文使用AntConc软件对《地下铁道》进行主题词的主题性(keyness)分析,结果显示,排在前10位的主题词分别为:slave (396.191) / slaves (184.687), colored (261.017), plantation (215.868), girl (208.814), white (165.744), men (149.247), boy (148.975), railroad (146.258), master (139.645), cotton (136.716)。下文对棉花共现语境的提取也借助了该软件。
② 引自怀特黑德(2017)。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
③ 南方植棉业兴起前的一段时期,美国国内反奴隶制的呼声曾颇为高涨,参见王金虎,2019年,第129页。
参考文献
[1]Arendt, 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2]Baptist, E.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3]Beckert, S.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4]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5]Schermerhorn, C. Unrequited Toil: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Slaver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6]Schoen, B. The Fragile Fabric of Union: Cotton, Federal Politics,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7]Whitehead, C.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M]. New York: Doubleday, 2016.
[8]Wood, A. L. Lynching and Spectacle: Witnessing Racial Violence in America, 1890-1940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9]陈伟.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J]. 学海,2004(2):43-51.
[10]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M].康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G].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2]史鹏路.历史重构与现代隐喻: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J].外国文学评论,2020(2): 223-238.
[13]王金虎.美国奴隶制史[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14]王卓. 黑色维纳斯的诗艺人生与世界观照:丽塔·达夫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15]翟乃海. 论怀特海德《地下铁路》的后种族书写[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9 (春季号):70-75.
(责任编辑:翟乃海)
收稿日期:2022-09-12;修改稿,2023-12-10;本刊修订,2023-0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非洲流散女性文学的中间航道书写”(项目编号:22CWWJ04);同时得到山东省青创人才引育计划“数字人文与外语创新研究团队”支持。
作者简介:张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非裔英语文学、当代美国文学。电子邮箱:fffzl@163.com。
引用信息:张琳.论科尔森·怀特黑德小说《地下铁道》中的棉花叙事[J].山东外语教学,2023,(1):95-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