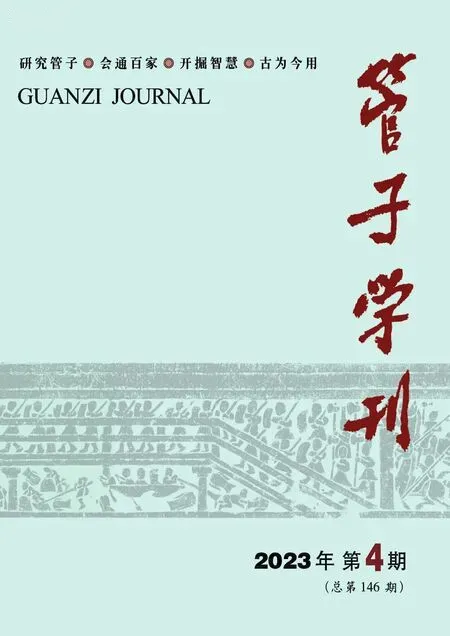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的发展
——以《论语》《孟子》《荀子》的“君子”所指为例
2023-10-24张涅
张 涅
(浙江科技学院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3)
现代以来,学界一般循着由概念到体系的西学范式研究诸子思想。其实,假如从文本的客观形态出发,可知其大多是经验性的认识,不在理性认识的范畴内(1)经验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别,前人论之甚详,这里不赘言。在诸子中,有对感觉性认识的阐述,见《公孙龙子》和《庄子·天下》的“十事”“二十一事”等;也有知识性、理性的认识,在《墨经》《韩非子》中即可见到若干。当然就整体而言,经验性的认识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具体当另文细述。参见张涅:《〈公孙龙子〉关于个体的自觉》,《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2页;张涅:《先秦名学发展的两条路向》,《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66页。。而且从春秋末到战国后期,经验性的认识有一个从特定性、类别性向一般性发展的轨迹。战国后期的荀子,已经开始自觉地作一般性的思考,当然类别性的表达也还存在;而且“一般性”不同于理性认识的“普遍性”,还在经验世界中。这一点,学界似尚没有充分重视,故本文试加以疏述。
限于篇幅,本文以《论语》《孟子》《荀子》中的“君子”所指为例。众所周知,理性认识的基本单位是概念,凡概念必具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如涂尔干、莫斯说的,“概念就是历历分明的一组事物的观念,它的界限是明确标定的”(2)[法]涂尔干、莫斯著,汲喆译:《原始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1-102页。。若著作内出现的“君子”意义是不一致的,则说明其不属于概念,由此展开的认识就是经验性的。这三部儒家著作分别形成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战国中期和战国末,阶段性明晰,而且“君子”又是这一学派的重要思想范畴(3)例如余英时说:“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1页。,故而以为对此加以疏述,可以展开本文的讨论。
一、《论语》的“君子”意义
我们首先来看《论语》中的“君子”。这里的“君子”是不是概念?许多学者阐释《论语》及孔子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把“君子”作为一个概念来认识。但是我们细读以后,会发现其并不具备这个特征。
在《论语》中,“君子”出现107处(4)据朱熹《论语集注》,计《学而》4处,《为政》3处,《八佾》3处,《里仁》7处,《公冶长》3处,《雍也》5处,《述而》5处,《泰伯》4处,《子罕》2处,《乡党》1处,《先进》3处,《颜渊》10处,《子路》6处,《宪问》7处,《卫灵公》14处,《季氏》6处,《阳货》8处,《微子》2处,《子张》10处,《尧曰》4处。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对于这些“君子”意义,前人主要有两种认识。(1)分为在位者和有德者两类。例如崔述说:“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称,而后世以称有德者耳。”(5)崔述:《崔东璧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杨伯峻《论语词典》的“君子”词条也分“有道德的人”和“在高位的人”释义(6)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1页。。(2)增加了兼有德、位者,分为三类。例如萧公权说:“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记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这两种认识,前者侧重于理论分类,后者就实际指称言,都是成立的。这已经说明“君子”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实质上指出了其并非作为理性认识单位的概念。
事实上,即使指示道德意义的,其具体内涵也有很大不同。粗略地区分,就有崇高无私的和兼有个人理性的两类。《论语·泰伯》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程子注:“节操如是,可谓君子矣。”(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页。金履祥说:“王文宪曰:‘可以’二字,犹以才言。‘不可夺’处,乃见其节。门人有曰‘不可夺也’贯上二句,朱子然之,故取程子之言,则才轻节重。”(9)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9页。宋明以来,一般以此为“君子”的准则。但是,在《论语》中另外又有指兼考虑个人利益的。例如《论语·卫灵公》:“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3页。皇侃《义疏》:“国若无道则韫光匿智而怀藏,以避世之害也。”(11)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7页。标点有改动。显然蘧伯玉还兼有现实利益方面的考虑,不肯以生命为代价作牺牲;他这一类的“君子”讲道德,也有生活理性(12)不少学者以为君子必定是崇高无私的,这就难以解释这类兼具道德和生活理性的“君子”意义。例如崔适《论语足征记》以为,前人所注的蘧伯玉“卷而怀之”是“为刘歆所误,乃歆之厚诬伯玉也”;并说:“事君者安则食其禄,危则避其难,而犹得称为君子,则全躯保妻子之臣,于计得矣,岂非害义之大旨?”这个兼有生活理性的“君子”意义,孟子以后多有忽略。其实,从社会道德教化和践行的普遍可行性言,特别值得重视。参见崔适:《论语足征记》,北京:北京大学,1916年排印本,第25、27页。。
同为道德指向,意义却有质的不同,这个问题前人已经注意到了。例如金履祥说:“朱子谓《论语》中说‘君子’处,有说得最高者,有大概说者。”(13)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第27页。陈大齐说:“君子用作狭义时、次于圣人,且次于仁者,只表示理想人格的第三级。”(14)陈大齐:《孔子学说》,台北:正中书局,1967年版,第252页。两位学者都指出了这个特征。狄培理也说:“我们可以把《论语》多数时候提到的‘君子’仅仅理解为‘gentleman’,它指的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些人具备有教养的风度、完美的态度以及得到良好发展的道德感。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尽管我会说是值得注意的少数——‘君子’才会扮演着非常崇高而且自我奉献的角色,这是一种要求尊贵者(noble man)成为其他人的领导人的角色。”(15)[美]柯雄文著,李彦仪译:《君子与礼》,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版,第22页。“gentleman”和“noble man”的不同翻译,也是表明意义的分别。笔者在此基础上,把《论语》中的“君子”分为四类:(1)指称有官位的;(2)指称兼有道德和地位的;(3)泛指具有道德者;(4)特指有道德又有生活理性者(16)分别有15、42、36、14处。具体考释参见张涅:《〈论语〉“君子”意义分疏》,高华平、张永春主编:《先秦诸子研究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377-415页。。这里完全旧义的占14%,单指道德义的不到半数。由此足以说明《论语》中的“君子”不是一个概念。
其实,这不过是《论语》表达的基本形态而已。《论语》语录的本旨与特定场景和特定对象相关联,原本是没有概念的,“仁”“礼”等都不是作为概念出现的(17)这一点已经有学者明确指出过。例如赵鼎新说:“孔子对概念的抽象定义不感兴趣。”参见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45页注①。。《论语》中的“君子”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以某一条语录中的“君子”意义所指当作所有“君子”的内涵规定。胡适以为:“孔子所说君子,乃是人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至少能尽一部分人道的人。”(1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牟复礼说:“孔子坚称:君子应该用来称呼那些德行智慧卓然其上的‘圣人’,任何人达到‘圣人’的标准才能作‘君子’。”(19)[美]牟复礼著,王立刚译:《中国思想之渊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这些都是以偏概全了。狄百瑞说:“孔子就是在文人与高尚的人这两重意义上说到君子的。”(20)[美]狄百瑞著,黄水婴译:《儒家的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注意到了《论语》中“君子”意义的不统一性,但是忽略了传统的在位义,犹有不周。这些不能顾及文本整体的问题,应该是从概念出发、系统构架的理性模式造成的。
二、《孟子》的“君子”意义
我们再来疏述《孟子》中的“君子”意义。在《孟子》中“君子”出现82处(21)据朱熹《孟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计《梁惠王上》2处,《梁惠王下》2处,《公孙丑上》2处,《公孙丑下》8处,《滕文公上》4处,《滕文公下》7处,《离娄上》3处,《离娄下》16处,《万章上》2处,《万章下》5处,《告子下》7处,《尽心上》15处,《尽心下》9处。参见何善蒙、池静宜 :《〈孟子〉的君子观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78-85页。,有63处是指示道德意义的,占了75%以上。其中有只强调道德修养的,例如《孟子·离娄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8页。指出君子的特质就是有对于“仁”“礼”的体认。也有指兼具地位与道德的,例如《孟子·公孙丑下》:“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2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41页。“君子”能决定战争与否,当然属于有地位者;其还能“战必胜”,肯定获得了民众的拥护,为有道德者。故尹氏注:“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41页。
若干“君子”是只指示有道德的,还是指兼具地位与道德者,难以确定。例如《孟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朱熹注:“言滕地虽小,然其间亦必有为君子而仕者。”(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6页。“为君子而仕”,指有道德者参与政事,则“君子”是有道德的在位者。然后又注:“所以治野人使养君子也。”(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6页。这里的“君子”似又只指在位者,朱熹所注的“君子”也内涵不同(27)笔者以为指在位者更为通达。这里讲一个国家内有“君子”与“野人”的社会分工不同。“将”是或者、抑或的意思。“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意或者是管理者,或者是被管理者。。当然,《孟子》的“君子”意义朝道德方向发展了是无疑的。它具体有两个特征:(1)趋向崇高,《论语》中兼有道德和生活理性的意义指向被放弃了;(2)着重于内心修养方面,强调“君子”必然由“性善”而体悟“天道”。
但是,这些尚不能使“君子”成为一个概念。概念必须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孟子》中的“君子”还不具备。最明显的证据是,其中尚有16处指示在位义,有3处与智慧、才能义相关,这说明其内涵并非确定在道德性范畴内。指示在位义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一条,其他列述如下:
《孟子·公孙丑下》:“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2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47页。这里讲“古之君子”有德,“今之君子”无德,“君子”只是指在位者。
《孟子·滕文公上》:“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2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3页。此又见《论语·颜渊》篇。“草上之风”喻指在上位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皇侃《论语义疏》:“君子,人君。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风也;民下所行,其事如草。”(30)皇侃:《论语义疏》,第314页。余英时也说:“此处的‘君子’和‘小人’两个名词当然是指‘位’而言。”(31)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275页。
《孟子·滕文公下》:“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朱熹注:“君子,谓在位之人。小人,谓细民也。”(3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68-269页。
《孟子·离娄上》:“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朱熹注:“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3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6页。胡炳文注:“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祸也。”(34)胡炳文:《孟子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页。
《孟子·离娄下》:“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只是就有位者的行政而言。故朱熹注:“言能平其政,则出行之际,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为过。”(3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0页。赵佑《温故录》:“君子,即谓子产。”(36)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6页。也一说。

《孟子·告子下》:“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朱熹注:“无百官有司,是无君子。”(3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6页。即“君子”指有地位者。
另外,与智慧、才能意义相关的3处也列述如下:
《孟子·离娄上》:“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3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84页。这里,孟子从目的、效果等方面加以阐述,即强调“君子”是具有智慧和才能的。在《孟子》中,有许多处阐述“智”的问题,例如《孟子·离娄上》:“治人不治反其智。”“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4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78、287页。《孟子·万章下》:“始条理者,智之事也。”(4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5页。故而出现这个意义指向的“君子”也不是偶然的。
《孟子·万章上》:“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4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05-306页。“野人”是没有见识的人。《论语·子路》:“野哉由也!”朱熹注:“野,谓鄙俗。责其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也。”(4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2页。则与之相对的“君子”,当指有见识能力者。
《孟子·尽心上》:“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朱熹注:“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学之之法。”(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2页。即“君子”讲教育原则和教学手段,是有才识者。
上述可知,从思想史的角度讲,可以认为《孟子》的“君子”意义朝着道德化方向发展了,但是并不能说其已经是一个概念。
三、《荀子》的“君子”意义
与《论语》《孟子》的类别性指向不同,《荀子》的“君子”所指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意义是一般性的。《荀子》中的“君子”(包括“士君子”)出现297处(45)据王先谦《荀子集解》,计《劝学》16处,《修身》11处,《不苟》29处,《荣辱》14处,《非相》20处,《非十二子》9处,《仲尼》4处,《儒效》25处,《王制》13处,《富国》4处,《王霸》4处,《君道》8处,《臣道》2处,《致士》11处,《议兵》2处,《强国》2处,《天论》9处,《正论》2处,《礼论》20处,《乐论》7处,《解蔽》7处,《正名》6处,《性恶》10处,《君子》2处,《成相》5处,《赋》4处,《大略》23处,《宥坐》6处,《子道》6处,《法行》9处,《哀公》5处,《尧问》2处。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基本上都兼具道德修养和才干能力。例如:
《荀子·劝学》:“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46)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页。“博学”与才识相关,梁启超注:“博学则智识日明。”(47)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日参省乎己”即有道德修养。俞樾以为“‘省乎’二字,后人所加也。……参者,验也”(48)俞樾:《诸子平议》,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25页。,即认为荀子只是强调经验认识方面。但是下文“行无过”也与道德修养相关,其说不周。王博“把知明理解为道德知识,行无过理解为道德践履的能力”(49)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页。,只强调道德一面,也不周。
《荀子·非相》:“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50)王先谦:《荀子集解》,第86页。“贤”“知”“博”“粹”包含道德修养和才干能力两方面。“兼”,《说文解字》:“持二禾。”(51)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349页。引申为同时关涉几个方面或几种事物。“兼术”即为多方面包容的原则。故杨倞注:“兼术,兼容之法。”(5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86页。
在具体阐述中,或只展现君子一个方面的素质,但是把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另一方面的素质也是内在的,两者统合在一起。例如《荀子·王制》:“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53)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1页。这里讲君子必有才干;当然另有品德作为基础,故而下文接着说:“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54)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1页。李滌生注:“君子,具有公平、中和、知类的人格之圣哲。”(55)李滌生:《荀子集释》,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165页。即指出了其相统一性。再如《荀子·儒效》:“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56)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28页。重点在“修其内”“积德”;而下文又说:“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5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30页。讲的是才能方面。
这个“君子”意义的认识,从思想内容看是综合集成的表达,从思想形式说则是朝着一般规定性的发展。在荀子之前,关于“君子”意义的认识有两个方向的发展:(1)侧重指有道德修养者,(2)侧重指有能力才干者。前者以孔、孟为代表;孔、孟也有关于能力才干方面的认识,例如孔子有关“器”的阐述,上述《孟子》中的三例,但是其主要的发展在于道德方向。余英时说:“孔子以来的儒家是把‘君子’尽量从古代专指‘位’的旧义中解放了出来,而强调其‘德’的新义。”(58)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275页。这无疑是合乎思想史的客观事实。后者在《易经》《左传》《国语》《商君书》《战国策》等著作中多见。例如《左传·襄公三十年》:“季武子曰:‘晋未可偷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后可。’”(5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2-1173页。“佐”“咨度”“保”都是指才干能力方面的。故季武子说:“晋未可偷也。”“偷”是轻视的意思。《商君书·算地》:“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60)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页。此“君子”原本无地位,“事势以成名”,即表现出才干后得以成功。《国语·晋语九》:“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祸福之门。是以君子省众而动,监戒而谋,谋度而行,故无不济。’”(61)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国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无不济”即功业有成,是才识能力的表现,邬国义等译此“君子”为“有见识的人”(62)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国语译注》,第268页。,是准确的。荀子从儒家本位出发,赋予“君子”道德与才干相统一的内涵,并且作为一般性的意义规定,这也是他对先秦思想的一大贡献(63)参见张涅:《先秦“君子”意义的流变》,《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2期,第87-100页。。
四、由类别性向一般性的发展
由上述可知,《论语》《孟子》的“君子”意义朝道德方向不断加强,但是其还有旧义,尚无确定的内涵和外延,还是类别性的。到了《荀子》那里,一方面是所指意义的集成,把道德性和才干要求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形式的质变,基本上都有一般性的意义规定。即凡是称为“君子”的,都兼具道德修养和才干能力。这个一般性认识的思想史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现代以来,学界高度评价荀子集大成的思想贡献,但是对于其在思想形式方面的发展贡献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这个发展,从表面上看,是原始的对话语录体向文章体转变的表现,而本质上应该是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的质变。《论语》属于原始的语录体著作,原本绝大多数语录有具体所指。故而其本旨与进行着的经验活动相关,意义是特定性的;我们在理解时需要结合语录涉及的具体语境和特定对象(64)张涅:《走近诸子的另一条路径》,《光明日报》2019年3月2日,第11版。。当然,意义总是在接受的过程中被赋予的,后人的阅读接受总是从各自类型的社会角色和成长的阶段性需要出发的,语录的意义就自然地由特定性发展为类别性的。例如《论语·里仁》的“父母在,不远游”(6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原本当是对于父母生活需要其照顾的某一个对象而言,是特定性的表达(66)假如把这条语录作为一般性的要求来理解,那怎么也讲不通。孔子周游列国,跟随的弟子也不可能都父母亡故。;后来对类同情况的后学都有指导意义,就成为类别性的认识。那些“君子”意义,或评价遽伯玉的“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6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3页。,或曾子说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也”(6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4页。,原本为特定性的,后来不同类别的人作为各自的座右铭,就成为类别性的存在。一般地,经验认识由特定性向类别性的发展有两种类型:(1)通过归纳和分类的方式。这样把日常的生活、生产经验总结出来,成为指导相应活动的规范准则。(2)以典型作为范式。各个领域领袖人物的行为话语原本是特定性的,因其为“偶像”而具有示范意义,就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指南。《论语》的语录意义成为类别性的,主要属于后一种类型;即那些表达对于相应的实践活动有指导意义而成为“类”的认识。
《孟子》的大多数篇章也依然保留着对话记录的形式。对话总是在场景中,其话题原本只就当时的对象而言;后来的读者与当时对象同类,才可能从中获得直接的指导意义。有一些涉及了一般性意义的讨论,例如“性善”说,但是其原本是出于游说君王自上而下实现仁政的考虑,并非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始终坚持。故而《孟子·尽心上》“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6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0页。,《孟子·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7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3页。,都是强调“性善”的只是少数“君子”。从整体上看,《孟子》的意义显然也是类别性的。例如“义利之辨”,是对梁惠王这个对象而言,对与梁惠王一类的君王(官员)才有意义。因为君王(官员)已经有了“利”的保障,该去追求“仁义”境界。故而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7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但是假如为贫民,谋生的“利”还没有,则不该只用“仁义”与否去考量的。所以又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7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1页。就是认为,对贫民首先得考虑“利”的问题;没有固定的“利”,贫民就不会有恒定的“义”。假如不能温饱,去偷盗抢窃,那责任在君王身上。宋明以来,普遍以为孟子的“义利之辨”是对所有人说的,是对全社会的普遍要求,具有一般性意义,这显然是不合本旨的。从实践层面上看,把类别性当作一般性来认识,会产生负面影响,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73)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1页。就是典例。
到了《荀子》,还有一部分的意义指向是类别性的。例如关于人性论,是“性恶”还是“性朴”,就没有一定之论,如蔡元培说的“间有矛盾之说”(74)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页。,后人可以根据需要来接受阐释(75)学界有《荀子》讲“性恶”还是“性朴”的争论。其实,在《荀子》中有讲“性恶”的,也有讲“性朴”的,各有“类”的意义。有关人性论问题,《荀子》也是着重在经验层面作“类”的总结,原本没有理论建构,也没有核心观点。后人以为“性恶”(或“性朴”)说更有价值,自可加以阐述发挥,但是不能说其就是理论核心。。但是因为发展到了文章体,不再与具体的对象或场景相对应,许多内容对于所有相关的经验活动都有意义,表现为一般性的。显然,这一方面是文体特征的内容表现,另一方面还在于思想形式发展的要求。所谓类别性的意义,还是与具体的、某一类别的实践活动相关;而一般性意义则基于经验又在经验之上,能指导该领域内所有的经验活动。《荀子》虽然没有完全离开类别性的认识,但是已经开始进入一般性的门槛。关于“君子”的阐述即是对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指导,并非《论语》《孟子》那样只对于相应的对象才有意义。对此《荀子》已经有自觉的认识。《荀子·解蔽》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76)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93页。“体常”就是指认识一般性意义。《荀子·正名》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7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3页。《说文解字》:“期,会也。”段注:“会者,合也。期者,要约之意。所以为会合也。”(78)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第332页。“期累实”指“名”是对某一类经验的“实”的归纳表达,即为一般性的要求。《荀子·王制》说:“以类行杂,以一行万。”(79)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3页。更是说明了认识由类别性到一般性的要求。“杂”是聚合、集合的意思。《方言》:“杂,集也。”《广雅》:“杂,聚也。”(80)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6页。“以类行杂”指在集合、混合状态中作类别性的认识。“万”指纷繁现象,“一”即一般性认识。“以一行万”较之“以类行杂”进了一步,意思是:达到了“一”的认识就可以“行万”(81)“以一行万”,从文辞原意看,当就认识与实践的方式、路径而言。杨倞注:“行于一人,则万人可治也。”不确。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3页。;即在纷繁的经验世界寻觅一般性的意义。显然,《荀子》既指出认识对象的客观性:“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8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20页。建立了经验性的基础;另外也强调“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83)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15页。,强调通过主体性认识获得“同”(即一般性)的结果。
由此可见,从《论语》到《孟子》再到《荀子》,经验认识由类别性朝一般性方向发展了(84)佐藤将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先秦思想的发展,实经历了从以伦理价值的提倡为核心议题的‘伦理论辩’(ethical discourse / argumentation),转换成对社会政治论题和形上学议题的分析,即‘分析论述’(Analytical discourse)之过程。”而且具体分析了《论语》《孟子》与《荀子》在思想形式方面的差别。但是以“伦理论辩”概之《论语》《孟子》,尚侧重于思想内容方面;以“分析论述”概之《荀子》,也没有落实到其作为思想形式的特殊性。参见[日]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3页。。荀子的思想贡献,除了从儒家本位出发对先秦诸子思想内容做了集大成工作,还有在思想和表达形式上的发展。我们假如“把思维过程本身的一般形式和在不同时期与此过程有关的具体内容区别开来”(85)[德]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1页。,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五、一般性认识在经验的范畴内
那么,《荀子》的一般性属于理性认识吗?其中的“君子”已经是一个概念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可能在于是否认为经验认识能够发展到理性认识。假如两者是认识发展的两个阶段,那么可以认为,从《论语》《孟子》到《荀子》,经验认识由量变到质变,进入了理性层面;至少在《荀子》中,“君子”已经是一个概念了。假如两者是平列存在的两种认识方式,各有意义领域,那么经验的一般性也是在经验的范畴内,没有进入到理性世界。这样,“君子”也不能作为概念来阐释。
学界周知,关于经验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相关的对于“概念”的规定也有质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把经验认识到的某一类对象的共同特点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从概念出发,进行逻辑认识活动,即进入了理性层面。因此概念是在经验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本质上与实践活动相统一。例如休谟说:“我们的理性如果不借助于经验,则它关于真正存在和实际事情也不能推得什么结论。”(86)[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8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验本质上是有限的,不能达到“全部”“所有”,故而不会有具备普遍性、绝对性特征的概念;概念只存在于形而上的理性认识中。例如黑格尔说:“逻辑是对于纯粹理智的抽象活动的一种意识(而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东西的知识)。”(87)[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66页。“这个概念本身是不能以感性来直观或表象的;它只是思维的对象、产物和内容,是自在自为的事情。”(88)[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页。显然,两者所指的“理性”和“概念”都有质的不同,从各自的界定出发,都是自洽的。这里只是认为,把经验性与理性加以区别,有助于把握诸子思想的特质。
不少学者以为《荀子》具有逻辑理性。例如牟复礼说:“他花了大量笔墨厘清概念的意义,确定概念的分类和关系。荀子的思维已经是系统化的了。”(89)[美]牟复礼著,王立刚译:《中国思想之渊源》,第62页。其实,假如认为经验必然是有限的,“类”的认识再发展也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普遍性,那么就会注意到《荀子》思想的一般性并不在理性范畴内,其“君子”也不能称为是概念。荀子融“法”入“礼”,“礼”“法”并重,旨在建立一个有文化思想的新政治体制,有关“天”“人性”等的论述都是为了佐证其礼治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90)不少学者以为关于“天”“人性”的认识是荀子思想的基点。例如刘又铭说:“强调‘天人之分’与‘性恶’,进而主张‘以人制天’‘化性起伪’‘隆礼义杀诗书’‘法后王’,这是《荀子》一书里头明明白白表述与呈现的理路。”这只是一种出于理论性建构需要的现代阐释,并非《荀子》的本旨所在。参见刘又铭:《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他的所有认识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都基于社会历史的经验之上。蔡元培说:“其思想多得之于经验。”(9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页。徐复观说:“欲了解荀子的思想,须先了解其经验地性格。即是他一切的论据,皆立足于感官所能经验得到的范围之内。为感官经验所不及的,便不寄与以信任。”(9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6页。这些都是不刊之论。廖名春说荀子有“政治实用主义倾向”(93)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也是由此而发。这种经验认识达到了一般性的程度,但是与理性认识中的普遍性还是不同的。
这里对“一般性”和“普遍性”作一个辨别。在日常语言中,“一般性”和“普遍性”往往意义同一(94)《汉语大词典》“一般规律”条:“与‘特殊规律’相对。又称‘普遍规律’。即各种事物普遍具有的共同规律。”查“360搜索”:“一般性,事物的一种性质。是指具有普遍性,如公式、公理、定理等等,对所有的对象都适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般性”不同于“普遍性”的表达。例如“一般性支出”,只包括主要的、常规方面的费用支出。“一般管辖”,是与“特殊管辖”相对而言,不包括后者。参见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但是哲学表达需要则把两者区别开来:(1)从量上看,“普遍性”指“全部”“所有”;“一般性”只是指绝大多数,存在着例外。(2)从质上看,“普遍性”与逻辑性、必然性相关联;“一般性”不具备逻辑的必然性,只是大概率而已。作这样的辨别,是强调“普遍性”是理性认识才能达到的,而“一般性”为经验认识发展的结果。在理性认识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确定的,所展开的系统论证具备逻辑必然性,从而有绝对的普遍性意义。而经验认识的对象原本是特定性的,经过总结发展为“类”;而“类”都在经验世界中,不同的“类”经验只对于相应的实践有指导意义。显然,最大的“类”也是有限的,不能包含“全部”“所有”;基于“类”的关联性认识,也不具备绝对的普遍性意义。
落实到《荀子》文本,这一点显而易见。例如《天论》“明于天人之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95)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08、309页。,就强调认识要放在“人”的经验世界内;一般性只是在“人”的范围内,并非包括“天”“人”的整个宇宙世界。关于“共名”的阐述更说明其经验性认识的特质。《正名》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96)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18-419页。“单”指全称,“兼”指特称。从理论上说,“单”和“兼”已经可以包括所有的指称。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往往同一个“实”,有时可用全称(“单”),有时可用特称(“兼”)。例如一匹白马的“实”,可以称“马”(“单”),也可以称“白马”(“兼”)。所以荀子提出“共名”,认为“白马”也可以称为“马”,“单”也可以是“兼”。这显然是出于实际使用需要的认识,在经验性的范畴内,并非理论层面的界定。
这种经验的一般性认识在有关“类”的阐述中也有表达。《荀子·不苟》:“知则明通而类。”(9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3页。《荀子·王制》:“听断以类。”(98)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8页。显然荀子高度肯定经验认识中“类”的价值。但是,“类”的归纳只在相应的经验范围内发生意义,不能覆盖到相应的经验范围之外,《荀子》要求认识的一般性,就对“类”意义加以发展。故而《荀子·王制》又说:“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杨倞注:“类,谓比类。”(99)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1页。即在经验实践中,出现无“法”(条文)可依时,参考同类的“法”(条文),这样突破了原来的“类”意义限定。《荀子·劝学》也说:“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杨倞注:“通伦类,谓虽礼法所未该,以其等伦比类而通之。”(100)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8页。即“善学”者要超越“类”的局限。故而赞扬孔子“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101)王先谦:《荀子集解》,第95页。,“壹”就是能超越“类”的局限性。这足以证明:荀子的认识具备经验认识的一般性,但是没有理性认识的普遍性。这一点,前人也已经注意到了。例如牟宗三曾说“心智之运用固需限于经验,亦须遵守逻辑之法则”,而“荀子所缺”(102)牟宗三:《名家与荀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73页。。惜学界主流未予重视。
确实,发展至战国后期的诸子思想已经有相当的一般性表达,《荀子》正是代表作之一。但是,我们也得注意到,严格地讲,其尚未进入理性的门槛。这说明: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若从概念进入做系统的思想建构,那是西学的研究路径,并不合乎诸子文本的客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