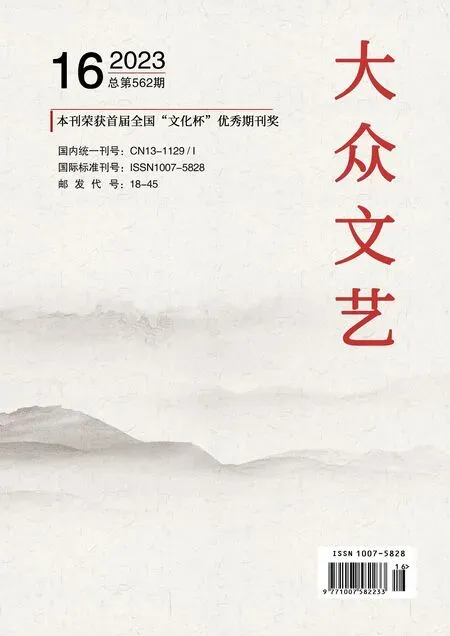介入与超脱: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短篇小说《尾声·摄影师》释读
2023-10-17薛琴
薛 琴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珠海 519085)
《尾声·摄影师》是艾丽丝·门罗的第二部小说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之“尾声”。在这篇故事里,已经成长为青年小说家的黛尔,不仅对小说创作中材料的组织以及技巧的使用进行了思考,而且还以自身亲历的故事实践着这些思考。这些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凝结为她对生活和创作关系的别样认知:生活是创作的原始质料,创作是生活的升华和超越,但是创作却无论如何也难以把握生活深处最深的奥妙。博比·谢里夫的故事就是她能给出的最好例证。戴尔这种书写人物书写小说的方式,也是她独特的书写历史的方式。换言之,她所呈现的历史,是小写的历史,是生活化个人化的历史。
一、生活之于艺术的介入
摄影师在《尾声·摄影师》中并不是故事的主角;它只占短短的三个段落,其中一个还只有两行。所以这个人物只是引子,或是隐喻,通过他,“我”要引出真正的主题,也就是关于艺术创作的话题。如此,这个故事可以被视作“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在故事里,摄影师的相貌充满了“邪恶的流动的能量”。他拍的照片,有着令人惊悚的变形效果,“在他拍的照片中,人们看到自己衰老了二三十年。中年人在面部特征里看到与他们死去的父母可怕的又不可避免的相像;年轻鲜活的女孩和男人现出他们五十岁时才会有的憔悴、呆滞、笨拙的面目。新娘子看起来好像孕妇,小孩则如同患了腺状肿疾病。”[1]显然,摄影师拥有可以刺穿当下生活表层的创造神力。
在此意义上,摄影师的作用很像作家。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摄影师是作家的隐喻。因为作家虽然关注生活的表层,但是生活的表层仅仅是他写作最原始的质料,他还需要对此进行深度加工,包括删减,变形,重构等等,使熟悉的生活读起来不再为人所熟悉,用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话说,就是要创造出“陌生化”(defamiliarzied)的效果,以给读者全新的思考和体悟,但是读者依然会感觉到这样的效果非常真实。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两种真实,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对于作家而言,艺术真实的重要性远远胜过生活真实,就像黛尔所言,“关键的是它对我是真实的,不是真的但却真实,仿佛是我发现而不是编造了这样的人物和事件,仿佛那个城市就紧贴在我每天穿行其间的这个城市的背后。”[1]PP281-282作家的功力主要就在于他将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能力。
那么,如何将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呢?在《尾声·摄影师》中,成长中的青年小说家黛尔以她自己创造小说的个例来阐释这个问题。她把在生活中听闻的悲剧性家庭故事改头换面加工成“我把他们的姓改成霍洛维,死去的父亲由店主改为法官……我照原来的样子写那位母亲,和我在圣公会教堂看见她时一样,她风雨无阻,憔悴而庄重……我把他们搬出他们一直住的芥末色灰泥粉刷的平房,搬到我自己虚构的房子里。”[1]P278除了改写故事情节本身,“我”还改写故事发生的环境,“在这本小说里,我也改写了诸伯利,着重选取了一些特点,对其他的则予以轻描淡写。它变得更古老,更黑暗和腐败,充斥着没有粉刷的木板栅栏、破烂的马戏团海报、破落的市场、一直起起落落的选举。”[1]P281此外,“我”还对原有的生活素材进行增加或删减:“在我的小说里,我去掉了长子,那个酒鬼。”[1]P279怪异且腐败的环境,怪异的人,就这样一部哥特式作品呼之欲出。诸伯利单调乏味的生活,经“我”处理后,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经过这样变形后的作品,由于打上了“我”的鲜明印记,和原始质料已经相去甚远。
林林总总的生活为什么会触动黛尔的创作冲动呢?这也是作家的创作动力学问题。首先是她对市政厅图书馆没有合适她读的书这种状况不满足。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艺术是人原始欲望(主要是性欲)不得满足后升华产生的结果。对性的不满足可以通向艺术作品的创造,同样,黛尔的不满足促使她决定要写出自己的书。写出自己的书(虽然在故事结束时,“我”的书还没有完成),是黛尔经过整本小说集中所有故事的塑造和滋养后而最终成为青年小说家的初步体现。无论怎样的经历,日后都变成了养料,成了她写作时可资利用的宝库。“我”的妈妈,班尼叔叔,范里斯小姐,弗恩·道夫提,杰里·斯多利,克雷格叔叔等等重新出现在《尾声·摄影师》中,通过这些人物,她更好地懂得了自己;通过《洗礼》等故事中的性,她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欲望,更好地理解了男人,从而成功地超越了性,超越了男人。她在那些故事里介入,又成功地超脱出那些故事之外,这种方式让她获得了极佳的写作立场。当她从介入走向超脱,也就从生活走向了艺术。刘再复在《文学常识二十讲》中认为,真实是文学的第一天性,超越是文学的第二天性,“文学创作既要把握现实经验,又要超越现实经验。”[2]但是,她的书写不同于克雷格叔叔男性视角下的历史书写。在她的故事里,见不到大写的历史,也见不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的只是她以独特的方式对生活中平常人的关注。她书写的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是历史的个人化。
在这个故事里,黛尔通过她的亲身经历,给读者展现出一种思考问题的别样视角。从精神病院回家的博比·谢里夫,在她的叙述中,读者无法看出其精神病的任何迹象,这引起了人们对精神病崭新的思考。广而言之,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其实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种开放性一直是门罗小说的特色。在《理性的崩塌:艾丽丝·门罗的缺席话语》中,赫贝尔就指出,“在门罗的小说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确定的。”[3]比如,门罗小说的结局就基本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向着生活广阔的可能性敞开。《尾声·摄影师》的结尾是,“‘好的’。我说,没有说谢谢。”[1]P288“我”想当然地接受了博比·谢里夫对我的好意,至于为什么想当然,“我”并没有交代。而且,他对“我”的好意是什么,“我”并无法弄清楚,“这个动作,伴随着他优雅的微笑,似乎是一个笑话,与其说和我分享,不如说为我表现,它似乎有一个简明的含意,程式化的意思—一个字母,或一个单词,在我不认识的字母表里。”[1]P288生活并不是一眼望去可以看穿的平面,而是平面下有深渊,是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触摸得到的。在这里,生活的复杂性超越了文字的表达力。文字,不管经过怎样的组合重构设计改造,都无法覆盖到这谜一样的深渊。这让黛尔感觉绝望。如此看来,她之前关于艺术真实大于生活真实,艺术比生活更加复杂的观念又不得不被暂时地搁置了。原来最复杂,最深邃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本身。生活里有太多的神秘,任凭人通过怎样的方法能力,都无法探测到它的深处,就像精神病患者博比·谢里夫那样。在他和“我”那段时间的交流接触中,他条理清楚,彬彬有礼,看不出有任何精神病的征兆。但是,他又是确定的精神病患者,其中的奥秘在哪里?“我”无法明白。既然生活深不可测,那么怎样的文字才能涵括得了这样的“黑洞”呢?对于作家而言,剩下的唯有遗憾,“对这些任务的准确性的希望是疯狂的,令人心碎的。”[1]P287
可以看出,在“我”走过很长的路(整本书所有的故事)后,终于在思想上变得独立。当母亲说“这个城市流行自杀”时,黛尔说,“很长时间我都记得这个神秘而独断的说法,信以为真—相信诸伯利比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自杀。……后来我对母亲所说的一切的态度变得怀疑和鄙视了。”[1]P277“我”超越了母亲所代表的成人世界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在男女关系中,“我”也有自主的意志,超越了传统男权社会所要求的女性形象。“我”和曾经的男友杰里·斯多利渐行渐远:他对文学没有任何兴趣;但文学却是“我”生命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我”丝毫没有打算屈从他的意思。“我”也超越了克雷格叔叔把詹肯湾以大写的历史进行书写的方式;“我”感兴趣的是书写普通的生命和普通的生活,是小写的历史。这是“我”个人化的历史观。“我”终于从生活的介入者上升到旁观者。这一路的成长,也就是“我”的思想从“我”之中剥离,以超然的姿态,去观察自己观察生活的过程。艾丽丝·门罗在谈到她的《一盎司的药》时,提到故事的叙述者“超越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从自己故事的参与者成长为一个旁观者(gets out of what had happened to her by changing from a participant to an observer)。”[4]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尾声·摄影师》中黛尔的成长轨迹。
在《尾声·摄影师》中,黛尔也对小说的价值做了初步的思考。小说除了是对生活的思考和提升外,它还有一些实际的功用。比如,它可以作为人和世界和生活对抗的中介。当杰里·斯多利对我的爱好不屑一顾时,“我”就回到“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中,“感觉好些了;这似乎让他所说的话变得不重要了,即使是真实的。”[1]P279当杰里·斯多利和黛尔一起在高架桥上散步的时候,从桥下经过的他们班同学对着他们按喇叭,但是他们想不到,“我”在小说中会“把他们置于怎样的危险之中。”[1]P282
在小说中,经过“我”各种艺术手法的调配后,生活素材原初的模样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形,但是生活还是原封不动地在那儿,这让“我”讶异不已,“马里恩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卡罗琳发生了什么事。当他停止烤蛋糕回到精神病院,博比·谢里夫又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小说怎样,这些问题不断重复。当你巧妙而有力地处理完事实的时候,回来发现它们还在那里,这让人震惊。”[1]P285生活有自己的逻辑,并不会因为艺术对它的改造,就俯首称臣,“马里恩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句加粗,说明生活还会时不时地侵入艺术的领地,嘲弄艺术的有限。无论艺术家的技艺如何高超,生活中总有些地方是艺术无法涵括无法洞穿的。艺术世界里的条理性和秩序感,一方面是对生活复杂化的处理;另外一方面,也是对生活简单化地对待。这正如批评家阿杰·赫贝尔在《理性的坍塌:艾丽丝·门罗关于缺席的话语》中精辟论述的那样,“虽然门罗因为语言能够反映世界的可能性而被深深地吸引,但是她也痛苦地意识到写作永远无法完全地捕捉到真实的生活。”[3]P23
故事结束时,黛尔的小说还没有完成。虽然她已经能够对小说创作的诸多方面发表初步的思考,但是还不完善,因而还不能算是成熟的小说家。此时的黛尔有些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斯蒂芬。《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是门罗的第二本小说集,发表于1971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加拿大民族主义的高涨,加拿大人开始对本国文学和本国文化充满了热情。在这种语境下,门罗的作品进入了更多加拿大人的视野,成了一个冉冉兴起的文学新星。显然易见,写出《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时门罗的状态也是《尾声·摄影师》中黛尔的状态。《尾声·摄影师》中已成为青年艺术家并且对艺术创作有了自己独特理解的黛尔,也是彼时作家门罗本人的写照,所以这里可以感觉出一种“深层意义上的,更根本的(a deeper,more essential,level of autobiography)传记的感觉。”[4]P254黛尔关于写作的这些见解通过《尾声·摄影师》展开,所以虽然有看似理论的内容,但是读起来并不会觉得枯燥,这也和门罗相似。她对文学批评家一直持保留态度,这也很可能是她为什么要在故事中让黛尔自然地呈现出她对小说创作各个方面的理解。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因为对黛尔这个青年女作家成长之路的呈现,使得它成功地汇入到西方文学成长故事的传统中。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再来看小说的题目,《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可以理解为 “我”如何从女孩成长为有鲜明个性和独立思考的青年女作家,在成长的过程中,亲情,友情,爱情,性等都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种的经历如何变为她日后小说创作的质料,再经过她的艺术加工,最终以艺术的真实呈现出了丰富且复杂的生活。它也可以理解为女孩们和女人们的生活画像,比如“我”,“内奥米”,比如“母亲”和“弗恩”等,是青年女作家描摹出的女性群像,展现出不一样的女性风貌,她们不依赖男性,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们也从不同的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成长。
二、艺术之于生活的超脱
理解作者的创作技巧对理解故事同样重要。著名文论家马克·肖勒(Mark Scholler)在《技巧的探讨》中认为,“现代批评向我们表明,只谈论内容本身绝不是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身时,我们才是批评家。内容(或经验)与完成的内容(或艺术)之间的差距便是技巧。”[5]在这篇文章的另一处,肖勒又说,“技巧是作家用以发现、探索和发展题材的唯一手段,也是作家用以解释题材的意义,并最终对它做出评价的唯一手段。”[5]P33《尾声·摄影师》这个作品呈现的方式也表明黛尔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青年小说家。首先,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故事贴着女主人公叙述。因此,黛尔看不到的,她不明白的,作者也没有替她交代;她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比如,弗恩·道夫提和内奥米都说马里恩是因为怀孕,才自己走进了瓦瓦那什河。但是“我”的母亲并不认可这一说法。最终的真相是什么,作者并没有给出,因为“我”也没有确定的答案。至于博比·谢里夫这个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在他和“我”的交往中,他温文尔雅,话语逻辑清晰,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病的征兆。至于个中缘由,“我”最终也不明白,“他对我甜甜地微笑,有理智地谈话;他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吗?疯狂一定有某种秘密,某种天赋的成分,某种我不知道的东西。”[1]P286此外,因为故事中有很多意识流式的自由联想,所以故事在叙述过程中会时而显得突兀,读者会感觉跟不上叙事的发展逻辑。比如,“我”上一段还在讲博比·谢里夫正在给“我”讲老鼠不吃面粉的事,而在下一段没有任何过度的情况下,就写到“十点钟银行开门,对面街上的加拿大商业银行和自治银行的状况。十二点半,公共汽车经过城市,从伦敦的欧文湾向南开。如果有人乘车,海因斯饭店前会挂起旗子。”[1]P286接下来的一段又接着说老鼠和白面粉的事情。罗素说,“情感的联结很少能够和外界的秩序相符合,它使我们用自身状态作镜子去看宇宙,忽而光明,忽而黑暗,全视反映的心态而定。”[6]情感世界如是,意识世界亦如是。它就是一条无序的河,四处奔腾,它是生命的奔流,无法用线性的理性逻辑来框定。
汤拥华先生在《文学批评入门》中认为,小说中的聚焦可以分为内聚焦和外聚焦,“内聚焦则是集中于某个人物,尤其是他的内心活动;外聚焦则是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某个人的外在表现。”[7]《尾声·摄影师》读罢,读者会感觉关于“我”和博比·谢里夫之间的故事,作者采用了外聚焦的写作手法,“站在故事外看”,无法走进人物的内心,所以“我”无法明白看似如此正常的博比·谢里夫为什么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不仅“我”看博比·谢里夫是如此,作为叙述者的“我”看作为故事中人物的“我”,也是如此。“人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奉献,是我想当然接受的东西,令我有点儿心烦意乱,似乎它们从来就不是我应得的。‘好的’我说,没有说谢谢。”[1]P288外聚焦使用的一个效果就是塑造超然的人物,上面的引用中,读者完全感觉不到“我”的情绪,一切都是冷静和理性,典型的“旁观者”态度。作家只有具有超然的态度,才可以把自己从纷繁的生活中超拔出来,重构来自生活的各种质料,最后以艺术的真实呈现出经过深度思考过的生活。从第一篇故事《弗莱兹》中的小女孩到最后这篇故事《尾声·摄影师》的青年作家,“我”终于从所有的故事中走出,站在一段距离之外和之上,以旁观者的态度观察那变动不居的生活和那生活中的众生(也包括“我”自己)。
《尾声·摄影师》是整部小说的尾声,这里,青年小说家黛尔初步长成。她过往所有的经历,都已化成她创作的质料。她把一部分的自己从自己身上成功地剥离,完成从生活的参与者到生活旁观者的蜕变。现在的黛尔,拥有摄影师一样的魔力,用她的作品反映生活,超越生活,刺穿到生活深处一部分的深渊。说是一部分,因为从故事中读者知道,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可能性,生活深处黑色的奥秘,远非任何故事可以完全地涵括。尽管如此,相对于整本小说,这个故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所有故事起始的地方。有了对《尾声·摄影师》真正地理解,理解了小说家创作的诸多方面,读者就可以更好地阅读这部小说中其他的故事,看清楚每个故事为“我”向作家的长成贡献出了什么要素,以及贡献的方式。比如《弗莱兹路》中的班尼叔叔,他对生活中怪异事物的高度热情,“把孪生女孩喂给猪吃的父亲;一妇女生出猴孩;疯狂僧人在十字架上强暴处女;邮寄丈夫残骸”等等。如果读者率先读完《尾声·摄影师》,那么黛尔对生活中涌动的暗流之热情就可以看出班尼叔叔的影子。张磊在《崛起的女性声音—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中认为,班尼叔叔是“黛尔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导师,对她未来的艺术之路有深度启发。”[8]再如故事《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的张伯伦,他在黛尔面前展示自己的私处,但是一直渴望得到性欲满足的她在那一瞬间却认为“那家伙猥亵而蠢笨,颜色像伤口一样丑陋,让我觉得脆弱和幼稚,像长着突出的长鼻子的动物,奇形怪状的单纯样子反而是善意的保障。(和通常意义上的美相反。)它没有唤起我的兴奋。它似乎和我毫不相干。”[1]P195戴尔在突然之间就可以把自己拉出欲望的泥潭。如果了解了《尾声·摄影师》中对作家超越性的强调,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时刻引向黛尔超越性的养成。表面看来,《摄影师》似乎和小说题目《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关系并不太大,但它确实是一个核心隐喻,展示出青年小说家黛尔对小说创作过程的理解。它和整部书的关系看似疏离,也让门罗在出版这本书时,对于要不要将它包括在内,举棋不定,“写这整本书。然后我决定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又想把它(《尾声·摄影师》)拿掉。……然后我又重新写了它(《摄影师》),又把它放进去。”[4]P254可以看出门罗最终对它的重视。
结语
《尾声·摄影师》呈现了黛尔对自身创作过程和生活原初质料之间关系的阐述。通过这个故事,读者可以看出黛尔在走过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诸多的故事后,终于得以从介入生活的状态中超越出来,借用特定的创作手法,重新加工来自生活的质料,最终成功地超脱了生活本身,创造了艺术的真实。黛尔的书写,从本质上说,是历史的另一种书写。这里的历史不是克雷格叔叔大写的小镇历史或者家族历史。这里的历史是宽泛的历史,生活化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个性化的历史,是对传统上由男性社会界定的法则的否弃,“我们所说的历史未必总是特定的历史事件,更多的时候是指与作品发生着‘历史关联’的‘外在世界’。”[7]P278在黛尔的笔下,历史终于从大写的人走向了普通人,从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高在上走向了烟火气十足的生活。而这一切,都在黛尔从介入到超脱的过程中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