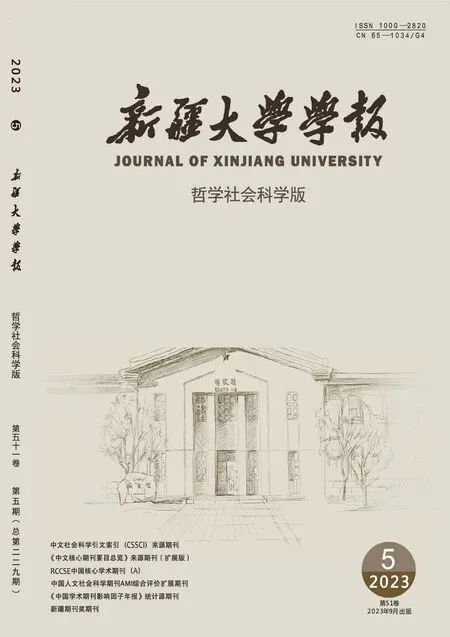突厥菴罗之可汗号商兑
——基于历史语境的考察*
2023-09-13雒晓辉
雒晓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可汗是四世纪以后北亚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每一个可汗都有修饰性称号,这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可汗号与可汗称谓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每一个可汗都有专属于他的可汗号。①参见罗新《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7页。菴罗,是突厥第四任大可汗佗钵的嫡子,在佗钵之后一度继任大可汗。由于突厥汗国的内部争执,不久便让位给堂兄阿史那摄图,即沙钵略可汗,菴罗则降居匈奴故庭所在的独洛水(今蒙古国土拉河),成为突厥汗国中押领九姓铁勒的北面可汗,由此汉文史籍中产生了关于其北面可汗封号的争驳。
以成书于唐初的《北史》和《隋书》为肇端,出现了“第三可汗”和“第二可汗”的两种记载。基于“三”和“二”在字形上的相近,显然两者之间定有一方存有讹误。
《隋书》之后的《通典》《册府元龟》等唐宋官修政书、史册大都支持“第二可汗”的说法,然而只有《资治通鉴》的“胡注”给了“第二可汗,言其位次沙钵略也”[1]5450的解释。近代已降,专擅朴学的岑仲勉仅将此事概述为“《北史》九九作第三可汗者误”[2]等寥寥数字。换句话说,“第二可汗”的说法虽广为众采,②参见林幹《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页;刘学铫《突厥汗国》,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3页。却始终缺少翔实且合理的解释。
基于北族向日崇拜的习俗③参见汤惠生《北方游牧民族萨满教中的火神、太阳及光明崇拜》,《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87-93页。,以及多位东面可汗继位大可汗的史实,有学者认为,在突厥汗国中,统押契丹、奚等东胡族系的东面可汗乃是约定俗成的储君,类似于匈奴的左贤王,是象征“副王”的“第二可汗”,而依此位序推排,北面可汗即为“第三可汗”。④参见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作为系统性地辩驳“二”“三”差异的观点,此说法不仅被部分学人认可,⑤参见包洪军《前突厥汗国分裂与灭亡问题探微》,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8页。甚至被《中国历史百科全书》⑥参见徐寒《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卷6《民族民俗卷》,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和时下的通俗史学⑦参见柯胜雨《丝绸之路千年史——从长安到罗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5页。所采纳。
在先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还原历史语境,结合突厥汗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漠北地缘政治关系,对此上两“说”进行考论,以求证于方家。
一、突厥“储君”与“第三可汗”的位序
“第三可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北史》,同时也只见于《北史》。换言之,在传世的相关汉文史料中,《北史》“第三可汗”的记载乃是孤例,其曰:
他钵病且卒,谓其子菴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及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菴罗实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中曰:“若立菴罗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摄图长而且雄,国人莫敢拒,竟立菴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罗,每遣人詈辱之。菴罗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子,摄图最贤。”因迎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居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三可汗。大逻便乃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3]
自第二任大可汗科罗以后,在突厥的汗位传承中,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业长时期交叉并存。①参见肖爱民《试析突厥汗位的继承制度——以前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为中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第55-60页。以兄终弟及式上位的第四任大可汗佗钵,面对“四可汗子”的血亲群体(参见图1),认为第三任大可汗木杆的长子大逻便是最合适的汗位继承人。其一,在佗钵可汗看来,其兄木杆不仅是突厥汗国崛起的英雄式领袖,也是一位顾念亲情的好兄长,促使他在情理上做出了还位于侄的抉择。其二,相比之大逻便的骁勇善战,佗钵深知己子菴罗性格懦弱,即使继位也压制不住“四可汗子”的争竞乱局。是故,在临终时抛开菴罗,指定大逻便为汗位继承人。然而,佗钵可汗的另一侄子摄图却公然联合“国人”,以大逻便“母贱”为由,违背佗钵遗命,推举菴罗为大可汗。

图1 突厥汗国前期大可汗世系②参见劳心《东突厥汗国谱系之我见》,《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58-63页。
窘于“四可汗子”并立的局面,菴罗可汗既不能在实力上压服大逻便,也不愿接受摄图的政治扶植,故而将大可汗之位再次越过大逻便,让给摄图,即突厥的第六任大可汗,史称沙钵略可汗。从反对大逻便,到扶植菴罗为自己进身的过渡,不难看出摄图对大可汗的位置早有觊觎。然而要坐稳大可汗的位置,摄图不仅要妥善安置好先可汗遗命中的法定继承人——大逻便,同时也要在地位名分上给主动让位的菴罗以政治补偿。
作为游牧政权一贯遵循的政治传统,“两翼”“三方”“四面”③参见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9-131页。等分区治理的方式,是游牧帝国在急速的领土扩张下常用的一种地方统治制度,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分封制。④参见肖爱民《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以匈奴、突厥、契丹、蒙古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页。爰至摄图为大可汗时,突厥汗国已存有东、西两面小可汗。为消弭因汗位更代而产生的政治危机,摄图再次继续分封大逻便和菴罗为小可汗,其中以菴罗为押领九姓铁勒的北面可汗,建牙帐于匈奴单于故庭所在的独洛水。基于制衡东西面可汗和经略汉地的需要,漠南和中部区域一直都是由大可汗执掌,故而沙钵略只得将突厥的发源地——金山(阿尔泰山)封给大逻便,①王譞认为阿波可汗的牙帐应在天山东北麓的可汗浮图城,参见《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历史研究》,1982 年第2 期,第17-36 页;而松田寿男、段连勤认为阿波牙帐在于都斤山西北,原突厥汗国的金山旧牙,即清代科布多辖境;参见〔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年,第298 页;段连勤《关于西突厥与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论著选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5页。让其成为东、北、西三面可汗之外的小可汗,称阿波可汗。
至此,算上摄图(下文中称沙钵略)这个共主,突厥同时出现了五位实力强横的大小可汗②隋文帝开皇时期,突厥汗国内共有几位小可汗,相关研究论述不一;其中以“有七位大小可汗”的说法为主流,但实力较强的则上述五位;可参见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见图1),其中西方的达头可汗和阿波可汗,不仅在地缘战略上相互衔接,而且在反对沙钵略、自为大可汗的政治倾向上,也联盟互应。所谓“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4]1330,从而为隋朝对其实施离间分化策略提供了基础。
在沙钵略为大可汗之后,其弟处罗侯代为东面可汗,后又以东面可汗的身份继大可汗位,称莫何可汗。莫何可汗亡后,又以东面可汗雍虞闾继位,称都蓝可汗。结合匈奴以东方左贤王为储君的传统,有学者认为东面可汗即是突厥汗国的储君,应称之为“第二可汗”。按照游牧习俗中,北方低于东方,西方又低于北方的位序推排,北面菴罗可汗即为“第三可汗”,西面达头可汗则为“第四可汗”。③参见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但事实绝非如此。
首先,东面可汗并非是突厥政权组织中的固定化储君,只不过是在诸方面小可汗中,即位人数最多者。在大可汗之下的诸多小可汗、设、特勤中,东面可汗押领的部落最为特殊,是异于铁勒族属的东胡系部族,是以汗国初期常以年长有能力的汗族子弟担任东面可汗,例如沙钵略即是“四可汗子”中的年长者,因此也就出现了个别时期东面可汗权重势强的局面。也就是说,权重势强的境况并非是基于制度的加持,更多的是得益于东面可汗的个人经营。
相比之东面可汗的强弱不定,匈奴左贤王的“位尊权重”在单于之下的二十四王将中乃是常态化的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单于多是由左贤王继承,也正因如此,单于也多将心目中的继承人封为左贤王。然而,无论是匈奴,还是突厥,其游牧民族的特性,即游牧、征伐、掠夺等客观环境都要求首领必须是一位强有力的、有威望的领导者。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北方游牧政权中很难出现类似于中原王朝的固定式储君。④参见肖爱民《试析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3期,第33-36页。相较于匈奴政权中父死子继的主流形式,突厥自土门可汗之后,实则是兄终弟及与子承父业交叉并存,突厥大可汗也就很少有目的性的册封继承人为东面可汗。易言之,以东面可汗比拟匈奴左贤王,只是基于所处方位的相同,而缺少实质性的共同点,属于模糊化的类推。
再者,比之匈奴政权为集权而施用的“二十四王、将制度”,突厥大小可汗的分统制度更为松散,其立国的思想基础,是整个阿史那氏族共同拥有汗国的氏族性观念。⑤参见〔日〕護雅夫《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苍き狼の子孙たち》,東京:讲谈社现代新书,1967年,第78-118页。基于这种制度与观念的惯性,诉诸在汗位传承时,也就更加重视继任者的个人(部族)实力。按照佗钵可汗的遗命,菴罗既然要让位,大逻便无疑是最合乎法理的人选,而最终获得汗庭核心成员支持的,确是部落实力强大的沙钵略。此前大逻便敢于在各种场合辱骂菴罗,却不得不接受沙钵略的赐封,以表示臣服,其中前倨后恭的态度差异,所映现出的正是各自实力的对比。
至于沙钵略为抵制大逻便所联合的“国人”,乃是汉文史料中的模糊式记载。这里的“国人”并不是对普通百姓的概称,而是指在突厥汗国中拥有“决定战、和、可汗继位人选以及各种重大问题”[5]的蓝突厥族属。这种蓝突厥族属组成的贵族会议,诉诸在选举领袖的形式上,类似于后世蒙古帝国的库力台大会。事实上,无论是突厥汗国,还是之前的匈奴、之后的蒙古,在“选”的过程中,所凭恃的还是各方实力。而这也恰从侧面佐证了突厥的东面可汗,以及匈奴的左贤王,在崇尚英雄的游牧族群中从来都不是固定化的王储。简而言之,作为部落联盟的突厥汗国,虽然王权集中在阿史那氏一族之中,呈现出家天下的形式,但在传位的具体方式上,“世选”的程度明显要高于“世袭”。
其次,诸多东面可汗成功入继大可汗位,也并非是基于储君的政治地位。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就是沙钵略本人。佗钵可汗在临终时,先是嘱咐菴罗不要争位,后又命定大逻便为继承人,却始终没有考虑过、甚至提及到时任东面可汗的沙钵略。而沙钵略的成功上位也是基于其一系列的政治运作,而并非是已定的储君地位。至于此后的处罗侯和雍虞闾继位大可汗,或是出于时势所逼,或是得益于个人的才具出众。
处罗侯,即莫何可汗,是沙钵略的亲弟弟,也是突厥诸多小可汗中唯一支持和始终追随沙钵略的方面可汗。在隋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4]1331的分化离间下,阿波和达头联合反对沙钵略,并在之后的交兵中占据漠北的于都斤山汗庭,迫使沙钵略迁至漠南、向隋朝称臣。在隋朝和突厥强弱易势的大背景下,处罗侯则成为突厥在漠南存国的关键性人物。其一,处罗侯的东面可汗牙帐就在幽州以北七百里的漠南地区,统押奚、霫等东胡族系,实力强劲,是沙钵略的军事依靠之一。其二,处罗侯本人勇而有谋,早在五可汗并立时代就能曲取众心,为“国人所爱”[1]5451。其三,处罗侯还是突厥汗国中的少数亲隋派,一直负责监护突厥工作的隋将长孙晟便是其早年的结拜兄弟。①参见李延寿《北史》卷22《长孙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7页。就现实局势而言,无论是实现规复漠北、平定阿波可汗的长远规划,还是短期内立足漠南、保持大可汗名号,南迁后的突厥都离不开隋朝的支持和庇护,而综合诸多考量,处罗侯无疑是沙钵略之后最合适的大可汗人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沙钵略,还是处罗侯,乃至是雍虞闾,之所以能继任大可汗位,都不是基于东面可汗的储君地位。
概言之,相比中原王朝强化下的中央集权,突厥所建立的游牧汗国在组织结构上要松散许多,以东西两翼制度为基础而演化出的大小可汗分治的地方统治方式,虽有利于管辖帝国急速开拓的领土和部众,但也加剧了内部的离心倾向。表现在汗位传承上,即没有约定俗称的储君,遵循的乃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即胜者为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突厥东面可汗并不是象征“副王”的“第二可汗”,而北面可汗也就不是次序相承的“第三可汗”。
二、“双中心”的地缘格局与示尊崇的“第二可汗”
自柔然汗国以可汗作为政权组织中的元首以来,无论大小可汗都有属于彼此的修饰性称号,这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如同大逻便的“阿波”封号,就是取其形义相近。《通典》解释“大逻便,酒器也,似角而麤短,体貌似之,故以为号”[6],而“阿波”则音译为aba,其义为“有熊”,阿波可汗即为“骁勇剽悍的可汗”。
关于菴罗可汗号中的“第二”或“第三”,史载与碑铭中始终未见有突厥语的音译。也就是说,传统史家对于二者的辨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以沙钵略继承汗位的最终结果,属于汉文史籍中的推定式书写。因之,可汗号“第二”也就比“第三”更贴近汉家史官的初衷。
诸史载中,关于菴罗获封为北面可汗的原因并无二致,皆是出于菴罗的主动让位和沙钵略对其政治位分的弥补。《隋书》记载:
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复捨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菴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竟立菴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罗,每遣人骂辱之。菴罗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之子,摄图最贤。”因迎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4]1864-1865
相比《北史》,《隋书》多了沙钵略曾任东面可汗的记载。沙钵略成为突厥的共主,是在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下实现的。基于汗位传承的政治世系与合法性,以及“尚贵种”的北族传统,决定了沙钵略必须要尊崇菴罗、打压大逻便。而大逻便不仅是木杆可汗的长子,同时也是佗钵可汗的遗命继承人,更兼个人骁勇、部落实力强横,是以沙钵略在东西北三面可汗之外,册封其为统合金山祖地的阿波可汗。而对于主动让位的菴罗,沙钵略在分封其为北面可汗的同时,只能在政治名号上尊崇其地位。
首先,抬高菴罗的政治名分,可以让沙钵略掌握压制达头和阿波的政治大义。仅就实力而言,西面达头可汗是五可汗中实力最强的存在,沙钵略若是以亲弟弟处罗侯为“第二可汗”,按位序以菴罗和达头为“第三”“第四”可汗,无疑会给达头及其部下以离心的名义和反叛的借口,因为达头本就对大可汗的位置虎视眈眈。开皇元年(581)长孙晟在建议隋文帝对突厥实行离间分化时,认为其计策实施的成功基础,就是达头与沙钵略的名实不符,以及达头的个人野心,其言曰:“玷厥(达头)之于摄图(沙钵略),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4]1330换句话说,并立的五可汗中,达头和阿波已在明里暗里与沙钵略对立。若是再压制菴罗,抬升自己的弟弟,沙钵略不仅会在实力上落于下风,甚至连继位的政治名义也将失去。是以,沙钵略可以将原属于自己的东面可汗给予处罗侯,但在政治地位上必须尊崇菴罗,将其抬升为仅次于自己的“第二可汗”[1]5450,借此在政治大义上压制达头、阿波二可汗。
其次,从地缘位置来看,菴罗降居独洛水乃是与沙钵略东西分据漠北,体现出了“第二可汗”在政治名分上的尊荣。漠北是相对于漠南的地理概念,也称为“碛北”。史书中的“碛”和“漠”,在空间实体上,大致是指今天的外蒙古戈壁。其中戈壁北侧与贝加尔湖之间的鄂尔浑草原,便是早期突厥汗国的核心区域,①参见罗新《汉唐时期漠北诸游牧政权中心地域之选择》,载《王华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阙特勤碑》南3 及6—7行载:
只要突厥可汗在ötükän山实施统治,境内便无忧患……如果你们试图移居到南方的总材山区及吐葛尔平原,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7]
ötükän 山,即是于都斤山,位于鄂尔浑草原西南侧,②参见包文胜《古代突厥于都斤山考》,《蒙古史研究》第十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62页。与独洛水源头所在的狼居胥山,在地形上呈现出“倒八字”型分布格局,共同遮护起漠北的鄂尔浑草原,③参见〔美〕高菲池、张国平《打破鄂尔浑河传统:论公元840年以后黠戛斯对叶尼塞河流域的坚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97页。此外,由于连接漠南碛口的大漠南北通道也位于鄂尔浑草原的南端,④参见许程诺《唐李靖定襄道行军中所见“碛口”考释》,《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4期,第159-165页。因而漠北的鄂尔浑草原也就成为突厥汗国的中心地带。而近些年在鄂尔浑河流域先后出土的《翁金碑》《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阙利啜碑》等⑤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77-267页。诸多碑碣,无疑是此地曾作为政治核心区的有力佐证。
从政权组织所追求的稳定性来看,以鄂尔浑流域作为游牧帝国传统的中心地带,不仅可以满足突厥汗国发展的经济需求,也是其政治传统。就稳定性的具体呈现而言,游牧政权需要在“风水”优越的地方建立牙帐,甚至像中原王朝的都城一样,有一些固定性的建筑和标志,⑥参见宋国栋《回纥城址研究》,太原: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12页。而背山阻水正是建立汗庭牙帐的首要地理条件。其中,突厥大可汗牙帐所在于都斤山东南麓,既有山麓阻凭,同时也是鄂尔浑河的源头周近,是以这里先后成为薛延陀、回纥等汗国的汗庭以及蒙古帝国的都城(哈拉和林)。⑦〔俄〕Н.Я.梅尔皮尔特《哈拉和林的历史》,载〔俄〕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吉谢列夫《古代蒙古城市》,孙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2-137页。
在政治地理上,鄂尔浑草原东段端的独洛水流域,也是一处背山阻水的绝佳地区。独洛水是鄂尔浑的支流,发源于狼居胥山(今肯特山)的西南麓,在山水夹峙中的独洛水河谷中,不仅水草丰美,而且气温也较高于同纬度地区,同时更有狼居胥山作为军事屏障,阻隔室韦、靺鞨等东胡族系势力的威胁。是以,早在匈奴时代此处就成为单于的王庭。⑧参见〔日〕内田吟风《关于单于的称号及匈奴单于庭的位置》,载《北亚史研究》,東京:同朋舍,1975 年,第98-102 页;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第145-152页。仅就漠北游牧政权的建都(牙)传统而言,独洛水流域与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东南麓,实则是蒙古草原上东西往复、左右徘徊的两处政治中心。菴罗可汗在独洛水流域建立牙帐,恰好可与都斤山的大可汗牙帐东西分掌漠北核心地带,在地缘政治上形成大小相辅的“双中心”式格局。
再次,紧邻式的“双中心”格局与九姓铁勒势力的桀骜难治,菴罗之北面可汗虽享有“副王”的尊政治崇,但实则是充当大可汗镇抚北面铁勒的附属。换句话说,较之东、西面小可汗的独立性,菴罗的北面可汗对大可汗的依附性更强。《隋书·长孙晟传》记载:
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候),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4]1330-1331
文中“匈奴”是对突厥的代称,此不赘言。此段史料,但凡关注隋突关系的学者,无不熟稔。因为长孙晟针对突厥内部矛盾提出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不仅一举加促了突厥汗国的分化和瓦解,为隋朝皇帝赢得了“圣人可汗”[4]1873的尊号,同时也成为唐王朝初期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主要策略。①法国学者沙畹总结隋唐两朝对付突厥的策略,其言曰:“总之,中国始终用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政策,是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的要因。设无此种反间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之,数百年后蒙古之得势,可为例也。”载〔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4-195页;也可参见马大正《长孙晟述论》,《民族研究》,1985年第4 期,第46-54 页;崔明德《论长孙晟“离强合弱”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5 期,第73-76页。不客气地说,隋唐部分君臣对此策略都有些痴迷。
然在先贤时哲的诸多研究中,都忽视了此段材料中的两个细节。其一,在隋朝立国之初,沙钵略、达头等四可汗联兵南犯的大军中,为何独缺菴罗可汗?其二,长孙晟在分化、离间突厥五可汗时,为何选择阿波、达头,乃至于沙钵略的亲弟弟处罗侯,而不选择菴罗?按道理说,菴罗作为突厥曾经的大可汗、时下的“第二可汗”,比之其他三位小可汗无疑更有政治号召力。
关于“突厥南犯”和“隋廷外联”都不选择菴罗,是不是因为菴罗在此时已经去世了呢?不可否认,这种猜想也有可能,但可能性极低。佗钵可汗病逝,沙钵略最终出任大可汗,事在陈太建十二年(580);突厥四可汗联兵南下,事在陈太建十三年,即隋开皇元年(581),而长孙晟上疏离间突厥也是在同年。②“及突厥入寇,晟上书曰……。”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5450-5451页。如若菴罗去世,只能是在这一年之内。然而正值壮年的菴罗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去世吗?只能说可能性极低。
若就北面可汗的实际处境来看,作为统押九姓铁勒的北面势力,菴罗虽另立牙帐于独洛水的匈奴旧庭,在政治形势上,呈现出与大可汗东西分据漠北的“双中心”式态势,但在五可汗势力的整体格局中,独洛水牙帐又居于——传统东西两面翼护下的——中部大可汗的势力范畴内。如此一来,菴罗所居的北面可汗虽能够在政治名分上彰显出“副王”的尊崇地位,却因与于都斤山大可汗牙帐咫尺相邻,从而难以摆脱大可汗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威慑。加之,九姓铁勒的桀骜难治、屡伏屡叛,③参见钱伯泉《铁勒国史钩沉》,《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91-100页。又需要在军事上借助于大可汗的力量,是以菴罗代表的“第二可汗”势力范围也就在潜移默化间变为大可汗的附属。
总之,沙钵略在政治名分上尊崇菴罗,不仅有利于稳定因汗位传承所引发的政权动荡,而且在东西两面小可汗之外,设置一位北面可汗也有利于对铁勒诸部的镇抚,从而便于大可汗对南方汉地的经略。从开皇初年沙钵略、达头等四可汗南下攻隋,而独缺菴罗的史实来看,菴罗的北面可汗确是承担起了镇抚、留守的职责。反之,菴罗本人在性格上的软懦无主见、缺乏政治才能等弱点,则恰好符合沙钵略对汗国“副贰”的政治期许。综上,菴罗的可汗号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中更应当是《隋书》记载的“第二”,而非是《北史》中的“第三”。
三、小 结
《隋书》与《北史》中关于菴罗“第二可汗”“第三可汗”的记载,由于缺乏底本和善本的校雠,难以确认在抄写过程中“谁”是讹误。然而,基于上文的梳理和论证,大致可以推定:
一是结合《通鉴》胡注对“第二可汗”的解释,可知汉家史官并不熟稔北族可汗号中“生称谥”①参见罗新《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7页。的政治传统,是以汉文史籍中相关菴罗可汗号的“第二”“第三”等不同称谓,都不是源于突厥语的音译,而是修史者对菴罗退位,沙钵略给予其政治名分补偿的推定式书写。
二是在突厥汗国的政权组织中,没有约定俗称的“太子”之设,是以东面可汗也就不是象征储君的“第二可汗”,而依此位序推排的北面可汗也更不是“第三可汗”。
三是沙钵略为压制西面达头可汗和阿波可汗,需要尊崇菴罗的政治地位来彰显其继任大可汗的政治合法性,而名不符实的“第二可汗”更能符合大可汗之下的位次。
要之,就政治伦理和时势局面来看,“第二可汗”也确实比“第三可汗”更符合突厥政权内部的博弈纷争。相应地,《通典》等文献在记载关于菴罗的可汗号时,也就遵循“第二可汗”的说法。
总之,围绕着菴罗让位和沙钵略继任的纷争,看似以分封大逻便和菴罗为方面可汗而告终,从表面上看五可汗各得其所,但实际上却种下了矛盾和猜忌的祸根,成为日后突厥汗国内部分权、分势乃至分裂的内因。而同一时期,代周初立的隋王朝也正是基于五可汗间的矛盾,对之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分化离间策略,为新王朝稳固政权、统一江南赢得了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