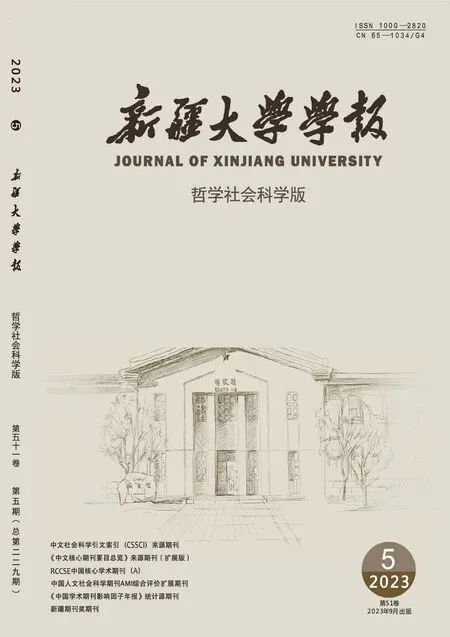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关系考论*
2023-02-24陈露
陈 露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他与钱大昕、王鸣盛等重要的汉学家既是同学,又是同年,彼此之间交谊甚笃。钱大昕称他“自为诸生,即负重名,诗词之工,纸贵吴下”[1]。就学术而言,王昶辑有《金石萃编》160 卷,被视为金石学的集大成之作。他曾受惠栋影响,讲求音韵训诂之学,名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分属汉学阵营。姚鼐则以宋学为尚,着力构建桐城文统,与汉学派争衡。尽管学术宗尚存在差异,但王昶、姚鼐二人自青年时代相识,保持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友谊。王芑孙将二人并举,称:“此事(指碑版创作)于当今几绝而勿绝者,赖公(王昶)与姬传数公之力而持之也。”[2]608-609可是到了晚年,王昶编纂文集时因刊落姚鼐所作《述庵文钞序》,引发后者不满,多年挚友,遂致交恶。王昶与姚鼐及桐城派的关系,也由此呈现出一种复杂面貌。
一、王、姚深交与晚年交恶
王、姚二人的交恶始于姚鼐为王昶文集而作的《述庵文钞序》。当时姚鼐主讲于钟山书院,收到王昶所寄《述庵文钞》,因“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发而读之,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3]61于是提笔作《述庵文钞序》。后来,王昶诗文集付刻,姚鼐请姚椿寄来刻本,却发现自己所作之序竟不在其中。对此,姚鼐感到十分困惑:“《春融堂集》得观极荷。鼐昔作《述庵文序》,今其集中乃不载。岂述庵以序内称誉之犹不至而不录邪?抑其后人择取而遗之邪?此不可解也。”[4]166《春融堂集》虽经王昶门生校勘,但篇目乃由王昶手定,因此,姚序被删削自是他有意做出的选择,而不会是因“其后人择取而遗之”。[4]166姚鼐揣测王昶刊落其序,原因或在于“序内称誉之犹不至”,[4]166从“犹不至”一语中不难体味,姚鼐对于自己序言被刊落一事,不仅十分困惑,同时更是万分不满。
经此之后,姚鼐对王昶的评价可谓一落千丈。在写给门人陈用光的尺牍中,姚鼐道:“顷见《王述庵集》,论子瞻诸铭在昌黎上。此何其谬邪。以此叹解人难得。时之为诗文者,多乱道耳。”[4]120《王述庵集》即《春融堂集》,亦即姚椿给姚鼐寄送的《春融堂集》刻本。在看到刻本之前,姚鼐已经收到过王昶寄来的《述庵文钞》四十卷①《春融堂集》包括诗集、词集、文集三个部分。参见王昶著,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春融堂集》卷首“前言”,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4页。故姚鼐应当先看到《春融堂集》的文集部分(即王昶寄送的《述庵文钞》),并为之作《述庵文钞序》。此处提及的《王述庵集》则是合诗集、词集、文集于一的《春融堂集》刻本(由姚椿寄送)。,并为之作序。姚鼐批评王昶“论子瞻诸铭在昌黎上”之内容见于《与朱竹君书》:“若夫行状、神道、墓志,文忠乃实胜韩”[5]598,所以,姚鼐实际上在写序之前便已读过王昶此论。而在写序之时,他依然不遗余力夸赞王昶,称“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3]61看到刻本后,姚鼐却一改往日态度,对王昶之论痛下针砭,甚至将之归入“乱道”之列,这不仅与序言中的夸赞之辞相互矛盾,也与五十年来二人的君子之交形成强烈反差。
据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回忆,他和王昶相识于京师。当时姚鼐二十四岁,王昶三十岁:“鼐少于京师识先生,时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独贵其才。”[3]61具体时间为乾隆十九年(1754),王昶入京参加会试,由此结识了同样因赶考而来到京城的姚鼐。从“心独贵其才”一语的追忆中不难想象,姚鼐对初识的王昶青眼有加,印象颇深。
那一年,王昶与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朱筠、沈业富等人同登进士第,姚鼐不幸名落孙山。之后,姚鼐计划还乡,与王昶相别于白衣庵,王昶写诗两首为之送别,道出二人的相交之情和对姚鼐的惜别之意,并以“名士从来多落拓”之语鼓励、安慰落第的姚鼐。同年秋,王昶应山东盐运使吴凌云之请,曾去往济南。从济南乘舟返京途中,王昶写了一组《怀人绝句》,内有一首表达对姚鼐的思念之情:
萧寺钟残夜漏迟,香销酒冷共论诗。蓟门皖水俱千里,肠断红亭送别时。[5]402
可以想见,王昶与姚鼐初识的乾隆十九年,应当是二人感情的“蜜月期”,因此,王昶才在乘舟途中回忆起姚鼐,诗集中才一再出现姚鼐的身影。至36年后,王昶再次给姚鼐赠诗:
绿槐高馆驻征舆,把臂相看更起予。六代江山依讲席,廿年风雨叹离居。性情恬澹先辞禄,经义纷纶早著书。闻道门墙多俊侣,莫教寂寞伴樵渔。[5]402
此诗题为《访姚姬传钟山书院》。据《桐城派三祖年表》,王昶到钟山书院拜访姚鼐并写下此诗的时间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这也与王昶集中《杏花春雨书斋集六》下自注的“己酉庚戌”时间相合(乾隆庚戌年为1790 年)。此时,姚鼐年届六十,刚刚主讲钟山书院不久①姚鼐曾两次主讲钟山书院,此时当为第一次主讲钟山书院期间。参见汪孔丰《姚鼐掌教钟山书院新论》,《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第59-62页。,王昶在处理完公务后,“独往江宁”[5]1167,拜访姚鼐。梳理二人的人生历程:乾隆十九年春,两人于京师相识。同年秋分别后,王昶去往济南,后返回家乡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之后辗转扬州、钱塘等地;姚鼐则滞留京师,后返回安徽桐城。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进士及第,授庶吉士;此时王昶在京任内阁中书之职。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昶随军西南,离开京城。据此可以推测,姚鼐及第后留京与王昶任职京中的这段时间,当是二人再度重逢并有所交往的时期,具体当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乾隆三十三年间。
此外,《访姚姬传钟山书院》一诗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王昶此处将姚鼐辞官解释为“性情恬澹”下的选择。然而,姚鼐入四库馆不到一年便辞官返乡,实际却和四库馆臣因学术宗尚差异而导致的龃龉有关②关于姚鼐辞官的原因,参见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二章《四库馆内:不称的颉颃》第五节《告退的主因》,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41-45页。。可见,王昶虽与钱大昕、纪昀、戴震、王鸣盛等著名汉学家往来密切,同时,他本人也热心参与金石学、考据学等汉学事业,但王、姚二人并未因此产生嫌隙,汉宋对抗的阴影也没有投射到这段友情中来。这在王昶《送张总宪墨庄先生若溎予吿南归三十六韵》③此诗收录于《杏花春雨书斋集二》,集下自注时间为“戊戌己亥”,可知此诗写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之间,此时距王昶从西南回到京师已经两年有余。一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张若溎是康、雍、乾三朝元老张廷玉之子,和姚鼐同属安徽桐城人。王昶在其送别诗中写道:“岁星可望不可即,安得接席闻舂容。忽忆吾友乞身去,读书学道兼畊农。”在“忽忆吾友乞身去”一句中,王昶自注此处“吾友”即“姚郎中姬传”[5]308。王昶写作此诗时已从西南回到京师,他在送别张若溎的诗中回忆起姚鼐,亲切地称之为“吾友”,并想象姚鼐辞官后“读书学道兼畊农”的生活图景,可见他对其辞官之事始终持以轻松欢快之笔调。自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五十五年,三十多年过去,两人始终保持着相敬相惜、不浓不淡的君子之交。
到钟山书院拜访姚鼐的四年后,七十一岁高龄的王昶获乾隆皇帝允准,辞官还乡。姚鼐曾作《为王琴德昶题泖湖渔舍图即送旋里》一诗赠别:
王郎昔居泖湖里,出户观渔并湖水。王郎今作《渔舍图》,纸上芦菰北风起……晓来网得淞江鲈,尊有清酒饭炊菰。芦帘纸阁夜飒飒,风雨坐伴青镫孤……拂衣归思向云闲。秋风夜火松陵驿,唯有渔人认客还。[3]410-411
泖湖渔舍亦称三泖渔庄,是王昶辞官后的家居之所。为《泖湖渔舍图》作诗的诗人多达数十位,姚鼐是其中之一。姚鼐在诗中细致描绘《泖湖渔舍图》之画面,想象王昶居于其中的情景,晓来网鲈,清酒炊菰,颇得子厚“晓汲清湘燃楚竹”[6]之神韵。此诗与之前王昶写给姚鼐的赠诗一样,充满着隐居山林的萧闲适意之感。此时,两人相识已逾四十余载,在面对彼此的时候,他们始终仿佛置身红尘之外。不论是初期论诗时的禅窗听雨,还是晚年辞官的题图赠诗,均体现出二人感情的纯净、不染杂质。一如《湖海诗传》小传中,王昶对姚鼐所作之评价:“姬传岂弟慈祥,而襟期潇旷,有山泽间仪,有松石间意。簿书刀笔,雅非所好也。诗旨清隽,晚学玉局翁,尤多见道之语。望其眉宇翛然,已知在风尘之表矣。”[7]103这样的关系,或许不能算作十分亲密,但至少可以说是令人愉悦、和谐融洽,两人对彼此的赏识,亦是显而易见。
王昶辞官返乡后,便着手整理自己的诗文集,同时为刊刻《湖海诗传》和《湖海文传》做准备。姚鼐对王昶及其名山事业一直无比关切。他曾多次致信姚椿,询问《湖海诗传》《湖海文传》及《春融堂集》的刊刻进展,并嘱托其“觅一部见寄”[3]293。姚椿是姚鼐的入室弟子,在拜入姚鼐门下前,曾游于王昶之门。王昶高度评价姚椿之诗,赞许为“他日中流当砥柱,此时大雅合扶轮”[5]484。姚椿编《国朝文汇》,曾借《湖海文传》以观,并在《国朝文汇》中选入王昶之文多达36篇。总之,姚椿与姚鼐、王昶两人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姚鼐曾提及姚椿给他寄送《湖海诗传》之事,并问及《湖海文传》的成书情况:“赐寄《湖海诗传》乃未至,不知于何处浮沉?述庵先生想尚健,其《文传》成书未耶?”在这篇书信中,姚鼐言及自己“顷自皖移来金陵,主钟山书院”[3]293。据汪孔丰考证,姚鼐第一次执掌钟山书院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五年(1800),第二次是在嘉庆十年(1805)至嘉庆二十年(1815)间。①参见汪孔丰《姚鼐掌教钟山书院新论》,《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第59-62页。《湖海诗传》刊刻于嘉庆八年(1803)②参见王昶《湖海文传》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页。,故此时当为姚鼐第二次主讲钟山书院期间。之后,姚鼐又一次询问姚椿关于王昶文集及《湖海文传》的情况:“闻王述庵有《湖海文传》,想未刻,足下见其钞本不?其文集当已刻。吾昔为作序寄之,然竟未得其刻本,幸觅一部见寄,《诗传》则吾已得矣。”[4]165此时,姚鼐已经收到《湖海诗传》,同时又表现出对《春融堂集》和《湖海文传》的强烈兴趣,他对王昶诸部著作的关切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在这封书信中,姚鼐提到自己曾为王昶文集作序,并请姚椿寄送《春融堂集》刻本。姚鼐所说的序言,即前文所述《述庵文钞序》,也是引发二人由相交终至相离的导火索。
回顾二人大半生的交游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姚鼐发现王昶《春融堂集》刊落自己的序言之前,两人关系始终非常融洽,这集中反映在他们对彼此的评价以及两人的赠诗中。《春融堂集》写定后,王昶还在给王芑孙的书信中称赞姚鼐:“姬传退居日久,心定神闲,涵养纯粹,发于文者,实得宋元间名家气韵,昶何敢望其肩背耶?”[2]609姚鼐在发现自己序言被王昶刊落后,他对王昶的态度便急转直下,再不复旧日烟月往还、相与论文之融洽。
二、“通儒”与古文家的冲突
面对姚鼐尺牍中对序言被刊落一事的诘责,姚椿及当事人王昶都没有给出回应。当代学者王达敏、蔡锦芳、漆永祥与蓝士英几位教授留意到此桩公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多从王昶的汉学家身份入手,认为王昶是出于对宋学的排斥,故而刊落姚鼐所作之序。因此序关联甚大,此处先将其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在序中,姚鼐申发了其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一的古文观念,认为文之至美在于三者兼收、相济:“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3]61而王昶之文则是兼具义理、考据、辞章之美的典范:“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先生历官多从戎旅,驰驱梁、益,周览万里,助成国家定绝域之奇功。因取异见骇闻之事与境,以发其瑰伟之辞为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谓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独异于人。吾谓此不足为先生异,而先生能自尽其才,以善承天与者之为异也。”[3]61
序中对王昶揄扬备至,称其善承天与,能自尽其才,创作成就达到人所未有的高度。王达敏从“三者兼具”的角度入手,认为王昶剔去姚鼐序文的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学贵专精,是汉学诸家普遍奉持的信念。王昶作为汉学名流,不以三者兼收为妥。二是王昶对姚鼐表彰自己之文做到了三者兼收不敢承受。三是姚序提出三者兼收说,有意与从戴震到孙星衍等汉学家争衡,令王昶不安、不快。”[8]177针对“学贵专精”一点,蔡锦芳提出异议,认为王昶对于古文创作并不奉“学贵专精”为圭臬,而是主张先师法百家,再自成一家。①参见蔡锦芳《清代学人王昶诗文述论》,董乃斌主编《文衡》2010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就此一点而言,王、蔡二家之说实际殊途同归。王达敏在“学贵专精”一条中引王昶“柳子厚论文戒杂。杂则断不能精”[8]194一语作为注释,这是从文章整体风貌出发;蔡锦芳所指王昶师法对象之广阔,却是从师法层面而言。前者着眼于约取,后者立足于博观,两者之间实际并不冲突,王昶和姚鼐在此一点上也不构成对立。此番解释虽有一定道理,却不足以令人信服。此外,蔡锦芳认为,王昶的衡文标准在于内容的有助教化和词章的峻洁清峭,这与姚鼐所持三结合之审美标准有一定出入,再加上姚序中所含对汉学考据家之排斥,自然也会为王昶所不喜。②参见蔡锦芳《清代学人王昶诗文述论》,董乃斌主编《文衡》2010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王、蔡之说虽有不同,但二人均坚持王昶的汉学家身份是致使此段公案发生的缘由之一。然而,对比《春融堂集》中所采用的法式善之序可以发现,姚序中所谓“对汉学考据家之排斥”并不能成为王昶刊落姚序的理由。因为相比姚鼐,法式善之序对汉学家的批评更为直截刻露:
文章之途不一家,弋功猎名者无论己,即一二好奇嗜博之士浏览诸家,弗求归宿,出其性情以成其术业,有失之隘者焉,有失之偏者焉。夫日罗载籍,低首下心,一名一物辨析于几微疑似之间,穷其理而致其曲,仅自怡悦而己,纲常名教何裨益乎?甚或胶持己见,入主出奴,是犹味枣粟之甘,遽诋姜桂之辛烈也,可乎哉?[5]卷首,3
姚鼐《述庵文钞序》对执汉、宋一端的态度尚且各具微词,不仅批评了“为考证之过者”[3]61,同时也批评了“言义理之过者”[3]61;此处法式善则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好奇嗜博”“日罗载籍,低首下心,一名一物辨析于几微疑似之间”的考据学家,然而王昶对此却不以为意。可见,姚鼐序言中对汉学家本就不甚严厉的批评并不是序言被刊落的原因。王昶既与姚鼐相交已达数十年,且对其多有赞赏,那么,将王昶刊落姚序解释为“汉学家无视其学”[9]的表现,似乎也缺乏说服力。
以上几种解释,都没有脱离汉宋之争的立场。此外尚有蓝士英也立足于王昶的汉学家身份,认为王昶“注重考证,以考证为实学,自然不会乐意接受这种顶着义理的名义、以考证为次的调和方式”[10]。此论指出,王昶对姚序弃而不用是出于义理与考证之争,这既是对《述庵文钞序》的误解,也是对王昶的误解。首先,姚鼐在序言中并未过分突出义理的作用;其次,王昶本人并不反对义理,他不仅对宋儒之学不加排斥,而且颇能采纳其说。在《与彭乐斋观察书》一文中,王昶曾云:“古人之文,文其道也,故文与道合。后世之文,文与道分,故文日以衰。”[5]615这种对古人之文“文与道合”的推崇,明显带有沿袭宋儒“文道一贯”说的痕迹。与此同时,王昶还强调:“文以明道也,道明然后文工。”[5]615而明道之途径,则在于“察于心而著于身”,“能存养则心正,身修而天下之理得”,[5]615这也正是宋儒的论调。在《四家文类自序》中,王昶表现出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文章的喜爱,认为其文不无可取之处:“夫八家以外,若朱子熹、陆氏游、陈氏亮、黄氏溍、戴氏表元、虞氏集暨明宋氏濂、方氏孝孺、归氏有光、唐氏顺之,于韩欧为苗裔,斥而弗录,固也。”[5]734-735他认为朱熹等人的文章是“韩欧苗裔”,以往的文章选本不选其文是固步自封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王昶曾多次明言自己对宋儒之说的吸收借鉴,如《与孔洪谷主事书》:“仆《易》宗王氏,《诗》宗毛郑氏,《周礼》宗郑贾氏,此后宋元儒先之说及已有所见者,采之附注于章末,以庶几于信而好古之谓。”[5]628又,王昶曾对同乡沈柏参“浸淫于六经之旨,反覆于宋四子之书,始悔少时所作”之言表示“读之信然”[5]743,“宋四子”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理学大儒,王昶对宋儒的兼容态度,可谓明矣。
事实上,王昶不仅对宋儒之学不排斥,对辞章之学也不忽视。在《困学编题词》中,王昶曾说:“吾学文以道为体,然法不可不效也。于韩取其雄,于柳取其峭,于苏取其大,于欧、曾取其醇懿而往复,又取《尚书》《仪礼》为学韩本,取《檀弓》《公羊》为学柳本,铭、颂取诸《易》与《诗》矣,《太玄》及《易林》辅之,赋取诸屈原,下逮宋玉、贾谊、扬雄之徒,纪事莫工于《史记》,《五代史》其继,别者旁推交通,兼综条贯,如是而吾学为文者始全。”[5]793王昶主张学文应当效古人之法,“于韩取其雄”“于柳取其峭”等例子表明,其所效法的内容包含文章风格在内。在《与彭晋函论文书》中,王昶指出:“所谓文者,理与词已耳。词非理不立,理非词不达。”[5]672“理”即文章的内容,“词”即外在的形式,内容固然重要,形式之美也不可或缺。
如此看来,王昶并非出于与宋学相争而刊落姚鼐的序言。无论是从义理还是从辞章立场看,王昶都持融通态度,并不排斥。一方面,他通晓宋明理学,对宋儒多有肯定;另一方面,他又重视辞章之学,认为“求士之明道,必以文为衡”[5]672。亦即,在对义理之学和辞章之学的肯定上,王昶和姚鼐并不存在重大冲突。刊落序言之举,显然另有缘由。
将姚鼐《述庵文钞序》与鲁嗣光、赵怀玉等人为王昶所作之序作一对比可以发现,相比于“汉学家”这一身份,不废汉、宋,兼通训诂和辞章的“通儒”角色,实际更为符合王昶的自我期许。这种期许,一方面体现在他积极参与汉学事业,同时又融通义理和辞章之学的态度中;另一方面,从王昶所采用的法式善、鲁嗣光、赵怀玉等人为《春融堂集》所作序言中亦可见一斑。鲁嗣光在《总序》中称王昶为“包孕富有,博大醇懿”的“巨儒”,“恢恢然莫窥其涯涘,浑浑然莫穷其底蕴也。海内一材一艺之士,欲仿佛其形似,而卒不能得,即出生平憔悴专一之业以相较,而亦不能逮也”[5]卷首,1。鲁嗣光认为“一材一艺之士”不仅在“包孕富有”一点上不足与王昶相较,且就其专业而言亦达不到王昶的成就,这无疑已将王昶推尊至集大成者的地步。赵怀玉的序言则将“一材一艺之士”表述得更为具体:
今海内操觚之士,其趋不出二端:曰训古之学,曰词章之学。通训故者,以词章为空疏而不屑为;工词章者,又以训故为饾饤而不愿为。胶执己见,隐然若树敌焉。夫董生、扬子奥于文,于经未尝不深。匡鼎、刘向䆳于经,于文未尝不茂。彼好为异同,交相訾议,必其中有所歉,浅之乎窥古人,而意犹未尽融也。若去二者之弊,又克兼二者之长,则世颇难其人,而人且宜以为法,吾于侍郎述庵先生见之。[5]卷首,5
赵怀玉认为,王昶能去词章之空疏与训故之饾饤,而兼二者之长,这同鲁嗣光一样,是以王昶为兼采众长者。需要加以辨明的是,赵怀玉对王昶既能䆳于经,同时又能茂于文的肯定,与姚鼐所言王昶之古文能兼收“义理、考据、辞章”是有所区别的,这一点将在下文姚序与法式善序言的对比中详细说明。在乾嘉文坛,时人亦多以“通儒”赞许王昶,其中既有汉学巨擘阮元,也有桐城后学管同。阮元在为王昶所作的神道碑铭中称:“尊汉学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许、郑;公兼通之,履蹈贤圣”[11];“姚门四大弟子”之一的管同称他“汉宋之学,皆深究之”[5]1181;道光年间的李元度在《王兰泉侍郎事略》中亦目之为“通儒”[5]1199。在王昶所编的古文选本《湖海文传》中,固然体现出鲜明的学人特色,“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12];但另一方面,书中也选沈德潜、袁枚等人的文章多达27 篇。二人在选文数量上名列前茅,足可见王昶对排斥汉学之深如袁枚者也不否定。周寅宾指出《湖海文传》“未能体现出考证派的分明的阵营”[13],正说明了王昶融通百家、不入藩篱的态度。
与王昶的“通儒”态度相较,姚鼐之序虽看似兼收“义理、考证、文章”,实际却欲以文章统摄三者,通过义理、考据、辞章的相辅相成,来成全其所倡导的古文极境。姚鼐所追求的是“以考证助文之境”[4]100,其目的在于借助考据等手段使得古文既充实,又有气韵,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辞章。王昶倡导的则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之学各得其所,各尽其妙。两家宗旨实际大相径庭。将姚鼐《述庵文钞序》与法式善所著之序作一对比,这种差别便昭然若揭。法式善称王昶“所著《春融堂文集》,又能贯串群经,陶镕诸子。考据之文,期于综古今也;辨论之文,期于穷识见也;阐幽抉奥之文,期于教忠孝而动鬼神也。一代之典常,四方之风土,胥于是乎在。徒惊其藻采高翔,犹浅之乎视斯集矣”[5]卷首,3。法式善将王昶之文分为“考据之文”“辨论之文”和“阐幽抉奥之文”三类。其中将文章之功用指向“期于教忠孝而动鬼神”的“阐幽抉奥之文”,实际即义理之文。法式善和姚鼐的区别在于,法式善以考据、义理作为文章的不同分类,姚鼐却执着于构建一种既具考据之实、复有辞章之美、更备义理之深的古文,三者统合,最终成全的却是“藻采高翔”的外在形式之美。两者看似不过差之毫厘,实际却谬以千里。正如郭绍虞所说,姚鼐“毕竟是古文家,所以这种理论也只成为古文之学中比较全面的理论而已”[14]。
综上所述,王昶刊落姚序,并非因其出于汉学家身份而排斥宋学,恰恰相反,王昶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位兼宗汉、宋,融通百家,不偏不倚的“通儒”。王昶对于“通儒”身份的追求,与姚鼐在序言中着力于强调古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在王昶和姚鼐之间表现得并不明显,“通儒”与古文家取舍的不同恐怕才是王昶刊落姚序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三、王昶的桐城学缘
虽然王昶最终刊落了姚鼐的序言,但他与桐城派之间的种种关联并不为此所掩。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学业角度看,王昶的两位业师均为方苞弟子,其古文观念在形成之际就曾受到桐城先辈的影响;其次,从交游角度观之,王昶与服膺桐城之学的许多古文家都往来密切,且相互之间非常投契。
王昶对桐城之文不乏赞赏之词,对桐城文论也不无吸取之处。在古文创作上,他曾亲受桐城先辈指点。乾隆十四年(1749),二十六岁的王昶入紫阳书院读书,当时的书院院长为方苞受业弟子王峻。王峻(1694—1751),字次山,号艮斋,江苏常熟人。在《与梦文子座主荐士书》一文中,王昶提及王峻对于自己学问的启蒙意义:“某生二十九岁矣,自幼习为制举义,于他文懵然无闻知。偶为诗,雕刻鞶帨焉尔。既长,从王次山侍御、沈确士宗伯游,稍知学问之途径,与功力之浅深次第。”[5]595后来在《祭王次山先生文》中,王昶追忆师生间“昕夕相从”的情景,再次言及先师对自己的教导、雕琢之功:“岁在已巳,某初见公。侍公几席,昕夕相从。自顾生平,学问踳驳。辱公训行,加之雕琢。朂以立德,期以古人。从容叩击,经义纷纶。”[5]884王昶指出,在王峻的教导中,经籍义理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王峻在紫阳书院传经的功德,王昶大为推赏:“嗟彼俗学,不知根柢。谁抱遗经,用究终始。公来主讲,手画口陈。昌明绝业,一发千钧。经师人师,维公奚愧?”[5]885王昶赞扬王峻深具根柢,不同流俗,认为王峻主讲紫阳书院时有发明经义、昌明绝业之功。王峻对经义的强调和阐扬,在王昶的学问之途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除王峻外,以方苞弟子身份对王昶古文创作产生影响的还有沈彤。在致门人张远览的一封书信中,王昶论及乾隆文坛,对方苞、刘大櫆及姚鼐三人的古文创作分别表示肯定:“乾隆初言古文者,推临川李巨来、桐城方灵皋两公。仆生晚,不得见其人。稍长,始识蒋编修恭棐、杨编修绳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渊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后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刘教谕大櫆、钱唐杭编修世骏、大兴朱中允筠、桐城姚仪部鼐、嘉定钱中允大昕、族兄鸣盛数人。”[5]600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评述中,王昶剖析自己乃是在结识沈彤等人之后,方知古文渊源曲折之所在,由此可见沈彤对王昶古文创作的深远影响。沈彤曾师事方苞,他在《与望溪先生书》中说:“彤于先生虽未具师弟子之礼,而实以师事。”[15]372有学者立足于此,以沈彤为中介,将王昶和方苞相联系起来。如陈柱《中国散文史》:“吴江沈彤,皆师事方苞;而苞湛于经术,其文尤粹;彤再传为青浦王昶,则古文家而兼考据家者也。”[16]沈彤曾从方苞学习经术,其《果堂集》中有不少是考订经学的篇章。王昶所称自沈彤处知晓的“古文渊源”正是指经术而言。王昶在《与门人张远览书》中指出,“学古文而失者,其弊约有三”,其中之一便是“挟溲闻浅见为自足,不知原本于六经”[5]600,倡导学习古文应当上溯经典。在《与陆耳山侍讲书》中,王昶对王士祯古文“纂入唐宋间小说语,又于经术颇疏”[5]610之不足表示遗憾,也是从古文应当以经术为本的批评视野出发的。王昶《湖海文传》中选沈彤之文8篇:《释周官地征》《丧所生母杂议》《诗硕人说》《周官颁田异同说》《古文尚书考序》《尚书大传考纂序》《与顾肇声论墓铭诸例书》《都督洪公祖烈传》,除最后两篇外,其余均与经学考证相关,可见王昶对沈彤的认可与其经学造诣密不可分。此外,王昶集中还有《与沈果堂论文书》,与之探讨墓志义例,称其“所示论文书,明白深切,皆可法,而于墓志尤详”[5]592,可知两人于作文之法亦有切磋。
王峻曾在《沈冠云文集序》中赞扬沈彤之文,称:“余往在都门,少宗伯方望谿先生每为余称吴江沈君冠云之著述能守朴学,不事浮藻……今冠云之学,笃古穷经,尤精三礼。其解经诸文于群疑聚讼之处疏通证明,一句一字必获其指归而后已。其记序碑铭诸作,亦皆具古人之法而立义醇慤,盖凡在兹编,无不有用而可久。”[15]339解经之文疏通疑难,记序碑铭之作醇厚质朴,总体而言,追求文章之有用可传,这既是沈彤古文的特点,也是王峻的文章观念,同时又是王昶继承且一以贯之的评文准则。渊源上强调古文当原本六经,功用上主张古文创作应当“以蕲禆于世教”[5]594,应当足以“励名节而厚风俗”[17],王昶的这种论文旨趣,正与王峻、沈彤一脉相承。且王昶受二人教导之时,年尚不足三十,这种影响,从他学古文之初便已奠定,之后也始终未曾改变。
正因王昶本人有着深厚的桐城学缘,因此他和许多服膺桐城之学的古文家都非常投契。桐城派古文家中,与王昶关联最为密切的当属鲁九皋和秦瀛。鲁九皋(1732—1794),原名鲁仕骥,字絜非,号山木,江西新城人,他曾从姚鼐学习古文义法,两人之间多书信往来。鲁九皋的受业甥陈用光是姚鼐的入室弟子,其与桐城派的渊源不言自明。乾隆五十六年(1791),鲁九皋和王昶初次相见,此次见面之前,两人神交已达十余年之久。王昶《鲁絜非山木居士集序》中曾记载两人相见的曲折过程:“乾隆庚子,余奉命按察江西,既至,即知鲁君絜非名,盖君成进士已十年矣。会余在任三月,遽以忧归,未及见君也。及戊申冬,复量移江西布政使,方以得见君为喜,君亦具书来约。君又以母忧不果,而余旋被召入京师。盖两人相见之难如此。”[5]710虽然两人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十三年(1788)两次欲见都因事未果,但后来鲁九皋仍将自己的文集寄送给王昶,并请其作序。王昶在序中赞许鲁九皋得朱熹之余绪,认为其文“淳古澹泊,逾于寻常”,称“吾两人慕悦如此,久之得见其文,又久之始得见其人”[5]710,其间的相慕相悦之情可谓跃然笔端。在《祭鲁絜非文》中,王昶又一次追忆二人的相知相惜之谊:“京华相见,意合心倾。谓我知己,遇李之荣。我亦喜君,如珀拾芥。”[5]889同时称赞鲁九皋的品行追踪程朱,创作比肩曾王:“蕴为德行,程朱是求。发为文词,曾王是俦。”①原文中“曾”字误为“会”(會)字,据嘉庆十二年刻本之影印本改。原文见王昶著,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春融堂集》卷五十《祭鲁絜非文》下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889页。影印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8页。王昶集中还有《送鲁絜非赴夏邑任序》《长夏怀人绝句·南城鲁明府絜非孝廉习之》等篇章。其中的“孝廉习之”即鲁絜非之子鲁嗣光,他随父识王昶于京师,并在之后以师事之。鲁嗣光殁后,王昶曾作《哭门人鲁孝廉习之嗣光》两首,表达丧予之痛。诗中称他“少年高蹈擅词场,文字家传一瓣香”[5]472,可见王昶对鲁氏父子的深情厚谊。
与鲁九皋相比,秦瀛和王昶在生活中的关联更为密切。秦瀛(1743—1821),字凌沧,一字小岘,号遂庵,江苏无锡人,与姚鼐文风相近,二人互为推重。秦瀛和王昶常有文酒之会,王昶集中有《秦小岘招同潘侍御兰垞庭筠及万秀才近篷福游龙井寺》《秦廉使小岘移任长沙招饮湖楼话别》《长夏怀人绝句·无锡秦观察小岘》等作。秦瀛集中也留下了很多与王昶相关的诗篇,如《王述庵先生引年退休来游武林饭僧云栖寺余以事牵未得往访以诗奉寄》《又寄述庵先生》《谢王述庵少司寇惠问》《寿述庵少司寇八十》等。在《湖海诗传》小传中,王昶评价秦瀛“性情萧澹,虽勤于吏治而素无宦情”[7]126。临终之前,王昶嘱托其子求铭幽之文于秦瀛,足见王昶对秦瀛的信赖。秦瀛《刑部侍郎兰泉王公墓志铭》中记载两人“折辈行交”之况:“余官中书,后于公者十九年,而公折辈行交,以文章道义相砥镞,垂没,犹以铭辞属余。”并指出王昶“穷研诸经,汎滥子史百家,著述等身……诗文闳富,足备知人论世者之采择,有非他人所能及,晚年尤阐性命之旨,以宋儒为归”[5]1186的学术旨趣,对王昶来说可谓知言。
总而言之,王昶不仅与桐城派众多成员过从甚密,而且他本人也深受桐城先辈的影响。由此亦可佐证,王昶和姚鼐晚年的一番公案并不涉及汉宋之争的立场选择。在今人的论著中,王昶有时还被纳入桐城谱系。如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称王昶之古文“闳博渊雅,醇谨深厚,虽胎息‘唐宋八家’,于古合以神而不袭其貌”[18]。《桐城派文集叙录》一书也将王昶归入桐城一脉的作家之中,称其“师事沈彤,受古文法”[19]。姚门弟子中,姚椿和鲁嗣光均曾以王昶为师,王昶还曾劝勉姚椿要“知古知今,积为经济,无以寻章摘句,搜僻矜奇,至独角麟类于万牛毛也”[7]173。姚门四大弟子之一的管同也对王昶推崇有加。王昶虽为汉学大家,但一方面与桐城先辈有师承授受之关联,与姚鼐、鲁九皋、秦瀛等同时期的桐城派古文家有相知之谊,同时还对鲁嗣光、姚椿等桐城后学有教导、奖掖之功。从王昶与桐城派的种种关联来看,乾嘉时期虽存汉宋之争,但两派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多有沟通、交流乃至渗透。片面强调对立、分歧而无视其交融互渗,显然不利于全面、准确把握这个时代的学术与文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