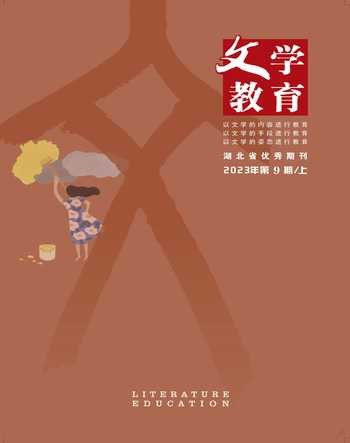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中的性别对话
2023-09-01李艳
李艳
内容摘要: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新锐的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在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中展现了她独特的女性观。她从性别平等的人格尊严入手赋予了性别对话的可能性,又通过呈现男女共同的人性缺失使性别对话回归到人性对话,进而在生命选择的冲突中寻找两性共同的价值归宿。
关键词:艾略特 《弗洛斯河上的磨房》 性别对话 人性对话
当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因其独有的特色兴盛起来的时候,19世纪的英国文坛也因为一批女作家的加入而活跃起来:布朗宁夫人、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如果说这些女作家的出现在当时并未兴起像20世纪以来那样的女权文化的热浪,但至少那些来自女性的真实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当时的维多利亚文化注入了一种鲜活的思想,使我们开始真正能够通过女性的声音听闻女性,通过女性的眼睛体察社会。在这些女作家中,乔治·艾略特无疑是特别的一位,她以女性特有的眼光摄取女性所生存的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她“不曾把自己称作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甚至可能反对被称作一个女权主义者”[1],因为她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人性的问题是首要的,而女性的问题是次要的。”的确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作为主体的存在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但与此同时她并未停留在张扬女性独立价值的层面上,她总是试图打破那种将男女性别放置两极的模式,寻找性别平等对话的契机,从而在两性共有的生存场景中呈现出人性的真实面貌,从而超越性别的局限凸显人生存的境遇。艾略特的作品《弗洛斯河上的磨房》最终男女主角的死亡给我们留下了悲剧的思索,而要真正理解悲剧就不得不回到艾略特的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观中,因为与其说这部作品最终目的是关注性别,不如说是超越性别,艾略特试图在性别对话的空间中展开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的追索。
一.人格的平等:性别对话的可能性
生活在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艾略特当然不能算是幸运的,当时英国保守、封闭而又充满偏见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义也只是“低劣人等”、是男人的“玩偶”,而女性的“美德”和职能也只是“作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毋庸置疑艾略特投入小说创作不仅为自己证明了自我独立的存在,而且也为所有女性的存在彰显其超越世俗陈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她大胆坚持在她的小说里寻找、发现并掘取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识过程以及女性形塑自我独特存在的历史。于是我们看到了弗洛斯河边的麦琪,她跳跃奔放的天性就像不断涌流的河水,使她永不停息的去追逐新奇事物的奥秘和人生的真知灼见,尽管这一切在父亲看来只是一些不值得去推崇的“优点”,在哥哥眼里更是不屑一顾的“缺点”,然而她还是以她的任性和率真证明自己不逊色于这个家族中任何一个人的智慧和决心。当传统的伦理规范要求她亦步亦趋的去扮演贵族小姐、贵族夫人时,她拒绝了世俗的安排,简简单单的把自己嫁出去并不是她追求的爱情理想;在家庭变故袭来时,她熬过最沉痛的悲观和绝望,最终选择自食其力的去打拼属于自己的生活;当圣奥格镇的人企图用流言蜚語淹没她的意志和热情时,她不愿作一个放弃的逃兵,她想要留在众人眼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高尚。总之,只要我们去聆听,我们总能在艾略特的女性世界里听到哪怕是细碎但却是真实的声音:她们的热望、她们的挣扎、她们的诉求。有谁能说艾略特没有发现属于女性自我的真实存在呢?她们有着女性的尊严,有着女性对自我价值的寻觅和形塑。
然而,艾略特并未只停留在女性的关怀上,如果说每一个抒写人性关怀的作家手中都有一面明澈的镜子,无疑艾略特的镜子既映照女人也映照男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独特的情貌和个性。她既彰显女人的丰富潜质和隽永的灵魂,也不回避男人广博的智慧和深邃的心灵。艾略特珍视每一个独立个体自我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正因此我们的视野里同样也不断活跃着坚韧勇敢的汤姆,敏感聪颖的费利浦,多情天真的斯蒂芬,他们的身上都焕发着个人独特的热情和活力,在展开的人生舞台上他们不断表演着自我追逐理想、追求完美的率真个性。在艾略特看来,男性并不是一个相对于女性存在而被批驳和颠覆的对象,她只是要把男性和女性一样放置在平光镜前照出他们本有的样子,照出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应有的自我价值和意义。艾略特对女性价值的确认以及对男性价值的肯定就是要从根本上还原人性的真实面貌,使男性和女性在具有平等人格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能够成为对话的双方,从而打破性别之间的二元对立,使人们“进一步认识艺术的潜能、人性的潜能、生活的潜能”[2],使性别之间的对话不再只是关于性别的对话,而是回归到对两性共同存在的世界的关注上,进而探求人类生存于世的价值和意义。
二.人性的缺失:性别对话的必然性
探询性别之间平等的生存价值和人格尊严是艾略特走向人性关怀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她并没有故意营造一种“人性的乌托邦”,而是更加痛心疾首的发现使性别对话真正走向历史前台的力量恰恰是两性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人性的缺失。
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中主要人物几乎都经历了人生从激情亢奋到忧郁创痛理想不断幻灭的生存洗礼。艾略特着意刻画了两个人物的成长过程:一个是汤姆,一个是麦琪。汤姆从小就表现出与他所熟悉的土地一样的质朴率真的个性,他熟悉土地上每一个生物,与它们游戏嬉闹时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默契;他对自己的劳动技巧生存本领有着倔强的自信,也正因此当家族遭受厄运时,他毫不犹豫的把重振家业的重任扛在自己的肩头,誓死也要夺回自己家族的土地和磨房。汤姆骨子里有一种莽撞少年的简单执着的信念,正像他从小就对学问对抽象的推理缺乏兴趣缺少潜质一样,简单的头脑容易促使他血气方刚的独闯天下,也容易使他产生偏激的思想观念。他自以为个人的意志代表了家族的意志,于是武断的用家族的仇恨阻断了麦琪与仇人之子费利浦之间的爱情;他把自己想象成孤胆英豪,然而倔强的个人奋斗可以换来家族命运暂时的转机却无法换来家族永久的和平和安宁。悲剧的结尾中狂暴的洪水成为一种永恒的意象,它瞬间摧毁一切的力量警醒我们去发现人性深处的脆弱和缺憾:汤姆的坚韧并不能成就绝对的完美,他的个人意志也不能绝对左右生存的秩序。
仅仅指出男性的弱点并不是艾略特的完整思想,同样她并不庇护女性。如果说汤姆的性情属于土地:质朴刚毅,那么麦琪的天性属于河水:细腻温柔。她从小喜欢在书本里寻找梦想,随着岁月的成长,她将自己充盈成爱的河流:想要和汤姆一辈子在这条河里嬉戏,也想要让它滋润残疾而又敏感的费利浦的心田。尽管她在家族利益与爱情之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反抗和妥协,但她唯一不变的信念就是不能停止去爱和同情,哪怕是为所爱的人自我牺牲。于是我们看到麦琪俨然变成了“天使”,她关爱、垂怜、拯救在痛苦中的父亲、哥哥和费利浦。然而结果呢,麦琪最终也只是“受难的天使”:在费利浦面前,她越是投入的爱越是感到对父亲对哥哥的愧疚;在汤姆面前,她越是要挽回兄妹的情谊越是感到对费利浦的痛悔;而更加残酷的现实是她无法抑制欲望的冲动又爱上了露西的未婚夫斯蒂芬。麦琪的爱和同情没有换来她所向往的伊甸园,反而使她一再伤害她所爱的人。她始终摆脱不了在心灵的旋涡中挣扎,是因为她不了解自己的感情到底能承载多少,她想要用一个人的爱去拯救所有受伤的心,结果也只是留下破碎和痛苦。
当花样的生命在我们眼前绚烂开放又匆匆凋谢时,不得不让人在命运的起伏跌宕中沉思人性的复杂。艾略特在其中预言着一个严肃的现实: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人生的境遇中都要面对重重考验,于是受难、彷徨、迷惘、沉沦对于两性都是必然共同要经历的,也正因此他们在其中所暴露出的人性的脆弱、道德的缺失也都是一样无从回避的。“作为一个男性或女性个体,人只生活在一个确定的片面性和有限性之中”[3],既然如此,两性之间也便不应有所谓居高临下的距离,人与人之间应该更加宽容真诚的面对彼此的弱點,通过平等的对话共同探讨超越个人有限性的生存方向。
三.终极价值的寻找:性别对话的前景
对人性世界的敏锐感知使艾略特对于性别话题的关注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身份争执,而回归到一种更加深邃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思考上来。当汤姆与麦琪、费利浦与麦琪以及斯蒂芬与麦琪的爱恨纠葛一幕一幕的上演时,我们更多的是被吸引到这样一种充满疑惑的思考中:为什么麦琪一再试图融洽沟通和他人的关系,在挣扎与妥协之后结果仍然只是一个苍凉的悲剧?的确,在小说中麦琪与汤姆、费利浦以及斯蒂芬之间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引力,但他们之间却又始终存在着一种很微妙的离心力使麦琪和他们很难毫无阻隔的紧密依靠。而这种微妙的离心力恰恰存在于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选择上。汤姆亲历了家族的荣辱兴衰,在倾家荡产备受凌辱的窘境中临危授命,他有着和父亲一样强烈的爱恨分明的家庭荣誉感和责任感,也正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汤姆毕生的追求就是报仇血恨,重新夺回世代相传的家族产业。他把必胜的信念写在《圣经》的首页,足以看出在他的心里再没有比家族荣誉更加神圣的存在了。然而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麦琪会成为家族的叛逆者。尽管麦琪也爱父亲爱汤姆,同样也依恋着和睦的家庭,但麦琪对这一切的爱不是基于一种家族荣誉感,而是一种个人的爱与同情。她始终天真的幻想并追求着一种尽善尽美的爱的乐园,每一个人都相亲相爱,因此她不顾汤姆的威胁爱上了仇人的儿子——天生残疾而又多愁善感的费利浦。至于麦琪后来在汤姆的威逼下,暂时中断了和费利浦的往来,支撑着她的信念依然不是家族的责任和尊严,而是因为她不愿离开汤姆、丢开汤姆,她深爱着汤姆,这种爱同爱费利浦一样在她心中是神圣的。而费利浦不能理解,因为他只想拥有和麦琪的爱情,他只愿躲在自己爱情里,而麦琪要爱的又何止一个费利浦。紧接着斯蒂芬的出现曾使麦琪一时间心驰神荡,但很快她悔悟了,还是因为她不忍看到纯洁善良的露西伤心欲绝,她也不愿汤姆离弃她。与此同时,斯蒂芬在锦衣玉食的闲适生活里唯一的信仰就是个人的欢娱,他无法真正进入麦琪的内心世界。由此我们看到,他们四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命信仰:麦琪的信念是个人的爱和牺牲;汤姆总是把家族荣誉奉若神明;而费利浦唯一的心灵依靠就是获得个人的爱情;斯蒂芬的人生信条只是个人的享乐。正因为他们各自坚守着彼此的心灵追求,所以即使他们能够互相面对,但冲突、争执、矛盾始终纠缠在一起,使他们很难心心相映和睦共处。
男女两性对自我价值的选择最终促使对话产生了争论和交锋,然而对话的目的不是争辩而是为了达成共识,是为了男女两性能够从对话中找到生命的真谛,找到人生存最终的价值和意义。可是,什么样的终极价值又是永恒的值得依靠的信仰所在呢?艾略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她所营造的悲剧氛围却又给了我们启示:无情的洪水卷走了生命,也卷走了人们心中曾经追求的虚妄的信念,麦琪和汤姆在死亡中相拥是两性真诚的面对彼此后开始的共同祈许。我们需要去寻找真正的价值归宿和永恒的价值依恋,只有在这种寻找中,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才能在对话中摈弃冲突纷争拥有明天。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一度冲击着固有的社会和信仰体系,盘踞千年的基督信仰和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道德渐渐失去了影响力,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加速着人性的异化。艾略特一方面对教条化的福音派越来越反感,对科学精神越来越亲近,另一方面她又始终对基督教内在精神有着执着的信仰。正因此,在艾略特的笔下,男性和女性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常常面临着深刻的价值撕裂。当然两性越是沉沦,越是需要救赎。艾略特试图调和理智和情感的分裂,弥合现代精神与传统伦理的隔阂,与此同时也积极主张两性通过价值对话的方式建立沟通和互信的桥梁,回归人性的反思,从而寻找重建信仰体系的可能。
从《弗洛斯河上的》中性别对话中不难看到乔治·艾略特非同寻常的性别观照,她对男女对话的反思是建立在独立的女性思考基础上的。乔治·艾略特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整个英国社会现实领域不仅对男性也对女性开放的时候,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产业劳动和社会活动中。不仅如此,英国的妇女们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乔治·艾略特所代表的新女性正是在变革的时代通过知识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艾略特十分喜欢阅读和学习,她在早年就广泛涉猎了包括历史、政治、科学、艺术等不同门类的书籍,这些不断展开的知识图景给予她不一样的人生维度和思考的深度,她一生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还有诸多诗歌、散文和评论文章,她用书写的方式,完成了对英国社会对开放和多元的探索。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将艾略特列入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三位大作家之列,并且赞美她的创作有着“托尔斯泰式”的高度。
但另一方面,艾略特作为女性书写者,她并不想把笔下的女性推向男性的对立面。艾略特在女性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她以写作的方式诉说的再不是作为“女人”的类的本质,而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呈现的“人”的本质。她从发现男人和女人平等的人格尊严开始,赋予了性别对话的平台,当她进一步呈现两性共同所要面对的人性缺失时,性别的冲突就超越了性别的对抗,开始向人性的主题复归,于是性别的对话成为价值选择的对话。艾略特执着于人性的研究,是因为她看到性别关系真正的未来不是要造就一个分裂的女性世界或男性世界,而是要寻找一个共同的终极价值,在永恒信念的感召下同心协力超越生存的悲剧。
注 释
[1]Dorothea Barrett,Vocation and desire: George Eliots heroines[M],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175
[2]F.R.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15。
[3]刘小枫主编,杨德友 董友等译,《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C],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1:1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