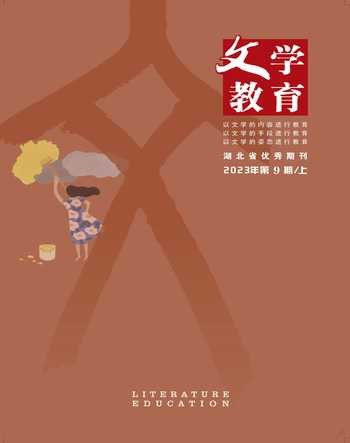论徐则臣小说中的城乡叙事
2023-09-01李晓庆
李晓庆
内容摘要:徐则臣是“70后”学院派作家的代表,他在文学创作中持续关注并思考城市化进程对乡村、城市以及掙扎在城乡冲突中的个体的深刻影响,“京漂”与“故乡”系列小说是其重要的创作版块。徐则臣的小说描写了当下中国的两个情境:城市和故乡,并着重描写了城市和故乡中生活的人,他们的内心感触、生活情态。连接两个社会形态的城乡叙事揭示出其笔下的花街70后青年与乡村、城市乃至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接续了当代文学的城乡书写,构成新世纪城乡叙事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徐则臣的“进城”与“返乡”叙事进入他的小说世界,从而窥见当代中国的城乡形态。
关键词:徐则臣 进城 返乡 叙事
在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上,徐则臣有着自己的见解与追求。古典形式与现代意蕴相结合是他初入文坛时的写作观念,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创作的成熟,他的想法逐渐转变,认为“寻找一种与时代现实和精神相匹配的叙述和结构的模式”[1]更加重要,也能更有效地反映当下的时代状况。在叙述花街70后青年为实现心灵安宁往返于乡村与城市的过程中,他成功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叙述视角,使小说内容与形式相互作用共同营造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叙事效果。此外,在异乡与原乡、城市与乡村、出走与回归等多重叙述张力之中,徐则臣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富有意味的叙述形式展现了现代转型过程中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与生存处境,超越了“乡下人进城”“底层叙述”的历史局限,表现出从现实经验层面向精神探索层面的突进。
一.叙事视角
在小说叙事中视角关注的是“谁在看”的问题,视角不同产生的叙事效果自然也不同。在叙述花街70后青年为实现心灵安宁往返于乡村与城市的过程中,徐则臣透过儿童、女性及游子的视角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1.儿童视角
徐则臣在苏北水乡度过了童年生活,幼时记忆成为他关照故乡的重要来源,因此他更擅长以儿童视角展开纸上故乡的言说,即“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2]。
儿童与少年是作家徐则臣在“故乡”系列小说中主要的书写对象,也是“故乡”系列小说中的典型形象。儿童与少年时期是每个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这是最单纯、最善良的年纪,也是成长的关键时期。花街上的儿童与少年们正在经历这一阶段,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十分困扰、苦闷,他们渴望快快长大,但长大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儿童时期纯真梦想的破灭、成人世界的复杂多变,给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增添了许多伤痛。
在《苍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主人公少年木鱼成长过程中的苦闷和困惑,他在成长的隐痛中默默生长着。儿童、少年时期,男孩的声音是高亢、响亮、清脆的;而长大后,由于声带的变化,声音变得低沉、沙哑、浑浊。小说以“苍声”为题,以主人公声音的变化揭示其成长的轨迹,而“苍声”,即最终长大的标志。主人公木鱼想要拥有低沉、沙哑、浑浊的声音,因为在他看来“苍声”是最终长大的标志。但木鱼逐渐“苍声”的过程却是十分煎熬的。作为学生,木鱼见证了校长何老头被抓、被批斗、被游街、被折磨的整场闹剧。作为孩子,木鱼旁观了大米、满桌、三万、大年诱奸韭菜的全过程。儿童、少年时代的纯真、懵懂无知与无忧无虑,被成人世界的复杂、冷漠与人心的恶浇灌,故事的最后,木鱼最终长大,成为苍声的“大人”。在木鱼成长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孩子,他对周遭的恶是被动的,他无力反抗,无能为力,悲痛又无奈。在成人的世界中,孩子们只能作为沉默的见证者、无言的旁观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褪去天真,接受残酷的现实及成人世界的复杂,默默地成长最终苍声。他们在成长的隐痛中,遵循着自然的生长逻辑,在最终长大之前,在沉默中翻滚挣扎、遍尝苦楚。
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视角实质上是徐则臣在创作中反映现实的隐喻和载体。根据与创作主体的关系,以儿童视角为主的小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作者借助儿童视角追忆童年,表达对故乡人与事的眷念,如鲁迅的《社戏》、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另一种则假托儿童的口吻叙事,故事情节与作家本人的幼时经历并无关联,如凌叔华的《小英》、萧乾的《篱下》等。徐则臣的小说属于后者,他试图通过虚构的花街故事和儿童视角关注乡土社会的苦难,暴露和批判成人世界的种种丑陋和罪恶,“像鲁迅说的,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3]。
2.女性视角
女性角色,是徐则臣“故乡”系列小说中塑造的最多,也是最成功的形象,女人,是“故乡”系列小说中的典型形象。“花街”,一条因寻花问柳而得名的小街,其名称的由来,也和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花街”,本叫水边巷,因靠在运河边,聚集了许多南来北往的人们。船上的男人们常在水边巷过夜,一些为了生活的女人们便在这里租一个房间,在门口挂上灯笼,关起门来做夜晚生意。于是“花街”的名头越来越响,久而久之,人们便遗忘了水边巷这个名字,改称其为“花街”。
在这条“花街”上,有着形形色色的女人。她们有的是本地人,因为遭遇变故为了生存而不得已开始做夜晚生意;她们有的是外地人,为了获得容身之所,在花街中求得一丝生机。《失声》里的姚丹,丈夫入狱,独自生活的她,为了守住家、等待丈夫归来,不得已挂上灯笼做夜晚生意支持生活;《耶路撒冷》里的秦奶奶,因为饥荒贫寒,为求生开始做皮肉生意;《古代的黄昏》里的秀琅,命运悲惨,最终沦落到“花街”出卖自己……
透过这些经受着苦难的女人们,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景象,而是在生活的困境中,坚韧地生存着。其实,她们本就是一些温柔善良的普通人。“她们很安静,无声无息地挂上灯笼,又无声无息地取下,和花街上的人一样沉稳平和地生活。”[4]生活给了她们沉重的苦难,她们却以柔克刚,用柔韧的心性和对美好生活的一点谈不上奢望的简单信念活了下去。她们的精神如同给养着她们的运河水一般绵长。苦难让她们人生的河流涌起惊涛骇浪,而她们本身却总能在回归平静之时让水面泛起粼粼波光。
3.游子视角
除了儿童和女性视角,徐则臣还采用了游子这一离乡又返乡的特殊视角带我们感受故鄉的变化,游子是徐则臣“故乡”系列小说中的又一典型形象。在游子的眼中,童年时期的故乡是非常美好的,行于异乡的游子们往往难舍对故乡的牵绊。然而,在徐则臣的笔下,重返故乡的游子面对的却并不是童年印象中的美好故乡,而是受现代化、城市化影响的面目全非的故乡。
小说《还乡记》中的主人公“我”就是一个游子。作者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带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主人公的精神困惑。主人公“我”是一个归乡的游子,因为亲人的离世而回家奔丧。然而,走在归乡的路上,自然环境的变化就让“我”疑惑不解、十分不安。路边原有的柳树、白杨树没有了,地里除了庄稼光秃秃的,连古老的河流都被填土造田。故乡迈向现代化,熟悉的景象变得难以辨认,触目惊心的变化让“我”难以接受。在送葬仪式上,乡村传统也变了味。原本的送葬仪式是对死者生命的尊重和虔诚的祭奠,声势浩大,十分严肃。而“我”在回乡后看到的送葬仪式却十分低俗,如同一场闹剧,变成了一场集体的娱乐。乡村传统的风俗和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消解,变得面目全非。此外,故乡的人也变了。童年伙伴的出轨,让“我”觉得十分陌生。“我”最终意识到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只能逃离故乡,让故乡再次成为精神意义上的故乡。
行于异乡的游子把故乡当作心灵家园,故乡是他们的精神原乡,然而物是人非之后,游子们面对眼前故乡的变化充满了精神困惑。这其实正是时下的乡土现实。何处是归乡,游子们也在故乡的变化中不断追寻着……
二.叙事张力
在异乡与原乡、城市与乡村、出走与回归等多重叙事张力之中,徐则臣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富有意味的叙述形式展现了现代转型过程中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与生存处境,超越了“乡下人进城”“底层叙述”的历史局限,表现出从现实经验层面向精神探索层面的突进。
1.人与身份——异乡、原乡——身份认同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来确证自己的身份。乡土亦是如此,无论是异乡或是原乡,都是通过与他乡的对比从而确定的。在徐则臣的“京漂”与“故乡”系列小说中,“京漂”即是异乡,“故乡”即是原乡。它们形成对比,但共同指向的都是人与身份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在异乡或是原乡,作家徐则臣都展现了小人物们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及对自我身份的确证。
在“京漂”系列小说中,作者徐则臣着重塑造了三类“京漂”形象。在北京这座充满欲望与竞争的大都市中,“京漂”们属于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没有立足的身份可言,无法得到社会的扶持和庇护。无论是“游离者”“零余者”亦或是“局外人”,它们指向的都是与这座城市没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表面上呈现为一个身份、一个户口,深层则体现为心灵归属问题。
在“故乡”系列小说中,徐则臣透过儿童、女人及游子的视角向我们讲述了花街上的故事。在这条老街上,有默默成长着的少年,有经受着苦难的女人,还有飘荡着的游子。透过他们,作者徐则臣向我们展现了渐行渐远的故乡。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游子身上。行于异乡的游子把故乡当作心灵家园,故乡是他们的精神原乡,然而物是人非之后,游子们面对眼前故乡的变化充满了精神困惑。这其实正是时下的乡土现实。
无论是“京漂”系列小说还是“故乡”系列小说,其中都充满了异乡与原乡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种关系在这两类小说中体现的路径不同。“京漂”形象们对于异乡,即大都市北京是十分向往的,他们渴望留在北京。虽然他们本身可以在故乡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他们都不满足于现状,纷纷逃离故乡,来到北京这个满是欲望与竞争的大都市,渴望在北京扎根,过上不错的生活。他们希望北京能成为第二故乡,但这显然是矛盾的。一方面,“京漂”生活十分困难,北京这座城市始终拒斥着他们,即使他们有能力过上不错的生活,但他们也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京漂”们也无法真正割裂与故乡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北京的漂泊生活与在故乡的稳定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四处漂泊的状态加深了他们对于故乡的思念。
而在“故乡”系列小说中,作者徐则臣通过游子这一离乡又返乡的特殊视角带我们感受故乡的变化。在游子的眼中,童年时期的故乡是非常美好的,行于异乡的游子们往往难舍对故乡的牵绊。然而,在徐则臣的笔下,重返故乡的游子面对的却并不是童年印象中的美好故乡,而是受现代化、城市化影响的面目全非的故乡。行于异乡的游子把故乡当作心灵家园,故乡是他们的精神原乡,然而物是人非之后,游子们面对眼前故乡的变化满是困惑。
通过这两类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徐则臣浓浓的乡土情结。徐则臣本人作为一名“京漂”,他在其作品中抒发了对少年时期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深深眷念,还抒发了异乡人在都市历经身体漂泊和精神荒芜之后对精神原乡的回望。对“京漂”们,或是“花街”上的人们来说,故乡不仅仅是一抹浓浓的乡愁,更是灵魂得以安妥之地,是人之心安的精神寓所。
2.人与环境——城市、乡村——精神重塑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京漂”系列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城市生活,“故乡”系列小说则主要描写的是乡村生活。作家徐则臣出生于7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方面都向现代化迈进。这一时期,城市兴起扩张快速发展,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或是衰落,抑或向城市化发展。社会震荡变化,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巨大的变化都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发生改变。
城市与乡村环境的差异对个人精神的重塑在“京漂”们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尤其是对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京漂”形象而言,她们往往在城市的浮华中迷失了自己。《浮世绘》中的王琦瑶原本是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来到北京的。她颜值身材都十分在线,在外观上占据很大优势,所以王琦瑶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充满信心。但现实很快就打了脸,竞争残酷的北京并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会对你特殊照顾。王琦瑶在北京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辛。颇受打击的她很快就沉溺在情爱的温情世界中,逐渐失去了理智。第一次付出真心后却得知这是一场欺骗,心灰意冷的王琦瑶很快就认识到爱情并没有那么重要,但她却依然游走在各个男人之间。她觉得在北京与其坚贞地过着窘迫的生活不如放纵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堕落让她体验到了复仇的快感,也逐渐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我们也许不禁会发问,城市生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回到故乡呢?然而事实是,城市容不下肉身,家乡安放不了灵魂,这几乎是徐则臣笔下小说人物形象的死局。待在大城市热闹、多彩、包容,可除了几平米的出租屋,这个城市的喧哗璀璨似乎跟自己没半点儿关系。想回到家乡,以为欢迎自己的是淳朴的乡民,旖旎的村貌,父母的温存,可回到现实面对的,是穷山辟水的局促,是邻里劣根上的势利,是地头垄沟间狡黠的算计。乡亲们乐于对你的生活格外“关心”:做什么工作,拿了多少钱,什么时候结婚……你混好了他们妒忌,出了“糗事”他们说三道四奔走相告。
处于这种状态的“京漂”,不是内心不够强大,不该在意他人评价,而是对这种行为的厌恶,是不可名状的别扭,是深深的无奈……更无奈的是父母观念陈旧倔强,很难心平气和地沟通,难以改观根深蒂固的思想,与其在短暂相处时间内置气,不如假意顺从应承,于是,“京漂”们逐渐和亲人形同陌路。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烦恼困难,家乡的亲人们不能给予帮助指导;同样地,“京漂”们对亲人们的生计和结婚生子的俗世夙愿同样无计可施。“京漂”们都是普通人,为在北京活的像个人样儿都已经费尽力气了,他们被生活蹂躏了无数次后,到最后,只得认命躺平,接受原本那个讨厌的样子。“京漂”们偶尔累极了的时候也想过回到家乡,守一方平静尽儿女孝道,但是回去了,工作怎么办?别人怎么看……真正又能改变得了什么?现状?关系?到头来还是和家乡、父母渐行渐远。在北京苦苦挣扎的他们都明白,有的人出不去,有的人也回不来,只能在命运的轨道里各自爬行着。徐则臣在“故乡”和“京漂”系列小说中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让我们听到了许多“京漂”们的心声。
徐则臣在“故乡”和“京漂”系列小说中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其以‘故乡‘京漂小说分别建构了“花街”与“北京”两大物理空间,并以‘空间的变换书写出乡土变迁与城市突起的‘现代风貌,呈现出社会众生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困惑,提出现代个体意识觉醒后对于自我存在的思索与迷惘问题,以此传达出对现代性下个体如何打破精神困境的探索。”[5]
3.人与理想——出走、回归——精神救赎
是,或者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而对于徐则臣笔下的人物而言,出走或是回归,这也是一个问题。出走与归来看似是两条相反的路径,但这实际上都蕴含着主人公对理想的追寻。对于“京漂”与“故乡”系列小说这个整体而言,作家徐则臣在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都用一条线将其串联。徐则臣笔下的人物們一开始往往因为想要逃离故乡而来到城市生活,而异乡漂泊的生活让他们没有归属感,这时家乡就成为他们的精神原乡。而想象中美好的故乡也变了样,故乡难回带给他们的失落,让他们重新思考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徐则臣笔下的人物们完成了对自我的探寻,对个人理想的重新审视,对自我与故乡关系的重建,以及对自我精神的救赎。
徐则臣作品中“出走”的主题反映了乡下人进城的社会现实。“从家乡出走者到京都‘边缘人的角色转换,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动迁徙的社会生活。”[6]当个人从家乡出走,他们就不仅在地理关系上也在伦理关系上与故乡剥离,成为异乡人。对于选择“出走”的“京漂”们而言,行于异乡城市所面临的尴尬境遇和精神焦虑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对于离开家乡在外拼搏的人来说,故乡永远是最美丽的安慰,却也是回不去的地方。逢年过节的匆匆一游,都只是个过客,而不是归人。城市、故乡,哪里才真正是自己灵魂栖息的地方,“京漂”们在寻找的路上。对于选择“回归”的“花街”小人物们而言,故乡也渐行渐远。
“徐则臣在创作中想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家园破败之后的出走,行于异乡所感受到的隔膜,难归故里带来的失落,以及在整个出走过程中,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探讨,对自我与世界和解的探寻。可以说,徐则臣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追寻,完成自我与故乡情感的重构,实现个体的精神返乡,也即‘归来。这正是从原乡出走,在异乡中重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漂泊的个体生命最终纳入非空间依附的故乡,回归精神原乡。”[7]其实,人就是在不断流动的。古代的重土安迁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社会用市场把人调来调去,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没有故乡,或是失去故乡。异乡是故乡,我在何处,何处即为吾乡。追寻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才是当代人的基本使命。无论是“京漂”们,还是“花街”上的小人物,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你来自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往何方。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只要不失去方向,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
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徐则臣是难得的严肃思考生活和文学的写作者,深度介入到中国城乡结构转变的进程中,言说同代人在告别乡村、拥抱城市的心路历程中的理想与奋斗、挣扎与失望、卑微与无奈,书写一代人漂泊城乡的心灵史,代表了70后作家在当今文坛的思考深度和精神高度。当城乡从作品的幕后背景走向创作的聚光灯下﹐并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叙事主角,如何有效地传达出一代人鲜活的生命体验仍是当代作家未竟的事业。正如韦勒克与沃伦所说,“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8],当下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发生着陌生的新乡土经验,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也在进行之中,今天的“城市经验”似乎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如何在两种新的经验中汲取“营养”,真切而深刻地写出一代人或几代人在这个大时代中置身于“城乡之间”的命运,对于作家而言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艰巨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徐则臣,何晶.徐则臣:好作家要做思想和艺术的先知[N],《羊城晚报》,2014.2.18.
[2]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1).
[3]徐则臣,姜广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和叙事资源[J],《西湖》,2012(12).
[4]徐则臣.花街九故事[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
[5]张琼方.现代性下的空间哲思[D].厦门.集美大学,2020.
[6]常毓峰.成长·出走·荒诞[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20.
[7]杨建英.“故乡”“异乡”与“原乡”[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20.
[8](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2022年研究生校级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编号:2022XKT124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