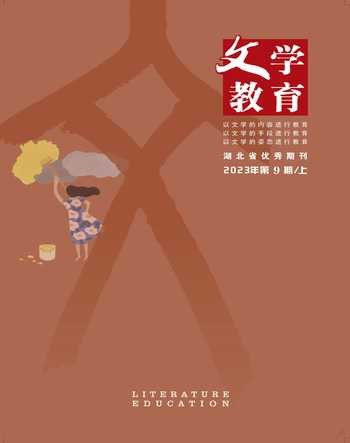从白先勇与陈谦小说空间叙事管窥华文写作嬗变
2023-09-01袁媛
袁媛
内容摘要:白先勇和陳谦的小说都体现了较强的地域空间感,但对本土、异域空间的描写投射出截然不同的主观情感和精神思想。白先勇以故国家园空间叙事和异域空间的异托邦书写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家国”乡愁空间,而陈谦通过对故乡的异化书写和对异域空间的暖色书写呈现了个体的价值以及内化的价值认同。作家的迁移经历、创作经验特别是写作的时代背景的变化可理解为海外华人写作嬗变之根源。
关键词:白先勇 陈谦 空间叙事 海外华文写作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空间理论兴起、发展并逐渐渗入文学领域。跳出传统时间叙事的理论框架,以空间替代时间推动情节的发展,运用不同的空间和场景描写突出叙事的主旨,“空间叙事”已然成为现代小说中的一种重要技巧。[1]白先勇和陈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脉——海外华文写作的笔耕者,分别代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留美作家和新世纪新一代大陆留美作家,他们的创作都具有丰富的空间素材以及跨越式空间感,但两位作家小说中对相似空间呈现出的情感色彩和心理趋向却具有明显的不同。从空间维度对两位作家的小说进行分析并比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其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此同时,空间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两代留美作家的文学生态流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白先勇的空间叙事
(一)故国家园空间叙事
白先勇的“故国家园”存在于他小说重点塑造的两类空间人物——“台北人”和 “纽约客”的回忆和话语里。他所谓的“台北人”并非台湾本土人,而是出于时势政局的原因从大陆某个城市背井离乡到台湾的大陆人;而“纽约客”则是从台湾或解放前的大陆到美留学的学生或移民美国的群体。这两类空间人物身处“他乡异国”,心中都饱含对大陆故国家园深深的眷恋之情,衍生出桃源式的“故国家园”空间作为民族性的精神原乡。
在《花桥荣记》里,“我”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随国民党战败撤到台湾的国军眷属,为生存在台北开起家饭馆——花桥荣记,与当年爷爷在桂林开的“招牌是响当当”的米粉店同名。显然,“我”借饭店名寄托对家乡桂林的思念之情。当回忆昔日米粉店的风光时,文字透露出安逸的空间氛围和对生活的满足:“……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不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2]《谪仙怨》中的黄凤仪原是位官家小姐,父亲离世家道衰落,母亲带着年幼的她跟着落败的政府撤到台湾,成年后又勉为其难送她到美国留学。而“从小不是一块读书的材料”的黄凤仪最终沦为纽约地下酒吧的风尘女郎。小说开头黄凤仪写给妈妈的信里,提到去纽约近郊阔人住宅区玩耍时看到一幢花园别墅,“花园非常大,园里有个白铁花棚,棚架上爬满了葡萄……我竟忘情地走了进去……一个人在棚子下面一张石凳上坐着,竟出了半天的神…… 妈妈,你还记得我们上海霞飞路那幢法国房子,花园里不也有一个葡萄藤的花棚吗?小时候我最爱爬到那个棚架上去摘葡萄了。……”[3]黄凤仪对童年幸福的“家”的迷恋跃然纸上。可以说,《花桥荣记》里故乡的桂林米粉店和《谪仙怨》里上海霞飞路的家都代表着富足和安逸,如同让人产生归属感的母体家园。不仅如此,白先勇还用这种“回忆”的方式来构建“台北人”、“纽约人”精神家园。《秋思》里的华夫人由台北园子里盛开的一畦菊花追忆起打跑日本鬼子的那年秋天,自己丈夫带着军队“班师回朝”的荣光场面;《国葬》里的秦副官站在老长官的灵车上,一声“敬礼——”让他忆起同老长官还都南京谒拜中山陵的威武场景;《冬夜》里的过气教授余嵚磊回想当年在北大带头闹“五·四”学潮的英勇壮举…… 小说中的人物在感叹再也回不去的光辉时光的同时,也从对过去的回忆中获得认同,找到精神原乡,从而获得归属感。
(二)异域空间的“异托邦”书写
白先勇小说另一个常见的地域空间是台北、纽约、芝加哥等他乡异国。《冬夜》里下着绵绵冷雨的台北市的温州街小巷,《谪仙记》的寒冬清晨中无比空荡寂寥的纽约大街,《夜曲》里在曼哈顿的暮色冷风中的中央大道,《芝加哥之死》里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的地下室……,浓缩成为白先勇笔下的他乡异国,给人一种孤寂悲凉的空间意向。在这个空间内,相较于仍然生活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台北人”,“纽约客”对他乡异国的感受要强烈得多。“李彤”、“黄凤仪”、“吴汉魂”们面对西方霸权强势文化时,自身携带的中华文化“基因”莫名处于劣势地位,这些“漂”在美国的“纽约客”在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和对抗中,“根”被消磨殆尽甚至折断,在他乡异国这个空间上演着迷失、彷徨、堕落乃至死亡的悲情戏码。返乡无望的“纽约客”们会由于空间位移与差异性空间激发出的漂泊感构建出异托邦空间场景。比如《谪仙记》里多次出现的空间场景——麻将桌,“四强俱乐部”的成员们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但只要上了牌桌,就与外面的纷扰再无关联,空间的封闭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割断了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表面上看打麻将是李彤们私下打发寂寥的法子,但这何其不是她们在异国他乡缓解无法融入“他乡”的孤独和寂寞的办法呢?她们固守着打麻将这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为的是获得与精神原乡联系的机会。而李彤对麻将失去了兴趣,与姐妹们渐行渐远,所以当听到李彤的死讯,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李彤就不该去欧洲!中国人也去学哪些美国人,一个人到欧洲乱跑。这下在那可不真成孤魂野鬼了?她就该留在纽约,至少有我们几个人和她混,打打牌闹闹,她便没工夫去死了。”[4]这一方麻将桌如同小小家园,呆在内里是安全的,只要迈出一步去外面“乱跑”,就面临风险。正如福柯在《另类空间》一文中说到的:“异托邦是个真实的所在,供行为异常的个体置身其中,共同反抗某种社会秩序。”[5]这个封闭的空间是身在异域的“纽约客”们能相互慰藉、麻痹神经、释放他者身份焦虑、对抗西方异质冲击的异托邦。
这种意蕴丰富的“空间意向”在《芝加哥之死》里也可窥一斑。地下室起初也是作者替吴汉魂在大洋彼岸芝加哥城构建的异托邦。刚住进这间地下室时,吴汉魂听到窗外喧哗,看到窗上人影幢幢,总不免要分神,于是他每逢看书就用手把耳朵塞住。“听不见声音,他就觉得他那间地下室,与世隔绝了一般”,冬天大雪把地下室的窗户完全封盖起来,这让吴汉魂“很有安全感”。[6]透过地下室窗子传来的芝加哥街头的噪音、浪笑、扭动的人影、各色路过的小腿如同西方工业文明的浓缩符号,构成了与平和、含蓄、温雅的中国气质完全不同的异质空间,而地下室让身处异国他乡的吴汉魂生出安全感,说明在这个喧闹、嘈杂、充满欲望的西方城市里,吴汉魂精神上的隔膜和疏离感一直困扰着他,他始终是个局外人,地下室是他唯一容身之所,是他逃避现实的、用书籍、知识筑垒起来以隔离外界重压的希望空间、精神异托邦。即使后来读博得了奖学金,他也没搬出去,他把钱省下“寄回台北给他母亲”。由此可推测,吴汉魂能在这“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的地下室苦读六年,除了“求知的狂热”,临出国留学时母亲在他耳边的嘱咐——“趁我还在,回来看我一趟”也许才是他的精神支柱。这间位于芝加哥城中区南克拉克街的老年公寓的地下室,承载着他要在母亲有生之年与其见上一面的期许,这是漂泊苦读的吴汉魂与母体家园唯一的勾连。然而,母亲的离世斩断了吴汉魂内心残存的母体文化之根,当他煎熬地度过考试和毕业典礼并回到这间地下室,濒临麻木的吴汉魂重新感知地下室的空间肌理,四面八方涌入的噪音、“幻灯片似地扭动的人影”、室内的霉味混着炒菜后的油腻,特别是地下室书架上的书本“全变成了一堆花花绿绿的腐尸”,发出“一股冲鼻的气味”,他夺门冲出这间地下室……。由于原乡亲缘寄托瓦解,地下室已丧失与“根”相连的空间功能,从而异化成类似于“古墓”的社会空间,由此产生的疏离感和恐怖感让失“根”的吴汉魂“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他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定心力”。[7]在这里,白先勇交互进行地下室空间书写与人物的内心空间描写,在写实与象征的交融中,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具有深远意蕴的文化表征空间。
二.陈谦的空间叙事
(一)故乡的异域化书写
中国广西是陈谦小说里常见的地域空间,这与她的个人经历相关。从小与父母住在广西农学院,又上了一墙之隔的广西大学,用她的话说是在“大专院校扎堆,自成一体”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大”,成年以后,“一离开广西就到了美国”,所以广西对陈谦是“一种很自然的经历”。[8]换而言之,当陈谦决定在大洋彼岸进行书写的时候,广西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她的叙事框架。
“真是重峦叠嶂啊,深浅不一的黛蓝,拥到窗前的是那么墨绿的凤尾竹,再远处是苦练楝,那是画都画不出来的美。所以听人讲‘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就说,那样的山水,广西到处都是,更美的都有啊……”[9]这是作者在《繁枝》里借叶阿姨之口发出的对广西大山的赞美。这种在广西随处可见的美,时隔多年由身处美国多年的陈谦笔下输出,往往产生了一种颇具魅力的陌生、奇特和神秘感。以《特蕾莎的流氓犯》为例,“那里的山是青白的峻险,土是红色的赤贫;融江穿城而过,岸边很多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凤尾竹低矮茂密,将江水映成碧绿。朱瑾花硕大艳丽的花朵,沿着河岸高低错落的怒放。一些江湾上,翠竹蔽过江面,江水清澈见底,忽然抬头,就是万仞峭壁。山民就凭垂下的青藤攀崖而上,采药挖宝。”[10]“很多芒果树,很多扁桃,菠萝、木瓜、香蕉, 酷暑和溽热,白热化的天色,疯长的植被铺天盖地,碗口大的朱槿花红白黄粉。 金包铁、银包铁、五步蛇、竹叶青,数也数不清的毒蛇,它们一口能要人一命。”[11]作为叙事背景的南疆亚热带地区空间,其颇带野性的特色给人物的故乡添了一抹异域色彩。有论,当迁离故土的人对故土或批判或怀念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是一个作为故土他者的域外之人。[12]陈谦在美国生活多年,当她借笔下人物对故乡进行回望的时候,赞美是由衷的源于对故乡的怀念与热爱,但同时,故乡广西是否已内化为一个异域空间?她在访谈中提到:“我还乡, 都找不到我以前的故乡了。”[13]所以,她笔下呈现的故乡,无论对现今仍居住在故乡的本土人还是身处异地的外乡人,包括作者本人,在现代文明的关照下,都如同一个异域空间的存在。对小说中的人物而言,比如《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的静美(特蕾莎)、《繁枝》中的立惠,她们成年后在国外留学、成家、立业,故乡作为其年少时期的本土地域,无论是明艳还是阴冷,往往承载年少成长经历的欢乐、痛苦和困惑;而对作者,“广西的记忆对我来讲, 就是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是对已逝去青春期成长记忆的怀念:“我所有关于故乡和青春时代的记忆,只能留在我的小说里了”。[14]于是,小说中的人物与作者一样,多年之后在美国重启对故乡的印记时,多重时空的隔绝与变迁使得广西这片湿热的土地如同怀旧的青春电影一般,在回忆中化为漂浮的异域。
(二)异域空间的暖色书写
相对于融合了人物成长经历的对广西故乡异域化的书写,陈谦小说中对身处的异域空间——美国的书写显出不同传统的笔调。以移民华文文学中十分常见的地下室空间描写为例,“当深夜里房内的灯终于黑下,她一抬眼就能看到半截埋在地下的小窗,铁栏杆外街灯暗暗的光亮从窗帘下泄入。人行道上只要有人走过,路面跟下水道间的铁板就发出空洞而沉重的响声,她一时有些恍惚, 好像是躺在了在华北农村插队时躺过的炕上。郭妍摸了摸枕下仅有的七十五美元,生出很强烈的预感——她将在这个传奇的大都会正式开始她传奇的一生。”[15]这是《无穷境》里的郭妍回忆初到哥大与同学住在哈林区地下室的场景,相比半个多世纪前白先勇笔下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要温和得多,地下室里升腾起的跨域想象将过去记忆、当下处境与未来预期联系在一起,弱化了其作为移民边缘身份标识的空间功能,被赋予了希望,承载了个体对未来的正向预期,而不是毁灭的“坟墓”。此外,陈谦对异域的室内场景和室外空间描写也显现出可控的平和:“立蕙抬起头,看到高高木架上盛开着各色指甲花的铁网吊篮,稀疏有致地随风微微摇摆。它们在加州初夏明艳的阳光下,……变出一片柔和迷幻的彩色,让她本来忐忑的心境安静下。”[16]这是《繁枝》里,立惠与叶阿姨见面场景空间的风物景观,作者从人物所处的空间入手,细腻而生动的描摹让人觉得随意而柔和。再看一段融于《特蕾莎的流氓犯》叙事中对室内场景铺陈摆设的细致描摹:“她回过头去,看向左边,……墙色是明黄,……灯光透过花蕾样的铁雕灯罩四下洒开,在黄红的基调上打出暧昧而温暖的光色,令她觉得安全,又有点儿感动。”[17]这些对异域空间的描写给人温暖而亲切的感觉,如同作者从熟悉的有感情的生活中信手拈来,“是异域在日常化熟悉的笔触中不自觉传达出的本土在场。”[18]这种对异域空间的安全感和认同归属感还体现在小说人物的行为和价值观里,比如《繁枝》里立惠的丈夫,留美学成定居硅谷,工作之余热衷的是到旧金山当义务城市导游,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看那些漂亮的维多利亚建筑群,这何尝不体现了新一代华人异域生根的接受?《无穷境》里的珊映,在初次创业时“意识到由一代代斯坦福校友所秉持的‘通过创业改变世界的传统”在自己身上落实下来,无论是面临技术、资金困难还是遭遇女儿夭折、婚姻破裂,她仍然坚持不懈创业,福斯坦的价值观、硅谷文化精神与她内置的“烟花梦” 相辅相成并内化交融,体现了作者对斯坦福价值观以及硅谷文化的认同。
三.白先勇与陈谦空间叙事比对及分析
白先勇和陈谦的小说创作同属海外华文写作,以异域为叙事主场的叙事空间在异域、本土间不停跳转,但两者对本土、异域空间的描写投射出截然不同的主观情感、精神作用或美学思想,我想这是源于作者的迁移经历、创作经验和写作的时代背景的不同。
白先勇的童年正值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时局的变化以及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导致他自幼年起就不停辗转于桂林、上海、南京几个城市,后来又不得不去了台湾,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到美国继续学业,最后学成留美定居。多次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迁徙深刻地影响了白先勇,造就了他强烈的空间体验感,他又将不同的地域空间给予的不同情感体认投射到小说中。特别是1963他大学毕业后从台湾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当时的白先勇处于极度精神困境中:他对美国的印象很不好,因为他姐姐之前也赴美留学,可三年后却因精神分裂而被接回台北;赴美前几天,被白先勇视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母亲刚去世,而父亲已到暮年。偌大的家族四分五裂,父母庇护不再,在此境遇之下由台赴美的迁徙对他的冲击要比当年从大陆到台的迁徙大得多,大到犹如“断根”。他在回顾自己文学创作经历时说:“初来美国时,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19]赴美一年后,他才重拾文学创作,陆续写出《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天》以及《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冬夜》等反映留学生、移民生活以及那群身在台北心在大陆的异乡客境况的故事。对第一次迁徙,白先勇以一本《台北人》祭奠,道尽了繁华不再,乡愁无解。对第二次迁徙,他以《纽约客》的故事记录下来,说尽了“无家可归”的彷徨与恐慌,揭示那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乡愁。如果说第一次迁徙时白先勇年纪尚小、家境优渥,没让他生出离乡的伤痛,那么第二次迁徙空间转换对他产生的影响之大让他不仅体验了“生离死别”“人生忧患”,还切肤感受到了父辈的“繁华不再”“返乡梦碎”的无奈与凄凉,并影响了他几乎整个文学创作主题。再考虑到作者创作的年代集中在上世纪60-70年代,这段时期里,一方面台湾经济尚未出现起飞,在极端务实的美国政权眼里,台湾是个败退到边陲的旧政权的残余,全靠美国的经济、政治扶持才能在国际政坛上存有一丝存在感,而在美国民众眼里的认知度极低。白先勇作为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在美国自然能感受到被无视的“loser”(失败者)的凄凉;另一方面自50年代起,中国大陆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隔离在国际社会之外,海外的中国人接触不到也无法感受到中国的存在。阖家返乡幻想的破灭、与母体文化的失联加上异域的巨大文化冲击衍生出浓重的孤独感,让白先勇“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20]可以说,20世纪60-7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白先勇海外留学与生活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战后台湾与整个海外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从上文的文本分析我们看到,白先勇通过人物的言语和回忆构建了一个或繁华,或祥和,或荣光的“故国家园”意象空间,这个空间显现出“乌托邦”的意味。“烏”意及“乌有”,消解了实现的可能;“托”指承托、寄托某种完美的希望;“邦”是“地方”的意思,可理解为一个空间。“乌托邦”式的“故国家园”叙事映射出作者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对“故国家园”的归属感和无限的依恋与缅怀。对“异国他乡”这一异域空间的表达,作者主要呈现的是一个与中国气质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工业现代化的意象空间,喧嚣、扭曲,并在这空间内部同时搭造“异托邦”,这个“异托邦”是与中国母体文化相连的有意或无意的封闭,有形或无形的界限,在身处的西方文化空间里呈异质、不同和另类的存在,可依托和寄托故事中人物和作者本人对故土的思念或某种本真的希望。正如Mike Crang(迈克·克朗)在Cultural Geography(《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说到:“‘家被看作是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的地方……开头总要背井离乡,因此返家总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数不清的故事不断地证明着返家是多么困难,……通过这种结构所创建的‘家的概念可以称作是怀旧小说,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21]“家”的概念在迈克·克朗那里是已经被扩大了的地域空间,到了白先勇的笔下则进一步漫延到“过去”的时空场景,囊括了家、故乡和一切能给予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事物,成为一个时代游离在母国之外的华人的精神家园。白先勇作品里对故国家园的乌托邦式的叙事和在异国他乡的异托邦书写始终围绕“乡愁”这一主旨,承接了海外华人写作的 “离散”“漂泊”“寻根”主题传统,他通过小说创作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乡愁空间,将个体的悲剧融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精神遗传性。
陈谦的叙事时空结构与白先勇很相似:现在-过去-现在、异域-本土-异域、硅谷(美国)-广西(中国)-硅谷(美国)。故事发生在现在异域的美国,过去本土广西发生的事情成为本场叙事发生的起点或原因,叙事在现在/过去、异域/本土、硅谷/广西场景空间不停跳换。回忆里的故乡不再是类似白先勇的希望的寄托和精神的慰藉,而是真实地承载了人物青春年少的经历,融合在叙事里,推动叙事发展,在多重时空的隔绝与变迁下已被重新构建成异域。陈谦的故乡异域化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多年在美国的生活影响了她的价值理念:“美国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强调个人身份标识的地方。你的经历越独特,你的自我 ID,就是所谓身份的标识就越清楚。你的来历若与众不同,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22]这份故土的异域抵达是她对自身价值的呈现,彰显了作者和人物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成为一种艺术得以成为艺术的框架,内在于其创作思维之中”。[23]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本场的异域(美国)叙事时,不同于前辈白先勇笔下冷漠、粗暴、喧嚣、扭曲的异域空间,陈谦的异域空间叙述弱化了来自差异空间的极端的情感体验,更服务于人物成长的实现。异域空间被赋予了暖色,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温暖的色调和安逸舒适的环境不仅给读者一种安定亲切的感觉,还投射出人物对自己所置身的空间的归属感。陈谦对异域空间的暖色书写消解了异域的陌生和冰冷,无形中弱化了长期以来北美移民文学中所侧重的“文化冲突”主题。在我看来,陈谦从广西南宁到美国硅谷的两级跳,更多的是自己人生水到渠成的规划的实现, 而不是动荡时局下随波逐流的无奈选择,更不是生离死别,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返乡无望的悲凉、无家可归的惶恐,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探寻、人性的反思,她涉及本土和异域双重空间结构的叙事消弭了以白先勇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台湾留学生的“乡愁”主旨,不再局限于国家民族的先验性叙事框架,成为探索个体心灵之旅的场域,这是作家的身份使然。正如霍尔所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24]白先勇和陈谦分别作为两个时代的海外华文写作主体,在其社会生活经历中形成的对自我的认同不同,时间与环境的流变,海外华文写作主体的方方面面也发生改变。陈谦是1989年从大陆赴美的留学生,中国改革开放已有十年,相信陈谦对美国是有所了解的,对留学生活的艰苦也是有预判的,离开故土踏上异国他乡而带来的异域文化冲击不会滞留成心头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是成为空间转换过程中的正常过渡。此外,作者在美国奋斗的三十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的三十年,是华人群体身份、地位转变提升的三十年,待到她从事创作的时候已年近中年,作为在技术精英荟萃的美国硅谷拥有职位的工程师,过上了祖辈难以企及的优裕而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她对本土、异域空间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完全异于半个世纪前处于精神困境中的白先勇辈,所以在陈谦笔下,本土和异域“两者都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戏剧化场景,而是意味深长的生活世界”。
地域空间感是移民作家特有的创作资源,白先勇和陈谦都充分挖掘这一来自自身经验的宝库,围绕本土和异域进行极具特色的空间叙事,并在各自的文学叙事中投射出不同的空间感知。这种空间感知包含着地理层面空间位移带来的怀乡与具有疏离感的审美,也涵盖文化层面上的与他者文化间的隔阂、对抗或认同、兼容。时隔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国政治、经济地位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增强,华人在美社会阶层变化都使得作为海外华文写作重要标签的地域空间叙述的表述方式已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空间场域不再戏剧化、前景化,且远离了“文化冲突成为基本的叙事动力,个人的悲欢离合被放大成民族国家的整体遭遇”这一民族寓言的审美模式;另一方面,各种空间元素交汇融合,作为现代主义的布景和符号,成为一种“类似面具标示的生活成分和身份要素”。
参考文献
[1]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14:40.
[2]白先勇.台北人(汉英对照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53.
[3][4]白先勇.纽约客[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9-40, 29.
[5][法]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52-67
[6][7]白先勇.芝加哥之死.https://wenku.so.com/d/9b48ba66363a3644510a480cceaba963(2022.1.12)
[8][13][14][22]黄伟林,陈谦.“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海外华人作家陈谦访谈录之一[J].东方丛刊,2010(02): 192-202.
[9][16]陈谦.繁枝[M]//我是欧文太太.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7:1-108.
[10][11][17]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M]//谁是眉立.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2016:1-37.
[12][18]秦姣娟.花果非飘零,灵根在自植---論陈谦笔下本土和异域的置换及其意义生成[J].名作欣赏:115-117.
[15]陈谦.无穷境[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29.
[19]黄宇晓.白先勇赴美前后的困境与突破[J].华文文学.2003(02):30.
[20]白先勇.树犹如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85-386.
[21][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60-61.
[23]颜敏.异域的位置——探寻陈谦小说特质的可能路径[J].南方文坛.2015(01):81-85.
[24]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2):40.
基金项目:2018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桂籍海外华人文学创作比较研究”(项目号:18FWW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