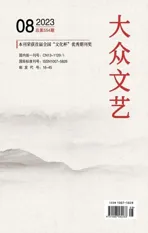论石川啄木诗歌中的物哀美
2023-08-22罗凤
罗 凤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 116029)
一、知物哀
当物哀作为一种审美范畴被承认时,它与人类艺术史上的那些极其特殊的样式概念不同,即不仅仅是某个民族、某个时期的特殊产物,而是必须能够概括美的本质,至少要在理论上具备体系性和超越时间的普遍性。自其问世起便如阴影面纱一般笼罩了岛国日本民族的漫长历史,宗教、文学、美学等都不同程度上着上了物哀的底色,甚至说物哀是日本美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不为过。
事之心,也可以叫作知物之心,即知晓物哀之心。将“物哀”作为日本民族特有的美学概念展开讨论,须将其置于一般意义层面展开讨论。物哀之哀与汉语中表现哀伤、悲哀、哀痛之哀不同。在《大言海》中,大槻先生从三个方面对“哀”进行了解释:作为表现喜怒哀乐等人类一切感情时所发出感叹之声,与汉字“噫”相同。而在同“噫”字时,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表现赞叹、赞赏之意,可译为“值得赞赏的、优异的、很棒的”,与汉字“优”同。而具有“可爱、很疼爱”意思的动词憐れむ(ffわれむ),则是这个词的活用;二是感叹词“哀”以名词形式专门表示悲伤情感时,可以理解为“可怜的、令人伤心的”意思,这时与汉字“哀”在表现上相同[1]。而物哀之物,是指世间万物。具体来说可以表现为人们精神思想中想象的某物、感受到的各种事物;通过耳目口鼻感受到、认知到的事物。一言以概之,物哀之物包括的范围极为广大复杂,但也存在不属物哀之列之物。
因而物哀一词可以解释为人们在谈论某事物,赞叹某事物,观看某事物,讲述某事物,恐惧爱恋某人某事物时表现出来的、感受到的一切情感:喜怒哀乐也好,爱恨离苦也好,均在其中。
在本居宣长看来遇到应该感动的事物而感动,并且能为之缘由动容理解即知物哀,而在面对应该有所感悟却无动于衷之人则为不知物哀之人,自然也不能理解感动之心。[2]163更为细致的话可以这样表达:看见春日盛开的樱花林感动于樱花之美,又深深地为其虚幻无常所震慑;看见花、月忍不住感动赞叹“多美的月呀”“多美的花”;听见或眼见身边的亲近之人承受痛苦,能明白其哀伤之因,自己也悲从中来,自然地感而哀之,叹之。而这正是石川啄木诗歌中第一层物哀美所在。
不论是面对自己的情感、面容相貌抑或是身边亲近之人的遭遇,甚至是素不相识之人,石川啄木总能敏锐而深刻地感受到并在诗歌中呈现出来:
森林里边听见枪声,
哎呀,哎呀,
自己寻死的声音多么愉快。[3]7
一生都处于人生穷困逆境的软弱诗人,一面畏惧于生,一面又畏惧于死,始终向往着幸福生活的平静或是死后世界的寂静。然而诗人的散漫、慵懒性格使得石川啄木既无法改变赤贫的现状,长久地过着卖文为生的生活,又怎么也做不到从自己的死亡之中寻到解脱[4]。关于这样的心境与现实,可以在《可以吃的诗》中有所了解。
因而,听到他人自寻死的枪声对他而言是愉快的,在那枪声之中石川啄木既感受到了他人的不幸与勇敢,勇敢地追求死后世界的安宁,而这也是石川啄木所追求的,好比暗夜行路,突然发觉身边竟有同志之士,自然而然地觉得愉快了。“面对应该感动之事而感动”正是如此,面对他人的悲哀与寂寞,石川啄木总能敏锐地感受到,并在其中寄寓自身对其的情感,或悲伤,或痛苦,或深深的同情。这与本居宣长所说的看见花月而感叹“哇,多美的月啊”“啊,多好的花呀”是一样的,体现了诗人知物哀之心神之所在。面对他人的情感能感动,并理解感动之心,明白地通晓事物之心。
在面对自身时,不论是内心的精神感受还是肢体举止与外貌,石川啄木的感受更为敏锐、深刻,甚至达到了过分的地步。
说是悲哀也可以说吧,
事物的滋味,
我尝得太早了。[3]56
正因为抱有崇高的理想,
才会启程,
也才会有辛酸的眼泪。
流水不复回。[3]82
诗人自己的无奈、可怖、悲哀、吃惊,离开故乡的迷茫,失败后的苦涩体验等情感诗人向来是不回避的,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就表现出来什么。然而有几点需要说明。[5]10
第一,物哀非哀。物哀并非特指以悲哀为代表的消极类情感,沐浴着物哀美的事物并非只能是消极的。面对喜悦、惊喜、愉悦等积极情感也是能产生物哀感、形成物哀美的。人们若能感受到喜悦等情感,并为之感动,那同样是知晓物哀。只是人们面对高兴之事、有趣之事的感触并不深刻与持久,而面对悲哀之事、思恋之事的感受,却不由得刻骨铭心,其中尤其是受阻的男女恋情之事。喜悦之中的物哀美与悲哀之中的物哀美,虽同为物哀,但是其美学风格究竟不一样。石川啄木诗歌中的流泪、吃惊、无奈、寂寞等,往往比其诗歌中的喜悦、愉快更加动人。那些表现消极情绪的诗中有着更浓郁的物哀美感在其中。
第二,人类之所以与其他物种不同,是因为人类拥有情感与思想,人为万物灵长,心底聪慧,思虑亦深,经历的种种事情皆有所感。但虽同为人类,人们对事物的辨别与认识也是存在差距的。有的人仿佛在感受之上天生优于其他人,与深知物哀的人相对照,有的人近乎不知物哀。遗憾的是不知物哀者往往是大多数,不过也并非完全不知,只是程度深浅存在较大的差异。石川啄木的诗歌之美也得益于其优胜的物哀美。
二、超脱之美
石川啄木诗歌中常有超乎道德的美显现,或者说是不包含道德的美显现,这极具物哀之美。这似乎与其革命家的形象相悖,不过实际上确实如此。首先需要说明“物哀”这一词与道德的关系,关于物哀论的问世有着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出现总的来说是由内外力合力而形成的。它对日本民族古代文学特色的阶段性历史性的概括,可以看作其内因;而外因则是当时的日本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审美概念,因而尝试突破长久以来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依附和依赖,证明其独特性一种表现。此外,也可以将其视作日本民族审美观念的一个转折与变化。概括来说的话,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论,其意图在于希冀将日本民族的文学与审美从伦理、政治、宗教等领域中独立出来,剥离其多余的社会学属性,更多地保留其作为文学的审美属性。而同时在历史上的日本人很早便有了“国际”与“先进”这样的观念,尤其是在文学、政治制度等方面,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观念与零散的相关理论,在任何时代都以先进为目标,在古代,或以古中国为榜样,或以中国为比较对象,政治经济上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这是符合日本“和”的文化的。
因此,日本人常在解读其本土文学,如和歌、短歌、物语,乃至俳句,常常以中国的文学观念作为标准,证明其合理性、合法性,显示其优越性。尤其是在物语文学方面上,甚至到了忘却日本民族文学的特色的地步;加之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不断衰弱,经济、政治、军事上,日本民族尤其有深刻的认识,中国的文化宗主国形象不断弱化甚至消散崩溃,呈现出大国落败的景象。不仅如此,这样的认识也辐射到了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物哀论主要基于以上两点趁势而出,俨然一跃而成日本民族的文学标语与口号。它与中国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以佛教说教、不以儒家伦理纲常、不以法家法纪为标准来审判文学,在回归文学审美的自律性的同时试图彰显出日本文学、美学思想方面的独特性。因此物哀这一观念自然就不包含道德,或者超乎于道德之上。
这一存在于日本民族精神的观念自然也影响了石川啄木,石川啄木诗歌中这样超乎道德或者不含道德的美时常可以发现:
交换了很长的接吻后分别了,
深夜的街上,
远远的失了火。[3]145
这里的“失火”,并非浪漫想象上的恋人的脸红,是实实在在的火(火灾),却又给人恋人脸红、接吻温柔的想象。同时没有“同情”“怜悯”“集体与个人”等道德思想掺杂在里面,这首诗就只是描写恋爱的美好的。在夜晚火灾的光热照映下,想到的是恋人的脸红,不禁又想到恋人的温柔可人,光彩夺目。这里的“失火”恰到好处,“火灾”事大,“恋情”事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好比国家事大,个人与家庭事小一般。石川啄木的诗歌将这一点反转了,大的火灾下仍想到的是恋情,更突现其恋情的美好可贵,宛如夜里的火一样,终会消失在夜的黑暗之中,正是如此更觉恋情可贵,让我们更多作为普通人的脆弱的情感有机会在凛然庞大的家国大义面前存活下来,不含教诫之论。
同时“失火”的作用不仅在此,也为体验物哀提供了一个时空上的场所。最能让人知物哀的是刻骨铭心的男女之情,即男女恋情,而在恋情中最使人知晓物哀的是包含着悖德的恋情。石川啄木这首夜晚失火的诗歌便可以归入其类,然而这并不是对于悖德的欣赏,也绝非推崇,任何国别的文学作品绝不会以单纯的悖德作为审美对象,更多的是借助悖德这一形式表现其背后的东西。在石川啄木这里而是为了表现物哀。关于这一点本居宣长有个精彩绝伦的比方:将污泥浊水蓄积起来,并不是要欣赏这些污泥浊水,而是为了栽种莲花。因为如果要欣赏莲花的美丽,就不能没有污泥浊水,任何草木花朵离开土壤都无法生存。日本民族文学作品中常有对悖德的恋情的描写,而这正如蓄积污泥浊水,是为了得到美丽的“物哀之花”[6]84。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多处悖德的恋情多有此意。夜里的失火好比蓄积的污泥浊水,而恋情则是美丽的物哀之花,失火时的恋情,是存在于人心真实可贵的悖德,也是知物哀的表现。当然还有其他诗句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比如:
认真的拿竹子打狗的,
小孩脸,
我觉得是好的。[3]23
想把爱犬的耳朵切了来看,
可悲呀,这也由于这颗心对事物都倦了吧。[3]13
这些诗歌都可以很好的佐证其悖德的美感这一观,诗人当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三、脆弱之美
石川啄木诗歌的审美效果中有着物哀的脆弱性。所谓的脆弱性,在日本民族的社会中是指就一般而论,真实的个人情感不论年龄大小都如同无力的、年幼的孩子那样幼稚而胆怯,个人情感的本质并不是他人看得见的那么个性坚强、充满智慧得,而多数情况下都是假装出来的,或者是背负如何如何的身份不得不去做的。但是如果能剥离其社会人的属性与伪装,那么就很容易发现外在看起来怎样怎样坚强的人、怎样怎样智慧的人其内心深处多与孩童无异:胆怯、懦弱、愚昧。
日本文学史上多有这样坦白地或者隐秘地表现脆弱的文学作品。由于日本与我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因而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对于这一点是极力隐瞒的,甚至是批判的,很少是正面褒扬的。对于英雄男子是不允许有这样的情感表现出来的,那是默认专属于懦弱胆怯者或者女子的,成人男子甚至是少年多是勇武豪气的形象,然而这是极不真实的,人情的真实仿佛女童,本色天然自成,无所依傍。[7]
古代中国人写的书,即使是武士奔赴沙场献身的时候,也多是描写他们表面的英勇行为,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边塞的凛冽旷丽风光。而实际上,如果不加掩饰地表现那样将士的内心世界的话,会发现这些将士在死前也会想念家乡父母、想再和妻子见上一面、不舍温柔的恋人……这些都是人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会有的人之常情。没有这样的情感的话,是连草木都比不上的,即沦为不知物哀之列。然而,古代中国人写的书却隐瞒这一点,隐瞒这样的真实人情,只描写其冠冕堂皇的一面,一味表现其如何为君效命、如何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这样就失去了人情脆弱的一面,湮灭了真实的人性,如果只管写出自然真实的人情,将世间种种人情真实地呈现出来,那样使得读者了解人情实态并“知物哀”,那样的书可论为佳品。那样的脆弱性是可贵人性的一部分,不论男女,不分老少,都会有的一种性质,是真实生命的组成部分,伴随人的一生。
石川啄木的诗歌呈现出来的那份令人感动的脆弱性更是优美,可以说石川啄木诗歌的美很大部分都是由这份脆弱性支撑起来的:
在东海的小岛之滨,
我泪流满面,
在白沙滩上与螃蟹玩耍着。[3]7
说是悲哀也可以吧,
事物的味道,
我尝得太早了。[3]53
不论是“流泪”,还是“悲哀”这样的字眼,一方面,无一不是坦率直接地表明了诗人作为男子内心深处如女童般幼稚愚懦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些情感又普遍存在于读者和其他人心中,石川啄木不过真实地表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只管描写真实的世间人情,把人类情感中的脆弱性表现出来,又不失为优美。将人们从成人的社会里解放出来,暂时消除其社会人形象,回归年幼时期无所依傍的自然状态。物哀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追求自然纯真,不论是谈论某事物,讲述某事物,观看某事物,面对某事物,欣赏某事物,遇到应该感动的事情而感动,该悲伤时而悲伤,欢喜时欢喜,若遇到应该感动的事物却麻木不仁心无所动,就是毫不理解人性中那份脆弱性,就是“不知物哀”,更甚者则是无心无肺之人。这样的观点与现代美学所说的“移情”“本来的移情”“象征的移情”等观点有着相似之处。从这一方面来看石川啄木的诗歌,就不难理解其为何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他作的诗歌是“千古不易”之调,而非“流行”之作,自然而然吸引了广大读者。石川啄木的诗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总能诱发人们心中怜悯、脆弱、难为情的部分,然而在石川啄木看来是人都会有、都应该有的部分。其诗歌中的“悲哀”“哭泣”“流泪”等,实际给读者提供了一条通往寻找真实自我、真实人性的道路,也就是为读者体验物哀、感受物哀提供了一条便捷,其诗歌又因此而具备独特的纤细的物哀美感,可以说是人情的美感。脆弱之物自然有其脆弱之美,豪山存在其美,杨柳枝亦存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