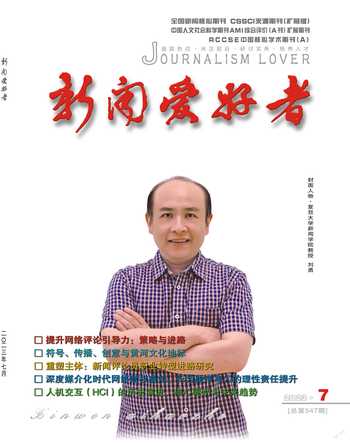基于扎根理论的粉丝文化对个体长时段影响研究
2023-08-10刘纯懿
刘纯懿
【摘要】粉丝文化日益成为一种显性的青年亚文化,同时作为一种不断溢出自身文化边界的网络流行文化而受到商业资本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瞩目。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搜集了15位受访者的资料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性编码,对中国本土粉丝文化对个体的长时段影响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粉丝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发展、社会化、价值创造和媒介素养四个方面,同时这些不同的影响层面又发生着交叉和缠绕的相互作用关系。
【关键词】粉丝文化;青年文化;扎根理论;长时段影响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后,伴随着媒介技术变迁和文娱产业的数字化、平台化转型,加之一批在韩工作的本土练习生的归国和回流,粉丝文化开启了一个以“流量明星”和“饭圈文化”为关键词的新时期。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在内嵌于互联网治理大背景中的“清朗”政策的开展,以流量、数据为支撑的互联网文娱产业以及在资本逻辑和平台规则型塑之下产生的新一代“产业倒逼型”粉丝又一次地被问题化和对象化为需要引导、治理和规范的客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粉丝文化研究甚至是受众研究开创以来一个古老但从不过时的命题再一次被重提,即媒介文化与受众的关系,具体到迷文化领域就是迷文化对粉丝个体而言究竟影响强度何高、影响层面何在、影响范围何广。在文娱产业和治理政策均风起云涌的当下,重思这些基本问题展现出了格外重要的时代及历史价值。
一、本土粉丝文化研究纵览
粉丝文化/迷文化研究是一个较为晚近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粉丝文化研究浪潮开启至今也不过三十年的时间。伴随着世纪末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粉丝文化研究也终于在中国本土登陆并开始了在地化的发展历程。于是,来自西方的粉丝文化研究理论和中国在地的、具有另类实践的粉丝文化产生了碰撞和交融,中国的粉丝文化研究也因此具有了携带有本土经验和印痕的其他面向。
国内最早的粉丝文化研究开启于20世纪90年代,其诞生的背景除理论的引进之外,还有我国港台地区流行文化之风吹向大陆或内地并由此引发的大陆或内地第一轮“追星热”。中国早期的粉丝文化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精英主义立场对偶像崇拜行为的批判,比如将偶像崇拜看作是一种低龄的、盲目的、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的行为[1];又比如将追星文化视作一种带有青少年青春期特征的、需要被引导和教育的客体化对象[2]。可见,这一时期的粉丝文化研究更多采取将其“病理化”的叙事,这些研究往往基于一种“拯救病态者”的父爱主义式态度将追星文化看作是需要被解决的社会问题:对其表述也主要从迷群行为的负面影响和引导策略等方面进行建构,如《痴迷男女追星忧思录》(1994)、《追星现象与审美引导》(1999)、《青春期“追星综合症”观察与透视》(2002)等研究都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展开。
本土粉丝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开启于2005年,这一年产生了现象级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以及由此诞生了国内最早一批组织化、规模化的粉丝群体,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虽然依然延续之前的研究框架,但国内粉丝文化研究分水岭也开始出现。突出表现是开始辩证地看待粉丝文化,一改之前全面否定的态度倾向,比如有學者将追星行为看作一种“正常的准社会交往行为”,具有选择认同、情感控制、行为节制等理智特征,并将其与完全认同、迷恋、行为投入的偏执追星区分开[3]。也有研究将中国的迷文化看作是一种仪式性的交流活动,这种传播仪式观的分析框架时至今日都活跃在粉丝文化研究的领域之内[4]。
《超级女声》的流行和中国本土大众流行文化的发展使得粉丝文化日益跳脱出青年亚文化的范畴而成为一种更为大众化的文化现象,本土学术领域也展现出了对于粉丝研究建构自身学术框架和理论话语的紧迫性。首先是对国外粉丝文化理论的引进工作,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就从“粉丝与文化消费”“粉丝的情感与认同”“粉丝实践中的身份政治”“粉丝社群与赛博空间”这四个角度梳理了国内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5]。其次是有意识地建立国内的粉丝文化研究框架,《青少年偶像崇拜系列综述》从年龄、性别以及代际差异三个维度对当下中国青少年偶像崇拜所作系列研究进行了总结,同时也为学界了解中国年轻一代的迷文化提供了具有本土经验的研究材料。2010年台湾学者张嫱所著的《粉丝力量大》是国内第一本粉丝研究的专著,该研究基于大陆、港台和日韩的迷文化中偶像与粉丝的关系,叙述了偶像崇拜和粉丝文化的形成,从文化研究和科技变迁相结合的视角说明了粉丝经济与偶像产业的内在机制,重点分析了粉丝在当下的文化产业和创意社会中所占据的关键性地位[6]。
在本土粉丝文化研究开展近30年的过程中,粉丝文化对个体的影响研究始终是该研究领域中被重点关注的议题,有研究认为偶像给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一定的导向作用,但是也存在拜金、功利、无为、主体性淡化等消极影响[7]。也有研究从辩证的角度看待粉丝文化的影响,其积极一面有满足心理情感需求和提供动力支持,其消极一面也展现出误导性行为(如暴力)、偏离主流价值观和影响正常生活[8]。
在众多较为笼统的粉丝文化影响类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具体的面向和视角,比如性别视角的研究认为粉丝文化是女性突破家庭领域介入非体制性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女性欲望的安全表达的场所[9]。粉丝社群成为年轻女性自主表达,积极作出社会行动的过渡空间,是一个“公共人”的娱乐性演练。再比如基于媒介视角的研究采取网络民族志方法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粉丝行为会影响粉丝的人际关系社会化、角色社会化和价值社会化[10]。另外,随着近年来资本对粉丝文化的介入和粉丝文化所出现的“饭圈化”新形态,也引发了人们从产业角度重新思考这一命题。比如有观点认为资本市场干扰和网络社会发展使得饭圈文化偏离了文化自身的公共性和公益性进而呈现出资本逻辑下的商业化、产业化特征以及群体的组织化和极化特征,外在表现是粉丝的低龄化趋势和非理性行为[11]。
二、基于扎根理论的粉丝文化研究框架革新
基于对国内外粉丝文化研究的综述,笔者发现在该研究领域中针对粉丝文化的影响成为一种“显学”,并且呈现以下几种特点:一是将粉丝文化影响的对象主要放置在青少年和女性身上,从而产生了一种年龄和性别视角的偏差;二是将粉丝文化看作是一种对受众施加强大影响的文化类别,并且这种影响更多是负面大于正面的,因此粉丝文化在学界和政策两方面都被建构为一种需要被引导、被治理、被规范的对象;三是这类影响研究往往缺少一种历史化的长时段视角,研究总在关注对青少年、对成年女性的当下研究,而很少探讨曾经受粉丝文化影响的人群在跨越了一个生命阶段之后回顾自己的成长经验所发现的该文化对个体的切实影响。
基于这三个特点,笔者革新了本土粉丝文化研究的视野框架,选择了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作为粉丝文化研究的核心方法,扎根理论在国内外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多个研究领域,这是一种强调系统搜集和分析经验事实并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行理论抽象的方法。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中国早期参与粉丝文化(即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一代粉丝,并著重探讨在跨越一个生命阶段之后这一群体对曾经参与其中的粉丝文化的整体影响评价,因此本文对受访对象的要求是:(1)参与中国最早粉丝文化的粉丝,包括但不限于早期港台偶像粉丝,最早的日流、韩流文化粉丝以及最早的《超级女声》粉丝等;(2)深度参与粉丝文化活动中,包括但不限于参与早期线上论坛、加入粉丝社群、参与早期投票拉票活动以及一系列线上、线下应援活动等;(3)距离参与早期粉丝文化活动已然跨越了一个生命阶段(从青少年进一步社会化进入成年)。
根据本文研究对象的特性,笔者采取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最终选取了在性别、地域、年龄、学历、职业均具有差异化和最大化信息表征的15份粉丝样本,以及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的3份额外样本,从而保证了抽样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对每位受访者进行了40—60分钟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最终整理了共计12万余字的访谈文本,根据扎根理论方法并应用ATLAS.ti分析软件对该文本进行了三级编码分析:
在第一级开放式编码分析中,本研究提取出41个初始概念,如职业道路选择、大学专业倾向、国族观念、社会关怀、团体意识、情感投射、社群归属感、群际强化、生产媒介文化内容、转型公共论坛、型构媒介规范等。而这些初始概念又进一步被归纳为16个范畴,分别是:发展道路、认知观念、情感支持、性格品质、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群建构、生产价值、消费价值、功能价值、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媒介更迭、媒介型塑和社会价值。
第二级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阐释和归纳,进一步识别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提高范畴的稠密度,从而形成相关的主范畴和副范畴。基于开放式编码的16个范畴,通过主轴编码可归纳为个体发展、社会化、价值创造、媒介素养这4个主范畴,各个主范畴及其对应的范畴及内涵也进一步得到了明细,比如“社群建构”这一范畴的内涵即为“个体构建或加入社群并获得群体身份的过程”,“社会认同”被进一步阐释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完成的社会分类和群际强化”,媒介型塑是指“个体对媒介规则、媒介内容和媒介形态的塑造”等。
第三级选择性编码是基于对主范畴的深入分析,理解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可统筹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解释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以及主范畴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描绘整体状况和脉络,从而搭建相应的理论框架。本文以“粉丝文化”为核心范畴,明确了相关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见图1)。在该典型关系结构的梳理和内涵基础上,粉丝文化对个体的长时段影响模型也得以搭建和阐释。
三、粉丝文化影响模型构建及结果讨论
(一)模型构建及概念阐释
本文根据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构建了粉丝文化对个体长时段影响模型(如图1所示)。由于扎根理论需要对模型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笔者选用额外的3份访谈样本,再次进行了编码工作。经过对比分析,没有发现新的主范畴关系结构和新变量,进而说明该模型已达到了理论饱和。
(1)个体发展。个体发展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个体对发展道路的选择,比如对所学专业的选择、对职业道路的选择、对兴趣爱好的选择等;个体发展还伴随着认知观念的建立,比如价值观的确立和对社会、国族以及世界的认知;个体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性格品质和道德精神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个体发展必然携带着生命周期的跨越和转折期的阵痛,因此情感支持的获得在个体发展过程中也尤为重要。粉丝文化对个体的作用恰恰经常出现在青少年时期或者人生转折期,并作为一种发展动力来源和情感放置场所对个体成长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社会化。社会化是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逐渐形成对社会的认识,适应并积极融入社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人格并发展出一套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仅包括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社会交往的形成和深入,还包含个体对特定社群的找寻和建立,以及个体如何在特定社群中确立群体边际、获得身份认同、拥有社群的归属感,而粉丝社群正是这样一种拥有明确群际、给予人身份和情感寄托的趣缘社群。
(3)价值创造。价值创造是指个体在发展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功能价值等。其中,经济价值主要指个体在参与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社会价值是指个体除经济价值之外的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包含文化价值、精神价值、传播价值在内的贡献。功能价值主要指个体在社会组织中所担任的职责、携带的组织功能等,比如粉丝在社群中所担任的贴吧管理员、后援会组织人员等职务。
(4)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12]。媒介素养包括对媒介的认知程度,对媒介的使用和参与、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媒介技术和媒介能力,以及长此以往地对媒介的反向塑造作用。而粉丝文化正是具有强媒介性的文化,不管是此前的大众媒介还是现在的互联网媒介,粉丝在参与粉丝文化的过程中都是以媒介为基础和中介的,因此在粉丝文化的影响中,媒介素养成了一个重要的面向。
(二)研究结果讨论与反思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粉丝文化对个体的长时段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发现对于青少年时期参与粉丝文化的人群来说,粉丝文化在其个体发展、社会化、价值创造、媒介素养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不同的影响又互相发生交叉和缠绕的作用关系。个体发展和社会化在粉丝参与粉丝文化实践中相互影响,二者共同作用在青少年的人生阶段跨越过程中,并型塑着青少年的发展道路选择、认知观念形成、性格品质养成、身份认同建构、社会关系组建等方面,因此也进一步推动着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创造。而在个体发展、社会化和价值创造过程中,媒介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也担任着彼得斯所说的“后勤型媒介”的基础作用[13]。因此,包含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媒介技能、媒介型塑在内的媒介素养也成为粉丝文化反身作用于个体的一个重要坐标。
在理论价值方面,本文主要讨论了粉丝文化及其内在所蕴含的媒介特性、组织机制和实践活动对个体的长时段影响。首先该研究突破了粉丝文化理论奠基人费斯克所认为的迷群和普通受众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类别上的不同[14],从而赋予了粉丝文化独有的差异性特征和合乎该特征的具体范式。其次,该研究将媒介视角纳入粉丝文化研究之中,因为伴随着媒介技术变迁和传媒体制的改革,粉丝文化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外显和内隐特征,仅从话语层面上来看,从“粉丝”到“饭圈”,从“偶像”到“爱豆”,从“追星”到“养成”,粉丝文化也经历了文本内外的更新换代,而这背后则是大众媒介和互联网及移动终端之间的媒介差异性,因此在本研究的样本选取中,特地选择了跨越媒介发展阶段的粉丝人群,以弥补粉丝研究中的“媒介视差”。再次,该研究将中国本土的粉丝作为研究样本,因为当前对粉丝文化的研究常常呈现出一种“削足适履”式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来自当前绝大多数粉丝文化研究框架依然是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舶来品。因此,通过对中国早期粉丝文化进行研究,有利于为当下的粉丝研究补充更多的一手本土资料,从而为粉丝研究理论更新提供更丰富、更有效的在地化经验。
在实践价值方面,本文著眼于从长时段的历时性角度考察粉丝文化对个体的真切影响,从而为当下对互联网粉丝文化乃至更广泛的青少年亚文化的治理提供更具有实证意义的参考。近年来,饭圈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不断“出圈”的网络流行文化,不管是中国本土养成系偶像TFboys从同人论坛走向春晚舞台意味着一次亚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抑或是肖战粉丝与耽美创作平台AO3的“227事件”和由此引发的偶像与粉丝关系、文化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关系的讨论,再或是近两年不断被点名但屡禁不止的饭圈集资现象和因“倒奶”事件而被叫停的平台选秀节目,以及在2020年8月发生的“饭圈女孩出征”事件等,都向我们彰显出粉丝文化在当下的新媒体社会和消费主义社会中越发突破青年亚文化的分众性而不断与主流意识形态、商业资本、政治空间所发生的强有力的连接。借助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对青少年粉丝和粉丝文化时,既不能采取“杨丽娟”式的病理化处理方式,也不能采取将粉丝全然视为“积极受众”的文化民粹主义态度。
总体而言,本研究是一次基于经验和实证层面的与以往研究框架的对话与突破,期望能将理论话语与现实经验进行叠映,从而改变和纠正现代性社会对粉丝文化的普遍偏见与视觉误差。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限于质性研究方法的范式,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主观偏误。其次,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模型可能存在概念的交叉、冗余和缺失等问题,后续研究还需要对该模型的相关变量进行测度,通过更精细化地检验变量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该理论模型。再次,本研究的访谈样本在性别上呈现女性多于男性的特点,在地域上呈现东部多于西部的偏向,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代表性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希望随着未来研究的继续推进,该模型能够覆盖到更多样化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群体。
参考文献:
[1]刚子.“追星热”与传媒误导[J].新闻界,1993(6):38.
[2]刘小钢,赵宪生.广州青少年“追星热”与辅导对策[J].青年研究,1993(8):25-27+31.
[3]章洁,方建移.从偏执追星看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浙江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调查[J].当代传播,2007(5):29-32.
[4]陆亨.共享游戏:从传播“仪式观”看网络时代的电视迷群文化[D].中国人民大学,2008.
[5]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张嫱.粉丝力量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孟令乔.粉丝文化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D].沈阳:辽宁大学,2012.
[8]张振华,张宁.偶像崇拜对90后大学生成长的影响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89-91.
[9]黄淑贞.成年女性粉丝中的性别政治[D].南京:南京大学,2011.
[10]邓何苗.新闻体环境下追星行为对粉丝继续社会化的影响[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11]黄楚新.警惕资本裹挟下的“饭圈”文化对青年的影响[J].人民论坛,2021(25):36-40.
[12]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11-13.
[13]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7.
[14]Fiske J.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M]//Lewis L A.The adoring audience: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Routledge,2001:30-50.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