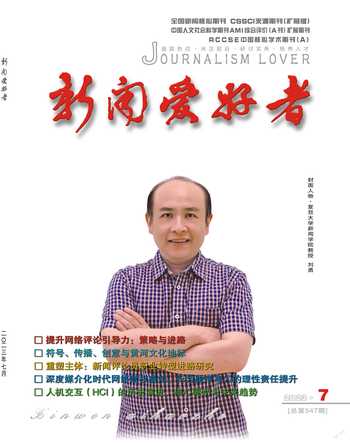网络舆论的话语逻辑及话语引导策略的改进路径
2023-08-10韩云
韩云
【摘要】网络借助于“多中心、开放性、互动性”的优势,正在成为社会舆论发生发展的主阵地。身份多元的社会主体通过网络参与到社会话语的构建、对抗、狂欢、消解过程中,呈现出多方博弈的局面。网民不仅是意见的表达者,同时也是舆论实践的参与者、话语权力的争夺者。政府和媒体在“元叙事”供应和话语构建能力上具有优势,但是对于介入网络舆论场,实施引导和干预的途径与方式仍需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舆论;话语;权力;暴力性解释;同构
突飞猛进的互联网技术,在服务人民、提升社会效率、催生新业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的同时,也给全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作为人类的“拟态生存”空间,其影响领域和效力越来越大,对真实生活的建设、干扰和破坏作用也越发显著。它时而是正能量的扩音器,时而成为负能量的搅拌机,时而推动全社会高度凝聚,时而令社群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愈加突出。同时,网络正在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社会舆论形成、发展、壮大、高潮,直至消退的主要阵地。身份多元的社会主体通过网络参与到社会话语的构建、对抗、狂欢、消解过程中,呈现出多方博弈的局势。网民不仅是意见的表达者,同时也是舆论实践的参与者、话语权力的争夺者。本文试图从话语分析视角入手,对网络舆论的话语特征、主体身份、博弈方式加以考察,并据此对网络舆论引导的机理展开探讨。
一、网络舆论的话语逻辑
(一)在场——网络围观是一种权力证明,开启对话语的介入
“围观就是力量”“转发即是正义”已经成为网络舆论场的共识,其表述本身就暴露出权力在网络话语场域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一旦新闻事件发生,原本分散在四面八方、置身事外的网民迅速聚集在网络世界,形成话题高度集中、言说极其密集的“公共空间”。对新闻事件“表态”,是网民实现“在场”的主要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围观就是力量”中,“力量”不仅是公众给予当事一方的社会压力,更是网民为自己争取到的社会话语力量——通过社交媒体,把自己的信息和表征放进大的信息流,以维持自己的公共存在。[1]“在场”是年轻人参与公共空间的方式,因为他们面对面公共生活的实现能力往往受限。某种程度上,“在场”是个体与社群保持联系或“抱团”的基本需求。个体也在群体累积中获得了自己的象征性资本,并据此获得了“发言人”的授权。[2]数量众多的网民不约而同“在场”,在某一时段形成了价值认同和群体力量,并以草根势力的姿态介入公共话语空间。
(二)对抗——网络话语对文本资源再配置,以消解权威意识
网民自愿表达态度和意愿的背后,不仅有情感、道德层面的需求和宣泄,也隐藏着对符号权力的寻求。[3]代表“正义”一方对另一方进行道德评判,是网络中最常见的关系再造。网络舆论参与主体因身份和意识不同,参与网络活动呈现结构性差异。各方时而合作,共同强化既定的话语秩序;时而斗争,引发原有秩序失衡。对话语权力的掌握是对文本资源的控制:现实是稀缺的,注意力是稀缺的,谁更多地获取文本资源,谁便更多地拥有了配置能力,拥有了将敌对一方“挤出”的优势。在场、转发、评论,是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渠道,也是武器,当然,有时也是民粹主义生发的温床。
(三)狂欢——意义从实践中抽离,符号获取新权力
在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一位叫马保国的老人成为全国网民争相调侃、戏谑的对象。来自B站的UP主们,通过各种视频特效,把经典电影、二次元、说唱等元素运用到了短视频的创作中,说B站每天都会有数十个马保国相关主题的视频发布,加上各大数字平台的推波助澜,最终形成一个全民参与的网络狂欢行为。
马保国装腔作势,外强中干,缺乏自我认知,其形象具有高度象征性,浓缩了网民想要但又不好直接批评、揭露和嘲讽的各种对象,所以才引發了网民持续不断的转发、点评和恶搞。如果说人们最初是因为对马保国好奇才去刻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行为就“变了味”——原本“有意味的形式”却因其重复的仿制而日益沦为失去这种意味的形式,变成规范化的一般形式美。[4]在制作和观赏各种恶搞短视频的同时,人们忽略了新闻事件的所指——传统武术产业的弊端,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展示技巧、创新恶搞、吸引眼球上面,使得话语文本从具体实践中抽离,凭空建构起一个符号化的全新对象,诸如“大意了”“不讲武德”“年轻人耗子尾汁”等原本简单空泛的文本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而公众对此心领神会,迅速成为流行语。新符号的产生有可能触动既定话语秩序,对它的日常化、频繁使用具备了仪式化的特征,公众通过符号狂欢,集体塑造并行使了社会话语的权力。梵·迪克认为,“话语和新闻都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它必然表达和确认其制作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5]通过对马保国这个文化符号的持续消费,衍生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公众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外强中干、缺乏认知,但又蛮横无理的某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消解和反叛。无论是传统武术界,抑或其隐喻的其他社会领域,原有的话语秩序被嘲讽、被挑战,甚至被驱逐。当然,过度的消费和狂欢,后果可能是既定秩序的大面积失范。
二、现实舆论干预的常见误区
回避对抗——在网络时代,脱离网络就意味着脱离群众。遗憾的是仍有一些领导干部面对网络问政采取了掩耳盗铃的态度,面对网民呼声与诉求视而不见,对互联网监督自动屏蔽或者畏惧逃避。这些消极行为不仅违背互联网发展大势,也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背而行。明智的做法是,媒体和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要善于把情绪和身份的对抗,转化为话语的对抗,即通过配置文本资源,在话语场域中占据主动。
对空言说——当前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自说自话的内容,比如一些主题报道和成就报道,只见数字不见人物,或者一味拔高人物却没有个性化的表述,激发不起网民的共情和价值认同;还有一些媒体言说,因为价值取向的偏颇,不仅没有能够强化话语秩序,反而遭到强烈“反弹”。2020年5月3日B站推出《后浪》演讲视频,赞同者听得热泪盈眶,而反对者对其中“弱小的人才习惯嘲讽与否定,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啬赞美与鼓励”的描述无法苟同,认为整个文本过于向年轻人献媚,反而和年轻人有了隔阂。一味礼赞“后浪”,其实也是在呈现“标准”答案,这种“标准”,恰恰是“年轻”的对立面,骨子里是一种傲慢,而不是平等意义上的理解和对话,这样的话语构建,如同“号错了时代的脉搏”。
强行关闭——以实践暴力替代话语博弈,即靠删帖、封号、“网络游街”甚至人身威胁等手段,对抗不同意见者,以起到迅速驱离“在场者”,终止话语对抗危机的作用。这是近些年时常出现的一种“网络景观”,其实质是依靠强制手段关闭网络公共空间,扼杀文本配置,强制结束话语。事实表明,话语一旦产生,就成为一种权力,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现实层面的“暴力终结”,并不能真正消解这种权力,有可能只是将积怨和压抑暂时遮蔽,而更大的对抗和狂欢,也许正在酝酿之中。
三、改进舆论引导的话语策略
(一)叙事——配置文本资源,扩大话语赋权
媒体通过对渠道和介质等资源的控制,掌握了配置文本的能力,继而行使自己议程设置的权力。在表面看来,客观、公正的新闻传播背后,是对权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维护和强化。其中,通过叙事来引导舆论,是最主要的介入和干预舆论场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媒体通过发起、唤醒、聚集、赋权等行为,让公共话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边缘走向中心。
2019年,一个叫张富清的老人经湖北省当地报纸报道后,引起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纷纷跟进。数十家媒体对当事人的故事进行二度挖掘,展示出更加丰富感人的细节,同时也将故事的主题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深藏功名、奉献基层。一个“地方性”人物从此进入全国视野,并且创造了长达半年的持续热度。张富清老人的事迹,在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旗帜宣明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诉求——奉献社会的家国情怀。老人那种近乎“憨傻”的选择,唤醒了公众对奉献二字的再理解和潜意识中对崇高的渴望。无数网民通过各种平台对老人表达了钦佩和赞叹,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拿老人与社会中某些急功近利、计较个人得失的官员与干部进行对比,甚至跟一些影视明星对照,表达了不满。
上述案例中,媒體通过两个环节控制话语权,引导舆论走向:一是“重复”。媒体将同一个或类似的故事反复地讲,故事会起到文化传递者的功能,形成一种社团意识并建立起特定的群体、组织或亚文化……这一重要性不在于其信息价值,而在于它所具体体现出的一套特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并使它们在合法化的过程中起作用。[6]重复是媒体在话语场域中充分竞争的有效手段,新闻实践中我们称之为“形成合力,打好主动仗,奏响主旋律”。二是“赋权”。各种身份的网民聚集在媒体“提供”(设置)的平台(公共话语空间)中,被邀请发表各自的见解和主张,并彼此交流,形成更多人参与的话语空间,我们称之为“赋权”。无论是对积极或者消极的网络话语参与者,如果内心的价值认同感被“唤起”,则倾向于参与到跟媒体的话语同构过程中。在《人民日报》和央视的相关微博下面,对张富清表达敬意的网民动辄成千上万。应当看到,社交平台的交互属性有利于媒体通过赋权来发挥引导力,而那些自说自话、缺乏公众参与的新闻报道,会因为自身的“封闭”无法与网民形成话语同构,消减了引导力。除了评论、转发、点赞,形成意见的共同体,公众还有权力主动进行“勾连”——将原本无关的A事件与B事件联系起来,产生新的意义。比如,人们在评价张富清老人时,会借机批评现实中某些官员做派:贡献没多大,架子倒是大得很,政绩吹到了天边,生怕上级不知道!“把元素之间建立联系的任何实践称为勾连,这样他们的身份就因勾连实践而被修改了,清晰的勾连产生了结构化的整体,我们称之为话语”。[7]实践中,很多人喜欢将新闻报道和网友评论连在一起看,以获取对整个话语体系的把握,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经过“重复”和“赋权”,媒体唤起公众的普遍参与,共同构筑了具有强烈一致性的话语空间。从这个角度看,媒体的舆论引导,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实践,在这个实践中,主体和参与各方共同构建着自己的世界,而且话语一旦被创造出来,便具有了某种权力。
(二)定义——暴力性解释与定义霸权
如果说“叙事”是媒体舆论引导手段中比较“温和”的一种,那么“定义”就充满了威权和暴力的成分。在马保国的话题甚嚣尘上之际,《人民日报》一篇评论《马保国闹剧,该立刻收场了!》对全民狂欢的网络现象给予当头棒喝。此后各平台关于马保国的相关视频陆续下架。可见,无论是平台方还是网民,不约而同默认并“践行”了《人民日报》的“解释”和“定义”——不过是一场闹剧,是结束时候了!整个过程如行政命令般高效、直接。媒体凭借自身的官方背景,对业已失范的话语秩序进行了严肃的“纠偏”,集体无意识语境下的符号狂欢如同气球一般被刺破。公众重回规范化的认知范畴——一个靠传统武术骗财的角色没有理由持续“红下去”,公众凭借这个符号无限度地狂欢和盈利,亦不能被支持。
定义、解释、定性,本身就是典型的舆论导向,要么是将之前的话语合法化,赋予其正当性(比如对丁真事件),要么是对之前的话语施以打击,使其坍塌,最终退出社会舞台(比如对马保国事件)。这也是为什么福柯一直都认定:在言说之物背后,始终有一张暴力性解释的大网。谱系学家在每一种演说中发现“暴力性解释”的游戏,他们追问在话语和符号庸常的背后潜藏着的暴力状况。[8]“定义”和“解释”本身就是话语权力,其背后,一边是政治权力的高耸,一边是社群对威权的恐惧。因此,定性和解释本身毫无疑问是一种政治行为:媒体作为“训诫权力”的实施者,出现在舆论场中,在必要的时候会出面以“暴力性解释”的方式来压制个人行使话语权力的本能。因为这种本能未必总是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方式,有时甚至具有极强的破坏力。
跟“叙事”不同的是,“定义”无需“重复”,也无需向公众“赋权”,它是媒体和政府居高临下对话语体系的“硬介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行使权力的快感被剥夺后,不可避免地要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另一种幻象中重现。
四、结语
在网络中,新闻事件和公众舆论发生多层次互动:打火、助燃、漫射、迁移……最终形成特殊的文化符号、社会景观,甚至从“拟态”走向“真实”,从“清谈”化身“实践”,直至形成推动社会进程的“第三方力量”,整个过程伴随着公众权力意识的唤起、疏导与压制。正是基于此,网络空间治理构成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网络空间的引导和治理,亦有别于传统媒体时代。尝试从话语合作与对抗的逻辑来审视我们的舆论引导工作和媒体的引导艺术,或许是一个有益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3.
[2]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M].索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6-87.
[3]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M]//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306.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8.
[5]Van Dijk.T.A.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DISCOURSE & Society,1993(4).
[6]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M].陈德民,陶庆,薛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4-125.
[7]E.Laclau,C.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M].London:Verso,1985:105.
[8]菲利普·拉尔森.福柯[M].李红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8.
(作者为郑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