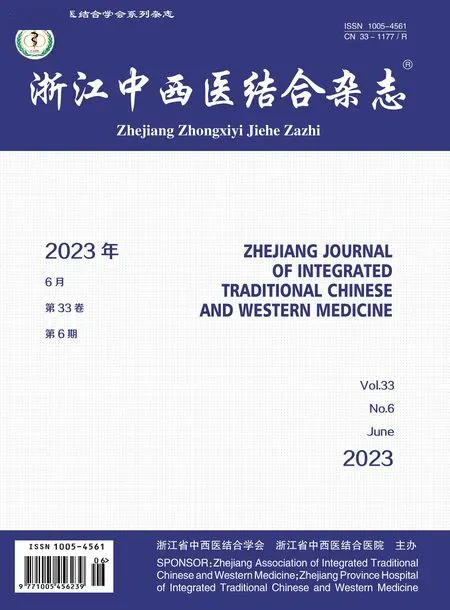曹毅从脾胃论治寻常型银屑病
2023-08-10潘思懿朱启航
潘思懿 朱启航 曹 毅
银屑病是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表现为局限或广泛分布的鳞屑性红斑或斑块,我国发病率约为0.47%,并呈逐年上升趋势[1]。银屑病不但增加患者罹患代谢综合征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易引发焦虑情绪,甚至出现自杀倾向[2]。西医治疗多采用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等,存在价格昂贵、个体疗效差异、副作用大等问题[3]。曹毅教授从事中西医诊治银屑病30 余年,根据寻常型银屑病的皮损特点以及江南地区的地域特点,从《脾胃论》中得到启迪,提出疾病以“脾虚”为本,化生出“郁火、瘀血、湿毒胶结”为标的核心病机,并主张从“血分”论治该病。笔者有幸跟诊于侧,现将其临证经验以及思路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1 吐故纳新,以内伤脾胃论述银屑病之发病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是李东垣《脾胃论》中的重要思想,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旁(《素问·玉机真脏论》),脾胃内伤,正气生化无源,形体百窍不得充养,若此时外邪扰动,则外忧内患而生百病。故后世又有“百病多为脾胃衰而生”之说。曹毅教授结合江南地区的气候特点及饮食习惯,认为江浙地区多水湿,饮食又以甜腻为主,脾喜燥恶湿,湿邪困脾难以运化肥甘厚腻,则易伤及脾胃。脾胃居于中焦,《灵枢·营卫生会》中云:“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凡素体不足或劳倦过度,外湿侵扰或过食甘腻,均可致脾阳、脾气不升,水谷精微无以上注肺脉。肺为华盖居于上焦,上焦如雾,升而逐之,通过肺气宣发将中焦上注之精微布散至全身皮肤毛窍,曰肺主皮毛。若后天运化不及,中焦湿邪泛滥下趋,化源匮竭无以上注,皮肤毛窍濡润不足,遂成“内湿外燥”,则发为白疕。至此形成“脾虚不运—水湿停聚—毛窍不濡”的恶性循环,病情迁延难愈。
《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为热中论》云:“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由此可见,李东垣所指的“阴火”是建立于中焦气衰之上的内伤之火,并且火热征象见于三焦,涉及多脏,变生虚实二端。元气与阴火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两者相互制约。元气充足,则可震慑阴火于下焦,不得妄越;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则阴火不敛,妄动于肤,症见大片鲜红色皮疹、斑丘疹布于全身[4]。因此,内伤脾胃是形成“内湿外燥”和(或)“阴火妄行”复杂病机的核心。
2 谨守病机,从血分论治热瘀湿毒损
中医认识银屑病历史已久,自隋朝起已有记载,随后并陆续出现了“干癣”“松皮癣”“白疕”等多个病名[5]。在皮疹、斑丘疹基础上出现鳞屑、瘙痒、皮肤皲裂是寻常型银屑病的典型皮损特征。近代医家多从血分认识银屑病,具体又有血热、血虚、血瘀、血燥等之分。曹毅教授主张“师古而创新”,在传承“血分论治”的同时,对于“脾虚”这一核心病机格外重视。脾胃功能失常,一则津液运化异常,水饮不化,湿浊内生,聚而成毒;二则脾主升清失职,气机不畅,气滞则血不行,瘀血内阻;三则湿毒、瘀血日久化热,郁火内生,灼伤肌表营阴。曹教授认为,银屑病患者出现皮肤鳞屑、皲裂乃脾胃虚弱,无法输布津液至肌表所致。肌表血分津液亏少,血液黏滞涩而不行,瘀久化热,继而灼伤津液,故见此症。其中缘由,乃为脾胃虚弱不化水湿,外有湿邪乘虚入里,两者相合,湿邪泛滥。湿邪黏滞,阻滞气血,又易化热,湿与热合,日久则藏匿血分。因此,银屑病是由脾虚而衍生出的多种血分病机合并而成,复杂多变,难以着手。
曹教授认为,银屑病患者病程日久,湿毒、瘀血、郁火三者搏结,藏于血分,内不得自泄,外不可透达,扰于肌表,发为白疕。湿毒内蕴,则见皮损肥厚,破溃渗液,迁延不愈;瘀毒内阻,则见肌肤暗红,斑块坚硬,刺痛不移;热毒炽盛,故见斑疹鲜红,破溃出血。综上所述,银屑病是在脾虚基础上,由于湿毒、郁火、瘀血三者胶结难解所致的疾病。
3 圆机活法,探寻临证治法纲领
3.1 分期论治 寻常型银屑病病程缓慢,根据皮损特点以及全身症状,可分为进行期、静止期、退行期3期。曹教授认为,银屑病虽以脾胃虚弱,湿、热、瘀内聚为主要病机,但不同时期病机亦有出入,故应当分期论治。银屑病进行期,常以皮疹不断扩大,颜色鲜红,鳞屑较厚可有渗出为主要特征,其形成乃湿毒、郁火波及血分,搏血为瘀,迫血妄行所致,此时当遵从叶天士“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散血”之意,治以清热凉血解毒,并配伍少量活血化瘀之品。但上述药品过于苦寒,可伤及脾胃,因此治疗过程中切不可一味攻邪而伤正。曹教授主张将顾护脾胃贯穿于疾病治疗始终,在进行期的治疗中于解毒活血之外少佐茯苓、白术、米仁等健脾之品,灵活运用,收效颇丰。银屑病退行期或消退期,常以白屑脱落,肌肤甲错为主要表现,此期一则由于瘀血内停,阻滞津液运行,导致肌肤干燥瘙痒;二则是余毒热邪未清,营血阴分暗耗,加之脾胃虚弱生化不足,导致生风生燥。曹教授认为,皮肤白屑乃气血所化,层层脱落更易耗伤阴津气血,故在此期多选用益气健脾、滋阴养血之品,从本源扶助。
3.2 治法核心 水谷精微的代谢输布有赖于脾胃的正常功能。脾胃运化失常,一则水谷精微化生不足,无以上注肺脉,充养皮毛;二则水湿不化,与他邪相合,疾病难愈,最终导致肌肤鳞屑遍布、干燥皲裂。因此,顾护后天之本,方可从根本治疗疾病。同时“脾主卫”,气血生化有源,机体卫外有力,有助预后。
3.3 治法特色“分期论治”为曹教授治疗该疾病的临证总纲,根据三个时期不同的虚实偏盛,施以相应的理法方药,为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曹教授根据多年临床效验,并结合基础理论,提炼出一系列特色治法,于三期灵活运用,收效颇丰。
3.3.1 开通玄府,透达气机,引湿毒外泄 湿邪重浊黏腻,易闭塞玄府,开玄府宜使用藿香、佩兰等芳香宣透之药,一则疏通肌腠,引湿邪外出;二则利用自身清轻上浮之性,增肺气宣发之力,有助于引上注肺脉之精微外布于表,濡润肌肤。有形之湿若祛,则无形之热无所依;则气血流通,行而不滞。曹教授善用风药中之润剂者辛扬清透,秦艽、威灵仙等品辛而不燥,“风性开泄”,“风可祛湿”,既可使里湿还出表解而无内陷之虞,又可宣发肺气,输布津液。并且,风药更有升举肝阳之功,肝脏得疏,则脾土不壅。因此,开通玄府,疏通气机,湿邪方可外泄。
3.3.2 治湿之要,更需保津,固未伤之阴 临床中部分患者,形体丰腴,红斑糜烂有渗出,舌苔厚腻,一派痰湿阻滞之象。又有肌表脱屑皲裂,瘙痒难忍,是为燥邪扰动,风邪犯于肌表之征。治湿之药,无论化湿、利湿、燥湿,均可损伤津液。《温热经纬》有言:“若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因此,祛湿之药当选温和之品,治湿之余,当需保阴固津,不待阴伤再固阴。
3.3.3 祛瘀通络,增水行舟,津与血并行 后天之本不足,水谷精微化生无源,无以充养血脉,血分阴津不足,血液黏滞不行。加之湿邪阻滞气机,“气为血之帅”,气不行则血瘀。故在活血化瘀通络的同时,可佐养阴活血之品,有“增水行舟”“津血同源互生”之妙。然体内实邪盘踞,大用养阴之品恐有碍邪之弊,故只可少佐其品。
4 验案举隅
患者,女,72 岁。2018 年6 月3 日初诊。主诉:全身红斑脱屑伴瘙痒17 年,加重1 个月。患者17 年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片状红疹,上覆细小鳞屑,轻度瘙痒,无明显渗出。遂至当地医院就诊,诊断为“银屑病”,予相应药物(具体不详)治疗,疗效尚可。后病情反复,逐渐加重,皮损肥厚不消,瘙痒难忍。曾间断外用“他克莫司乳膏”“卡泊三醇乳膏”等药物,皮损始终有所反复。1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全身皮损增多,剧烈瘙痒,夜寐难安。刻下见:肌肤散在暗红斑疹,瘙痒明显,畏热,口干,小便短黄,大便干结,每周1~2 次,夜寐不安,舌红,苔黄腻,脉滑数。体格检查:头皮、躯干、四肢泛发片状鲜红色肥厚性斑块,部分破溃渗液,甚则渗血,边缘可见红晕,覆有灰白色鳞屑,斑块周围可见红色细小斑丘疹。西医诊断:寻常型银屑病进行期;中医诊断:白疕(血热内盛夹湿证);治法:清热凉血,祛湿解毒;处方:丹皮30 g,焦山栀12 g,淡竹叶15 g,土茯苓30 g,赤芍10 g,白鲜皮、生白术、炒米仁各30 g,蜂房6 g,大黄10 g,天花粉、水牛角各15 g,生地炭20 g,威灵仙10 g,麻黄、桔梗各9 g。14 剂,每日1 剂,早晚饭后温服。同时予青鹏软膏、卤米松外涂。2018 年6 月17 日二诊:斑疹颜色较前转暗,边缘红晕部分消失,斑块肥厚鳞屑同前,瘙痒稍有缓解,未见渗血,皮疹未见新发。口干、大便干结缓解,小便仍黄,夜寐仍差,舌红,苔黄,脉滑数。宗上方,大黄减至6 g,去生地炭、水牛角、天花粉,加石膏30 g、枳实15 g、紫草6g 。14 剂,每日1剂,早晚饭后温服。此后均于本方基础上随症加减,前后服用2 个月后,皮损部分消退,颜色淡暗,肥厚浸润明显减轻,鳞屑脱落,偶有瘙痒,二便、纳寐均调。遂改为养血润肤饮(当归、黄芪、白术、山药、生地、熟地、天冬、麦冬、桃仁、红花、升麻、黄芩、天花粉)加减,长期调服,未有再发。
按:本例为典型的血热内盛型银屑病进行期,且兼夹有湿邪。患者病程已久,湿毒气滞留血分,煎熬阴血,加之平素情绪焦虑,气滞血瘀,郁久而化火,引动血分热毒外泄肌表,故既可见全身泛鲜红色斑块斑疹、甚则破溃出血等血热妄行之象,又可见口干、便秘、尿黄等实热内盛之征。且病患久居江南多湿之地,本有内热致使腠理不固,外湿循此入体,碍于脾胃,与热相合,故又有皮损破溃渗液,舌苔黄腻等征象。曹教授认为,热毒藏于血分日久,若非以大剂寒药祛之,恐毒热难清,血分难宁。故方中选用大量清热解毒凉血之品,有苦寒直折之意。大黄、丹皮、赤芍又有活血化瘀之功,体现了曹教授“清热凉血,勿忘活血”之意。然患者脾胃本虚,清热力雄必有伤及脾胃之弊,故少予白术、米仁“健脾和胃,顾护后天”,而无碍邪之虑。更有麻黄、桔梗、威灵仙之辈开宣肺气,透达玄府,一则引津外布,二则引湿外出,同淡竹叶、焦山栀、米仁利湿下行之品相伍,更有上下分消之妙。此外,土茯苓-蜂房为曹教授经验药对。土茯苓为阳明本药,可健脾胃同时去湿毒,现代药理表明,土茯苓可抑制炎性反应,改善银屑病样特征性皮损[6];蜂房质轻,性善走窜,尤适用于皮科风疹瘙痒为甚者。诸药共用,配伍精妙,效如桴鼓。患者前后服用本方加减2 个月,皮损转为缓解期,遂改用养血润肤饮加减以益气健脾,养血滋阴,长期调服,未有再发。
5 小 结
银屑病由于其病机复杂,目前尚未完全统一其病机及治法。曹毅教授创新性将“脾虚”这一病机贯穿于白疕的生存发传复过程。结合临证治法原则及纲领,主张根据疾病不同时期的病机特点从血分予以分期论治。本文不足以囊括曹毅教授临证思想之全貌,仅以此文略述一二,以冀同道治疗该疾病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