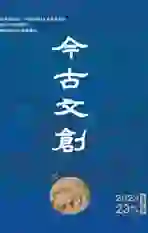《宠儿》中的黑人女性觉醒历程解读
2023-08-07夏珠雅
【摘要】托尼·莫里森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她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宠儿》描写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制度、种族、性别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压迫,体现出了奴隶制时期黑奴女性们举步维艰的生活状况。《宠儿》中暗含着莫里森对黑奴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本文旨在从一家三代黑人女性的悲惨经历进行分析,通过黑人女性在白人和男性的双重歧视下的叙述描写,去探求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识怎样从双重歧视的压制下走向自我觉醒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宠儿》;黑人女性;觉醒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3-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3.006
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其创作别具特色,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宠儿》是托尼·莫里森在看到《黑人之书》的一张简报之后,以玛格丽特·加纳的故事为灵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宠儿》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主要讲述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一个小岛上黑人奴隶制的存在给一家三代女性带来的悲惨遭遇。《宠儿》之名来源于被黑人女性赛丝杀掉的女儿,赛丝在无法忍受白人奴隶主对她的剥削时,带着年仅两岁的女儿逃跑,在逃跑被发现后亲手杀掉女儿并取名为宠儿,多年后宠儿变成鬼魂无穷无尽地向赛丝索取一切进行报复,耗尽赛丝所有的精力。20世纪90年代,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让莫里森去探讨“自由”对于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同工同酬、地位平等,进入学校、职场、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等等本应该是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于是莫里森开始去探究美国黑人女性的历史遭遇。在这段历史中,婚姻是被阻挠的,生育是必须的,做父母则是犯罪的。由此莫里森基于美国奴隶制度下的黑人女性的生活,创作了反映现实的《宠儿》。“女性主义思想是社会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1],而黑人女性主义是在特殊的黑人种族环境中社会对于黑奴女性生存困境产生思考的结果。黑人女性奴隶不仅和黑人男性一样受到白人的种族压迫,还受着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在双重歧视之下,黑人女性过着惨无人道的生活。这样的种族经历决定了莫里森的创作与黑人男性的创作有所不同,也与白人妇女的创作相区别。莫里森通过一家三代黑奴女性的描写,展现了美国黑人女性在惨痛的遭遇中不断自我觉醒,积极构建黑人女性主体意识的艰难历程。
一、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被压制
黑人的种族史可以说是一部惨不忍睹的苦难史。1619年,有记载的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运送到詹姆斯敦,这是英国移民在北美的第一个定居点,也是“新大陆”黑人悲惨的奴隶历史。19世纪30年代美国才开始废奴运动,这意味着白人对黑人种族的文明进行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破坏,黑人长期接受白人所给予的洗脑教育,深刻的与自己种族信仰割裂。《宠儿》中赛丝的母亲被戴上马嚼子,被迫丧失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当教育资源被剥削以及民族文化被破坏时,白人奴隶主便通过自己的文化统治“造就了整整一个种族的卑微感和奴隶感”[2],使得黑人长期拥有一种漂浮感,对于自我的认识处于一种朦胧乃至虚无的状态,自我意识严重被压制。
《宠儿》中的黑人一直处于被压迫的阶级,世世代代为白人所驱使。身为奴隶,他们失去了自由并且做着最低贱的工作,可以被买卖、交换、鞭打,失去身为人的自由。尽管在1863年林肯就宣布了废除黑奴制度,但是社会现状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废除”,黑奴们仍需要做出持久而艰辛的努力。而黑人女性受到种族歧视和父权社会的双重压迫。面对白人的压迫,女奴们忍受着生理上的不适在种植园经历着和男人一样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女人被迫按照男人所制定的规则与制度去生活,女性所拥有的生殖器官也当作白人发泄和繁衍黑人奴隶的工具。老黑奴贝尔·萨格斯忘记自己生过多少的孩子,她所有的孩子都被卖掉,开始不幸的一生,“我生过八个,每一个都离开了我”“八个孩子,可我只记得这么点”[3]6,而她自己也到了六十岁不能再为白人提供价值的时候才最终获得了自由,还是由她唯一留在身边的儿子黑尔牺牲自己的劳动力换来的,她曾愤怒地指出:“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4]6作品中的第二代黑人女性赛丝,是《宠儿》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位弑杀女儿的母亲。赛丝的孤儿身份使其自我意识更加迷离,没有人去教育赛丝应该怎样做出人生的任何选择。当年轻的赛丝选择了黑尔作为自己的丈夫并且拥有了两个人的孩子时,赛丝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好起来,而白人并不会因为尊重黑人的感情而让他们结婚,允许黑人的结合只是为了阻止他们逃跑。有子女的黑人奴隶和有老公的黑奴妇女在逃离时会更加不舍,而黑人家庭的存在则能保证黑人后代的繁衍,世代为白人服务。赛丝所说的“活着才遭罪呢”[5]8是对自己黑暗人生的概括。
莫里森在作品中大力描写女性时,对于男性也有所叙述,但是文本中的男性的身份是处于一种缺失状态,莫里森对于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强烈关注,在其作品《秀拉》和《爱》中也以及其细腻的手法呈现出来,作为《宠儿》中着墨最多的黑人男性保罗·D在知道赛丝逃出之后想的却是“不快的是她始终没有需要黑尔,也没有需要他”[6]9,这是保罗在男权社会下影响下所产生的“优越感”,赛丝用更像一位长兄来形容自己的丈夫。赛丝作为“殖民地的他者”,男权社会要求她是一定要有所依附的,而依附的主体一定是男性。在保罗知道赛丝杀婴之后,保罗的反映典型地体现出一位女性在颠覆男性赋予她的权利时的愤怒。种族歧视和男权社会只需要女性无休止的劳动和永远依附他们,以此造成女性自我意识的压制。
二、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赛丝是《宠儿》中的第二代女性,在上一代以贝尔为代表的黑奴女性的努力下,她作为女性的反抗意识开始慢慢觉醒并有所行动。赛丝带着自己的女儿孤独而封闭地住在124号的农舍之中。保罗·D的到来,拉开了《宠儿》故事的序幕,莫里森用倒叙的手法展开对文本展开的描写,通过回忆将黑奴女女性的经历一一铺展开来,赛丝人物形象的塑造得益于莫里森本人在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期间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思考:“自从我开始创作《宠儿》三部曲,我一直好奇为什么比我年轻二三十岁的女孩完全不比我这个年纪或更年长的女人更幸福……她们能做能挑选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多了……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惨兮兮的?”[7]在1865年南北战争以北联邦失败而告终,这场关于国家统一和奴隶解放的战争并没有真正将解放奴隶的权益落到实处。在二战时期,很会女性参加工厂劳动,女性的社会价值逐渐体现出来。女性价值的体现促进女性意思的觉醒,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美国女权运动。贝尔在教育小丹芙的时候说:“奴隶不应该有自己的享乐,他们的身体不应该是那样的,不过他们必须尽量多地生孩子,来取悦他们的主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许有内心深处的快乐。她对我说别听那一套。她说我应该永远听从我的身体,而且爱它。”[8]242-243贝尔在当了六十多年的女奴生涯后,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赛丝在《宠儿》中典型的身份是一位母亲,其男权社会赋予她的“神圣”责任是生儿育女。赛丝是一位缺失自己文明的黑人,同时也是一位缺失母爱的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下,赛丝心理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直接导致赛丝身为黑人母亲对其女儿畸形的母爱。“塞丝背上的那棵树(苦樱桃树)是过去生活痛苦记忆的一个标记”[9],而赛丝在怀孕时被“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强夺乳汁,事实上是对赛丝哺育者(母亲)身份的剥掉。赛丝明白“甜蜜之家”并非真正的甜蜜,她说“这个世界除了白人没有别的不幸”[10]121。赛丝决定逃跑并在逃跑的路上杀掉年仅两岁的女儿,用弑婴的方式进行反抗并且出卖自己的身体为女儿换取墓碑,体现出她身为黑人女性的不幸。赛丝将杀掉的女儿取名为“宠儿”,表明了这个孩子的身上寄托着赛丝赋予的希望与爱。赛丝的“弑婴”行为超越了她母愛的本身,延伸出了自己对于种族歧视以及男权社会的奋力反抗。赛丝深知作为一个女黑奴,生存是一件多么痛苦而残忍的事。“仅在肯塔基,一年里就有八十七人被私刑处死;四所黑人学校被焚毁;成人像孩子一样挨打;孩子像成人一样挨打;黑人妇女被轮奸;财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断。”[11]208“弗吉尼亚州1662年通过的法令允许男性白人占有女性黑奴。如果母亲是奴隶,她的孩子也将是奴隶,女性黑奴成为提供奴隶劳动力的生产工具。”[12]赛斯杀掉“宠儿”可以说是白人对于黑人种族压迫的罪恶证据,是赛丝身为黑奴面对白人压迫“自杀式”的激烈反抗。
1845年,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首先提出将堕胎视为犯罪,尽管在1937年美国的妇女拥有了堕胎的权利,但是宗教大肆宣扬“堕胎有罪”以及社会对于“堕胎”的谴责,让很多妇女很难真正地拥有堕胎权。关于堕胎权合法化的问题“同奴隶制问题一样,引发美国的又一场内战”[13],母亲的生育功能是男性赋予女性的价值和义务,莫里森通过“弑婴”事件的描写,实则是对男性给予女性所制定规则的打破,充分地肯定了“堕胎”是女性的权力。“堕胎”不仅是避免女性成为生育的机器的一种反抗,而且还是妇女获得权利和妇女解放的关键。莫里森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去写《宠儿》,其“杀婴”的情节也体现出她对女性尤其是黑奴女性生育权力的高度关注。在第二次的女权运动中,很少的黑奴女性进行反抗,她们所接受的美国妇女教育是女性应该囿于家庭之中,繁殖下一代,照顾丈夫等无社会性质的家庭活动。1963年美国著名作家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在她写的《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中揭示了这套女性教育背后的谎言,揭示了女性“幸福生活”背后的苦闷与无奈,只在家庭进行活动事实上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与制约。在奴隶制废除后,黑奴女性也被迫加入这一家庭模式之中,除此之外,许多黑奴男性无法在社会上挣到钱,黑奴女性一方面被迫进入社会赚钱,另一方面家庭的琐事也消耗着她们精力,是女性独自将家庭支撑起来。在《宠儿》中塞丝一家人居住的蓝石路124号(124 Bluestone Rd)便是这种“一母独大”的模式。
三、黑人女性自我觉醒意识下的团结反抗
在女权运动热烈的进行中,凯西萨拉查尔德提出了“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的口号。“姐妹情谊是广大黑人女性谋生存、求发展的精神、物质双重保证。它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集体力量形成巨大的推动力。”[14]莫里森对于这个口号是给予强烈支持的。此口号在《宠儿》不同的女性身上都得到了体现,表现为黑白两个种族女性之间的联系与相互救赎。老黑奴贝尔是124号的精神领袖,当年轻的塞丝来到134号的时候,贝尔帮她清洁身体“她总共用了两壶热水来擦洗赛丝的两腿之间,然后用床单裹着她的肚子和阴部”[15]108,这次清洗象征着赛丝逃出后的重生,而贝尔对于赛丝的帮助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赛丝作为孤儿所缺失的母爱。黑人女权主义者苏珊·威利斯(Susan Willis)曾说:“当代黑人妇女作家倾向于将团体的存在与她们的母亲一代联系起来”[16],莫里森也是如此,在《宠儿》中的“黑人社团”和赛丝与小丹芙和宠儿以及黑尔之间的联系无不体现如此。
赛丝在逃跑的路上受到了白人丹芙的帮助,白人丹芙身为白人女性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她对于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具体而热烈的。丹芙向往威尔逊胭脂色的天鹅绒,也勇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她说:“我见过照片,他们那儿有漂亮的天鹅绒。他们不相信我能找到,可是我能。”[17]38赛丝生下孩子以白人丹芙的名字进行命名,希望小丹芙可以延续白人丹芙身上这种黑奴女性身上无法拥有的主体意识,而这个小生命身上也背负着白人和黑人女性的共同情谊“女性帮助女性”,是“姐妹情谊”口号的生动写照。
虽说小丹芙是第一代的自由黑人,但是她接受着赛丝和贝尔身上创伤对她的影响,而赛丝对于宠儿的过渡宠爱而忽视了小丹芙,使小丹芙的性格非常敏感自闭,总是一个人待在“翡翠衣橱”里,甚至在同学的责问下达到失聪的状态,这是小丹芙封闭式的自我保护。宠儿与保罗的到来打破了她和塞丝原本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后来宠儿的到来使小丹芙在照顾宠儿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的责任感,可以说是宠儿的出现成为小丹芙成长的助推器。在知道赛丝捡地上的果皮吃之后,小丹芙便独自勇敢地担负起整个家庭的重任,她已经不同于赛丝最初“畸形”的反抗而有了自我意识。她知道了宠儿对于母亲的伤害之后,说:“可孩子也不能说杀就杀妈妈”[18]297,怀着对于母亲的爱以及自己对于爱的渴望,小丹芙无畏地走出鬼屋,走出124号,积极寻求外界的帮助。小丹芙在老师的帮助下,最后走出社区赚钱养家,成为一位独立的女性,完成女性的自我成长之路。小丹芙的存在,是母亲和女儿的连接,也象征着黑人女性将会一代一代不屈不挠的挣脱被奴役的桎梏,达到人性的自由。文本的最后,黑人团体用自己的歌舞赶走了宠儿,宠儿的离开,也表现出莫里森对于姐妹情谊的高度赞扬。反观赛丝在逃亡时由于“甜蜜之家”里的黑奴女性对于赛丝的嫉妒,并没有向赛丝通风报信去帮助赛丝,间接的害死了宠儿。
四、结语
莫里森通过欲扬先抑的手法去书写宠儿的出现,在平静之中将血淋淋的事实摆在读者的眼前,以独特的视角写了黑人女性在美国奴隶制度下的悲惨遭遇。莫里森从一个黑人家庭反映出当时普遍的社会状况,通过对一家三代黑人女性的描写,描写出当时整个黑人女性的生活困境。同时莫里森用自己的作品表明了自己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在她看来,身体的自由只属于黑奴独立的一部分,思想的自由更是尤为重要的,自由的思想是女性走上独立道路的关键。1982年美国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发表了著名的黑人女权主义作品《紫颜色》并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该著作进一步关注到女性的生存困境,此后许多作家越来越关注到黑人奴隶那段不堪的经历。美国的奴隶制历史,是一段惨不忍睹的经历,女性主义作家以自己的文字,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描写女性的生存困境,表现出黑人妇女实实在在地存在这样一个铁的事实,给黑人女性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道路。
参考文献:
[1]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24.
[2]Aroger Matuzmutuz ToniMorrison[J].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on,1989,(55):198.
[3][4][5][6][8][10][11][15][17][18]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6,6,8,9,242-243,121, 208,108,38,297.
[7]ELISSA,SCHAPPELL.Toni Morrison:The art of the fiction[J].The Paris Review,1993,(128):68.
[9]鲍志坤.《宠儿》象征主义分析[J].英语广场,2019, (12):6-8.
[12]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35.
[13]赵梅.“选择权”与“生命权” ——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论争[J].美国研究,1997,(4):55-87.
[14]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概观[J].外国文学研究,2000,(04).
[16]Susan Willis,Black Women Writers:Taking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rom Making a Difference,214,220.
作者简介:
夏珠雅,女,河南信阳人,闽南师范大學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