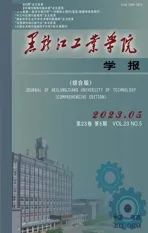短期语言切换经验调控双语者认知控制的研究分析
2023-08-07黄彦红何小敏
黄彦红,何小敏,程 荣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认知控制,又称执行控制、执行功能,是个体以目标为导向,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灵活调控其思想和行为的一种高级认知过程[1-2]。它能影响大脑对信息的感知、思考、决策等加工活动[3],其功能失调会导致诸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心理及行为失常[4]。因此,有关认知活动和认知控制的关系研究,尤其通过认知活动训练来增强个体认知控制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双语经验被认为是促进认知控制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双语者在进行非语言的认知加工活动时,会比单语者呈现出一定的认知优势,即“双语认知优势效应”。尽管这一结论受到一些质疑[5],但更多的研究支持双语经验对认知控制的促进作用[2,6-7]。那么,作为双语经验的核心环节,双语者的语言切换会如何影响他们的认知控制?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心理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实验考察。本文将双语切换短期经验调控认知控制的理论解释、研究范式、调控方式和结果四个维度阐述相关研究。
一、调控作用的理论解释
ACH(The Adaptive Control Hypothesis,适应性控制假设)[8]和CPM(Code-switching Processing Model,语码切换控制过程模型)[9]表明,双语实践与潜在的认知控制有关,为人们探索语言控制和认知控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动机。ACH认为语言控制过程与非语言控制过程的操作和协调的精确方式会随着具体语境需求的变化而获得适应性调整。在单语语境中,双语者在不同场所(如办公室和家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因此,不存在频繁的语言切换。在双语语境中,双语者在同一语境(如学校)中面对使用不同语言的对象会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因此,语言切换可能发生在话语之间。在密集切换语境中,双语者常常会在话语内部交替使用两种语言,因此,存在频繁的语言切换。CPM假设,在单、双语语境中,控制过程以竞争模式运行,以禁止非目标语言的干扰,涉及更多的整体控制。而在密集切换语境中,两种语言联合使用,需要保持高度活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语言需求,控制过程以合作模式运行,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冲突监测和局部控制。因此,与不经常进行语言切换的双语者相比,经常进行语言切换的双语者的认知控制及其潜在机制的加工方式会有所不同,语言控制对其他认知控制过程的影响可能是自适应控制系统整体变化的结果。可见,ACH和CPM为语言切换调节和监控非语言的认知控制任务表现提供了解释框架。
二、研究范式
根据实验设计,以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只设置语言任务或者非语言任务,用混合代价和切换代价作为指标,考察语言切换对认知控制的调节作用。混合代价,与混合语境中的多任务维护相关,体现持续的、全局的认知控制;一般以不同语境(单语和双语切换)条件下执行相同任务时所产生的认知耗费差异量计量。切换代价,是指被试在进行任务切换时耗费的脑力资源,体现了瞬时的、局域的认知控制;一般以加工切换和重复任务的认知耗费差异量计量[7,10]。焦鲁等[10]通过计算被试进行数字命名任务时的混合代价和切换代价,呈现了双语者在进行语言切换训练后认知控制成分的顺序性变化,诠释了语言切换促进“双语认知优势效应”的加工进程。
其二是跨任务适应范式,在当前应用得最为广泛。研究者通常以ABABAB……的方式依次为语言任务A和非语言任务B,语言任务A涉及单语语境和切换语境。被试在完成一个试次的语言任务后,立即完成非语言任务。这种设计背后的原理是,双语者在进行语言切换时会调用认知控制,并且这种认知控制的参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而能更好地解决后续非语言任务中的冲突,出现“冲突适应”[11]。相关研究一般设置四种实验情境:切换—冲突任务、切换—不冲突任务、非切换—冲突任务和非切换—不冲突任务,通过对比分析不同语境下被试执行非语言任务时行为或脑电差异,探讨双语者的认知控制能力在语言切换训练情境下的自适应调整进程[11-13]。尽管跨任务适应范式已获得广泛应用,但该范式仍有一定局限性[14]。在混合语言环境中,除语言处理和执行非语言任务之外,还会发生额外的切换(即语言任务向非语言任务的切换),而这个过程也有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控制表现,给衡量语境任务中(即语言切换)个体的认知行为表现增加了难度。
其三是Block(组块)范式,将语言任务和非语言任务分别作为独立的Block呈现,要求双语者在完成一系列语言任务之后,再完成非语言任务。这种设计可以克服跨任务适应范式的上述局限性,允许在不同的语境任务中测量认知控制,不需要在语言任务和非语言任务之间进行反复切换,因而更易于测量和监控语言切换加工对个体认知控制的影响进程。Jiao等[2]设置了带有瞬时切换的二个实验,实验一要求被试在完成含有和不含语言切换训练的图词匹配任务后,分别执行判断箭头方向是否一致的Flanker(侧抑制)任务,通过计算不同语境下的Flanker效应量,揭示语言切换经验的瞬时调节作用;实验二要求被试在完成含有和不含切换训练的形状—颜色任务后,分别执行Flanker任务,检验被试在实验一中认知控制能力的变化是否源自语言切换训练的调节,进一步考察了语言处理对调节认知控制的重要性。
三、对认知控制加工方式的调控
根据双重认知控制理论[15],认知控制可分为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主动性控制通过持续主动控制机制调整竞争任务集的激活,级别来实现。它由早期的、持续的DLPFC(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所支撑,伴随着多巴胺能对背景(显著)线索的反应。在即将发生的目标事件的驱动下,主动性控制会依赖目标线索对认知资源产生偏见,因此可以在潜在干扰发生之前进行预测和预防,所以它是一种受线索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局性控制。相反,反应性控制是对特定目标事件的回应,是在突发事件后重新引导注意力的一种“后期纠正”机制,由ACC冲突监测系统或时间联想记忆区域触发的短暂的DLPFC激活所支撑的。它源自由先前试验中任务集的激活引起的干扰解决,通过刺激激活后的瞬态反应控制机制实现,因此,是一种探测驱动的、自下而上的局域性控制。双语加工过程中的主动控制是通过在语言被激活之前调整语言的激活水平来实现的,从本质上来说,更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全局性(非试验特异性)。而反应性控制则与短暂激活两种语言后对非目标语言干扰的消解有关,由刺激激活后的瞬时反应控制机制解决,是短暂的和局部的(试验特异性)[16-17]。
Zhang等[18]分析了双语被试在接受为期10天的图片命名训练前后执行AX-TCP任务(the AX version of the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AX持续表现测试)时的行为数据和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s,事件相关电位)数据,发现,语言切换的短期训练改变了AX-CPT任务的表现,发现只有实验组主动控制的行为测量,即目标发生前的目标维持,在训练后阶段显著大于训练前阶段,表明主动控制发生了转移;其次,训练引起N2平均波幅的增加。N2是刺激呈现200ms左右,在中央顶区达到波峰的负波。N2平均波幅的增加,说明经历语言切换加工训练的被试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分配给线索检测,语言切换加工训练能增强双语者的主动控制能力。与之不同,Timmer等[7]通过对被试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语言切换训练(实验组)或单一语言命名训练(控制组),对比两组被试在语言切换训练后执行非语言任务(颜色—形状任务)时的混合代价和切换代价。结果发现,语言切换训练可以显著降低切换代价;其次,在训练后,两组被试执行认知控制任务时的混合代价都明显降低。这说明,短期语言切换训练能增强个体的反应性控制能力,但不会对个体的主动性控制产生影响。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源自实验设计的不同。Ma等[17]发现,随着CSI(Cue-Stimulus Interval,线索刺激间隔)的延长,切换代价和混合代价都会降低,说明较长的准备和反应时间有助于克服反应性抑制和主动性控制。在RCI(Response-Cue Interval,线索反应间隔)越短,切换代价的非对称性越明显;而只有RCI较长时,才会出现非对称的混合代价。这些发现为反应性抑制随时间的消散提供了证据,并证明较长的准备时间会使主动性控制机制对两种语言的相对熟练程度更敏感,导致对L1(一语)更强的主动性控制。可见,反应性控制和主动控制并不完全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依赖且具有动态性特征,会随加工语境和双语切换过程的变化而变化。
四、对认知控制加工系统的调控效果
抑制控制和冲突监控是语言切换中使用的两个主要加工系统[19-20]。具体来说,双语者监测交际环境中的冲突(即跨语言干扰),寻找触发语言切换的变化,然后启动语言控制过程来抑制跨语言干扰。
1.短期语言切换经验对抑制控制的调节
抑制控制,又称抑制,是指个体通过抑制优势反应或抑制来自竞争刺激的干扰来解决冲突的过程[19]。来自脑成像的研究表明,双语者在进行语言切换时,大脑活动区域与认知控制大脑网络有一定的重合。在语言切换时,ACC(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前扣带回)、IFG(Inferior Frontal Gyrus,额下回)、preSMA(pre Supplement Exercise Area,前补充运动区)、DLPFC都可能参与语言抑制[21]。
在语言产生中,抑制一般用混合代价和切换代价来测量。研究显示,双语者会通过抑制和解除抑制实现两种语言之间切换[19,22]。以图片命名为例,呈现在双语被试眼前的刺激图片会引发他们语言系统内双语词汇的共同激活,因而在大脑内部产生冲突。此时,双语者需要根据刺激线索抑制非目标语词汇,以产出恰当的目标语词汇,抑制能力随之得到强化。Kang等[23]对中英双语者进行了为期8天的语言切换任务训练。结果显示,切换试验比非切换试验诱发了更大的负向N2成分,表明经历语言切换加工的双语者在词汇选择时,会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施加抑制,即双语者在切换语境中对优势语L1的抑制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他们还报告,实验组在图片命名后测时,N2峰潜伏期会提前,而对照组没有变化,这说明语言切换训练有利于语言竞争中的冲突解决。
在语言理解中,一般用Flanker任务、Stroop(斯特鲁普)任务、Simon(西蒙)任务、Stop-signal(信号终止)任务、Go/No-go任务等非语言任务测量抑制能力。Wu和Thierry[12]首次揭示了双语加工处理与认知控制尤其是抑制的在线交互作用。他们发现,被试在双语切换语境中执行Flanker不一致性任务时,错误率更低,P300成分的波幅也更小。P300是由刺激诱发的潜伏期约300ms的晚期正波,其波幅大小反应了抑制强度。实验中,P300的波幅变小,说明抑制能力增强,即语言切换加工会促进个体抑制能力。也有研究发现,与阅读不含切换的句子相比,被试在阅读含有语言切换的句子后,执行Flanker不一致性任务时,反应更快,错误率更低。这可能是因为被试在进行语言切换加工时,需要调用认知控制程序,克服句子会继续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期望,抑制无关信息,解决当切换发生时不可避免地在词汇、语音和语法等多层面出现的跨语言表征竞争,并且这种抑制迁移到随后的认知控制任务中。这说明,在处理冲突时,双语切换增强了被试抑制无关信息的特定能力,从而有助于促进非语言任务中的冲突解决。Kalamala等[24]以自然会话场景中的双语者为被试,以Stop-signal任务和Stroop任务测量抑制能力,采用行为研究和ERP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考察语言切换对抑制的影响。与前两个研究不同的是,该研究未发现行为测量结果的差异。但与Wu和Thierry[12]类似,发现了ERP成分的认知差异量。具体来说,双语者在经历双语加工尤其是L1切换到L2(二语)的加工后,执行抑制任务中产生的混合代价更小,体现在非一致性任务和一致性任务时,P3(P300)和N450的差异更小。对ERP成分的调节表明,语言切换加工增强了与抑制相关的神经机制。
为考察语言切换加工作用于抑制能力内在加工进程,有研究将抑制进一步分为克服由竞争性刺激引起的冲突的干扰抑制和克服由优势反应倾向引起的冲突的反应抑制[25]。刘聪等[26]设计了2个实验,要求被试先后完成有线索提示的数字命名任务和面孔任务,通过分析双语者在经历语言切换前后的认知控制成分差异量和被试在不同命名任务中的行为表现差异性,揭示语言切换对认知控制的影响。结果发现,经历语言切换加工的双语者在反应抑制任务中的反应明显加快,在干扰抑制任务中的反应速度变慢,说明语言切换加工促进了非平衡双语者反应抑制的发展,但对其干扰抑制却形成了阻碍。这与范小月等[27]的研究结论不同,后者显示双语者的干扰抑制显著优于单语者,而在反应抑制上没有出现明显差异,他们认为双语优势效应是长期语言使用双语的结果。而刘聪等的研究考察的是语言切换加工对抑制的即时影响,在即时语境中,双语者因为不熟悉语言切换过程,可能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关注任务需求和线索提示,这有利于发展其反应抑制成分。因为双语者的认知资源储备是有限的,随着反应抑制耗费资源量的增多,分配在干扰抑制成分上的资源相应减少,从而阻碍了干扰抑制的发展。随着语言切换经验的积累,双语者对切换流程日渐熟悉,耗费在反应抑制上的认知资源量就会减少。此时,语言间的顺利切换,可能主要通过排除对非目标语干扰的抑制来实现的,所以在干扰抑制上呈现出优势效应。
2.短期语言切换经验对冲突监控的调节
冲突监控,或监控,是指个体监控环境中的冲突或信号的能力[17]。研究认为,大脑额叶中的特殊区域ACC,能检测到冲突,允许由DLPFC调节的注意力控制在线转移[28],这会频繁地调节认知控制。更具体地说,当与任务有关的输入和与任务无关的输入自动引发相互竞争出现差异时,冲突监测系统会检测到这种竞争差异,以减少与任务无关的维度对反应选择的影响,提高认知控制水平。
在语言产生层面,Jiao等[13]采用跨任务适应范式,用图片命名任务设置语言背景,用Flanker任务考察认知控制能力。结果发现,与单语语境相比,混合语境中的被试在执行Flanker任务时,诱发了更大波幅的N2和较小波幅的P3及LPC(Late Positive Component,晚期正成分),而且这种差异性在Flanker一致性任务和不一致性任务中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语言切换加工更多地依赖冲突监控机制来识别目标刺激的关键特征。但该实验并没有发现被试在反应时上的差异。与之不同,Struys等[29]直接研究了执行控制(Simon任务)和双语语言理解(语言分类)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双语参与者的语言理解和执行控制之间密切相关的证据。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对分类任务测度和Simon任务测度的相关分析,检验了语言控制和两个控制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语言控制措施在分类任务和Simon任务的整体反应时之间存在相关性,但语言控制措施和Simon效应之间没有相关性,验证了监控在语言控制和执行控制的相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这在Jiao等[2]采用独立呈现语言任务和非语言任务的Block范式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可见,语言切换加工会对一般认知监测产生短期适应的关键作用。
结语
双语者的语言控制过程会自发适应所处加工语境而做出调整。以混合代价和切换代价为指标,以往的研究通过测量双语者执行双语切换任务、交替或先后执行双语切换与非语言任务时的认知资源耗费差异量,考察了个体短期双语切换经验对认知控制的影响。结果发现,短期双语切换经验对能调节双语者的认知控制方式,随着实验设计的不同,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因为主动性控制和反应性控制具有动态性。其次,短期切换经验能够调节个体的抑制能力和监控能力,这主要体现在短期语言切换能刺激ACC、IFG、preSMA、DLPFC等不同脑区的活动,在N2、P3、LPC等不同的脑电成分上会诱发不同的波幅差异性,并体现在行为表现中。但不论是ACC等脑区,或者是N2等脑电成分,它们究竟反应的是抑制还是监控,不同的研究会随着自身研究目的的不同而给出不同的结论,这就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今后的研究应注意研究方法和实验语境的标准化和客观性,兼顾认知控制的动态性,从认知控制整体和分离的角度多方面深入考察语言切换加工经验对认知控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