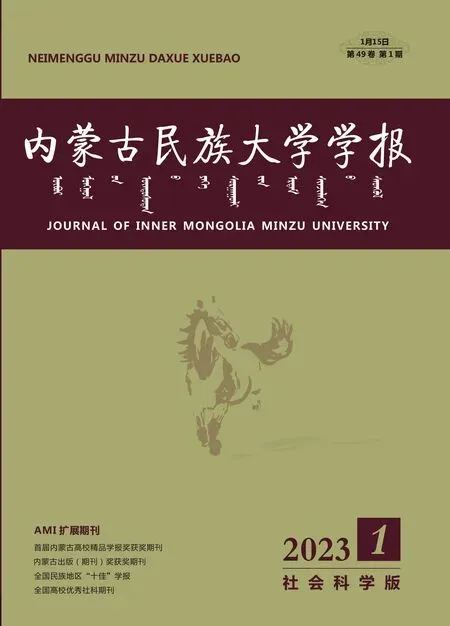模糊的法令
——塞奥多西一世时期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
2023-08-06陆琪庆李红云
田 明,陆琪庆,李红云
(内蒙古民族大学 法学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一直以来,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379—395年在位,以下简称“塞奥多西”)的宗教政策作为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备受学者们的瞩目。早在60年前,英国宗教学者金(N. Q. King)就指出,塞奥多西对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施加了决定性影响,通过强调他的军人背景,金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确立视为塞奥多西统治时期的一场宗教之战,而其高压统治的结果便是,基督教在4世纪末期成为罗马帝国多数人的宗教。[1]111998 年,由两位英国考古学者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与弗瑞埃尔(Gerard Friell)合著的《塞奥多西:困境帝国》则聚焦于塞奥多西虔诚基督徒的身份,认为他给予了基督教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此外,他们高度评价380年法令,称其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2]352020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赫布尔怀特(Hebblewhite)在他关于塞奥多西研究的最新著作中指出,在塞奥多西统治时期,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交融进程得到了极大的加速,基督教会权力的日益膨胀便是由此开始。在书中,他抛弃了基督徒的视角,重点分析这位皇帝的政治动机,并评价其为一位务实主义者和天生的帝王,而当提到380 年法令时,作者则认为“这不是一条意义重大的法令”。[3]53通过回顾英语世界塞奥多西研究60年的基本脉络可知,学者们均认可塞奥多西的基督教政策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但他们从未明确提及。正是在塞奥多西统治时期,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即使威廉姆斯和费瑞埃尔相当重视380 年法令的历史地位,他们也没有将其与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联系在一起,而在国内,关于塞奥多西将基督教正式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的说法流传甚广,并主要以塞奥多西所颁行的法令为重要依据,其观点主要有三种,一种持380年的观点,[4]一种持392年的观点,[5]此外便是模糊化的观点即避免提及具体的年份。[6]由此,本文旨在重点分析380年法令和392年法令,详细考察这两款法令的颁行背景,分析其是否标志着基督教作为国教在罗马帝国确立起来,并由此探讨塞奥多西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模糊的对象与380年的基督教国教化法令
颁行于380年的“塞萨洛尼基敕令”被认为是塞奥多西于该年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的关键性证据。该敕令的正式名称为《君士坦丁堡公民令》,由格拉提安(Gratian)、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Ⅱ)和塞奥多西在380年2月28日联名发布于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其内容如下:
这是我们的意旨,在我们治下的所有公民都应该信奉圣彼得(Peter the Apostle)给罗马人带来的宗教,他当初所倡导的宗教如今已十分清晰。显而易见,这是教宗达马稣一世(Pontiff Damasus)和如使徒般圣洁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Peter,Bishop of Alexandria)所共同追随的宗教,根据使徒教规和福音信条,我们坚信三位一体。
我们认为,遵循此法的公民将享有正统基督之名,至于剩下的那些痴迷异端的精神错乱者,他们所聚集的地方不能称之为教堂,他们先是会遭到神的报复,然后由我们来予以惩罚,这显然符合神的裁决。[7]440
在该法令中,“所有公民”的字眼显得格外突出,正是该词暗指罗马帝国已经将基督教抬升至国教地位,因为其明确指出了应当遵循该法令的对象群体。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便是该法令的正式名称——《君士坦丁堡公民令》,由此引出的两个疑问是,首先从名称上看,这是一款以君士坦丁堡的公民为对象所颁布的法令,这与法令正文中的“所有公民”存在较大差距;其次这部冠以《君士坦丁堡公民令》的法令也不在君士坦丁堡发布,而是远在塞萨洛尼基。考虑到该法令的模糊之处及其被赋予的重要历史意义,势必要对其颁布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一番考察。
《君士坦丁堡公民令》颁布时,瓦伦提尼安二世年仅9岁,关注的重点自然会落在21岁的格拉提安和33岁的塞奥多西身上,而此时身在塞萨洛尼基的正是塞奥多西,380年2月距离塞奥多西于379年1月在色米姆(Sirmium)登基刚刚过去1年。378年8月,东部皇帝瓦伦斯(Valens)在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兵败身亡,西部皇帝格拉提安于次年指名塞奥多西执掌东部帝国以应对危局。在教会史家狄奥多里特(Theodoret,约393—457)的详细叙述中,他声称塞奥多西是格拉提安缓解危机的第一人选,且在从西班牙火速赶往东方前线后,他就在色雷斯(Thrace)取得了一场对蛮族的大胜,这也让格拉提安最终下定了立他为帝的决心。考虑到狄奥多里特本人的基督徒身份及其叙述中的诸多神迹色彩和混乱表述,这个细节最为丰富的版本一直以来都备受诟病。[3]19—20
在狄奥多里特的叙述遭到质疑之后,重构塞奥多西的登基细节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考虑到379年1月距离瓦伦斯在亚德里亚堡阵亡已经过去了5个月,甚至有学者开始质疑塞奥多西获得政权的合法性。[8]从格拉提安的角度看,尽管与瓦伦斯有着亲缘关系,但这两位共治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格拉提安在增援东部时刻意造成的缓慢速度,便是导致瓦伦斯最终兵败身亡的间接原因。[9]佐西莫斯甚至说:“格拉提安获悉上述消息时并无多少悲恸”[10]115。由此可知,瓦伦斯的阵亡以及帝国东部的危局是格拉提安可以预见的结果。在瓦伦斯阵亡时,帝国仍然存在着两个皇帝,即使他的弟弟瓦伦提尼安二世尚且年幼,但也已经与她的母亲共同治理了意大利3 年,格拉提安完全可以在新选一位强有力的摄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家天下的局面。事实上,早在亚德里亚堡战败之前,塞奥多西就已经复职于多瑙河流域,无论格拉提安当时身处玛尔斯兵营(Castra Martis)还是色米姆,[3]27只要他有立帝之意,塞奥多西都是一个可以召之即来的将领,完全不需要拖延如此之久。5个月的时长不仅说明了格拉提安的犹豫不决,也暗示了当时的形势并非十万火急。无论如何,在格拉提安的动机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塞奥多西还是在379年的1月登基为帝,塞奥多西家族的政治运作和塞奥多西本人在与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作战中所取得的战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结果的发生。[11]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塞奥多西绝非一位篡位者,但他继承帝位的方式却称不上顺理成章。由此,在狄奥多里特的版本中所出现的那段充满神圣色彩的描述便具有了一些现实意义。他说:“万物之神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似乎看到了安提阿主教圣梅勒提乌斯(Meletius),他将他视为帝王,并将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12]换言之,在登基之前,塞奥多西曾通过基督教宣传的方式在主动争取自己的帝位,他将基督教视为自己帝位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位公开支持三位一体教义、反对阿里乌主义①的基督徒,[13]他声称梅勒提乌斯为他加冕,这一事件的意义并不一般。虽然直到今天,梅勒提乌斯的宗教立场仍然令人困惑,但他此前曾两度被支持阿里乌主义的先帝瓦伦斯放逐,又在偏爱三位一体教义的格拉提安的支持下复职,且当时宣导三位一体的教会领袖巴西尔(Basil)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14]由此,塞奥多西的这一宣传同时具备了政治和宗教的双重意味,他不仅赋予了自己神圣的合法性,还重申了自己与格拉提安共同的宗教立场,这些举动成为日后帝国三位一体教义的正统地位最终确立的前奏。
事实上,在登基之后,试图终止帝国东西两部分的基督教教义之争,一直是塞奥多西基督教政策的核心思想,《君士坦丁堡公民令》正是其典范之作。由法令的内容可知,这是一部以异端为打击对象的宗教法令,并不涉及异教,因为在此前的379年6月,塞奥多西在塞萨洛尼基发布的一款敕令中还声称:“我们遵循古老的传统和先祖的法律”[7]268,佐西莫斯也说:“而直到那时,他们仍允许踏入神庙,按旧有的方式祭拜众神”[10]118,此外该法令的出台也并非个例,而是与西部帝国遥相呼应的。在379年8月颁布于米兰的法令便提及:“所有的异端都是为圣法和帝国的法律所禁止的,它们应该永远消失。”[7]450就当时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环境而言,法令的首要打击对象便是阿里乌主义,而考虑到西哥特人的阿里乌主义成分[15],二者之间显然存在关联。
挟亚德里亚堡之役的胜利之威,西哥特人在帝国东部畅通无阻地行进,并于379年进入伊利里亚(Illyricum)。[16]可能与格拉提安返回帝国西部同时,塞奥多西也前往塞萨洛尼基开始整军备战,以应对西哥特人的攻势。尽管佐西莫斯抨击塞奥多西:“可是他的统治却开始走向浮夸与慵懒”[10]117,且“伊斯特河对岸的蛮族只要愿意逃亡过来的,无论有多少都将招募进军团”。[10]118事实上,至少在379年,塞奥多西确实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3]33也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君士坦丁堡公民令》出台了。
在当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一座笼罩在阿里乌主义下的都城。[17]96《君士坦丁堡公民令》在380年2月发布同样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双重意味。此时,塞奥多西已经初步稳定了与西哥特人的战事,通过颁布法令严惩异端,这位刚刚登基的皇帝向世人展现出了他将要与西哥特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此外,这同时也是一部暗藏政治野心的“告首都公民书”:自己即将带着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前往那里,帝国的都城将迎来新的主人。以打击西哥特人为由,塞奥多西将在那里进行一场以阿里乌主义为打击对象的基督教教义统一运动,而隐藏在这场宗教运动之下的,便是他以宗教为手段立威,进而稳固自己在东方统治地位的政治筹谋。由此,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公民令》中的“所有公民”一词,最佳的理解应为“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公民”。
《君士坦丁堡公民令》是一部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所颁布的针对君士坦丁堡公民的宗教法令,长期以来,由于“所有公民”一词的模糊性,这部法令被赋予了过高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君士坦丁堡公民令》并不涉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全境排他地位的确立。该法令出台的首要目的是扶持三位一体教义在首都的正统地位,并与当时东部帝国的军情和塞奥多西个人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二、模糊的限制与392年的基督教国教化法令
塞奥多西于392年将基督教正式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的说法流传甚广,由于涉及对异教的打击,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392年11月8日,相关法令由塞奥多西与他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和霍诺留(Honorius)在君士坦丁堡联名颁布,法令的内容如下:
所有人,不分高低贵贱,无论权势和荣耀,不管他是来自权门还是寒门,都不应在任何城市、任何地点向无意义的偶像奉献无辜的牺牲。他们不应怀着更为隐秘的邪恶之心以火祭拜他们的守护神(lar)、以酒祭拜他们的精灵(genius)、以芬芳祭拜他们的家神(penates),他们无需再为它们点灯、焚香或悬挂花冠。
如若有人胆敢以奉献为目的燔祭或以内脏为对象算卜,比附叛国罪对其提起诉讼,这是所有人都会认可的,虽然不涉及皇帝的安危,他还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为不论任何人妄图破坏自然的法则、调查禁忌之事、揭露深藏的奥秘、违反禁令、探寻他人的死期、许诺死后的希望,都将是罪大恶极的。
如若有人通过焚香的方式来祭拜那些由凡人创造且注定会被时间湮灭的偶像,或采取其他荒谬的手段,诸如突然敬畏自己制作的偶像、将丝带绑在树上、建立起一座草堆祭坛、向偶像献上礼物以表尊敬,即使这些行为轻微,但仍忤逆了宗教,并犯下反宗教之罪,一旦证实其异教迷信的行为,便可没收其房屋或地产。根据法令,若证实这些人香气缭绕,且这些土地归他们所有,则全部收归国库。
如若有人在公开的庙堂进行这种献祭,或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其建筑或土地行事,罚金25磅。如若有人纵容这种犯罪,他将受到同等的罚金惩处。
这是我们的意旨,这一法令由总督执行,各城市的军官和议员也应遵行,军官和议员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应立即告知法庭,并由总督完成处罚。此外,如若军官和议员因徇私枉法或玩忽懈怠而掩盖了此类罪行,则严惩之。如若总督对此类犯罪心存疑虑且因纵容而推迟惩处,罚金30磅;对其下属官员也施以等量惩罚。[7]473—474
从法令的内容可知,这是一部以异教仪式特别是献祭活动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宗教法令。值得注意的是,该法令的内容完全围绕着献祭活动展开,且详细规定了这些献祭活动的行为方式,除此之外,没有出现其他涉及异教的内容。以基督徒的观点看来,除却不承认上帝以外,在献祭仪式、神庙活动和偶像崇拜这三个方面投入大量的财富、时间和精力,是所谓“异教徒”的重要组成要素。[18]1119该法令既不涉及对异教神庙的封闭,也不涉及对异教偶像制造的打击。另需注意的是,东方总督鲁菲努斯(Rufinus)才是法令的总负责人。因此,虽然该法令限制了异教活动,但不论是在异教徒的行为方面还是在涉及的地域范围方面,制约都称不上全面。
在该法令中,与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可能存在较大关联的内容出现在第二部分,其中明确提及:“比附叛国罪对其提起诉讼”。[7]473若异教的献祭活动被视为一种叛国行为,那么似乎可以从侧面说明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然而纵观法令,异教的献祭活动不一定会导致叛国罪,只有与燔祭和占卜相关的献祭活动才会触及叛国罪,这主要是由于占卜行为有可能会牵涉到皇帝的生死,属于严重危及国家统治的异教活动,故将其视为叛国行为进行打击,而其他的献祭活动则均以财产罚为主。此外,后世的《查士丁尼法典》并未将该法令纳入其中的事实,也反映出该法令在帝国历史上的地位并非至关重要。事实上,无论是罗马帝国对献祭活动的限制还是塞奥多西本人的异教政策,都无法仅仅通过这一款法令得以体现。
若采信教会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约263—339年)的说法,早在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罗马帝国就已经出台了以全境为范围的献祭禁令。[19]若以《塞奥多西法典》为基准,君士坦丁一世的献祭禁令则仅限于家庭或私人领域:“其他人也可以效仿这一习俗,但应避免家庭祭祀,这是明令禁止的。”[7]472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献祭活动遭到法令明确的禁止。一条颁行于341年的法令称:“终止迷信,废止癫狂的献祭。如若有人胆敢违背我们神圣皇帝的法令从事献祭活动,他将立刻受到相应的惩罚。”[7]472一条在时间上存在争议但确由君士坦提乌斯颁布的法令重申:“这也是我们的意旨,所有人都应放弃献祭活动”[7]472,而发布于356年的法令则将打击的范围扩大:“一旦证实,有人进行献祭活动或偶像崇拜,判处死刑。”[7]472—473一年之后,造访罗马的君士坦提乌斯下令拆除胜利祭坛(Altar of Victory),这是维系罗马国家与众神之间关联的重要象征物。尽管在他死后,很可能在朱利安统治时期,胜利祭坛得到了修复,但在382年,格拉提安再度下令拆除胜利祭坛。[18]55
事实上,在392年的法令颁行之前,塞奥多西就已经在君士坦丁堡颁布了多款打击献祭活动的法令,如381年的法令提及,日夜沉溺于献祭活动的人将遭到放逐,382年的法令禁止在神庙内进行献祭活动,385年的法令则强调将会严惩通过献祭活动进行占卜的人。391年2月,君临米兰的塞奥多西指示罗马总督阿尔比努斯(Albinus):“任何人都不应以献祭动物的方式玷污自己,任何人都不应杀死无辜的牺牲”[7]473。由此可知,在4世纪,随着相关法令的不断出台,罗马帝国对异教献祭活动的限制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常态。392年法令的特殊性则在于其集大成的完备程度,通过借鉴此前帝国已经颁行的诸多献祭禁令,该法令以整合的方式重申了帝国官方对异教献祭活动的反对。
若以塞奥多西为视角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其异教政策具有极大的复杂性。由上文可知,塞奥多西从381年就开始打击异教的献祭活动,且根据佐西莫斯的说法,至少在383年之前,他就“派兵将帝国各地的神庙全都把守了起来,”[10]120值得注意的是,一条颁行于386年的法令却称:“尽管他没有遵从基督且仍在神庙里进行崇拜活动,但在选任大祭司时,更应考虑其在市镇服务方面的表现。”[7]358据此可知,在立法层面,塞奥多西并没有表现出清晰的禁绝异教的态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塞奥多西无法对异教进行全面打击。首先是军事形势,在当时的罗马军队中,异教仍然享有巨大的影响力。[3]7对于在与西哥特人的战争中登基的塞奥多西而言,无论如何,和议是存在风险的,他仍然需要得到军队的普遍支持;其次则是政治考量,异教精英仍然是塞奥多西希望争取的重要力量,他们能够为帝国政治的平稳运作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也能解释为何塞奥多西会在389—391年间对多位异教徒委以重任;[20]最后的顾虑或许是前车之鉴,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对异教进行了过于迫切的打击,最终造成了朱利安时期的异教复兴与政治动荡。[1]96即使身为基督徒的塞奥多西真的有心革除异教在罗马帝国的影响,他也不可仓促行事,因为政治的稳定才是他优先考虑的事项。
391 年2 月的法令却似乎使塞奥多西对异教的态度陡然严厉了起来。法令称:“任何人都不得接近神龛,不得在神庙附近游荡,不得敬畏凡人制作的偶像,这犯下了违背圣法与常法之罪。”[7]473一般认为,塞萨洛尼基大屠杀(Massacre of Thessalonica)及其后续事件[18]1492—1493与塞奥多西此时异教政策的转变存在重大关联,因为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在帝国决策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2]91391年的两款严格的异教禁令的发布对象需要注意,2月的法令由罗马总督负责,6月的法令则由奥古斯都长官和埃及总管共同负责。由此可知,即便是在安布罗斯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尽管是以异教传统非常深厚的两个地区为对象,塞奥多西的异教禁令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仍然十分有限。一方面,391年的异教禁令安抚了以安布罗斯为代表的基督教势力对异教打击的诉求;另一方面,由于禁令并没有触及更为广大的地理区域,塞奥多西的异教政策仍然呈现出克制的态度。
事与愿违,皇帝本人的冷静与基督徒的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92年初,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皮斯神庙(Serapeum)被基督徒摧毁。[21]虽然该事件的发生与391年针对埃及的异教禁令有关,但很难证明塞奥多西有下令摧毁过任何异教神庙,这种极端做法也与其一贯沉稳的异教态度存在反差。作为对此事的回应,塞奥多西颁行了那条以完备性著称的392年异教献祭禁令,之所以在此时重申帝国对献祭活动的反对,主要是由于塞拉皮斯神庙被毁事件是因异教仪式的纷争而起,法令颁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力图稳定当时紧张的宗教环境。[3]119—120对于狂热的基督徒而言,他们得到了自己满意的结果;对于异教徒而言,392年的献祭禁令不过是自381年就开始的献祭禁令的反复,他们仍然可以按以往的方式生活。
392年的法令是一款模糊的法令,这并不是指它的条文内容模糊不清,而是它无法作为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确定为国教的依据。它只针对献祭活动进行限制,且仅在东方大区推行。该法令在限制层面的模糊性是与该法令的政治背景紧密相关的,它的出台对应着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既是帝国一个世纪的异教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塞奥多西诸多异教政策的一部分,它无法被割裂地赋予过高的历史地位。
三、余论:塞奥多西与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国教地位
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公民令》还是392年异教献祭禁令,都没有直接提及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尽管它们都是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历程中的重要法令,但它们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背景,这也使它们无法承载过高的历史意义。由此,一个疑问便出现了,基督教究竟在何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据前文可知,至少在推行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方面,塞奥多西的态度是明确且坚决的。在381年的第二次全基督教大公会议上,基督教的教义之争尘埃落定,阿里乌主义再也无法立足于帝国,[22]塞奥多西对异端的打击是成功的。尽管在《塞奥多西法典》中存在着大量他对异教进行打击的证据,但塞奥多西在异教方面的政策却是克制的,进而有两个层面的事实需要注意。首先,这些法令是4世纪罗马帝国的常态。在百年中,罗马帝国一直在出台异教禁令,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异教活动的屡禁不止,有的异教活动直到6世纪时仍在正常进行。[23]其次,这些法令的实际影响力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在与塞奥多西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基督教学者的作品中,无法找到这些法令产生影响的明确证据。[24]对于塞奥多西而言,相较于仅存百年的异端,他无力亲手剿灭已经延续了千年的异教。塞奥多西的异教政策既是传统的也是冷峻的,相关的限制法令在不断出台,异教徒所能获得的经济支持也在逐渐减少,他既不支持基督徒摧毁异教的神庙,也不会惩罚那些确实摧毁了神庙的狂热基督徒。[3]123塞奥多西的目的是让异教慢慢地消亡,尽管他自己看不到那一天。
事实上,自尼西亚会议以来,[17]8罗马帝国就已经走上了难以逆转的基督教化之路,在392年异教献祭禁令中,“反宗教之罪”似乎便暗指当时的帝国已经存在一个官方的国教。诚然,塞奥多西的基督教政策给罗马帝国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和宗教影响,但他颁布律法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将基督教确立为帝国的国教,政治的稳定才是他首要考量的目标。基督教帝国国教地位的确立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标志,或许尚有讨论的空间。
[注 释]
①三位一体教义与阿里乌主义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教义认为二者是同一的,而阿里乌主义则认为圣子低于圣父。参见Eric Orlin (eds.),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Mediterranean Religion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6,pp.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