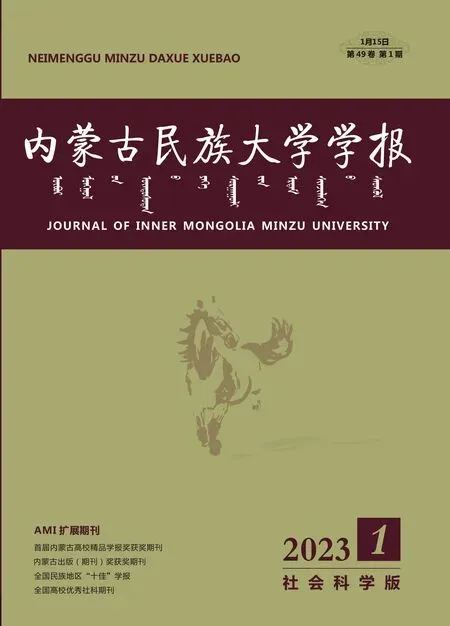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下跨民族友谊的心理内涵研究
——基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质性研究的证据
2023-08-06杨伊生
梁 静,杨伊生,李 傲
(1.呼伦贝尔学院 教育学院,内蒙古 呼伦贝尔 021008;2.内蒙古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3.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普通高校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心理教育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一、问题提出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既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民族工作要旨,也是全国各族同胞都应当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提出的族际接触理论认为,跨族际接触能够促进不同族群成员的相互融合,对不同族群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增加族群的接触也可能强化个体先前持有的刻板印象而增强群体之间的敌意[1],接触理论提出的最佳接触条件(合作、共同的目标、平等、权威支持)尤为重要,跨民族友谊至少满足了前三个条件[2],是一种理想的族际接触形式。民族团结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继续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等内容。基于民族团结工作在中国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本研究拟探究跨民族友谊的心理内涵,为民族团结工作提供实证支撑。
当前国内外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存在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跨民族友谊是一般性友谊在不同民族之间的表现,还是存在不同于一般性友谊的心理结构?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跨民族友谊只是一般性友谊在特殊人群中的表现,不存在特殊的结构。国外研究者通过将同种族友谊和跨种族友谊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同种族友谊和跨种族友谊在萌生、发展、维持方面存在差异[3];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了跨民族友谊的整体结构[4]。社会平衡理论(Heider’s Balance Theory)认为,建立同伴关系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亲近,但是亲近无法保证这种关系是积极的,也有可能导致个人之间的负面互动增多[5]。跨民族友谊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关系越亲密,越有可能近距离感受彼此的文化差异,也越有可能产生冲突和族群差异意识。
值得深思的是,在冲突和群际差异观念的驱使下,友谊双方仍然能够相处融洽的深层原因是否与跨民族友谊的独特心理内涵有关。跨民族友谊与同民族友谊的发生机制如果没有任何区别,那么跨民族友谊也应当仅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友好,如何将友谊转化为对待整个外族群的积极态度呢?本研究拟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探寻跨民族友谊的独特心理内涵。
以往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多采用量化的方法,通过大范围测量等方式揭示跨民族友谊与族际态度、个体社会适应等变量的关系。国外研究者虽然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对混合种族学校中的跨种族友谊进行调查[6],但是几乎未涉及跨种族友谊的内部心理机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量的方法比较适合在宏观层面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预测,质的研究比较适合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深入、动态的描述和分析[7]10。质性研究的方法适合探索未知的问题,尤其在建构理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跨民族友谊的独特心理内涵是一个新鲜的研究范畴,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依,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究跨民族友谊的独特心理内涵是恰当的。质性研究的有效性与所选案例的信息丰富性和研究人员的观察/分析能力有关,与样本大小无关。本研究以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为研究对象,从相对深入细致的层面探究跨民族友谊的心理结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虽然属于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但是在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进程中作出了不容忽视的巨大贡献。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黑龙江省等地区,同当地的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交往频繁,在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对其他民族作出了贡献[8],同时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由于对群体成员的高度重视,群体规模较小的群体成员比群体规模相对较大的群体成员表现出更高的群体认同感,在群体内与群体外的区别比群体规模相对较大的群体成员更加显著。在中国当前互嵌式民族关系格局的大背景下,对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的心理特点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跨民族心理结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中国民族团结等工作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跨民族友谊作为亲密的人际与群际之间的交往形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心理路径[9,10],在中国当前民族互嵌关系格局的大背景下,学界有必要探究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民族在民族之间融合进程中形成的跨民族友谊的心理内涵,为中国的民族工作提供积极性的心理证据。
二、基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质性研究
本研究通过开放式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同时采用反馈法、侦探法、比较法对资料进行效度检验;采用内容分析软件Rost Content Mining 6.0 和定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2.0,运用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分析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编码技术来分析、处理资料,为后续的相关讨论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实证基础。
(一)研究取样
第一阶段,通过系统分层取样和方便取样相结合的方式,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聚居地区选取开放式问卷样本,涉及的民族包括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满族。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56份。其中男性受访者124人,女性受访者132人。
第二阶段,采用方便取样和理论取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拥有较高质量跨民族友谊的鄂伦春族(5人)、鄂温克族(9人)、达斡尔族(7人)个体进行深度访谈,探究关于跨民族友谊的基本心理内涵。其中,男性受访者9人,女性受访者12人;在城镇居住的受访者11人,在嘎查/猎民乡居住的受访者10人;16岁至25岁的受访者8人,26岁至45岁的受访者8人,45岁以上的受访者5人。访谈对象的社会身份包括高校教师、公司白领、政府干部、牧民、个体经营者、退役军人、退休职工、医生、大学生、高中学生等。
(二)收集资料
1.开放式问卷收集资料。开放式问卷的题目根据前人友谊质量的研究量表[11]进行改编,主要用于初步调查跨民族友谊的基本情况及其存在独特心理内涵的证据,题目示例如下。
(1)与这位朋友相处过程中令您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2)与这位朋友相处过程中令您伤心的事情是什么?
(3)与跨民族朋友相处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2.预访谈收集资料。进行正式深度访谈之前,研究者随机抽取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各2位受访者进行预访谈。预访谈围绕“跨民族友谊”这一研究主题,邀请预访谈对象自由联想,报告自己的跨民族友谊交往经历和感受。预访谈的结构性相对较弱,研究者在预访谈中发挥辅助作用,鼓励受访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目的是了解不同民族个体对跨民族友谊的理解,为下一步设计正式访谈提纲打基础。
3.深度访谈收集资料。借鉴国外关于跨民族友谊的质性研究方法[6],个体深度访谈主要围绕跨民族友谊区别于一般性友谊的独特心理内涵和心理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展开,具体访谈提纲示例如下。
(1)您在与这位朋友相处过程中的整体感受是怎样的?能否讲几件相处过程中令您难忘或者感动的事情?
(2)您与这位朋友经常见面吗?与他的家人有接触吗?感受如何?
(3)您会向跨民族朋友分享自己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吗?分享后的感受是怎样的?
(三)分析资料
1.基于语义网络的资料分析过程。本研究逐一阅读回收的256份有效问卷,形成整体印象后进行编码和语义网络分析。
首先,研究者将所有问卷按题目导入微软公司开发的电子表格软件(Microsoft Office Excel),每个题目形成单独工作表,每位被试的答案占一行。
其次,根据每位被试的作答情况进行关键词提取。
再次,在提取关键词的基础上,将资料导入内容分析软件Rost Content Mining 6.0进行词频统计和语义网络分析。
2.基于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过程。本研究对深度访谈资料基于扎根理论进行收集、分析、理论建构。
首先,将21份访谈语音转换成文字,保存为微软公司开发的电子文档(Microsoft Office Word文档)。
其次,采取“投降”的态度对每份访谈文字资料进行多次逐一阅读并且校正。
再次,将文字材料作为21个案例导入定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2.0,依据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和类属分析,采用同类、异类比较及横向、纵向比较的方法[12]不断提取高一级节点,直至形成互斥的三级节点及类属关系。
(四)效度检验
1.开放式问卷效度检验。本研究采用反馈法[7]404对开放式问卷的资料进行效度检验。本研究在编制开放式问卷的过程中,分别同心理学专业、民族学专业教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拥有跨民族友谊的朋友/家人反复交流,最终确定开放式问卷的题目,发放少量问卷进行预测。研究者回收预测问卷后,继续与上述人员进行交流并且调整个别题目。研究者回收全部问卷后,继续同相关人员探讨,邀请1名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共同分析回收材料,以确保回收和分析材料的效度。
2.深度访谈效度检验。本研究采用侦探法和比较法对深度访谈收集的资料进行效度检验。侦探法是一个开放渐进的过程,研究者按照研究问题的性质、目的、依据的理论不断对研究的各个层面和环节进行搜寻,找出有可能影响效度的威胁并且进行检验,然后想办法排除这些威胁。比较法是在搜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比较,贯穿研究始终[7]406。本研究通过侦探法依次找到一系列有可能影响研究效度的因素,例如访谈对象对跨民族友谊理解不同、访谈对象不愿暴露隐私、访谈对象所谈内容存在社会赞许性等,结合对同一访谈资料的纵横比较、不同访谈对象的资料进行比较、访谈对象自我确认等方式保障研究效度。
(五)研究结果
1.开放式问卷研究结果。256名被试中有196人拥有跨民族朋友(占回收问卷总数量的76.56%),拥有6个以上跨民族朋友的个体占比接近50%,60人无跨民族朋友(占回收问卷总数量的23.44%),10人由于心理抵触或者恐惧等原因而不选择跨民族朋友(占回收问卷总数量的3.91%),其他个体无跨民族朋友的原因是受环境影响,并未表现出内心的排斥。此外,多数跨民族朋友都是在原有地缘、业缘基础上结识的。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社会交往结构非常有利于形成跨民族友谊。
从跨民族友谊的外显交往行为角度分析,跨民族友谊与一般性友谊没有较大的区别。访谈对象回忆与具体的跨民族朋友难忘的经历和共享性活动时,获取的访谈结果与一般性友谊的行为很类似,例如性格相合、彼此信任、相互陪伴、体贴亲密、共同话题多等,无法获取关于跨民族友谊不同于一般性友谊的独特元素。
从相对内隐的交往认知和态度角度分析,访谈对象认为跨民族友谊的确存在一些不同于一般性友谊的独特之处。访谈对象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对所有的跨民族朋友进行总结时,他们开始关注观念差异、文化新鲜感、民族性格等与民族相关的元素。
2.深度访谈研究结果。本研究采用定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2.0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码,在充分阅读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围绕“跨民族友谊互动”和“对跨民族友谊的认识”等内容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最终形成124个开放性节点(一级编码)。本研究在进行一级编码的过程中尽量保留访谈对象的“本土语言”,邀请两位访谈对象对编码情况进行检验以确保编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在一级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比较和归类的方法,对124个码号进行二次审视,最终萃取37个主轴性节点(二级编码)。本研究在二级编码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对不同意义单元的码号进行比较和归类,萃取6个选择性节点(三级编码)。6个选择性节点分别为内群边界知觉、自我体系重建、文化互动张力、冲突处理策略、一般性友谊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研究通过进一步上位理论分析发现,内群边界知觉和自我体系重建均指向跨民族友谊交往过程中的群体认知和自我认知,文化互动张力和冲突处理策略均指向跨民族个体对彼此文化差异的互动行为和认知,以上四个节点可以归入内外群重构和文化差异应对两个核心类属,属于跨民族友谊的核心成分。一般性友谊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跨民族友谊中起到观念引领性作用,本研究将二者归为跨民族友谊的观念性成分。
三、跨民族友谊的心理内涵剖析
(一)跨民族友谊存在独特心理内涵的证据
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初步说明,跨民族友谊的外显行为与内在观念似乎不同。行为层面体现了一般性友谊的基本内容,跨民族友谊双方的互动内容同一般性友谊没有本质差异,均包括共同活动、共同兴趣爱好、相互陪伴、相互关心、自我表露等。多数国内外学者对跨民族友谊的研究采用一般性友谊的测量工具和指标,这些研究工具很少涉及跨民族友谊的观念层面。一项元分析[13]研究显示,仅有少数研究者关注跨民族友谊的情感和认知维度。社会认知能力对建立和保持跨民族友谊特别重要,未来研究有必要探究跨民族友谊的多角度独特贡献,对跨民族友谊的观念和意识层面进行剖析,以探究跨民族友谊与一般性友谊是否存在差异。在开放式问卷调查中引导被试从整体意识与观念的层面对跨民族友谊进行分析,多数被试回答“与跨民族朋友相处时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时,能够从跨民族友谊与一般性友谊的差异角度重新界定和审视跨民族友谊,突出回忆跨民族友谊中文化、风俗、差异应对方式等与民族相关的因素。本研究根据开放式问卷的研究结果初步判断,跨民族友谊存在与一般性友谊不同的独特结构,而且这一结构主要体现在意识和观念层面。开放式问卷的研究结果为后续深度访谈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扎根理论分析的切入点。
(二)跨民族友谊的核心性内涵
1.内外群重构。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学者亨利·塔菲尔(Henri Tajfel,波兰人)和约翰·特讷(John C Turner澳大利亚人)创立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且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的社会身份并不单一,身份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分类的多维性。在跨民族友谊交往过程中,某一个跨民族的朋友究竟属于内群成员还是外群成员,个体依据民族群体还是朋友群体[14]划定内外群界限,哪一种分类标准对个体的意义更大,这一系列问题成为跨民族友谊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内群边界知觉主要指不同民族个体在与其他民族的朋友交往过程中对内群边界的感知,包括对内群范围大小、内群稳定性、内群规范、跨民族朋友是否属于内群等的感知。少数民族在某个群体中(例如学校)占多数时,不太可能形成跨民族友谊。从地位角度来讲,光环效应可以激励少数群体成员敞开心扉,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成员接触。有身份意识的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成员可能会避免与少数群体成员建立同伴关系。
综合来看,内群边界知觉在跨民族友谊的心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跨民族友谊的发展走向。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资料发现,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民族在交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群际边界感。学校和社区既应当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中注重不同民族接触的比例,也应当通过重新建构群界等途径促进民族团结。
自我体系重建主要指不同民族的个体在与其他民族的朋友交往过程中通过不断体会亲密性和相似性而将对方乃至对方所在族群纳入自我体系,进而重构自我甚至重构内群边界的过程。该过程体现着个体与他人及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体验和维护。已有研究证明,个体与所属族群联系的紧密性等都能够对个体的跨民族友谊产生影响[15]。个体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是考虑自己的身份还是考虑群体的身份,对跨民族友谊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根据个人特征和群体特征而选择的朋友是不一样的。自我体系是否能够突破边界而重新建构,在跨民族友谊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灯塔的意义,甚至决定着跨民族友谊能否改善族际态度。跨民族友谊与非跨民族友谊相比,首要特征是友谊双方来自不同的民族群体。探究跨民族友谊的独特心理内涵,必须考虑友谊双方对内外群的感知和建构。本研究深度访谈的分析结果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证。内外群重构是跨民族友谊交往中的核心心理要素,不仅包含对群际边界的感知,而且包含具体的自我体系重建。
11号访谈对象(鄂伦春族):我对从小一起玩的好朋友,感觉不到她是什么民族,都像自己家的亲姐妹。
16号访谈对象(鄂温克族):可能与她的民族有关系,感觉那个时候她的性格不是那么好,不跟陌生人来往,也不怎么说话,她以前还有洁癖。初中一年级、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一起,后来她受到我的影响,逐渐没有洁癖了。她现在变得爱说话、爱交朋友了。
2.文化差异应对。跨民族友谊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文化的差异必然给友谊双方带来互动方面的独特体验。文化互动张力主要指不同民族个体在与其他民族的朋友交往过程中对文化交流阻力和吸引力的感知与选择,主要体现为是否能够体会到与跨民族朋友交往过程中的阻碍或者新鲜感,体会的程度如何,与其他民族的朋友交往过程中对阻力和新鲜感的趋向或者回避等态度。
从文化互动的视角分析,可能由于不同民族的年轻人体会到的彼此群体的差异转化为一种阻力,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选择逃避阻力,导致双方接触频率降低。需要注意的是,互动张力知觉除了感受到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压力外,也会感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新鲜感。因此,文化互动张力在跨民族友谊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策性意义。
4 号访谈对象(达斡尔族):我说达斡尔语的时候朋友会模仿,可能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吧。
16号访谈对象(鄂温克族):我非常喜欢看他们演出,感觉和自己的民族不一样,有新鲜感。
2号访谈对象(达斡尔族):我们民族一般去老人家里的时候,要给老人请安,然后他就看不懂。有一次我带他去我姥姥家,进门的时候就做请安的动作,他以为我被绊倒了,赶紧过来扶我。
冲突处理策略主要指不同民族个体在与其他民族的朋友交往过程中面对由民族文化不同而引起的差异和矛盾等冲突时的解释与应对方式。已有研究表明,自我表露作为冲突处理策略的重要形式之一,在跨民族友谊的心理结构中处于重要位置,是影响跨文化友谊形成的重要因素,被列为构建跨文化友谊中关系认同的七种策略之一。本研究发现,除了自我表露策略外,还存在顺其自然、相互包容等策略,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挖掘。本研究基于发现的跨民族友谊交往中的独特策略,建议各级各类学校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工作中融入差异应对策略方面的课程或者活动。
8号访谈对象(鄂温克族):他乐意喝酒,我俩就一起喝酒。喝多了吵起来,谁也不理谁,自己回家。第二天见面都忘了,谁也不记得前一天吵架,又在一起可好了,根本不会往民族那方面想。
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对跨民族友谊双方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友谊带来新鲜的感受,也可能成为扼杀友谊的利刃。跨民族友谊双方个体在交往过程中正确认识并且权衡文化差异带来利弊,在面对习俗、语言等不一致的情况时采取有效的冲突协调策略,均是跨民族友谊的重要心理内涵。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通过开放式问卷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跨民族友谊与非跨民族友谊相比的独特心理内涵。核心性内涵主要涉及内外群关系的重新认知和建构、文化差异的认知和应对两方面。换言之,跨民族友谊双方个体在面对背景人群和背景文化的差异时,表现出来的认知和应对措施的差异。诸多因素会影响个体在跨民族友谊交往中的核心心理,例如个体层面的人格、民族本质论,社会层面的族群关系、社区构成、接触频率等。对跨民族友谊的核心心理内涵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能够通过改善跨民族友谊质量这一路径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
从内群、外群重构的角度来看,跨民族友谊双方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更快地打破民族边界,对自我进行跨族群的重新建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能够为中国学校教育和社区建设中的民族工作提供相关的条件假设。应对文化差异的角度、友谊双方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和取舍、面对差异和处理矛盾的方式,都直接或者间接决定着友谊的后续发展和群际态度、群际信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