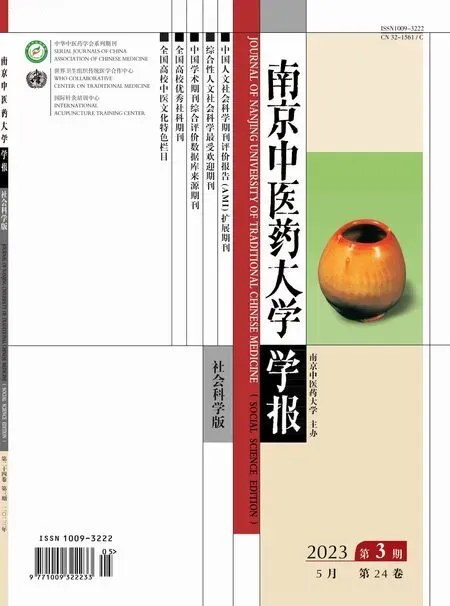批判与调适:近代来华传教医师嘉约翰对中国医学的态度
2023-08-04李计筹郭强
李计筹,郭强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1 嘉约翰关注中国医学的背景
嘉约翰关注中国医学的背景之一是西方汉学和博物学的发展。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神秘的东方文化知识成为西方科学家们努力追寻的目标。[1]16-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白晋(J. Bouvet)、巴多明(D. Parrenin)、殷弘绪(F. X. d'Entrecolles)、韩国英(P. Martial Cibot)等曾对中国的医学和本草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2]进入19 世纪,“科学工作者深受培根科学方法论和近代经验论思潮影响,书本研究与实地观察相结合、博物学考察与汉学研究相融合的研究范式愈发兴盛起来。”[1]当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多具有汉学家或是博物学家的身份,对中国的医学和植物学自然关注有加。
嘉约翰作为传教医师来华时,其前辈郭雷枢(T.R. Colledge)、伯驾(P. Parker)、合信、禆治文(E. C. Bridgman)等人已经探索出藉医传教的方法,并于1838年建立“中国以医传道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确立了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医学知识,配合道德和宗教的训练,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并使之接受基督教的目标。[3]但是要想在中国传播西医,必然要面对历史悠久、理论技术成熟的中医以及中国人普遍接受中医的社会现实,因此研究中医药、探寻中医药的优缺点成为传教士们选择的突破口。
2 嘉约翰对中医学的评价
嘉约翰来华后,在国外期刊上发表多篇批评中医的文章。1859年在TheNorthAmericanMedico-ChirurgicalReview(《北美外科医学评论》)上发表MedicineinChina[4],该文同年被法国Gazettehebdomadairedemédecineetdechirurgie(《医学与外科公报》)专栏转载[5];1872年在汉学杂志ChinaReview(《中国评论》)上发表ChineseMedicine[6];1877年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MedicalMissions[7];1893年在MedicalNews(《医学消息》)上发表NativeandForeignMedicineinChina[8]。这些文章主要从中医理论、解剖、脉诊、外科、中药和医学教育等6个方面对中医进行了观察和评价。
2.1 对中医理论的评价
嘉约翰指出,中国人认为:“在大自然中存在阴与阳两种元素或力量,类似于雌性与雄性,这两种元素共同在我们自身或周边世界引致生理性、化学性和其他重大的各种现象。通过引入这个充满想象性的阴阳理论,不仅所有令人费解的无机物变化可藉由阴阳元素的联动反应而得到解释,也可用以阐释有机体各器官健康与疾病的神秘机理过程”,“身体的每个器官或属阴,或属阳,当它们平衡时,就会呈健康状态。如果阳盛,就会产生疾病,而且是炎症;如果阴盛,就会产生下部的或寒性的疾病。还有器官与热、寒、湿、干之间的关系,以及热、寒、湿、干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对人体的作用与反作用,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医大量谬论,实在不可思议”[6]。他批评说:“在中国无数的医生中,从来没有人能够突破古老无知的束缚,开辟一条科学和理性的医学新路,正如西方医生所追求的那样。”[6]
2.2 对中医解剖的评价
近代西人对中医诟病最多的是解剖学。嘉约翰说:“所有半文明国家的医生都对解剖学和生理学完全一无所知”[7],虽然在古代“中国人拥有比现在更多的解剖学知识,但已经消失了好几个世纪。现今中国人对人体的结构和人体器官的功能完全没有任何正确的了解”,“中医书籍里的一些解剖图表和描述,展示了对人体结构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粗浅而错误的认识,解剖图里还出现不存在的器官”,“这些对于结构和功能的错误认识已经流传很久了,没有人能够超越过去的传统,也没有人能够进行调查以发现真相”[7]。
2.3 对中医脉诊的评价
嘉约翰对中医脉诊的态度先后有较大变化。1859年他在MedicineinChina一文中谈到脉诊时说:“这种检查脉搏的系统非常复杂,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才能掌握,无论对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何看法,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古代医生是最优秀的观察者,尽管我们可能会拒绝他们的理论和他们指出的适应症”[4],显示出他对中医脉诊的尊重。但1870年代后,他的态度变得傲慢。在ChineseMedicine一文中,他说:“如果详细描述每个手腕上的三个部位的脉象与内脏的细微关系会让读者感到厌倦和厌恶,这种谬论怎么能世代相传并被普遍接受”[6]。他认为中国的古人可能知道血液循环的事实,但不了解动脉和静脉的功能,脉诊虽然给中医师提供疾病的线索,但同时也掩饰了他们的无知,因为可怜的病人是无法辨别这些深奥的知识的。[6]
2.4 对中医外科的评价
嘉约翰认为,“外科在中国并不存在,因为对解剖学的完全无知,妨碍了中国医生外科手术的熟练程度”[6]。他认为“中国众多的医生中没有一个会自诩能做最简单的外科手术,他们没有尝试过切开脓肿或切除肿瘤,动脉结扎似乎从未被考虑过,对出血的恐惧阻止了任何切割工具的使用”[8]。“在西方科学和技术已经完善的外科治疗中,中国人得到了好处,他们承认至少西医外科在现代是没有任何对手的”[6]。
矿业废弃地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存在,尤其在一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些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各国从很早开始就重视矿业废弃地的治理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4]。澳大利亚是一个重要的矿业大国,在矿业废弃地的生态恢复工作中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该国要求采矿企业在矿山开采前就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且制定详细的恢复方案,并且实行开采与恢复工作同步进行,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虽然国外已经对矿业废弃地的生态恢复相关技术做了很多研究,表土复原是常用的技术,但该技术仅适用于新开采的矿山,而我国历史遗留矿山众多,引入推广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5 对中药的评价
嘉约翰认为中国人对药物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知的,他们“将龙齿、虎骨、珍珠、鹿茸、人参及饮食中的食材皆纳入药物范畴,但不知道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成分是什么”[7]。他把中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共同使用的,第二类是中国特有的,而且他认为西方国家比中国人更了解第一类药物的性质和用途,在第二类药物中,有许多是绝对惰性的(笔者按:即无药性),有许多药是令人作呕的。[6]在讨论中药的使用时,他认为:“中国人对于任何一种药物的使用,都选择五行中的一行与患病器官之间建立特殊关系,这种方法是非常错误和荒谬的。”[7]中国人的用药经验因为没有被科学验证而毫无价值,或者至少是不可靠的,比如“中国人认为人参的价值高是因为人参的根与人体的形态有现实的或想象中的相似性”[6]。“尽管中医理论和实践存在着种种无知和荒谬,但中国人对中药有着极大的信心,而且服用的药物比其他任何人都多”[4]。
2.6 对中医教育的评价
嘉约翰认为中国的医学教育是非常有限的,“中医所有的实践都是纯粹的经验,科学没有纳入中国的医学教育中,解剖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也没有成为中国医学教育的分支”[8]。中国没有专门的医学院对医生进行教育,“想要学医的人主要通过跟从私人教师学习和看书的方式学习常用的治疗手段,任何人都有行医的自由,大量的学习者都不算作是正规医生。那些无知的江湖郎中常常利用人体自我修复的能力,假装治愈病人的疾病,从而欺骗无知和毫不怀疑的人”[6]。
正如学者陶飞亚所说:“嘉约翰实际上从医学和药学的理论、临床实践、医疗体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几乎彻底否定了中医。”[9]
3 对嘉约翰错误认识中医的解析
中医药学理论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的现代医学截然不同,嘉约翰对中医的判断和评价多是从西医理论和相关制度体系的角度出发,因此在评价中医时存在许多认识误区。
在解剖学方面,中国医家很早就对人体脏腑进行过观察,《灵枢》《难经》等医书对人体脏腑的形态、大小和功能进行了描述,且与现代人测定的大小基本相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解剖图如《五脏图》《存真图》《脏腑明堂图》等,是古代医家长期实践并不断演绎、总结而形成的对人体脏腑的认识。嘉约翰认为中医解剖图中有现实不存在的器官,但实际上它们确实有参与维持人体生理活动的功能。比如三焦,有研究表明它“是一个具有明确结构的组织器官,其结构基础为‘肉分之间’而非实质之处,结合现代医学,……即三焦器官是一个间质组织,基本功能是气化,发挥的是通道作用”[10]。又如经络,在现实人体解剖中看不到,并不等于其不存在。嘉约翰只看到了人体中一个个孤立的脏腑,却忽视了联系、沟通这些脏腑的组织和通道。中医很早就发现了脏腑之间的这种微观联系,但西医只停留在静态解剖形态方面。不可否认,在11世纪之后,由于方法论、古代医学教育、封建伦理道德等因素阻碍了人体解剖在中国的发展[11],使得中医解剖图谱处于粗略状态,不似西医骨肉脏腑逐层剖验,形体真晰。
古代中医虽无现代的动静脉概念,但是很早就认识到血有“血出而射者”(即动脉血)和“血少黑而浊者”(即静脉血)的不同[12],并且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血脉在人体生理、病理状态下的运行规律,进而创造了脉诊方法,藉此了解人体脏腑的健康状态,但这是基于解剖和实证主义的西医难以理解的。
中医外科历史悠久,剖腹、切除、缝合、探取手术以及麻醉在文献中皆有记载,只是在古代社会外科技术被鄙视为“小技”,外科医生地位低下,导致从事外科的医生相对较少。不过尽管如此,明清时期仍然外科名家辈出,如陈实功、王肯堂、王惟德、高秉钧等。与嘉约翰所处时代相同的中医外科医家医著就有高文晋的《外科图说》、高思敬的《外科医镜》,这两本著作对中医外科器械有详细绘图和说明,展示了晚清时期中医外科发展的水平。嘉约翰妄言中国无外科以及中医不会做手术,显示了他对中医外科了解有欠深入,以及他的倨傲和偏见。
在药学方面,中国人从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来认识中药属性,并在中医阴阳五行等理论指导下用药治病,经过数千年的认识和积累,对许多药物特性的认识超越了包括嘉约翰在内的西人的认知。嘉约翰把西方药典中没有的药物及饮食中的食材列为惰性(无药用的)药物,说明他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中西方的药学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体系,他在对中国药学理论不了解的前提下,只从药物化学、药理的角度来认识中药及其临床应用,明显是不妥当的。
不可否认,中医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嘉约翰说中医没有正规的医学教育机构和考验制度,在中国学习中医,除了师带徒之外,还允许自学,只要不触犯朝廷律例,任何人都可以行医,导致行医门槛较低,这与西方现代医学严谨的医事制度和配套的法律约束相比是有所不及的。
4 嘉约翰对中医药的借鉴和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嘉约翰虽然猛烈批评中医,但在中国行医传教的过程中却常常借鉴和利用中医。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时,他经常借鉴中医的做法。其著作《内科阐微》中有大量事例,如“凡验病人之舌,而见其色,或红,或黄,或黑,与及或湿或燥,即知其病之轻重也。……间有舌微肿,一伸出而即现齿印者,医者亦不可不辨也。夫舌之干湿各殊,其干者口津少,或舌汁少也,由此而推,即知五脏内之津液亦少也。”[13]7-8这明显是中医舌诊的方法。又如诊脉,他说:“诊脉之法甚详,而大端有五。一宜用三指,向病者左右手之寸关尺处,先审其脉之或急或慢,抑或急慢之不匀,均宜细辨也。二将诊脉时,或病者乍觉惊慌,则其脉必不定,医者须少俟片刻,方可诊也。三不拘病者或坐或卧,其脉亦无不可诊。四倘病已沉重,而医者诊脉,或一次未得其确,则宜少停,再行细诊。五学医者欲习诊脉之法,宜先向无病之人,多行诊熟,然后以之诊病,方得谙练。”[13]17-18这些与中医脉诊并无二致。
另外,嘉约翰在其翻译的著作中大量使用中医的病名,有消渴、痨瘵、瘰疬、砂淋、鸡眼、麻风等。如1882年出版的《西医内科全书》云:“消渴症,此乃小便频多,内含糖质,状见口渴人瘦,愈渴愈饮小便愈频”,分为“消渴溺多”和“消渴溺甜”两种。[14]其实,嘉约翰之前的来华传教士在编纂英汉辞典时,通常也尽量选用中医既有的病名来对应西医的疾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传教士对中医的了解程度深浅不一、参照翻译的典籍不同等原因,造成了同一西医名词中文翻译五花八门的乱象。1890年,来华传教士为推动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成立了博医会名词委员会,负责统一医学名词的工作,由嘉约翰担任首任主席。1894年出版的《病症名目》(AvocabularyofdiseasesbasedonThomson’svocabularyandWhitney’sanatomicalterms) 就是嘉约翰在此间编纂的一部英汉医学术语词典,在当时具有一定权威性。该词典仍然优先使用既有的中医病名,而非采用对西医病名直译的方式,如“venereal disease”,嘉约翰使用中医的“花柳”作为其译名,而非直接译作性传染病[15]34;又如“calculus”,西医病名为结石,嘉约翰使用的是“砂淋”[15]4。
嘉约翰有时也借鉴中医疗法治病,如利用汞治疗花柳,利用朴硝泻法治疗淋病等。[15]治疗疾病在使用西药的同时,也使用中药,如鸦片、熟石灰、硫黄、硼砂、杏仁油、三仙丹、密陀僧、鸡蛋黄等。[16]在博济医院某些年份的年度财务报告里可以看到购买中药的费用,如1863年购买中药的费用是22.52元。[17]嘉约翰认同中医对某些疾病发病机理的解释,如合信将中医的热证视为炎症,但实际上中医所讲的热证并不都是炎症,对此嘉约翰在《西医热症总论》中特撰“辨明大热症与炎症不同”一则,云:“夫热症非在脏腑一处,亦非在肢体一处,先有病,而后串及周身者也。炎症者,乃在肢体中,或脏腑内,先有一处发炎,而后混身始见发热,迨炎症愈而身热即全退矣。而有热症者,乃因毒物之气入血内,周身先见发热,而后脏腑或有一处发炎,迨炎症虽除,而身热仍未能与之俱退者。是以热症与炎症有所分焉。故论热症,必先论身热,然而论身热,必须分辨先发热而兼变炎,抑先发炎以致身热,二者相因而实有异,且似是而非,淆乱最易,不得不反复明辨焉。”[18]除此之外,他还在其创办的博济医校招收中医出身的学生,“欢迎任何由中国医生致力于西医治疗的倾向”,“到1885年,‘已有两三位本地医生询问过来教学的问题’”。[19]180博济医校也开设中医课程,由关韬主讲并带领学生进行临床实践。[20]
由此可见,嘉约翰对中医药的借鉴和利用包括诊法、疗法、病名使用、药物使用以及疾病发病机理等,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嘉约翰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医药其实并非一无是处,实乃讽刺之极。
5 嘉约翰对待中医态度的原因剖析
嘉约翰对中医药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批判,另一方面又借鉴利用,看似自相矛盾,实际上都与其在中国传教的使命有关,作为传教士,其在华一切医疗活动都要为传教事业服务。通过对上述嘉约翰发表的论文进行爬梳,笔者总结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5.1 试图在中国用西医取代中医
嘉约翰认为西医比中医更科学严谨:“中医治疗病人时不知道疾病的本质和药物的用处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出现给错药,或在错误的时间给药,或在正确的时间没有给药等情况。所有这些危险都来自于中国过时的无知的错误的医学理论,因此很明显,传授给他们我们所拥有的科学且合理的医学知识,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好处。”[6]180作为中国以医传道会的一员,在中国传播西医是他的目标,他希望通过批评中医不科学、不专业,言说中医的种种不足,来展示西医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以使中国人失去对中医的信心,最终希望中国官方像日本那样废除中医进而全盘推行西医。[17]
5.2 呼吁更多传教医师来华传教
正如学者高晞所说,嘉约翰针对中医的批评,是“为强化医学传教在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1]。1850年代,许多西方教会对医疗传教持犹豫态度,认为开支较大,且对传教不一定产生良好效果。但嘉约翰认为中国落后的医疗状况,“显示了未开化民族的无能和身体上所遭受的痛苦,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疾病的本质和治疗的合理模式,以及完全缺乏医疗慈善机构,而这些机构是基督化、科学化医学的产物,这一切都表明医疗技术一定是在异域传播基督福音这项伟大工作的婢女”[7]。通过选择性地向教会展示中医在外科、眼科、产科等领域的落后以及西医在这些方面的先进性,向教会展示西医慈善医疗在降低民众敌视和基督教传播方面的加分作用,希望西方各教会支持在中国进行医疗传教,同时也能证明传教士在中国行医传教的合理性,以及对在华教会事业的推动作用。
医疗传教路线确立后,来华各教会普遍面临传教医师匮乏的难题。据老谭约瑟(J. C. Thomson)统计,1860年之前来广东传教过的医师为10人,1880年之前共16人[22],即嘉约翰来华20多年里西方教会选派来广东的传教医师非常少,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因此他通过展示中医的落后,呼吁更多传教医师来华,切实为传播福音助力。[4]
5.3 针对中医话语进行文化调适
嘉约翰借鉴利用中医,实际上是他针对中国本土文化而进行的调适,其主要目的有二:第一,减轻地方民众的排斥或敌视,避人耳目。由于西医为外来医学,如果单纯传播西医及进行西医诊疗,那么在这过程中出现的解剖尸体或割治手术,极易引起民众恐惧而视之为异类,在日常教学、诊疗活动以及翻译的西医书籍中加入中医药元素,可有效减轻国人的陌生感。“早期人们对西医西药非常抗拒,为了给人们用西药,博济医校学生常常不得不把西药混在中药里给人”[19]18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同化中医。博济医校招收中医出身的学生,使本土中医生深入了解具有实证主义特点的西医知识,逐步接受西医的诊疗思维,从而放弃甚至质疑中医的方法论,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医树立的典范。
6 嘉约翰等传教士批评中医产生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嘉约翰等传教士集中发文对中医进行批评,对近代中医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嘉约翰等用西医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标尺来认识和评价中医,存在认识片面甚至解读错误,从而向世人传递出中医不科学、不专业、不规范的信号,而且他们的言说被西方杂志不断转载和复述,使得中医理论体系被曲解,中医的实用性和有效性等得不到彰显,实际上不利于中西医学的交流和中医的西传。其次,批判中医的言论对中医话语权力日渐式微以及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加速度,其占领舆论广场的效果是不能忽视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批判中医的言论在他们刚进入中国这一时期发表较多,目的是通过批判中医以展示自身优势,为自身赢得立足之地。至20世纪初,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医势力在中国已具有相当规模,1900年在中国已有 196 名传教士医生,1913年达到 450人,1925 年全盛时达到 600 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教会医院,据统计,1920 年全国教会医院有 326 所,是当时全国医院数量的一半。[23]传教医师广泛涉足中国的医疗乃至卫生行政活动和事务,还创立了构建西医话语的社团组织博医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加之西方文化不断输入,西医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因此,民国时期传教士批评中医的言论相对少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西医地位已经稳固,另一方面传教士也无须亲自上阵了。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开始批判中医,其认为中医不科学的言论和以往的传教士如出一辙,这些人不限于传教士培养的和出国学习的西医生,也有非医学界但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士,他们成为了西方批评中医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