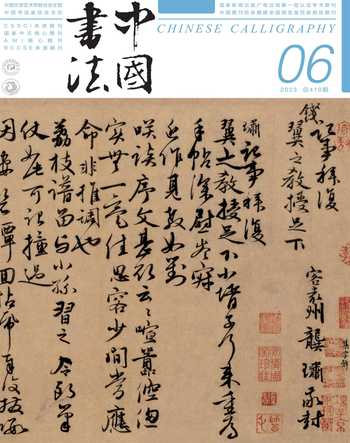羊毫毛笔与碑学实践探究
2023-07-25张机
张机
关键词:羊毫毛笔 金石气 碑学 重 拙 大
就现存的资料来看,唐宋时期已有关于羊毫毛笔的记载,但一直到清代羊毫毛笔才成为书家使用的主流,这与碑学思潮的兴起有关。碑学家的审美主张是『金石气』,是金石碑刻经历史沧桑所带来的厚重、苍茫、古拙的美感。关于清代碑学的审美旨趣,学者论述颇多,基本上以『重』『拙』『大』为主。为了使这种审美意识在自己的书法中有所体现,清代的碑学家们从取法范围到文房用具,再到执笔用笔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索。这其中荒野断碑都成了他们的取法对象,更别说将羊毫毛笔作为自己的使用工具了。羊毫毛笔比较柔软,可以使笔锋产生更多的状态,不同状态下写出的线条质感也就不同,这也为碑派书家们探索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可能。由于历史上没有关于羊毫的笔法流传,所以探究羊毫笔法是清代碑派书家们的当务之急。为此,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张在辛曾目睹郑簠的书写过程:『因自就座取笔栩管,作御敌之状,半日二回,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1]说明郑簠的写字姿势不符合人的生理习惯,也就是不属于正常的运笔方法。梁巘曾认为他的笔法有问题,尝云:『郑簠八分书学汉人,间参草法,为一时名手,王良常不及也。然未得执笔法,虽足跨越时贤,莫由追踪先哲。』[2]郑簠的例子说明,书家在探索笔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曲折。有的书家为了达到金石气的书写效果,更是将书写工具进行了改制,例如金农,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说:『金农截毫端作擘窠大字,甚奇。』[3]这就是说,金农把毛笔笔尖剪掉,改造成类似排刷的书写工具,但这一行为同上述郑簠写字的歪曲笔法一样,显然是不可取的,也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推广。
管随指转与『拙』
在碑派书家的审美中,『拙』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拙』具体是指『古拙』,是碑派书家们最想要表现的意味。在碑派书家的书论中,『拙』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在讨论中,除了关于『拙』的含义外,很大一部分是如何在书写中将『拙』表现出来。其实,在碑学的初期,想要在一根线条中表现出『拙』的意味,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包世臣的书论中,有不少关于探索这一笔法表现的记载:
及见山人(邓石如)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
今小仲(黄小仲)之法……而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
诸城(刘墉)作书,无论大小,其使笔如舞滚龙,左右盘辟,管随指转,转之甚者,管或坠地。
从上述包世臣的记载中,能清晰展现书家对『管随指转』笔法的追求。那么『管随指转』与『拙』到底有何关系呢?『管随指转』,是指在行笔的过程中利用手指捻动笔管,使其成裹绞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裹锋绞毫』,這应是邓石如等人笔法的核心点。羊毫毛笔配之裹绞法,写起来较为迟涩,可增加线条的变化,使线条形成老辣遒劲、苍莽雄劲、深厚迟涩之风采。其实这种线条就是『拙』的审美要求,包世臣自己也谈到了『裹锋绞毫』所带来的变化:
裹笔则专借他画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短长排阖之雄,弱者为便辟侧媚而已……及近人刘诸城,乃专恃此,又先以搭锋养其机,浓墨助其采,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显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几于龋齿堕髻矣。
包世臣梳理了『裹锋绞毫』的历史。他认为,刘墉等人因其裹毫,带来『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的效果。这种用笔方式虽不止一位书家在探索,但是邓石如凭其出色的书法实践,生动展现了『拙』的特点,遂成为一代名家。一八〇五年(嘉庆十年十月初四),邓石如卒,临终前还希望包世臣将其笔法发扬光大,云:
此生无憾。惟泾川碑刻未竟;及尚遗二子,一不及十岁,一不满月,余不能尽父辈之责,有赖诸亲友督导教养也;北魏碑学之探究,亦有赖慎伯(包世臣)继之倡之,当不负云霓之望!
此时包世臣年仅三十岁,邓石如将继承倡导『碑学』这样的历史重任交到了包世臣的手上,包世臣也不负众望。在其书论中,屡见关于碑派笔法的讨论,其中不乏源自邓石如的笔法观念。清人王潜刚在《清人书评》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
每观安吴书,便忆道州语。终身学北碑,平直无些许。《艺舟》尊怀宁,同时少所与。自谓宗『二王』,意若轻虞褚。实则学真山,更兼武氏女。良工不示人,安身立命处。乃我发其藏,玄秘可列举。可怜学包人,于包求机杼。
这首诗是耐人寻味的。『《艺舟》尊怀宁』说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遵从的是邓石如,而『可怜学包人,于包求机杼』是说当时人们跟随包世臣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邓石如的笔法。此后,邓石如受到后世许多书家的追捧,直到现代。『管随指转』的运笔法,对柳诒徵、马叙伦、王蘧常、林散之等书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不得不说是包世臣所做的贡献。
万毫齐力与『大』
碑学审美中的『大』,可以解释为『博大』『雄浑』,线条的『浑厚』『雄浑』是实现这一审美的重要形式。那么如何使用羊毫毛笔将一根线条写得『浑厚』『雄浑』呢?包世臣的『逆入平出、万毫齐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他尝云:
盖笔向左拖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取逆,而毫不得不平铺于纸上矣……锋即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是以指得势而锋得力。至于下笔,须藏锋,使笔向左迤后稍偃,笔尖着纸即逆,笔毫平铺,四面圆足。[10]
包世臣此段话主要讨论的是起笔与行笔过程中的具体要求。这种笔毫平铺中锋用笔,写出来的线条浑厚中实、四面圆足,即所谓『大』。包世臣不止一次提出『万毫齐力』的主张,他在《述书上》中云:
又晤吴江吴育、山子。其言曰:吾子书专用笔尖直下,以迭裹锋,不假力于副毫,自以为藏锋内转,只形薄怯。凡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少温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也。
包世臣认为,书写时必须时刻保持中锋用笔,才能达到其所主张的『四面圆足』。包世臣在《述书上》中说:
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王河之谤,唐文饿隶之讥,既属梦呓,而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锐精仿习,一年之后,画有中线矣。每以熟纸作书,则其墨皆由两边渐燥至中,一线细如丝发,墨光精英异常,纸背状如针画,自谓于书道颇尽其秘。
包世臣从对古人的临仿、学习中,体悟到中锋用笔所写的点画不同寻常,此即南宋陈槱《负暄野录·篆法总论》中所谓李阳冰小篆,点画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13]这种点画从视觉上看,中间颜色深,向外渐渐变浅,給人以中线向外突出的立体感,整根线条看上去像一个圆柱体,而不是平铺在纸上的一根线条,这即是碑派『大』的具体形象的展现。除了运笔时对笔锋的要求外,包世臣还提出了运笔时的注意事项: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长史之观于担夫争道,东坡之喻上水撑船,皆悟到此间也。
在这段话中,包世臣提到了『峻』和『涩』,这对审美关系的提出,与前面所言『万毫齐力』同属一个概念,只有『万毫齐力』笔杆倾斜,顶锋行笔,才能增强笔和纸的摩擦力,写出的线条自然『雄浑』。
何绍基对此也有同样的追求,他在《书邓完伯先生印册后为守之作》中云:
后见石如先生篆分及刻印,惊为先得我心,恨不及与先生相见。而先生书中古劲横逸、前无古人之意,则自谓知之最真……北碑方整厚实,惟先生之用笔斗起直落,舍易趋难,能得其神髓,篆意草法时到两京境地矣。
从中不难看出何绍基对邓石如笔法的渴求,其所云『使尽气力不离故处』与包世臣所说『担夫争道』『上水撑船』如出一辙,可见何绍基学习邓石如是受了包世臣的影响。何绍基对邓石如的笔法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改造,有了自己追求『大』的表达方式。他在《与汪菊士论诗》中云:
气何以圆?用笔如铸元精,耿耿贯当中,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万折可也,一戛即止亦可也,气贯其中则圆,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
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何绍基所说的『圆』与包世臣的『四面圆足』是同一个概念,即碑学审美中的『大』,追求笔画中的厚实和雄浑。除何绍基之外,伊秉绶也是这一审美实践的代表人物,其笔画雄浑静穆,备尽圆足。
康有为在总结清代学者阮元、包世臣论碑的基础上,写成《广艺舟双楫》一书,对碑学实践从理论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总结,成为当时最系统、最成熟、最丰富的碑学著作。[17]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凡诸篆虽工拙不同,皆具茂密伟丽之观,诚《琅琊》之嫡嗣。且体裁近古,亦有《石鼓》之意,必毫铺纸上,万毫齐力,而后能为。』[18]由此可知,康有为『铺毫纸上』『万毫齐力』的用笔,是在包世臣理论基础上的延伸,他的『雄浑』『古厚』是对碑学审美中『大』的进一步追求。『他「尊碑抑帖」「尊魏卑唐」,而且在众多的魏碑中他尤喜「野逸」与「天然」一路。他以自己「不践古人」的书法实践,成为近代书法史上最具个性的书法家。』『在他眼中「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这也是他在《广艺舟双楫》中不断重复表述的对于「魏碑」的推举和褒扬』。[19]作为晚清倡导碑学的风云人物,康有为的碑学审美追求有着引领作用。除何绍基、康有为之外,受包世臣这一用笔影响的亦不乏其人,如吴熙载、张裕钊、赵之谦、沈曾植等。
战掣顿挫与『重』
碑学审美中的『重』,可以解释为『方重』『庄重』『厚重』,这一审美效果与碑版书法的残破有密切关系。碑版书法历经千年沧桑,表面的『残破』『剥蚀』给人以『庄重』之感。这种线条中的残破,想要用羊毫毛笔表达出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战掣』笔法,通俗来讲就是『顿挫』『战笔』等。陶明君在《中国书论辞典》有对『战笔』的解释:『用笔法之一,指行笔带有抖擞颤动走势,在颤动中如遇阻力,迎难而进,以取线条遒劲刚峻的效果。亦「颤笔」「战掣」。』[20]可以说,『战掣』的用笔方法是对自然『残破』『剥蚀』这一特征的摹拟而产生的。康有为在书论中亦曾描述『战掣』的用笔方法:
欲提笔则毫起,欲顿笔则毫铺,顿挫则生姿。行笔战掣,血肉满足,运行如风,雄强逸荡,安有抛筋露骨枯弱之病。
康有为对『战掣』用笔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种用笔方式能够很好表现『重』的审美特征。刘熙载亦曾就『战掣』笔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古人论用笔,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以迟速为疾涩而能疾涩者,无之!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涩与战掣同一机窍,第战掣有形,强效转至成病,不若涩之隐以神运耳。
刘熙载在这里提出了『战掣』与『迟涩』是相同的,这一观点正如前文所述,『迟涩』是能表现『古拙』的重要的用笔方式。『战掣』也具有同样的功用,只是表现出的线条不一样而已。『迟涩』的用笔表现出线条的金石意味较为隐蔽,而『战掣』表现出线条的金石意味则更为外露和夸张。包世臣亦云:
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锋暗转,不肯撅笔使墨旁出,是留处皆行也。
包世臣这里所说的『步步顿挫』就是『战掣』之法。通过此法可写就苍劲有力的点画线条,以达到碑派书家对『重』的追求。赵之谦更是相信包世臣的话,半生寝馈于魏齐碑版,使尽气力,用柔毫去模拟刀刻的石文,转锋抹角,总算淋漓尽致。
何绍基亦为『战掣』用笔的代表书家。他擅用浓墨生宣,长锋羊毫,加上他独创的回腕之法,战掣顿挫,浓墨涩行,以求其『重』。刘恒认为,何绍基『回腕高悬』的执笔方法是违反人体自然习惯的,用这种姿势写字,整个手臂一直处在运动与僵硬的互相对抗之中。这种自身形成的对抗消解了手臂在运动中的大部分力量,使其难以舒展自如,因而写出的笔画造成『生拙迟涩』的效果,而这种效果正是何绍基所期待和努力要达到的。[25]王潜刚在评何绍基书法时说:『蝯叟书因悬臂用力,有笔笔战动者,究竟是病。学之者不能得其书之渊源,但有意学其战动,不得其长,专师其短,可怪也。』这里所说的『笔笔战动』,就是指何绍基以回腕『战掣』用笔方法摹拟碑刻中的剥蚀。虽然王潜刚批评何绍基这是病态的写法,导致后来学习者得不到其学书的渊源,且只能学习其『战掣』之法并流于弊病,但这并不能否认何绍基在这一笔法运用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