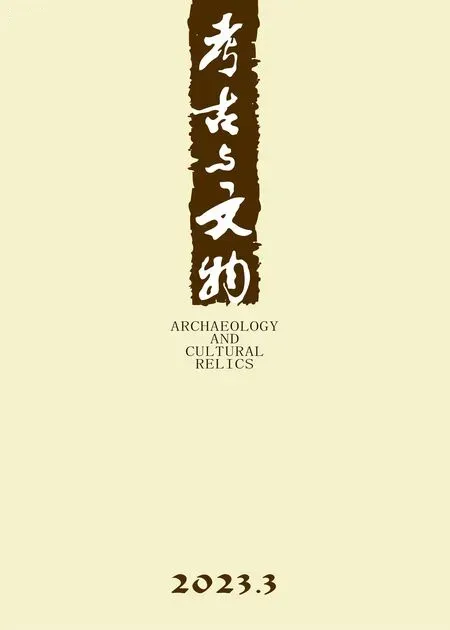农业起源与社会转型的三种模式
——以中国北方、西亚与墨西哥高原的比较为视角*
2023-07-19吴锦程
赵 潮 吴锦程
(1.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陕西历史博物馆)
考古证据表明,农业起源与扩散,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革命”,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通过跨区域比较不同地带农业起源模式,探讨相关经济、社会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推动农业经济的出现与发展,有助于我们在世界史前史的宏观框架下更清晰地认识我国史前农业起源的特征。
本文拟考察定居生活方式的建立与农业生计发展过程之间的关联,探讨西亚、墨西哥高原、中国北方农业起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定居生活的出现与发展,常伴随着社会组织模式的重大变迁,可作为观察社会转型的重要视角[1]。驯化动、植物资源出现的时间节点及其在整体生业资源中所占比重,则有助我们判断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发展过渡阶段。西亚、墨西哥高原与我国北方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3处农业起源中心,也是考古工作开展较为充分的地区,为我们复原史前栖居模式与定居生活发展过程提供了基础。
一、西亚地区
(一)西亚的农业经济建立过程
西亚是小麦、大麦、亚麻、多种豆科植物与绵羊、山羊、黄牛、家猪的驯化中心。研究表明不同物种得到驯化的时间有所差异,从对驯化物种野生祖本的强化利用,到对少数驯化种的小规模栽培,再到混合利用多种动植物驯化物种的成熟农业经济出现,持续了数千年时间,大体经历了后旧石器时代和前陶新石器时代[2]。
早在距今18000~12000年的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 Age),地中海东岸黎凡特地区的史前居民就对野生禾本科植物(包括驯化种的野生祖本)有了强化采集与利用,然而具有驯化性状特征的物种尚未发现[3]。在前陶新石器A阶段(PPNA,距今11700~10500年),具有驯化特征的二粒小麦、大麦等作物遗存被陆续发现,但野生植物遗存仍在遗址中占有较大比重,动物资源的获取仍然依靠狩猎瞪羚等野生动物[4],说明该时期农业生产规模有限,仅作为生业经济的补充而存在。至前陶新石器B阶段(PPNB)中期(距今10000~9300年),面包小麦、亚麻等更多种类的驯化作物被发现,野生植物资源占比明显降低,具有驯化特征的山羊、绵羊、黄牛等家畜开始出现,成为人们的主要肉食来源,成体系化的农业经济在西亚宜农地带得到普遍确立[5]。
(二)西亚地区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过程
西亚定居生活的出现早于成体系化的农业经济确立之时。最早定居迹象可追寻至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纳吐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在该文化一些面积较大的聚落中,发现有较固定的房屋建筑、墓葬以及与人类长期居住相伴随的动物遗存,暗示着人们对这些聚落有较为长期的居住与利用[6]。然而,这些定居化的聚落,仅分布在黎凡特地区资源富集的地中海栎林与草原交汇处[7]。在资源较为稀疏的草原地带,遗址面积更小,文化堆积更薄,居址建筑少见,体现出更为短暂的栖居方式[8]。而到PPNA与PPNB阶段,定居村落遗址数量增多,分布范围也日益广阔[9]。
图一反映了从纳吐夫文化到PPNB阶段聚落布局以及房屋建筑的演变过程。左侧为不同阶段典型遗址的平面图,可见纳吐夫文化和PPNA阶段的聚落由聚群分布的圆形房址组成,而PPNB阶段的聚落由密集的方形房址组成。发掘与调查数据显示:随时间的推移聚落规模越来越大,反映出社群人口规模的扩大。纳吐夫时期大型聚落面积往往在2000~3000平方米,聚集的人口规模据推测可达200~300人[12];而PPNA阶段,小型聚落的规模都在2000~3000平方米,大型聚落的规模则在2~3公顷左右,个别遗址可达8公顷[13];PPNB阶段,大型聚落更为普遍,部分聚落的面积超出10公顷,人口规模可达2000~4000人[14]。随时间发展,聚落内房址的分布密度也越来越高,至PPNB时期,聚落中房屋紧密相接,甚至连街巷的空间也已无存,人们通过屋顶相互交通[15],体现出人群居住密度的空前提高。

图一 农业起源之际西亚地区的聚落发展演变
图一右侧则是不同阶段居址建筑的复原图。纳吐夫文化的房屋多为半地穴的圆形或椭圆形棚屋,底部由石块奠基,上部结构则由树枝、芦苇、草席或是石块搭成,并由木柱支撑,未发现明显的墙体结构。PPNA阶段,泥砖被广泛用于墙体的构建,建筑变得更为坚固耐用。PPNB阶段,房屋从圆形变为方形。单体建筑发展成具有多重套间的建筑单元。房屋地表用小卵石和泥铺成,并在上面涂抹红泥,显示出对居住面更为精细的处理[16]。这一发展演变,体现出人群为长久居住而在建造房屋方面投入了愈来愈多的精力。
房屋使用与废弃过程研究显示随着时间推移,西亚地区的定居化程度不断提高。纳吐夫文化保存完好的房址中,往往出土数以万计的遗物,包括大量生活垃圾和成套堆放的生活用具。房址之外,则缺乏集中堆积废弃物品的地点。与之相比,PPNA房址居住面上的遗物往往较为稀少,而大部分遗物都集中出土于房址附近的灰坑或地层中[17],说明人们对房屋定期清扫的行为已经存在,暗示定居化程度的增高。PPNB阶段,房址居住面上更加干净,显示出人们对起居面更为精细的清理与维护[18]。恰塔尔胡由克遗址(Çatalhöyük)的发掘显示部分房屋的墙面甚至被重复粉刷了700次之多。人们在原先废弃的房屋上不断重建新居,以至不同时期的房屋层层相叠,在前后发掘过程中可识别出多达18个居住层,显示出上千年之久的连续居住[19],展现了非常稳定的定居形态。
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往往伴随着重大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至PPNA时代,除常规居址建筑外,还出现了粮仓、公共建筑、祭祀型建筑[20]。这些物质遗存的背后,映射着人们发展出更为复杂的文化调节机制,以应对社会—经济层面的重大变迁,例如通过储备盈余的手段为定居生活提供经济保障,利用公众性的仪式与宗教活动加强社群凝聚力[21]。
以上信息表明,西亚地区定居化生活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比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要快一个节奏。在强化利用野生物种的阶段,人们就在局部地区建立了半定居化的生活模式。而随着部分物种的驯化以及小规模耕种活动的普及,在农业尚未成为主导型经济来源之时,更为稳固的定居方式便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得以建立,社群规模也随之扩大。而伴随着成熟农业体系的确立,大规模的社群聚合与超稳固的定居模式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
二、墨西哥高原
(一)墨西哥高原的农业经济建立过程
墨西哥高原是玉米、菜豆、南瓜、甘薯、辣椒等农作物的驯化中心,以玉米、豆类、南瓜为主的混种农业,能够有效结合不同作物的长处,提高产量,并为人们提供全面的营养来源[22]。
考古研究表明,虽然玉米、大豆、南瓜在距今10000~3500年前的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就已被驯化,但将三者混种并作为主食来源的生计实践,则迟至距今3500年之后的形成期(Formative period)才得以确立[23]。最新研究表明南瓜最早在10000年左右即被驯化[24],玉米在距今9000~8000年之间得到驯化[25]。具有驯化特征的豆类在距今5000年之后的遗存中才有较为普遍的发现[26]。在漫长的古风时期,虽然驯化物种逐渐增多,但在整个可食植物遗存中所占比例很低,说明驯化物种的栽培与利用,起初仅被人们当作生计资源的补充,嵌套在已有的狩猎采集模式之中[27]。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在墨西哥高原经历了超过6000年之久的漫长过程。
(二)墨西哥高原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过程
考古证据表明,墨西哥高原先民在古风时代仍然过着随时节而迁移的流动性生活。该时期遗址可分为小型洞穴、大型洞穴、露天遗址。位于瓦哈卡谷地的圭拉那魁兹(Gulia Naquitz)遗址是小型洞穴类遗址的代表,使用年代为距今10500~8600年。下文化层发现有驯化形态的西葫芦,上文化层发现有驯化形态的玉米,但这些驯化种在总体炭化植物遗存中占比微小。植物遗存以夏末和秋季成熟的橡子、牧豆、豆荚、朴树籽、龙舌兰等为主,尤以橡子最多,不见晚春至初夏成熟的物种,由此推断遗址使用时间为每年的夏末秋初至来年早春[28]。该洞穴总面积仅有65平方米,表明居住在此的社群规模很小,可能仅是一个4~6人规模的家庭营地。遗物以打制石器为主,有少量研磨石器和绳索、篮子等有机质遗存。人工制品与动植物资源散布于各个层位,可区分出食物处理、工具制作、垃圾丢弃等区域(图二,1),但不见对居住面进行刻意修整、维护、清理打扫的迹象[29],显示当时人群在洞穴中的生活与工作有一定规律性,但尚未形成稳定化的居住方式。类似圭拉那魁兹的遗址在瓦哈卡谷地还有分布,根据遗址分布地点、出土遗存组合等信息分析,它们之间的功能与使用季节有所不同[30]。

图二 墨西哥高原古风期的小型洞穴遗址与形成期的聚落房址平面图
除小型洞穴遗址外,瓦哈卡谷地还发现了与圭拉那魁兹同期的露天遗址盖—欧希(Gheo-Shih)。该遗址坐落于河谷之中,推测是人群夏季栖居的地点,因为河谷地带密布的牧豆树在夏季成熟,可为人们带来充足的食物资源。盖—欧希面积为1.5公顷,大于小型洞穴遗址,体现出更大规模的人口集聚[31]。盖—欧希最显著的一处遗迹为由两排砾石围合的一处场地,场地内遗物少,场地外遗物分布密集,推测可能是一处举办公共仪式的场地[32]。遗址内没有发现明确的房址迹象,表明人群尚未在此形成稳定的居住方式。
瓦哈卡谷地和特瓦坎谷地的考古发现均揭示出古风时期不同性质的栖居遗址[33],显示人们在不同季节以不同的社会组织规模,从事不同的生计与社会活动。在食物资源分散的季节,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在谷地外缘的山区进行觅食活动,并在栖居地周围进行小规模的栽培,而在食物资源集中的季节,则在河谷平原聚合成更大规模的社群[34]。
墨西哥高原定居式村落生活的广泛建立,出现于古风期之后的形成期。瓦哈卡谷地的圣何塞莫戈特(San Jose Mogote)和蒂埃拉斯—拉勒嘎斯(Tierras Largas)两处遗址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揭示出早期定居的发展情况。两处遗址起初均为有10余座房屋所组成的小型村落,之后,圣何塞莫戈特的聚落规模逐渐扩大,在形成期中段(距今3000~2600年)发展成面积达20公顷、人口规模达2000人以上的大型聚落,并出现了建于高台之上的公共建筑。而蒂埃拉斯—拉勒嘎斯则一直保持较小的聚落规模[35]。两处遗址均发现有成群分布的长方形房屋(图二,2),多数房屋面积为10~30余平方米,墙体为木骨泥墙,部分建筑墙体外侧还刷有白灰,居住面经过硬化处理。房屋外侧通常会有2~6处钟形灰坑,营建之初多用作窖穴,之后被用来填埋生活垃圾[36]。这些特征反映该时期人群,建造了更加坚固耐用的房屋,并会储备充足物资,供长久稳定的栖居所用。类似的房址和大、小聚落并存的现象,在同期的特瓦坎和墨西哥河谷亦有发现。
综上所述,稳固的定居生活方式直至成熟的农业经济体系确立之时,才在墨西哥高原地区得以形成,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层面的重大转型。
三、中国北方
(一)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建立过程
中国北方是粟、黍、黄豆、家猪等动植物的驯化起源中心。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早在距今2万年左右,柿子滩遗址S14地点出土的碾磨工具上就发现有黍族草籽,暗示着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利用野生的黍族植物[39]。具有明确驯化特征的粟、黍炭化颗粒,最早发现于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东胡林遗址中。其形态特征与野生祖本明显有别,但颗粒仍明显小于现今的粟、黍,体现出介于野生与完全驯化之间的过渡状态[40]。
至距今9000~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具有驯化特征的粟、黍遗存在磁山、裴李岗、沙窝李、张马屯、西河、月庄、兴隆沟、大地湾等多处遗址均有发现[41]。贾湖、磁山等遗址出土的猪骨骸体现明确的驯化特征,暗示着家畜驯化的开端[42]。然而,多处遗址浮选结果表明,粟、黍在整体植物遗存组合中所占比例有限[43]。同位素分析也表示驯化植物在当时人群食谱中所占比例较低[44]。多处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也以鹿、野猪等野生动物为主[45]。这些发现表明,驯化的动植物在当时北方先民的整体生业经济中尚处于辅助地位。
至距今7000~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生产取代狩猎采集,成为北方先民生业经济的主导。多个区域性的植物考古浮选工作均揭示出粟、黍遗存的数量与比例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明显跃升的现象[46]。野生动物种类数量下降,家猪骨骼遗存的占比上升[47]。西安鱼化寨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显示,在仰韶文化早段的半坡与史家期,粟、黍的总数已经占据了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1%,而在仰韶文化晚期已多达4万1千余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9%,处于绝对主导地位[48]。家猪骨骼遗存的数量与比例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多,据动物骨骼以及载肉率的估算,至仰韶文化晚期,鱼化寨遗址家猪在人类肉食资源中的贡献率已经超出了60%[49]。
(二)中国北方定居化生活模式的建立过程
从强化利用野生黍族资源到驯化萌芽的出现,中国北方先民依然过着流动性的采食生活,遗址规模小,结构简单,未发生明显的聚落形态变化。而粟、黍驯化种出现阶段正值新石器时代早期,仅有的几处遗址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从流动迁徙向定居生活转变的趋向,例如李家沟遗址发现由石块围合而成的椭圆形圆圈,南庄头遗址发现较大的朽木、带人工凿割孔眼或凹槽的木柄、板块[50],这些遗存或许与搭建简易建筑的行为有关。东胡林与扁扁洞遗址还发现有人工刻意平整的居住面[51]。然而该阶段遗址中并未发现明确的房屋遗迹。因此定居化生活的证据尚不确凿。
定居生活的明确迹象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由半地穴房屋聚合而成的聚落遗址,不仅出现于华北腹地,还分布到了蒙古高原南部地带[52]。这些遗址的规模,明显大于北方地区更早阶段的遗址,其中多数遗址面积接近1公顷或在1~2公顷左右,类似现今的小型村庄。个别遗址的面积较大,超过5公顷[53],体现出更大规模的人口集聚。村落遗址形态多样,既有方形房屋成排分布式的布局,也有小型房屋三五成群聚堆分布式的格局(图三)[54]。一些聚落布局严整,体现出明确的规划思想和对社会秩序的强调(图三,1),另一些聚落的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复杂,体现出先民长时间的占据和对聚落的不断改建(图三,2)。

图三 新石器时代中期北方地区西辽河与黄河流域聚落形态比较
针对遗址使用—废弃过程的研究显示,分布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聚落,其定居化程度亦有明显区别。阴山北麓的裕民、四麻沟遗址,房屋内堆积有很厚的文化层,出土有大量石制品废片、工具和动物骨骼,而房屋之外未见灰坑等集中堆砌废弃物品的设施[57],表明居住者尚未形成定期打扫居住面、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定居化生活习惯,定居程度有限。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磁山、北福地等遗址则发现有在房址居住面或聚落地表上有意摆放成组器物的行为,这些物品多数可继续使用。因此推测人们可能只是暂时离开遗址,还考虑预期返回,对聚落的利用方式更像断续而反复的利用,而非长久的持续占据[58]。另有少数遗址,如舞阳贾湖,室内堆积较少,但不少房屋室内出现多个居住面相叠的情况,表明人们在原址上反复改建房屋,体现出更稳定的居住方式[59]。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多分布于山地与平川相接之处,或是靠近沼泽湿地的地带,这些地区往往具有较为丰富且多样的食物资源。在资源较为单一的高原与平原腹地,则极少见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的分布[60]。
而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先民的定居生活模式更为稳固。该时期遗址数量激增,分布范围变得更为广阔。先前鲜有村落遗址发现的黄土高原核心区域与西、北边缘,均发现了密集分布的村落遗址[61]。该阶段遗址的房屋居住面往往较为清洁,遗物稀少,体现出人群对居住址的打扫与维护行为。房屋居住面普遍经过硬化处理,甚至部分居住面的处理工序十分考究。这些行为习惯,与更为长久稳定的栖居方式紧密相关[62]。大量地处中原的聚落居址,有从早到晚各个文化期段的遗存,遗址堆积厚,叠压打破关系复杂,体现出在同一地点连续稳定居住的行为。此外,这一时期的遗址规模更大,布局更为复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甚至出现了超大规模的高等级聚落,体现出更大规模的人群聚合与初步的社会分化[63]。
综上,我国北方地带流动向定居生活的转变出现在动植物资源驯化的初期阶段。该时期驯化资源尚未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依然是人群所依靠的主要生计方式。伴随着农业生产取代狩猎采集经济成为主导性生业方式,人群的定居能力得到增强,定居化的生活模式也扩散到了更为广泛的地区,促进了人口数量的激增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繁荣。
四、讨论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可以把西亚、中国北方、墨西哥高原栖居模式与生业经济发展、转变的过程与对应关系置于同一个时间轴之上以便比较。如图四所示,西亚地区定居生活的开端与社群规模的扩大先于动植物资源的驯化。在墨西哥高原,定居生活与村落社会形成于较成熟的农业经济确立之后。在中国北方,定居村落出现在粟、黍资源初步驯化之后、成熟农业建立之前。

图四 农业起源之际西亚、中国北方、墨西哥高原三个地区生业经济与栖居方式变迁的发展轨迹
跨区域的对比研究显示农业与定居各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却又存在密切交织的关联。首先定居生活出现的前提并不绝对依赖农业,只要人群能够对局域范围内的资源进行集约化利用,保障充足食物供应,即可实现定居。因此,在野生食用资源分布最为集中的西亚地区,定居生活出现的节点更早。然而作为资源集约利用的一项重要策略,农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也会对定居生活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农业生产可在有限空间内为人们提供更多食物来源,弥补野生食物资源因分布稀疏或过渡开采而导致的不足。因此虽然定居生活出现的时间节点不同,但伴随农业经济的发展,西亚,中国北方、墨西哥高原的定居化程度都逐渐加强,定居社群的规模不断扩大,定居化的生活方式也从局部地带扩散到了更为广阔的地区。
而定居生活的发展,也会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推动力。虽然中国华北与墨西哥高原的案例表明作物驯化可在流动性的生活状态下进行,不必然以定居生活为前提,但定居生活似乎加速了农业发展的进程。本文所述的三个地区,早期的驯化迹象均发现于距今1万年左右,但在定居生活发展更早的西亚地区,从萌芽向成熟农业体系的转变历时更短,而在较晚出现定居的墨西哥高原,农业取代狩猎采集经济的过程也更为漫长。定居生活可为人们提供稳定的栖居环境,更好地照料栽培作物的生长,同时又限定了人群活动范围,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使得社会群体更为迫切地需要去提高局域范围内的食物产量。当人们无法通过强化采获野生食物资源以满足食物需求量时,发展与扩大农业生产便成了首选之计。此外,定居生活引起了社会组织方式的重大转变,人们需要通过宴飨、仪式、经济再分配等手段强化社会互动,从而导致对剩余食物资源生产的更大需求[64]。
鉴于定居与农业生产的密切联系,西亚、中国北方、墨西哥高原早期农业与定居生活发展之间的不同对应关系,也暗示着三个地区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有所不同。西亚地区定居出现最早,由定居引发的人群土地利用方式与社会组织转变为之后农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社会动因。而墨西哥高原在农业经济的初始发展过程中,并未经历显著的栖居方式转变与社会转型,定居生活的出现,更像是农业经济发展成熟后产生的结果。在中国北方,定居生活的确立受到初期农业发展的影响,并为之后向更为成熟的农业经济转变提供了推力,说明中国北方从狩猎采集经济向成熟农业经济的转变先后受到不同动力机制的影响。这一发现,提醒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打破旧、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藩篱,在长时段的视角下探寻我国农业起源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层面的重大变迁,为深入理解文明起源之根基提供基础。
[1]Kelly R L.Mobility/Sedentism:Concepts, Archaeological Measures,and Effects[J].Annual Revie wof Anthropology.1992,21:43-66.
[2]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3]彭鹏.试论近东地区的农业起源—以植物的栽培和驯化为中心[J].四川文物,2012(3):37-47.
[3]Goring-Morris K N.Foraging,Farming,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of the Southern Levant:A Review and Synthesis[J].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2002,16(4):361-440.
[5]同[4].
[6]Bar-Yosef O,Belfer-Cohen A.The Origins of Sedentism and Farming Communities in the Levant[J].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1989,3(4):447-498.
[7]Bar-Yosef O.The Natufian culture in the Levant,Threshold to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J].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Issues News and Reviews,1998,6(5):159-177.
[8]同[2].
[9]Asouti E.Beyond 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B Interaction Sphere[J].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2006,20(2/4):87-126.
[10]Goring-Morris A N,Belfer-Cohen A.The Southern Levant(Cisjordan)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C]//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Haklay G,Gopher A.A new look at shelter 131/51 in the Natufian site of Eynan (Ain-Mallaha),Israel[J].Plos one,2015,10(7).
[12]同[6].
[13]Moore A M T,Hillman G C,Legge A J.Village on the Euphrates:From Foraging to Farming at Abu Hureyra[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4]Kuijt I.People and Space in Early Agricultural Villages:Exploring Daily Lives,Community Size,and Architecture in the Late Pre-Pottery Neolithic[J].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00,19(1):75-102.
[15]Bar-Yosef O,赵志军,翟少冬.近东地区农业的起源[J].南方文物,2014(3).
[16]Bar-Yosef O,王佳音.农民与采集者的相互关系:来自西亚的认识[C]//考古学研究(九).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44-259.
[17]Hardy-Smith T,Edwards P C.The Garbage Crisis in Prehistory:Artefact Discard Patterns at the Early Natufian site of Wadi Hammeh 27 and the Origins of Household Refuse Disposal Strategies[J].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04,23(3):253-289.
[18]同[17].
[19]Hodder I.Inhabiting Çatalhöyük:Reports from the 1995–1999 Seasons[M].Ankara:British Institute at Ankara,2005.
[20]Love S.Architecture as Material Culture:Building form and Materiality in the Pre-Pottery Neolithic of Anatolia and Levant[J].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2013,32(4):746-758.
[21]同[15].
[22]Flannery K V.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73(2):271-310.
[23]Landon A J.The "How" of the Three Sister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Mesoamerica and the Human Niche[J].Nebraska Anthropologist,2008(40):110-124.
[24]Smith B D.The Initial Domestication of Curubita P e p o i n t h e A m e r i c a s 1 0,0 0 0 Ye a r s A g o[J].Science,1997,276(5314):932-934.
[25]Piperno D R,Ranere A J,Holst I,et al.Starch Grain and Phytolith Evidence for Early Ninth Millennium B.P.Maize from the Central Balsas River Valley,Mexico[J].PNAS,2009,106(13):5019-5024.
[26]同[23].
[27]Rosenswig R M.A Mosaic of Adaptation: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for Mesoamerica's Archaic Period[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15,23(2):115-162.
[28]Flannery K V.Guila Naquitz: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Updated Edition[M].Abingdon:Routledge,2009.
[29]同[28].
[30]同[28].
[31]Evens S T.Ancient Mexico & Central America[M].London:Thames & Hudson,2008.
[32]Marcus J,Flannery K V.The Coevolution of Ritual and Society:New 14C Dates from Ancient Mexico[J].PNAS,2005(52):18257-18261.
[33]MacNeish R S,Fowler M,Cook A,et al.The prehistory of the Tehuacan valley,Volume 5:Excavations and Reconnaissance.Austin &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2.
[34]Flannery K V.Arche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Early Mesoamerica[C]//Anthropological Archeology in the Americas.Washington D.C: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1968:67-87.
[35]同[31].
[36]Flannery K V.The Early Mesoamerican House[C]//The Early Mesoamerican Village:Updated Edition.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09:16-24.
[37]肯特·弗兰纳利主编,陈淳,陈虹,董唯妙,等译.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38]Flannery K V.The Early Mesoamerican Village[M].Abingdon:Routledge,1976.
[39]刘莉,Bestel S,石金鸣等.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次盛冰期人类对植物性食物的利用[J].南方文物,2017(4):247-254.
[40]赵志军,赵朝洪,郁金城,等.北京东胡林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J].考古,2020(7):102-109.
[41]赵志军.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证据[J].第四纪研究,2014,34(1):73-84.
[42]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43]吴文婉.中国北方地区裴李岗时代生业经济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
[44]Hu Y,Wang S,Luan F,et al.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Humans from Xiaojingshan Site: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Millet Agriculture in China [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08,35(11):2960-2965.
[4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J].考古学报,1999(1):1-22.
[46]a.Lee G-A,Crawford G W,Liu L,Chen X.Plants and People from the Early Neolithic to Shang Periods in North China[J].PNAS,2007,104(3):1087-1092.b.Jia X,Li H,Lee H,et al.Agricultural Adaptations to Topography and Climate Changes in Central China during the Mid-to Late- Holocene[J].The Holocene,2021,31(11-12):1705-1715.
[47]同[45].
[48]赵志军.仰韶文化时期农耕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会的建立—鱼化寨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J].江汉考古,2017(6):98-108.
[4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鱼化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50]a.王幼平,张松林,何嘉宁,等.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1(4):3-9.b.李珺,乔倩,任雪岩.1997 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0(3):361-392.
[51]a.赵朝洪.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J].考古,2006(7):3-8.b.孙波,崔圣宽.试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J].中原文物,2008(3):23-28.
[52]叶灿阳,陈胜前,赵潮.跳出固有模式—草原地带新石器文化新发现的思考[N].中国文物报,2022-1-7(6).
[53]陈明辉.裴李岗时期的文化与社会[D].上海:复旦大学,2013.
[54]同[53].
[55]胡保华.内蒙古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房址居住面上遗存分析[J].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2):47-55.
[56]信应君,胡亚毅,张永清,等.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2007 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0(5):3-23.
[57]a.胡晓农,包青川,李恩瑞,陈文虎.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21(1):26-49.b.包青川,陈文虎,胡晓农,等.内蒙古化德县四麻沟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21(1):51-74.
[58]李彬森.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废弃过程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
[5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60]Chen S,Yu P-L.Early“Neolithic”of China:Variation and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2017,73(2):149-180.
[61]刘莉著,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62]罗晓艳.试论关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房址的特点[J].文物,2016(7).
[63]同[61].
[64]Bender B.Gatherer-Hunter to Farmer:A Social Perspective [J].World Archaeology,1978,10(2): 204-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