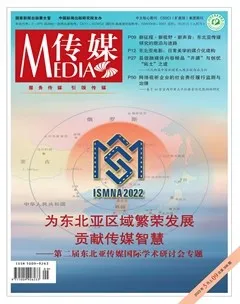国际舆论场中计算宣传隐患研究
2023-07-06党琼李时娴
党琼 李时娴
摘要:智能传播时代,人们由“网络社会”走向“平台社会”,社交平台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社交平台上计算宣传事件日益增多。本文追溯了宣传的历史脉络,从工具载体和内容呈现技巧两个维度探究了计算宣传的模式,进而揭示计算宣传中存在的隐患,即技术控制内容使得假新闻泛滥和群体极化突出的问题;权力规训技术时,计算宣传实质上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关键词:国际舆论场 计算宣传 规训 控制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曼纽尔·卡斯特注意到“相互连接的节点”具有建构新社会形态的潜力,因此提出了“网络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能力的发展,平台通过聚合海量用户和资源,逐渐融入社会运转系统。从物理层面到精神层面,社会建构开始依托于平台,社会转化成了何塞·范·迪克口中的“平台社会”,由此我们进入了人机共存的阶段。
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场中存在诸多力量相互影响。国际舆论场是各方宣传的重要阵地,宣传场会受到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等的影响。在算法和社交机器人等技术的加持下,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宣传模式之一。研究表明,计算宣传已成为新一轮“社交媒体新冷战”的主要手段,因此本研究首先从计算宣传的历史溯源出发,探究计算宣传模式,从而揭示国际舆论场中计算宣传存在的隐患,旨在为我国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借鉴。
一、历史溯源:从宣传到计算宣传
“宣传”的英文Propaganda源自拉丁文,表示农业生产中的播种、繁殖,而现代宣传则是“有目的地、系统地影响感知、操纵认知和引导行为的尝试”。宣传概念的转变与政治需求有关,现代意义上的宣传概念成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期间首次出现了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报纸和电影成为了宣传的主要媒介,宣传活动的目的是要在不被觉察的前提下,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支持某个政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以一战中的宣传为主题,撰写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
随着互联网技术演进,社交媒体替代传统的报纸和电影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宣传”升级为“计算宣传”。“计算宣传”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伍利(Samuel Woolley)和英国学者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在2016年提出,意指“依托于算法、社交机器人和人工策划展示等技术手段,以操纵舆论为目的,在社交平台上分发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的传播行为”。当前,计算宣传事件十分普遍,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赢得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还是经济领域的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都存在计算宣传的身影。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指出,截至2020年底,已经发现了有81个国家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计算宣传的证据,相比前一年增加了11个国家。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控制着信息和意见的可见程度,使得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言的“观点的自由市场”成为泡影。
二、计算宣传模式分析:工具载体与内容策略
计算宣传的模式不仅包括“怎么宣传”,也包括“宣传什么”,基于此本研究从工具载体和内容宣传两个层面分析计算宣传的模式。工具层面,计算宣传的载体为自动化的社交机器人账户,这些账户已对社交网络实现高度渗透;内容层面,计算宣传的策略沿用传统媒体时代的宣传方法,并且结合现代平台规则进行了改良。
1.工具载体:渗透社交网络的社交机器人。尽管宣传并非新鲜事物,但全球化的社交平台和智能技术提供的可供性,使得宣传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精细的程度上展开。目前,计算宣传普遍使用的工具是社交媒体账号,即自动化的社交機器人账户。
社交机器人是指基于自动化算法,以与人类进行交往为目的的机器人。实体化的社交机器人包括智能音箱、教育市场上的NAO机器人等,虚拟化的代表则是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号集群。国际舆论场中的计算宣传高度依赖社交机器人形成的账号集群,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Twitter上9%~15%的活跃账号就为社交机器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提出66%带有URL链接的推文疑似由机器人账号发布。
社交机器人账号集群的运作目的是在争议性议题中放大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点,进而营造意见气候,左右舆论风向。因此,社交机器人常常通过大批量发布文本,以及有选择性地在真人发布的内容下进行评论、点赞和转发等互动,提升这些文本的传播效果。当平台算法捕捉到这些“高热度”文本,就会赋予相关文本以更高权重,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师文和陈昌凤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运作逻辑,他们发现在Twitter上社交机器人反复转发《纽约时报》所发布的对中国负面的报道,在二级传播中占比达到17.04%。
社交机器人也会通过建立新的社交网络和渗透原有的社交网络,从而改变信息流动的结构,提升计算宣传的效果。这种社交网络包括两种:社交机器人与社交机器人、社交机器人与人。研究发现,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社交机器人对于社交网络的渗透率达到80%,冲突性议题中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也都存在社交机器人。尽管在目前,社交机器人在社交网络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但他们可以通过与网络中有影响力的人进行互动,从而对网络中的信息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社交机器人在内容上的互动方式与真人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基本都是以点赞、评论和转发为主,但社交机器人的社交性互动(如关注)更多。
2.内容宣传:传统技巧与现代规则结合。阿尔弗雷德·李 和伊丽莎白·李 (Alfred Lee & Elizabeth Lee)总结的七种宣传技巧在当今依旧适用,在某种程度上,计算宣传的策略技巧是在传统媒体时代宣传方法基础上的升级。首先,在视觉时代,表情包等图片能够实现病毒式传播,模因与“辱骂法”结合可以以最快速度抢占舆论场。深度伪造的图片成为假新闻的佐证,恶搞漫画丑化对手形象等手段屡见不鲜。其次,数据驱动下,个性化算法精准描绘用户画像,一方面通过“洗牌作弊法”使用户选择性接触信息,从认知层面上进行塑造;另一方面,算法的议程设置营造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意见气候,促使“乐队花车”的宣传方法得以生效。虽然算法提供的内容“千人千面”,但计算宣传的目的殊途同归。
除此之外,目前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存在流量监控和举报体系,计算宣传会“反向”利用这些体系进行活动。流量监控是指平台日常会关注每个话题的热度数据,如果出现异常的数据变动,譬如是机器人大量重复转发某话题相关的文本,导致在某个时间点话题量骤然增加,平台就会在短期内降低该话题权重并开始人工监测。举报体系是指平台赋予每个用户举报的权利,用户可以通过举报不合规内容来维护平台的内容生态。计算宣传就是通过这两个算法规则,将相对立场的话题和账号文本进行大量机械转发,使用真人账户进行海量投诉,从而引入平台的人工判断,这一行为可能会降低相关内容的曝光率,甚至会导致某些账号被封号处理。
三、计算宣传背后的隐患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从微观层次出发,关注权力的运作过程。他强调通过日常规范的检查、训练等行使的“规训性权力”尽管十分微小,与暴力、国家的法律制度等宏观权力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却更为有效和迅速。计算宣传亦是一种规训性权力:微观上,算法在不为大众所知的平台背后,默默控制内容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宏观上,算法其实是政治权力操纵舆论、影响民意的武器。前者会加剧假新闻的泛滥,并催化用户群体极化问题,后者则从根源上威胁公共舆论的自由和平等,挑战民主治理。
1.技术控制内容: 国际假新闻泛滥和用户群体极化。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争夺的场所和实施的媒介。话语是空间规训的方法,是一套陈述体系,旨在建立“排除的规则”,譬如何为正常何为反常。在计算宣传中,平台通过“热门搜索”等机制中的话语,定义“何为当前的流行话题”,通过删帖和官方公告,定义“何为假新闻”。
技术从传统媒体手中抢夺把关权,会导致诸多问题,而最直接的表现是国际假新闻泛滥。目前,计算宣传的算法基础尚未成熟,对新闻消息的真假判断水平仍处于初期阶段,再加上媒体平台自动化的分发扩大了传播面积、提高了传播效率,这使得国际舆论场上假新闻泛滥问题日益严重。2017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在警方尚未公布凶手信息时,Google的新闻板块就因为算法推荐而刊登出一条凶手指认信息,并称之为反特朗普者, 将枪击案与政治联系起来。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流行期间,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对疫情中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相当大比例的文本在攻击中国和亚裔族群,传播病毒起源的阴谋论和疾病的污名化。
应用于计算宣传的社交机器人更倾向于传播感性、极端而非理性中立的内容,通过在社交网络中的海量转发,建立回音室屏蔽对立的观点,引发沉默的螺旋效应,使得公众观点更加对立,难以进行理性对话,最终社交机器人的意见成为主流。我国学者对于Twitter上的中国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社交机器人基本都持反对中国的立场,高频发送的文本表达的也是反对态度。还有学者对社交机器人的舆论影响力进行研究,发现在议题讨论的过程中,哪怕只有5%~10%的参与者为社交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最终若能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参与者支持,其意见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2.权力规训技术:计算宣传成为政治斗争武器。社交媒体平台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是培育公民参与和实现民主的有力途径,但随着技术和权力的合谋,各种力量通过计算宣传使得这一目标成为幻想。
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和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曾提出“政治中介化”一词,用来描述 “中介化的政治传播已成为当今民主政治与公共生活的中心”的现象。社交媒体平台凭借着对用户资源和信息分发渠道的垄断地位,成为政治传播必须依赖的中介。观察美国的历史,罗斯福被称为“广播总统”、肯尼迪被称为“电视总统”,奥巴马被称为“互联网总统”、特朗普被称为“推特总统”,这些称号无一不在证明着信息传播技术对于政治的影响。但是,社交媒体平台与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逻辑不同,社交媒体的信息传递具有碎片化、注重视觉的特点。政治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时,必须顺应社交媒体的信息逻辑。即失去完整语境、只剩情感宣泄的文本开始泛滥,“后真相”成为日常。除此之外,凯文·德卢卡(Kevin DeLuca)认为,图像具有远超于语言和文字的社会动员力量和话语建构能力。因此,恶搞政治领导人和政治事件的表情包在Twitter、Facebook上病毒式传播。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出席活动时疑似晕倒,海外社交平台上就迅速出现了大量希拉里的表情包,政治泛娱乐化的趋势日益突出。
社交媒体平台塑造着政治话题的同时,也在被政治权力控制着。平台看似为无差别的内容呈现的舞台,但实际上其主导的商業公司以及所在的国家背景都使得平台天然具有政治偏向。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被多个国家和平台以“假新闻”的理由处罚和封堵,这无疑是利用对渠道的把控而实施的霸权行为。同年,美国大选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将抗疫政策措施作为争取选票的“武器”,在是否要佩戴口罩、保持多少社交距离等议题上剑拔弩张,导致民众的防疫认知被迫与政治立场挂钩。利用计算宣传进行权力博弈使得政府和专家的公信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疫情在美国蔓延和失控。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和艾弗拉姆·乔姆斯基((Avram Chomsky)曾经提出,为了制造共识,美国的媒体报道存在着系统性偏见。目前世界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大多来自美国,这些平台表面上看似在维护信息流动、追求新闻的客观真实、无国界地尊重所谓全人类的“人权”与“自由”,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平台其实是以美国为先,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为原则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曾创下一天发布200条twitter的纪录,担任总统期间总共发布25000多条推文,但在美国大选失败之后,Facebook和Twitter以“发布煽动性言论”为理由无限期封禁特朗普账号。在社交平台上,权力透过算法和平台精心制造同意,对持不同意见的账号进行干扰和封禁,并给大众塑造出“多数同意”的感觉。计算宣传在根源上威胁到了公共舆论的自由平等,挑战民主治理,计算宣传早已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
四、结语
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解决计算宣传对于公众舆论的恶意操纵问题迫在眉睫。在治理时,国家政府、科技公司和用户等利益攸关方应共同参与,从法律架构到具体实施层面进行完善。国家间也应通过理性讨论形成全球共识,共同努力重塑健康的全球信息生态系统。
作者单位 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社会网络的崛起[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José van Dijck,Thomas Poell,Martijn de Waal.The platform society: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3]史安斌,楊晨晞.信息疫情中的计算宣传:现状、机制与成因[J].青年记者,2021(05).
[4]Garth S.Jowett,Victoria J.ODonnell.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8.
[5]刘海龙.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从旧宣传到新宣传[J].国际新闻界,2007(09).
[6]Marco T. Bastos,Dan Mercea.The Brexit Botnet and UserGenerated Hyperpartisan News[J].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19(01).
[7]师文,陈昌凤.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基于《纽约时报》“修例”风波报道在Twitter上扩散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05).
[8]Stella Massimo,Ferrara Emilio,De Domenico Manlio. Bots increase exposure to negative and inflammatory content in online social systems[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8(49).
[9]陈昌凤,袁雨晴.社交机器人的“计算宣传”特征和模式研究——以中国新冠疫苗的议题参与为例[J].新闻与写作,2021(11).
[10]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J].国际新闻界,2014(05).
[11]师文,陈昌凤.分布与互动模式:社交机器人操纵Twitter上的中国议题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05).
[12] Cheng Chun,Luo Yun,Yu Changbin.Dynamic mechanism of social bots interfering with public opinion in network[J].Physica A: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its Applications,2020(01).
[13]Bennett,W.Lance,Entman Robert M.Mediated Politics: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4]DeLuca Kevin Michael.Image Politics: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M].London:Taylor and Francis,2012.
[15]赵永华,窦书棋.信息战视角下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嬗变:技术与宣传的合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03).
[16]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4).
[17]罗昕.计算宣传: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舆论新形态[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5).
【编辑:郭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