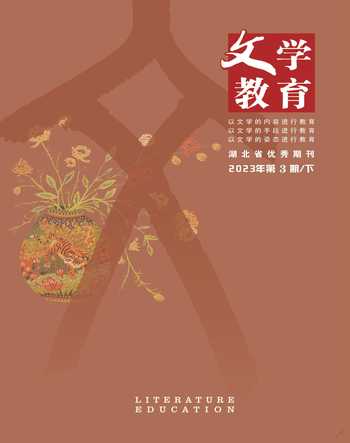残雪《吕芳诗小姐》的空间叙事
2023-06-07罗宁凡雷霖
罗宁凡 雷霖
内容摘要:《吕芳诗小姐》凭借丰富多维的空间结构、复杂多元的人物形象、诡谲多变的语言意象,建构了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显现出作家对于人性异化所产生的恐惧焦虑,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本文以残雪小说创作中的空间叙事策略为出发点,挖掘人物在现實与非现实的灾难冲击之下,如何堕落、重构、救赎的全过程,最终指向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反思当下的困境,展开对命运的抗争,从而真正实现自我主体性的突破与超越,展望新的生命图景。
关键词:残雪 《吕芳诗小姐》 空间叙事
在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日趋多角度、多层面、多元化的今天,残雪的写作具有外露的锋芒和内延的品格。作为中国先锋小说的另类拓荒者,许多读者将她的写作定义为“施展巫术”,因为她总是有意地疏离传统文学的形式,运用诡谲的意象、荒诞的情节、魔幻化的手法来建构一个非传统的、甚至是极度异化的文学空间,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倘若我们对其作品进一步的梳理和概括,可以发现作品的结构、人物、语言逐渐走向丰富,凸显了空间、角色、意象背后的深层意蕴和情感表达。这些转变也体现了作家一种赤忱、真挚的美学努力。
于201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吕芳诗小姐》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通过描写红楼性工作者吕芳诗同众多情人、友人、亲人之间发生的系列故事,展现人的感性、理性、本我在欲望、死亡、永恒面前的不同呈现,证明了人是如何在灾难性的生活中寻找圣洁的心灵故乡,如何挖掘一种有价值的人生意义。在已有研究中,姜玉平的《心灵空间的开拓——论残雪〈吕芳诗小姐〉中的三个空间意象》一文,以核心意象“红楼”“贫民楼”和“钻石城”来对文本进行剖析,以严谨的笔墨“书写了主体突破重围向本质自我挺进的艰难曲折的历程。”①本文在吸收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挖掘文本尚未解答的深意,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体量和方向上的不足。
一.“红楼夜总会”:感性的堕落
“红楼夜总会”作为文本的初始空间场景,承袭了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最为经典的色彩,描绘了一幅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的画卷。红楼如梦悠扬,佳人、肉体、欲望在此间交织相伴。那里又是现代感的融合,就像一个大闷罐,彩色的激光四处乱舞。人的欲求被不断唤醒,仅有的理智日益倒塌,也为故事中的人物带来了复杂的矛盾体验。
吕芳诗,高挑貌美,令所有的男人都为之倾倒,也直接指向了女性在异性关系中一直面临的处境——一种被他者化、欲望化的存在。残雪就是要让读者透过一个个男性的目光,去写一位游走在众人身边的女性,进而揭示她从未消失的隐秘屈辱和内心伤痛。吕芳诗是聪慧的,她或主动或被动地为所有人物提供一种内心的幻想,借此换取她所想要的东西:童年缺失的疼爱、父辈真切的关照,摆脱贫穷的金钱、供以居住的处所亦或是重新开始人生的捷径。很多伤痛和疑问,例如对女性的暴力,规训、打压,伴随着吕芳诗的一生。那个幼时被父亲鞭打的她,被“独眼龙”扔在钟乳石岩洞中,匍匐爬行的她,被“死去的T老翁”抛下的她……世俗规训着她愿为情欲付出多少代价,要为情欲付出多少代价,她像一个赌徒,在两性或者同性的博弈当中损耗自己,一旦变得习惯通过迎合一部分的主流叙事和男性审美来获得一些东西,其自身主体性的部分就在慢慢地减弱、丧失。如果她想要突围,想要逃离这种强者控制下的游戏,她就必须在既定的男权规则中学习、浸润,最后往往发现自己举步维艰。
残雪在《追求逻各斯的文学》中提到:“欲望是我创作的核心,它也是我的想象力的黑暗的母亲”②。她不仅写欲望,也写欲望对于人性的消磨和打压,正是具有欲望这一本能诉求,文本中的每一个人才会在“红楼”这个场域中盘桓、游荡,在乏味生活中 寻找激情。当欲望在世俗场内不断地弥散和扩张,变得永不满足,人物内心的天平便会倾倒失衡。这也是为什么,在“京城红楼”和“西部新疆”的隐形对照之间,吕芳诗一直在寻找自己灵魂的故土,对于她来说,京城繁华却冰冷、虚无缥缈,阳光没有一点真实的暖意,是一个肉体上暂居之地。而西部,是回想起来就让人的灵魂为之痛苦颤抖的故乡,那种痛苦是大海一般深广而澎湃的激情,同过往不死不活的阴暗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她叫嚷着:我们的禀性使我痛苦。她深知,在庸常和寂寞之间,那种无意义的生活似乎比死亡更为可怕。
二.“公墓社区”:理性的突围
名叫“公墓”的贫民住宅小区,是作家残雪创造的第二个空间场所,它的存在是如此的古怪而奇特,幽灵、鬼魂、守墓人都遍布其中,充斥着无名的阴影和噩梦。相较于“红楼”这个意象而言,它更加具有残雪创作风格中“魔幻象征化”的影子,是作家“侧重于通过虚拟的形象群,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抽象概括”③。在激情、暧昧的“红楼”中起伏挣扎的曾老六和吕芳诗,深感痛苦和折磨。自我在堕落中逐步走向异化和分裂,从而诞生了主人公的第二个“分身”——理性自我。
吕芳诗来到“公墓社区”定居,在那个一室一厅的狭小单元房内,段珠用一场盛大的表演完成了吕芳诗对于死亡的认知。“段小姐躺在那张舒适的床上,一张脸缩得只有手掌那么大了。”④“她虽然已经半昏迷,说着胡话,一双鸡爪一样的小手紧紧地抓着吕芳诗的手不放……她的指甲嵌进吕芳诗手掌的肉里头……然后她的身体抽搐了两下,渐渐变硬了。”⑤曾老六在“公墓社区”的经历也充满了奇幻、荒诞和虚幻的多重体验。在首次进入“公墓社区”的过程中,他战战兢兢地走出电梯,被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带入十五楼的玻璃房间,窥见不同楼层住户的生活:红棕色的母猫、争吵的男女、脸上文着黑色蝴蝶的白浴巾女人、空中垂死的灰鸽。他被辱骂为草包、懦夫,被当作小偷、哑巴,又被两个穿着黑衣的蒙面人痛打一番,推出了大门……
“公墓社区”在空间上是现实世界的映射,表达着世俗的欲望和生者的需求。在这个非现实的语境中,一切现实的意义和价值都被人为地搁置和抽空。吕芳诗、曾老六行走在这个如梦魇般的黑暗世界,或多或少迷失了方向,他们必须剥开世俗社会的伪装外壳,以一个真诚的模样面对自身。这也正是死亡和墓地之于人类的另一层意义,它使人变得更加理性,让人有能力将无形的情感变得有形,从而脱身于欲望的泥沼。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更是一个裹挟着恐惧、伤感、委屈的过程。于是,当吕芳诗在段珠房间看见纷飞盘旋的海鸥,当她直面相似身份、相同性别的生命的离去,就必须正视她作为人的情感,认识到肉体生命的短暂,知晓只有真挚热忱的灵魂才永远不会消失。而当曾老六能和社区里的幽灵一样,骑着自行车在空中飞翔那一刻,一种全然的欣喜和愉悦在他的身体里绽放。他混沌、孤独地在世上活了三十多年。曾经竭力地想要看清世俗黑暗中的某一种轮廓,现在,这种轮廓已然悄悄地浮现了。
吕芳诗和曾老六就是这样在理性自我的驱动和突围下,实现了一场感性自我和理性自我的相遇和审判,从而有机会脱离肉体的枷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曾经的自己与过去的生活。与此同时,人变得更为坚强、独立,世俗欲望被消解,生活的牵绊被打破,从而转向了更高的心灵需求。而“公墓社区”并不能为其满足其渴望,理性自我的约束甚至会带来心灵上的压抑和欲望上的反弹。在理性自我的突围和驱动下,他们更加向往一种全新的、自由的空间,以供心灵的遨游与探索,在这样内心渴望的驱动下,他们开始奔赴新的远方。
三.“钻石城”:本我的重塑
“钻石城”作为文本叙事发生的最后一个场域,对于吕芳诗来说,那是她的温柔之乡。当她被T老翁指引着来到钻石城,试图在这里寻找到一种心灵的满足,却不久听闻他游河身死的噩耗,只留下对岸那盏在风中浮游的电石灯。她的另一位情人“独眼龙”也在前往钻石城的旅途中飞机失事,站在那个透亮、空灵的机场内,她的神经陷入了巨大的崩溃,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她,使得“钻石城”俨然成为了一个烦恼之地。
在“哭郎山”,吕芳诗望着蓝紫色的天庭流泪,是对独眼龙,也是对T老翁。小花说:“情人只能生活在悲伤之中”⑥。这种矛盾不失为残雪的一种冷峻和幽默。她乐此不疲地为笔下的人物建造一座象征主义式的城堡,这座“城堡”不像作家卡夫卡那样建在山坡之上,而淫浸在世俗里头。T老爹、吕芳诗与曾老六,他们就像“土地测量员K”一样,都在“钻石城”这个场域内朝着更高的梦想迈进,却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挣扎終归无用。这种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所谓的创造也许不过是自欺,理想中的目标也总是在远处飘荡,追求者找寻不到确凿的证据,感受到的更多是寒冷、空虚与眩晕无力”⑦。在这种压抑的生活里,人总是凭借一种内在的非公正与非理性来摆脱虚无,就如他们尝试在黑夜里表达自己的愤怒,宣泄着对世界的困惑与不解,却无法撼动现有的疾苦,也常常忘记这种苦痛,然后在混沌的生活里继续行走。
在权力、欲望、金钱为中心的社会中,人类的幸福道路没有既定的模板,也没有恒定不变的可供参考或模仿的对象。吕芳诗这一类人要去实践、突破些什么,必须要去朝着未知而不断努力。这个过程也是挣扎、痛苦、充满有代价的。必然伴随着漫长的探索、挣扎、推翻、再重建的过程。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有机会看到人对于自由梦想的寻求,对重建生活秩序的渴盼。苦熬的人生不是一种纯粹的悲观主义,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有希望的压抑,是在绝望的缝隙里依然向上生长的勇气。或许,这就是他们表达内心希望的一种方式,以此来为她或他的生活带来正确的方向感,产生一种属于新生活的逻辑,引导他们向着不断地超越本我的境界攀升。
如果说“红楼”的存在是为了揭示欲望的本质和对人性的戕害,展现感性自我不断沦落的过程,而“公墓社区”是以死亡为切入点,表现理性自我在精神上的层层突围,那么“钻石城”则比“红楼夜总会”和“公墓社区”的内核更为复杂深邃。正如小花的父亲所说的:“沙漠里头有一种定力,因为它,我们的城市才被称为钻石城的”⑧。这种所谓的定力或许跟钻石的品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澄澈、透亮、清明,纯洁。这也是为什么“钻石城”能不断地接纳和吸收众多来自“红楼”与“公墓社区”的迁移者——那些内心燃烧着熊熊烈火的人、那些不满足于世俗现状寻求突围的人,那些渴望实现内在自我超越的人。“钻石城”以它的外在和内核表达着一种持久性的精神追求,关乎人的尊严,关于人生边界的探索,关于主流生活之外的想象,它教导人如何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如何追求自由、寻求真理,也只有这样的“钻石城”才能有动力将过往的糜烂生活抛却,将人的世俗欲望抽离、打磨、升华为具有质感的精神力量,去叩响永恒之门,从世俗人生跃入到真正的、艺术的、故乡式的生活。
残雪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小说和文字,建立在背离传统的文学阅读感受和日常经验世界的基础之上,以一种个人化的言说方式,打造了一座独具“残雪式”风格的文学王国。她被众多的呼声推向赞扬与追捧的漩涡中心,又主动地隐退到关注的人群之外,始终将深沉而辽远的目光投向人的精神领域。从结构布局到人物塑造,从主题蕴含到语言风格,行走在残雪的文字之间,我们似乎很难看到那些充满动感、欢乐、温暖的言语,在那些看似晦涩、奇绝、灰暗的意象背后,在那些跃动、多彩的“吕芳诗”式的灵魂身上,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它们的形态各异,内含着智性和诗意。就像文本中所说的那样,吕芳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内心的诱惑、潜在的情感,足以引发内心的伤痛。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望向他人而遗忘了自我的时刻,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吕芳诗。她的倩影融化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给每个人带来某种新的意义。
也正如文章所描绘的那个心灵的归宿——“钻石城”,那个纯洁的、热情、一目了然的不夜城。它是属于女性的心灵城堡,更是属于人类的心灵家园。这座神秘、动人、充满希望的城堡,是像吕芳诗一样的女性,通过自我精神的搏斗,灵魂的沦落与重构才能接近它、触摸它。即便距离我们当下的生活是那么隔绝而遥远,残雪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写作范式的构建,带我们进入那座城堡。在那个如梦魇般幽深、奇异和反传统的文学图景内部,残雪以一种决绝的勇气,不断地叩问人类应该如何寻找本真的自我与意义,促使人们直面自己的生存处境,展现了她对于世俗人生的另类反思,从而抵达了被传统观念所遮蔽的精神真实,使得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只要我们尚且存在,这种心灵的探索和灵魂的挺进就永远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残雪.吕芳诗小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2][美]乔恩·格里菲思,残雪.追求逻各斯的文学[J].作家,2010(3):110~120.
[3]徐宝锋.宇文所安中国诗学研究的“情”“欲”视角[J].阅江学刊,2015(2):108~113.
[4]姜玉平.心灵空间的开拓——论残雪《吕芳诗小姐》中的三个空间意象[J].宜宾学院学报,2015,15(8):49~55.
[5]姬志海.新千年残雪长篇小说“魔幻象征化”的创作考量[J].南方文坛,2018(5):148~153.
注 释
①姜玉平.心灵空间的开拓——论残雪《吕芳诗小姐》中的三个空间意象[J].宜宾学院学报,2015,15(8):53.
②[美]乔恩·格里菲思,残雪.追求逻各斯的文学[J].作家,2010(3):115.
③姬志海.新千年残雪长篇小说“魔幻象征化”的创作考量[J].南方文坛,2018(5):148.
④残雪.吕芳诗小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90.
⑤残雪.吕芳诗小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91.
⑥残雪.吕芳诗小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62.
⑦姜玉平.心灵空间的开拓——论残雪《吕芳诗小姐》中的三个空间意象[J].宜宾学院学报,2015,15(8):53.
⑧残雪.吕芳诗小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76.
基金资助:2021年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国家级立项项目“新世纪以来湖南长篇小说中的灾难叙事研究”(202110548023)结题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