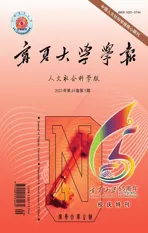选本视域下《诗经》编纂观对唐人选唐诗的多维影响
2023-06-06赵鹿园
赵鹿园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儒家经典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极高的位置。《诗经》的独特地位,使得后代诗歌选本常以《诗经》为旨归,形成独特的“宗经”理念。与此同时,《诗经》的编纂观念及其评价体系,也成为后世对诗歌选本评点的重要依据。唐人对本朝诗歌的选本即唐人选唐诗,在继承《诗经》选本观的同时,也通过对《诗经》意涵的阐释来表现自身编纂观念,形成独特的选本批评,反映出选家乃至唐代诗歌批评观念的时代特性,并影响到后世对于唐人选唐诗价值的评价。学界关于《诗经》对唐人选唐诗观念影响的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论述。下文以《国秀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箧中集》《御览诗》六种为例,从观念溯源、诗人评点、接受评价三个角度探析《诗经》及其选本观对唐人选唐诗的多维影响。
一 选本视域下《诗经》编纂观念的特殊地位
《诗经》独特的编纂方式,使之不仅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同样可视作最早的诗歌选本。总集与选本的概念皆晚出于《诗经》,现存最早关于总集的概念,见于《隋书·经籍志》:“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据此可知,总集观念源于晋代挚虞《文章流别集》,其主要原因在于建安之后文本的增加,给阅读者造成阅读的不便,故而通过“采擿孔翠,芟剪繁芜”的编选方法完成编纂。由此可见,挚虞《文章流别集》的编选过程已经具备一定的选择观念与编选原则,选本与总集之间并无明显分野。后世随着全集的编辑,选本概念逐渐成为总集定义的一个部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序》:“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2]后者所指,即为选本。根据文义可知,选本的概念包含两个要素,其一为编选的手段,即“删汰繁芜”的过程,编选符合自己标准的作品;其二,依据编选的标准而形成一定的批评观,即“文章之衡鉴”,通过选与不选、选置前后、选量数目、编选体裁等诸多要素,完成选家文学观念的具象化呈现。
基于以上概念考察《诗经》,可发现其在符合选本概念的同时亦具有其特殊性。其一,编选内容的收录与选择上,《诗经》对当时所存诗歌具有明显的选择过程。尽管学术界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存在一定质疑,然而《诗经》在编订过程之中存在编选、删汰与整理,当无争议。《诗经》的选择过程并非一人一时而为之,在成书过程之中至少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编写,首次为周代大师对所采诗歌的编选整理。《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3]又《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4]其中“比其音律”的采辑方式已包含对所采诗歌的基本编订,完成由口头文学向音乐文学的转化。其次为孔子等儒者对已存诗的整理删汰。《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5]又《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6]这一论据除见载于《论语》等材料外,亦可藉由《诗经》同时代未选诗情况予以佐证。一方面,根据清人马国翰《目耕帖》辑得《诗经》未选诗一百一十条,以及近年出土上博简及清华简所涉诗四十五条,未选诗数量已接近《诗经》篇目总数三分之二,可知《诗经》在编选过程之中对同时期诗歌的选择。另一方面,清华简所载《周公之琴舞》成王九首诗中的第一首见录于《诗经》,即《周颂·敬之》,组诗中其他部分则未能入选《诗经》,可见《诗经》编选过程中对同一类型诗歌存在删繁就简的过程。
其二在于依据编选主旨形成文学批评。《诗经》将郊庙之章与“采诗观风”之作依照创作者、创作地域及创作时间等信息,分为“风”“雅”“颂”三类。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诗经》的文学批评观在孔子及后世儒生的不断诠释下逐渐系统化,形成诗教传统,成为影响中国诗学的重要意涵。《诗经》的具体功用,在儒家经典之中记载颇多,于作品价值,则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7];于个人习得,则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8],“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9],“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10];于社会教育,则强调教化功用,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11]。故而《诗经》的主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12]。随着《诗经》经典地位的奠定,诗教的意义不再限定于个人与教育社会,同时包含向上约束警醒帝王的“怨刺”功用。如《毛诗大序》谓:“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13]释《风》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玄笺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14]在这一说法影响下孔颖达疏“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提出诗的“一名三训”说:“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15]《诗经》的主旨通过层层增补而趋于明晰,成为后世文人模仿和借鉴的标杆。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选本,《诗经》在编选过程与编选主旨的阐释上皆存在群体化和递补化的特点,编选主旨多以孔子所言作为论断的核心,并在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之中层层阐释而趋于丰富。从接受的角度,孔子在编选维度完成了《诗经》形制上的经典化,后世儒者在批评维度通过不断阐释,赋予《诗经》新的生命力,在诗歌选本体系之中成为独一无二的经典。
正是这样的经典化,使得后世儒家文人往往将《诗经》所涉篇目归为经部,将其束之高阁而不作选录,正如文选序所谓:“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16]因此,尽管选本之中不选《诗经》诗作,《诗经》的概念却对历代诗文选本产生颇为重要的影响。
二 《诗经》首肇地位与唐人选唐诗的祖述心态
《诗经》以其现存首部诗歌选本的地位及其儒学经典化身份,使得后世选本在表达选家主旨时,往往将《诗经》作为追溯的源头。对编纂源头的追溯现象,主要表现于选本序言之中,这一流程在唐前已基本成形,在唐人选唐诗之中进一步深化,各家所论又各具特色。
现存最早以序言形式溯源《诗经》的诗文选本为《文选》,主要体现在萧统《文选》序及《文选》目录顺序之上。尽管《文选》属于诗文选本,然而通过萧统《文选》序的阐释,可发现其对《诗经》及其意涵独到地位的推崇,主要包括两点:首先,根据诗之六义,言《诗经》对赋的直接影响。“《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17]尽管诗经之“赋”与赋体之赋并非同义,通过萧统的诠释,《诗经》已成为赋类文学的来源。其次,强调《毛诗·大序》“诗言志”的文学主张。“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18]将《诗经》言志观视为诗类文学的源头。根据《文选》目录,其首为“赋体”二十一卷,次为诗体两卷,此后方为骚、七、诏令、表、书、颂、论、诔、碑、吊等三十余体,可见二者在《文选》序列中的核心地位,亦可知《文选》编选观对《诗经》的继承。加之上文已述《文选》因《诗经》“日月俱悬,鬼神争奥”的性质而不选于内,更说明萧统编选《文选》时对《诗经》的尊崇之态。
尽管《文选》序涉及诗之六义、诗言志等与《诗经》相关的文学思想,但在具体编选主旨上,《文选》却能够宕开一笔,以古今有别为由,在编选过程中倾向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9],关注创作主体的情感与作品本身的辞采,使之编选标准与时代审美相贴合,由此形成了对《诗经》尊而不从的特点。
考现存诸唐人选唐诗之作,其中有自序或友人序者为《箧中集》《瑶池新咏》《窦氏联珠集》《河岳英灵集》《丹阳集》《中兴间气集》《玉台后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共10部,其中8部涉及对前代诗文的梳理,其溯源情况概述如下:《国秀集》与《箧中集》祖述于《诗经》,《丹阳集》祖述建安、太康,《又玄集》祖述于曹子建与谢玄晖,《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祖述《文选》,《瑶池新咏》祖述前代才女,《玉台后集》祖述于《玉台新咏》。诸选本因其编选观念之别而各有差异,然其中祖述《诗经》与《文选》者最多,加之上文述《文选》对《诗经》的尊崇,可见《诗经》在诸唐人选唐诗中的突出影响。《国秀集》与《箧中集》序在继承《文选》论述的同时,形成了自身阐述风貌,也凸显了盛中唐之间文学思想的因革变化。
《国秀集》为唐国子生芮挺章天宝三载(744年)所编,据楼颖《国秀集》序言,芮挺章受秘书监陈希烈、国子司业苏源明论述而编选《国秀集》,谓所选范围为“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的诗作,最终由楼颖整理编目而成,所选共90 人,诗220 首。尽管芮挺章在实际编选过程存在部分与陈苏二人论断不符之处,如将所选诗人扩大至初唐文人群,将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刘希夷、董思恭等诗人作品编选入集,但整体编选主旨依旧以陈苏二人论述为主。二人论述主要涉及诗歌的发展流变过程,包含三个阶段,首先为“礼乐大坏”时期,“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20],言《诗经》风雅之后,传统讽谏与言志说的丧失。其次为“否极泰来”时期,由子夏解诗传承至题名李陵的“携手上河梁”之作,虽“未协风骚”,却能“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这一论述,与《文选》序所谓“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21]颇类,皆言流变之后的新风貌。再次为开元天宝年间,即对同时诗作的评判,须“谴谪芜秽,登纳菁英”[22],以此呈现题目所谓“国秀”之旨意。借由这一段论述可见二人关于《诗经》的态度,一方面表示尊崇,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古今变化而转化评判标准,认为既“未协风骚”,亦自成特色,其对于《诗经》的引用方式类似于《文选》,对《诗经》保持了尊而不从的观念。
除与《文选》相似对《诗经》的尊引外,楼颖序首通过分析《诗经》的编选主旨,对《国秀集》的编选标准予以合理化解释,谓“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23]。从《诗经》选家方式出发,推断孔子删选标准为“顺泽”。顺,遵循其理。《说文·页部》:“顺,理也。”[24]《释名·释言语》:“顺,循也,循其理也。”[25]泽,光亮润泽。《说文·水部》:“泽,光润也。”[26]由此可知,此处顺泽可释为顺合儒家礼义且富有文采者。其中对文采及“弦而歌之”音律性的倡导,似未见于孔子诸说,当为楼颖对《诗经》主旨的别样发挥,为阐述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提供正统性与合理性。将文采与节奏作为评判的重要标准,与唐代国子监风尚息息相关。尽管国子监主要以习九经为主,然而诗赋举士的科场环境,使得以五言律为主的试律诗成为国子生关注的焦点。国子学官亦积极参与宫廷唱和活动,诗作尤重文采婉丽。作为国子生的芮挺章亦不能免俗,在《国秀集》收录五言律作(包括律诗与排律)共127 首,占全集一半以上。芮挺章与楼颖所选己作,即芮挺章《江南弄》《少年行》及楼颖《伊水门》《东郊纳凉忆左威卫李录事收昆季太原崔参军三首》《西施石》七首中,除七绝《西施石》语态稍显清新外,其余皆为辞采为盛、对仗工丽的五言律作,可见其审美取向。
《箧中集》为元结乾元三年(760年)编选唐诗选本,共收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位“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27]诗人作品共24首,皆为五言古体诗。《箧中集》序借由与他人对话表述其编纂主旨。首先,序言论《诗经》风雅传统的正统地位及其在后世逐步丧失的遗憾,将这些“溺于时者”称为流俗,主要表现为“拘限声病,喜尚形似”,即对音律节奏与描摹雕饰的重视。因此,元结的尊经复古观念认为齐梁至初盛唐的诗作皆不符合《诗经》风雅,以此凸显《箧中集》编纂的迫切性与必然性。尽管同样尊《诗经》,在面对诗歌古今风格之变时,《箧中集》采用了与《文选》及《国秀集》相反的观念,对后世文风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次,基于元结的复古观念,对能够继承《诗经》风雅观却湮没于诗歌风潮的作品加以编纂弘扬。元结一生倡导复古精神,尤对《诗经》诗教传统多有提倡,如仿照《诗经》美刺讽喻精神,行以规讽劝谏的举动。元结《二风诗序》:“天宝丁亥中,元子以文辞待制阙下。著《皇谟》三篇、《二风诗》十篇,将欲求于司匦氏,以裨天监。”[28]相较于《文选》与《国秀集》尊而不从的态度,《箧中集》意图通过编选完成对《诗经》风雅精神的继承。然而《箧中集》所选诗作主题较为单一,主要抒发了仕途失意贫苦悲愁的情感,即使偶有对归隐情感的向往,内在精神亦是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之语。因此,元结及其所选《箧中集》所倡《诗经》风雅精神,实则仅就《诗经》怨刺精神有所发挥,以变雅替换风雅。清施补华评价“小雅之哀音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亦谓元结:“所提倡的,固然是风雅诗,但我们不妨直截了当的说是规讽诗,更比较恰当”[29]。在诗歌取法上,《箧中集》诗人主要模仿汉魏古诗风格。《箧中集》收录诗歌存在三个特征:其一,在体式上,取法汉诗,不用对偶;其二,在文辞上,于直白字句间杂入少数艰涩词语;其三,在文义上,上下句跳跃而不连贯。由此可知,以汉魏五古为基本风貌且兼具“古体”“古词”“古义”特点的诗作满足元结对风雅之作的认知。除此之外,元结对汉魏之前诗体风格如对诗经、楚辞体颇多推崇,曾以诗骚之体作《二风》《引极》《演兴》诸诗,欲在形式上完成对古体的复现。然而,这一尝试正如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所论,“元次山《二风》《演兴》诸诗,填塞奇字以拟骚,反成浅陋”[30]。终因过度泥于古朴,反使作品与《诗经》风雅精神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可见,元结风格形式上对风雅精神的推崇,更多为以“古”代“雅”。综合而言,《箧中集》的风雅精神,是元结自身对崇古观念与怨刺的外化展示,作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别调,《箧中集》固然无法完全呈现中唐以来诗歌发展的脉络轨迹,在诗歌主旨上因其沉溺于《诗经》怨刺精神而对初盛唐诗歌评价颇多偏颇,然其独特的编选观念,对安史之乱后文人的悲苦心态及社会风貌的描述具有其自身价值。
除以上二者外,祖述《诗经》的唐代诗选本尚有慧静《续文苑英华》。据《大唐新语》所载慧静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31]及顾陶《唐诗类选》:“在昔乐官采诗而陈于国者,以察风俗之邪正,以审王化之兴废,得刍荛而上达,萌治乱而先觉,诗之义也。大矣远矣,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由政治以讽谕。”[32]既有对《诗经》编选删定的继承,亦有对采诗讽喻观的推崇,然而,由于这些选本所选诗作的缺失,这些选本编选理念的多维特性已难以了解。通过对比《国秀集》与《箧中集》编选主旨可知,尽管同样祖述于《诗经》,却因二者对《诗经》认知偏重的差异,使得不同选本的编纂主旨呈现出巨大区别。对《诗经》的祖述,实则包含为何祖述、祖述什么等具体观念的差异,反映出选家的文学认知与文学主张。正如鲁迅所言:“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33]。
三 《诗经》风雅精神与唐人选唐诗品评话语的衍进
相较于前代选本,唐人选唐诗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形成了选评结合的选本特征,为后世了解选家的编选心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现存唐人选唐诗诸集在选评选录诗作的基础上增添对诗人的品评者,有《河岳英灵集》《丹阳集》《中兴间气集》及《窦氏联珠集》四部,其中《窦氏联珠集》所评主要为作者生平,并未详及作品风格,其余三部在品评部分包含以下内容:叙述诗歌风格、评析诗篇诗句、论述诗风渊源,由此形成的评点模式,与评点类诗话颇为相近。
现存最早以评点诗人为主旨的诗话为钟嵘《诗品》。《诗品》将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对诗风渊源予以评析,形成“知溯流别”的评价体式。钟嵘《诗品》序中并未将《诗经》作为祖述对象而给予其独特地位,在品评诗人部分,《诗经》在《诗品》中的独尊地位方得以呈现。如评古诗,谓“其体源出于《国风》”[34];评魏陈思王植诗,谓“其源出于《国风》”[35];评晋步兵阮籍诗,谓“其源出于《小雅》”[36]。古诗、曹植、阮籍在《诗品》皆列于上品,与承于《楚辞》的李陵共同构成后32 位诗人沿袭之渊源,其中承于《国风》者14 位诗人,承于《小雅》者仅阮籍一位诗人,共占比为46%。关于《国风》风格,《诗品》评古诗谓“文温以丽,意悲而远”[37],《诗品》评曹植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38]。通过以上二者论述逆推可知,《诗品》认为《国风》风格主要体现在文辞上温婉自然又兼具典雅文采,在情感哀怨而不至刻薄,即“哀而不伤”。关于《小雅》风格,《诗品》评阮籍谓“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39]。以一己情思寄托于社稷忧患,是对《诗经》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的传承。
《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三集不仅借鉴了《诗品》评点模式,同时承袭了《诗品》对《诗经》诗学传统的发掘,形成以风雅为中心的评点范畴。《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为殷璠所编,《丹阳集》收丹阳籍18 位诗人,述丹阳一带诗歌风貌。《河岳英灵集》收24 位诗人234 首诗,起于开元二年(714 年),终于天宝十二年(753 年),体例与《丹阳集》相近,将《丹阳集》对诗人风格的评点方式,扩展到对盛唐诗人风貌的呈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收26 位诗人134 首诗,如其书名,用以论述中唐肃代二宗中兴时期诗坛风貌。尽管高仲武并未直言《中兴间气集》与《河岳英灵集》之间的关联,然而二著皆立足于诗坛整体,品评诗人及佳句风格特点,在立意与选家视野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在具体诗人评点上,基于《诗经》固有文化意涵予以凝练与衍化,形成独特的诗歌评价体系。其中部分评价语汇并非肇始于三集,因而不仅体现出以殷璠、高仲武为代表的盛中唐文学观,更能体现出文学批评观念层层递进下的丰硕结果。
殷璠《丹阳集》《河岳英灵集》及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对《诗经》凝练的继承,亦可称之为风雅概念的继承与诠释。在二人笔下,风雅含义概有两种。
其一,泛称本朝诗歌盛况,强调对风雅的继承。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40]。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国风雅颂,蔚然复兴”[41]。殷璠之风雅“南风周雅”不仅包含《诗经》,亦包含《诗经》之前圣贤之歌《南风》。《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42]。高仲武之风雅“国风雅颂”,则是对《诗经》内容的全面概括。尽管二人对风雅的阐释存在差异,皆能看出二者对于《诗经》尊崇地位及其中的复古倾向。
其二,以风雅代指与《诗经》相类的风格与特点。如同《诗品》评述诗人风格对《诗经》的继承,唐诗选本同样将风雅联用,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格予以论述,如《河岳英灵集》评储光羲诗“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43];《中兴间气集》评刘长卿诗“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44]。部分评论则以风或国风称之,如《丹阳集》评蔡希周诗,谓其“词彩明媚,殊得风规”[45],《中兴间气集》评朱湾之诗,谓其“哀而不伤,《国风》之深也”[46]。整体而言,上文中以风雅或风作为论断主要关注《诗经》作为儒家诗作所秉持的风格,即“伤而不怨、哀而不伤”的情感基调。
基于风雅论述的影响,亦体现在对风与雅观念的继承与演变之上。如对风的衍化,体现在对风骨观念的继承。《河岳英灵集》论述“风骨”的评价,如评整体诗坛谓“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47];评崔颢“风骨凛然”[48];评陶翰“复备风骨”[49],尽管风骨一词自魏晋以来已逐步脱离了传统“风”的范围而凝练为独特的文学风格,然而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开头即述风骨观念与《诗经》之关联:“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50]虽然刘勰对“风”的含义的解读已由诗体转化为对文义与情感的抒发,但依旧可以看出《诗经》的隐约影响。而在对诗人的评述中,殷璠以雅为基础,衍化出多重意涵。如《河岳英灵集》序提出“雅体”观念,并与“野体”“鄙体”“俗体”对举,成为“定其优劣”所推崇的文体风格。如《丹阳集》评谈戭“戭诗精典古雅”[51],评殷遥“闲雅”[52];《河岳英灵集》评王维“词秀调雅”[53],评孟浩然“半遵雅调”[54],评卢象“雅而不素”[55]。与之相似,《中兴间气集》同样强调诗歌的雅体观,如评于良史“诗体清雅”[56],评郎士元“稍更闲雅”[57],评崔峒“意思方雅”[58]。几者各有侧重,反映出对于雅的多维观照。
除直接以风雅观评点诗人风格外,二人对《诗经》的修辞特点即“讽”与“兴”观念有所关注。讽有谏义。《韩非子·八经》:“故使之讽,讽定而怒。”王先慎集解:“讽,谏也。”[59]《诗经》因其独特的编纂方式,使之具有独特的政治功用。郑玄《毛诗正义》释《风》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60]作为上下交互的载体,郑玄不释教化功用而着重强调讽喻怨刺功用。“兴”作为《诗经》六义之一,亦属于“兴观群怨”说之一种。郑玄《毛诗正义》:“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孔颖达疏“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61],强调文章的譬喻与说教作用。讽与兴相互结合,在怨刺过程中具备微言大义、说而不破的论说方式,形成兼具讽刺与象征化的诗歌风格,成为后世评判的重要观念。如《河岳英灵集》评崔国辅,谓其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味”[62],《中兴间气集》评张众甫诗“得讽兴之要”[63],以“讽味”“讽兴”评价诗歌对现实的讽谏特点。此外,随着后世的不断阐扬,“兴”的概念逐渐脱离传统社会功用观,成为一种纯粹文学化的表现手法。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64],强调“兴”的含蓄风格;钟嵘《诗品》“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65],强调文采含蓄隽永而留有韵味。这一特点见于《河岳英灵集》,如评刘眘虚“情幽兴远”[66],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67];亦见于《中兴间气集》,如朱湾“诗体清远,兴用弘深”[68],评张继诗“比兴深矣”[69],显示出其独特的审美意蕴。
整体而言,唐人选本的评点对《诗经》风雅精神的继承与衍进,在尊古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创建,与初盛唐陈子昂风雅兴寄理论、李白对“大雅”“正声”的推崇交相辉映,体现出唐人审美在复古与求新间的独特风貌。
四 《诗经》编选旨意与唐人选唐诗的后世评点
在众多唐人选唐诗选本中,《御览诗》因其独特的编纂行为而独树一帜。《御览诗》又称《选进集》,为元和九年(814 年)至元和十二年(817 年)间令狐楚奉唐宪宗敕而编纂的诗歌选本。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御览诗》文献者为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六跋《御览诗》:“右《唐御览诗》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学士令狐楚所集也。按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70]《御览诗》原书选诗310篇,南宋存30位诗人289篇,今所存30位诗人共286篇,皆为大历元和年间诗人之作。因《御览诗》编纂行为不再局限于编纂者自身文学观念,尚需结合帝王喜好、朝野风尚以及进诗的相关意旨,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御览诗》后世各版本如赵均跋、毛晋汲古阁跋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皆对《渭南文集》所载内容多有转引,其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总集一》误将“三百一十”改作“三百十一”,当为讹误。由此可见,陆游跋《御览诗》在后世认知《御览诗》意涵中的核心地位。陆游《御览诗》跋引卢纶墓碑文将令狐楚编选的举动视为“采诗”,这一说法与《诗经》采诗举动存在相似之处,皆是通过搜集诗作以备帝王阅读,完成了形式的“以下谏上”。除此之外,《御览诗》编选数量亦值得关注,310篇相较于《诗经》篇目仅少了一首,亦可作为《御览诗》与《诗经》相似性的旁证。
然而,由于史料的缺失,令狐楚《御览诗》相关序跋及进《御览诗》所附表状皆已散佚,难以直观了解令狐楚编纂《御览诗》所秉持的观念与态度,使得《御览诗》是否存在对《诗经》学习与模仿难以确证。然而,借由令狐楚同类型表状进诗的信息,可侧面略知《御览诗》编纂背景信息。令狐楚一生多提携后辈,对后辈诗文亦多有举荐。除进选《御览诗》外,令狐楚亦推荐张祜诗于朝,随诗附《荐张祜进张祜诗册表》,表首即谓“凡制五言,包含六义”[71],强调以《诗经》六义作为衡量五言诗的判断标准,可见令狐楚确存在以《诗经》为仿效的可能性。
宪宗朝野对诗文整体态度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在涉及诗歌议题上,朝臣往往习惯于以《诗经》旨意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如宪宗时期进诗和诗表状如权德舆《中书门下进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寮观新乐诗状》“洽慈惠于臣庶,播易良于国风”[72],《奉和圣制重阳日中外同欢以诗言志因示百僚》“宸衷在化成,藻思焕琼琚”[73],强调“播易良”“化成”功用。李益《诗有六义赋》“我皇乃以诗而条之国政,本乎人情。故得行于蛮貊,岂独用之邦国。修之身则寿考不忘,垂乎后则子孙千亿,乃知诗之为教”[74],较少提及诗歌以下刺上的怨刺功用。对《诗经》以下刺上功用的隐藏,与宪宗元和时期对刺谏行为的态度相关。宪宗虽为中兴明主,然其对刺谏内容并非大度,白居易曾因争谏而触怒宪宗,宪宗谓“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75]。除此之外,元和年间因诗文刺谏而获罪的文人颇多,如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因《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贬连州,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加之元和中晚期党争日兴,政敌间的相互攻讦使得怨刺的诗歌传统难以表现。
另一方面,宪宗对于诗歌的喜好更多体现于对文学情感的体验。尽管宪宗诗作已亡佚,然其对诗歌的喜爱,见载于史料。如因诗名拔擢李益,“宪宗雅闻其名,自河北召还,用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76],又如对卢纶诗文的搜集,“宪宗诏中书舍人张仲素访集遗文”[77],这些举措于政治功用并无干系,多为宪宗个人兴趣使然。
细观《御览诗》的编选情况,可发现其编选目的更多契合宪宗个人的喜好。首先,在选诗数量上,《御览诗》中受宪宗青睐的诗人李益、卢纶选诗数量分别为前二,为36、32首。其次,在情感主题上,《御览诗》多论述女性情感之作,或抒典故之旧情感,涉及巫山神女、班婕妤、王昭君等人物;或抒当下女子的美貌,多艳情之作,如梁锽《美人春怨》“落钗仍挂鬓,微汗欲消黄”。杨巨源《观妓人入道》“荀令歌钟北里亭,翠娥红粉敞云屏”,工于对女性服饰的描摹,着笔细腻华丽,反映出独特的审美趣味。除此之外,《御览诗》多有颂圣诗作,如卢纶《皇帝感词》“山呼一万岁,直入九重城”,马逢《宫词》“金吾持戟护轩檐,天乐传教万姓瞻”,梁锽《天长久词》“连吹千家笛,同朝百郡杯”,以较大视野抒写百姓观瞻帝王恩德的盛况,符合帝王对中兴风貌的期待。
综上推断,《御览诗》在编选上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御览诗》在形制与进状中主张效仿《诗经》编纂方式,然而依据宪宗朝风气及同时期朝野论诗内容,在主旨上忽视《诗经》以下刺上的怨刺功用,更多强调诗歌观风俗及教化百姓的功用。其二,《御览诗》忽略《诗经》的旨意,将编选《御览诗》作为纯粹文学活动,由此满足帝王的审美心态。
由于《御览诗》编纂心态已难以得知,使得明清文人批评过程中存在赞誉或否定的巨大差异,主要分为两种。
其一,试图以微旨、深思等角度为《御览诗》编选作出解读。如赵均《御览诗》题记将《御览诗》与《诗经》观念紧密联合,开篇即先言《诗经》功用:“夫诗为声教,亦为心声。故姬周之时,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君无异议,臣无异心。”其后通过《诗经》郑卫之风为令狐楚《御览诗》多妍丽抒情之诗作解释:“昔尼父删《诗》,不废郑卫,即二南首章,《关雎》《鹊巢》,犹且哀乐洋洋盈耳,何况吾人渐渍,能不从此入耶?盖诗缘情起,不由此入,沁人心骨,必不精至,令狐学士盖有深思在也。”[78]由此认为《御览诗》自有其编选的深刻旨意。毛晋《唐人选唐诗八种》《御览诗》后跋曰“唐至元和间,风会几更,章武帝命采新诗备览,学士汇次名流,选进妍艳短章三百有奇……无过集柔翰以对宸严,此令狐氏引嫌避讳之微旨也。宁曰改窜以立异,览斯集者,当自得之”[79],认为《御览诗》虽为“妍艳短章”之作,在具体编纂过程中难免“引嫌避讳”以达到“微旨”,与赵均“深思”之说接近。
其二,认为《御览诗》在编选过程中未能收录中唐反映现实的大家之作,亦未能完成以下刺上的功用。其中批判最厉者为何焯,其《御览诗》跋语谓:“此书又在《间气集》之下,大抵大历以还恶诗萃于是矣。”“此书所采大都意凡文弱,流淡无味,殆可当准勅恶诗耶!”[80]何焯对令狐楚《御览诗》编选的不满,在于令狐楚在获得采诗机遇之下,未能选择具有讽刺之诗,是《诗经》对于采诗以下刺上功用的背弃,亦未能反映中唐以来士大夫阶层的崇儒心态。傅增湘认为何焯之说虽苛刻,其整体观点却值得认可。《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集部九·总集类·断代·校唐人选唐诗八种跋·御览诗”谓:“义门于此选深致不满,至有‘准敕恶诗’之讥,其持论未免稍苛。然以宪宗英武,留情词翰,殆足嗣美文皇。楚厕身禁近,奉命采进,宜准风雅遗规,关于讽刺、鉴戒之作,如杜甫、鲍防、白居易、元稹、韩愈、李绅诸人,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而乃专录此轻艳浮靡之词,以导上于游佚,其失职甚矣!子晋乃谓其有引嫌避讳之微旨,其说未为允协也。”[81]在何焯感性化的评论基础上予以阐释,说明其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准风雅遗规”“以宣上德而通下情”,发挥《诗经》规讽的功用,造成“以导上于游佚”的恶果。
由此可见,后世对于《御览诗》评价的关键,皆围绕《御览诗》是否秉持《诗经》观念,即《御览诗》作为选进之作是否对宪宗施行《诗经》进诗传统“以下刺上”的观念,评价主要出于政治化而非文学化观念。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以《诗经》为主的批评观念对于《御览诗》的评点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使得后世诸多涉及《御览诗》评点的观念笼罩于《诗经》话语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御览诗》选本的风格特色及其对中唐风尚的反馈,亦忽略了其文献搜集与流传的独特价值。这一趋势,直至《四库全书总目》方有所改观,《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卷一八六《总集一》谓《御览诗》“雍容谐雅,不失风格”,探选诗原因谓“限于风气,不能自异”,故当“不以一二疵累弃其全书”[82],可谓持中之论。
结语
在性质上,《诗经》的内容及其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使其影响横亘于“经部”与“集部”,既有经学上《诗经》含义的阐释,亦有文学对《诗经》风格的继承与发扬,二者虽角度相异,却从不同角度影响到士大夫的“宗经”行为。加之以言志风刺说为代表的《诗经》精神,对于现实社会的关切,使得《诗经》兼具了学理性、文学性、政治性,与士大夫“学者、诗人、官员”三重身份相匹配而影响深远。
唐人在编选本朝诗歌选本过程中,对于《诗经》三重属性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脉络梳理上,立足于《诗经》作为选本之始的文学地位,衍生对《诗经》编选观念的选择性承袭。其二,在审美意涵上,对代表《诗经》艺术特性的风雅观及《诗经》表现特性的讽兴观予以细化阐释,完成对本朝诗人的评点。而在后世评点上,后世文人立足于《诗经》采诗之说,以《诗经》精神形式对存在仿拟《诗经》可能的唐诗选本予以评判。
唐人选唐诗对《诗经》观念的继承与发扬,本质上基于不同时期诗风与士风的变化。文中所涉选本编纂时间皆为盛中唐之际,对于《诗经》传承的差异,也显示出盛中唐之间文学风气的差异,盛唐选本如《国秀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更加关注于强调借鉴或阐释《诗经》的艺术特质,呈现出盛唐诗人对本朝诗歌的自信达观。《中兴间气集》虽参于《河岳英灵集》,然在具体评点过程之中,更加强调《诗经》“伤而不怨”“哀而不伤”的特点。《箧中集》更是高举复古旗帜,强调诗歌以下刺上的社会功用,显示出安史之乱以来面对国势急转、民生凋敝的现实困境,元结试图通过倡导儒家传统诗学观念改变时弊的殷切愿望。选家对功用化的倡导,与中唐诗风的演进相互应和,而《御览诗》在编选内容上未能明显反映同时代诗风的怨刺社会功用而遭到后世文人的贬斥。整体而言,《诗经》对唐人选唐诗的多维影响,对于了解唐人编纂选本的心理动机,对于全面认识唐代诗歌史具有其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