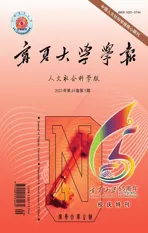由出土文献看中华文明基本特质与坚定文化自信
2023-06-06朱君杰
朱君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1]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予以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2]。
出土文献是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卷帙浩繁,种类繁盛,称得上中华文明之瑰宝,为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世界认可,中华文化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出土文献对于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对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信息可以进行有效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献将中华文明基本特质与精华更为清晰和鲜明地表现出来。以出土文献为依托,对于中华文明特质与精髓的分析便更为准确,也更有说服力。这便是出土文献对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历经的年代越久,传世文献便越容易出现流传过程中的散佚。因此,出土文献在同时期总文献中所占分量便越重,对中华文明特质与精髓研究的证明力和说服力便越强,对坚定文化自信的作用便更大。因此,本文依托先秦出土文献,对中华文明特质与精髓作出进一步申说,以期对传世文献的相关研究略作补充[3-7],进而对推动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和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贡献绵薄之力。
一 传承性与连续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自身表现出特有的传承性与延续性的特质,这一点自近代以来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梁漱溟认为,“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其与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他在这三四千年中,不但活着而已!中间且不断有文化的盛彩。”[8]这种文明的传承性与连续性以不间断的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李学勤认为,“对世界历史上各个远古文明的研究,都必须以考古成果为主要依据,例如对古埃及、对两河流域等,都是这样。中国的情况要不同一些,因为我们的历史脉络未曾中断,许多古代典籍得以传流,后世又有大量笺注,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宝库,足资研究。”[9]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认知我们民族过往的历史与文化,以后代史料佐证前代史事,对于古老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我们应该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远古的历史与文化在年代相对较晚的文献中得以记述和传承,主要依据之一是我们可以依托大量出土文献对年代相对较晚的传世文献中所见诸多发生年代较早历史的记述加以证实。近代以来,最负盛名并为人们所熟知的,当属王国维依托大量甲骨卜辞,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殷先公先王世系基本可靠。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讲道:“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近年来,随着更多出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的问世,带动了科技考古、古史史料学、古书年代学等多学科的长足发展,这一方面,使我们可以直接证明更多传世文献中古史记述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有坚固历史记忆传承作支撑的。随着各学科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我们可以依据现有的出土史料,通过科学分析,对于典籍文献中尚不能被直接证实的上古史事,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这其中不仅对殷商及殷商以降相关历史记述与传承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坚实的佐证,而且对后世文献典籍中所记述的夏代及夏代以前历史的研究也有所推进。
由于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成熟文字,是殷商的甲骨文与金文,因此夏代历史的有无问题一度成为中外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经过学界多年来的不断努力探索,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夏代历史的存在,并且对夏代的历史面貌与发展脉络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这归功于偃师二里头等遗址的发掘所呈现出的实物史料。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以一例来说明出土文献对夏史研究的重要贡献。通过甲骨文与金文的相互参证,以及对甲骨文与金文历史记述与书写性质的分析,学界已经认识到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出现了以笔墨和竹简为书写工具的文献。这类文献所使用的书写方式,明显比将文字契刻在甲骨上或者是铸造在青铜器上更为方便,这一采用相对简便书写方式的文献产生年代不会晚于甲骨文与金文。只不过由于历史年代太过久远,这一类文献没有实物保存至今[10-12]。这一点连一度质疑夏王朝存在的美国学者艾兰都是予以认可的。她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卜辞在刻上甲骨以前,先是以另一种形式记录的……这种记录可能是用毛笔和墨作出的”[13]。
我们有理由认为,典册文献中所记述与传承的历史与文化当比甲骨文与金文更为丰富,内容更为系统,流传也更为广远。因为发明文字的直接目的在于记述和传承思想、文化和知识经验,所谓“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14]采用笔墨与竹简作为书写方式很显然比在金石上篆刻更容易实现这一目的。甲骨文与金文,囿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能够书写的文献篇幅注定是相对有限的,一篇甲骨文长则不过几十字、上百字,短则寥寥十几个字;囿于神圣书写的目的限制,能够书写的内容是相对单一的。但将笔墨与竹简作为书写工具,首先可以用更长的篇幅记述更多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其次,突破了神圣性书写的限制,所记述的内容则可以包罗万象,将生产生活中的诸多知识与经验记述其中。再次,由于书写材料的相对廉价和容易获得,使得这一类文献流传更为广远。可见这种以笔墨和竹简为书写方式的典册文献,在记述与传承中华历史与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远远比甲骨文和金文重要。
既然我们通过甲骨文与金文等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了早在夏商时期,便有传承历史与文化功能更强的典册文献。我们便应该对于夏、商、周三代古人能够有效传承中华文明报以坚定的信心。在对目前已知先秦文献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而直观地感受到典册文献记述与传承中华文明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面貌。如学界已经认识到,《尚书》中《尧典》一篇忠实地传承了虞夏时期的历史文化记忆,“保留了尧舜时代的底色”,也在传承中留下了商周的文化印记[15-16];战国楚简《系年》中对于周代史事,尤其是两周之际的史事有相对准确的记述[17-20];楚简《厚父》一篇中记述和传承了上古时期便已经产生的民本思想[21-25]。楚简《尹诰》一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保存了商代史事,并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些后世史官对商汤君臣的美化[26-27]。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中则承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官人”之法[28]。另外,近年来,随着《五纪》《参不韦》等战国楚简被公布,我们对于蚩尤以及夏代历史可能还会有更新的认识[29-31],这有待学界作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由此可见,甲骨文、金文、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为论证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提供了坚实的证明,为回应近代以来对于中华历史,尤其是中华上古历史有无与真实性的质疑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历史与文化绝非古人在古籍文献中随意凭空臆造而来,当今所见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历经千百年来代代传承,仍较为忠实地记述和传承了灿烂悠久的中华历史与文化。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二 系统性与丰富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量典籍文献隐没于历史的尘埃。这使得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与丰富性不能有直观的认识。这一点在年代久远的先秦时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单凭流传至今的传世文献,我们很难对中国早期历史上文化的繁盛程度有充分的认识。距今数千年前的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究竟繁荣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从现存文献中知其一二。
如《左传》中记载楚灵王曾盛赞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32],如今所谓《三坟》《五典》只剩传世《尚书》中《尧典》一篇。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左传》的记载,楚灵王盛赞左史倚相学识渊博,大臣子革表示反对。子革直言,自己能记诵祭公所作《祈招》之诗,左史倚相是做不到的。可见阅读这些文献并不是当时的“冷门绝学”。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见《三坟》《五典》这一类的文献在当时的流传程度。再如《孟子》中记载:“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33]在《墨子》中也有“吾见百国《春秋》”这一说法。可见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均有史书,而如今只剩下鲁国《春秋》一部。因此,仅依托当今所见传世文献,我们很难对中国早期历史上文化繁盛的情形有准确的认知。
近年来大量不同类型出土文献的公布,为我们认识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效契机。纵观近年来陆续公布的大量出土文献,不仅内容庞杂丰富,而且知识体系相对系统,文献类型相对完备。无论诗、书、史传、诸子还是文书、方技数术类型的文献均层出不穷。这些文献大多不见于当今传世文献记载,是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补充。
具体来说,以“诗”类文献而论,司马迁曾感慨孔子删《诗》“十分去九”。关于孔子是否删《诗》,先秦“诗”类文献是否被删减了如此之大的数目,自汉代至今仍然有学者不断争论。近几十年来,在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中均发现了先秦逸诗。仅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一篇而言,这一组诗包含周公与成王各自创作的九首,总计十八首,简文完整记录了其中的九首。这十八首诗除一篇见于今本《诗经》之外,其余均为逸诗。有学者据此认为,“首次从正面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展示了文本范例。”[34-36]这一观点虽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37],但退而求其次,我们姑且不论孔子是否删《诗》,通过《周公之琴舞》这样一组逸诗的个案,我们应该认识到,先秦《诗》类文献流传至今,很有可能确实是“十去其九”,这一点当为学界之共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先秦时期“诗”类文献数量之众多、规模之繁盛。
以“书”类文献而论,清华简中出现了大量散佚的先秦“书”类文献。这些文献有的在传世文献中仅见篇目,有的甚至篇目无存。另外,部分周代的青铜铭文,从文献的类型上说,也足抵“书”之一篇,这对于先秦“书”类文献在数量上是极大的丰富。更让人振奋的是,清华简等出土文献对于“书”类文献的贡献,不仅仅是在数量上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与传世“书”类文献选本平行存在的不同选本[38-40]。对此程浩认为,传世“书”类文献更多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清华简的‘书’类文献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墨家的影响,可能与墨家选编‘书’类文献在楚国的传授有关。”[41]这对于我们认识“书”类文献传承与流变的多样性提供了翔实而充分的文献依据。
以诸子文献而论,在信阳长台关楚简、郭店竹书、上博简、清华简以及安大简中均有诸子文献问世。就目前已知战国简中诸子文献而言,不仅为我们呈现出诸多散佚不见于传世文献中的篇目,还为我们了解诸子文献的传承与流变、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派的分化与融合、百家争鸣的盛况等内容提供了新的契机。因篇幅有限,本文不对具体篇目展开分析,仅就学界共识性结论而言,大量诸子类出土文献已经向我们证明,汉代司马谈所言诸子阴阳、名、法、儒、墨、道等“六家”,或刘向、刘歆父子所划定的“九流十家”,抑或后世所言“道法家”“稷下学派”之类的学派划分方式,并不能展现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原貌。大量的出土文献向我们证明,战国诸子在激烈论战的过程中,思想已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以至于通过某一单篇文献本身的研究,很难对其作出学派归属判断。当今所见的诸子文献中,甚或还有不少是属于不见于《汉志》的学派分类[42-43]。战国百家争鸣的情形远比我们所认识的情形复杂和多样。
通过对不同类型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诗”“书”还是史传、文书、诸子、方技数术等类型的文献,在先秦时期均已经是汗牛充栋,这些不同类型的文献,承载着古人对名物制度、治政思想、道德观念、历史兴替等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系统而丰富的认识。众多出土文献的问世,让我们不仅直观地领略了中国早期历史上古人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创造出的丰富文化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献,对中国早期历史上文化知识的繁盛程度和系统性作出合理的分析。通过对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尽管目前所见甲骨文、金文与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已然是卷帙浩繁,让人叹为观止,但这只是穿越了数千年沧桑有幸保留下来的“冰山一角”。我们完全有自信认为尚有诸多我们不知道的文献类型和历史知识有待于进一步认知。在数千年前的古老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程度,只会比我们当今能够认识的情形更为系统和丰富。
三 统一性与多元性
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特质之一,便是共性与个性的兼具、统一性与多元性的共生。如果将这种精神特质放在比较文明学视域中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既保有自身凝聚力、向心力的统一性,又具备对不同文化宽容和接纳的多元性情形,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是较为罕见的[44]。这种统一性与多元性的特质,自中华文明起源时便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便是统一性文化特质的具体体现。通过当今所见出土文献,我们可以对中国早期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有一个更为直观和具体的认识,从而对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多元性的特质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关于中华文化“统一性”的特质,我们以齐侯镈钟与秦公簋的铭文记载加以说明。春秋时期的齐侯镈钟铭文记载:“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虩虩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齐国的叔夷祖上是宋国人,这段历史记述是其在追溯祖先的功业。这段记述暗含了两个重要的历史信息。首先,叔夷的祖先翦伐夏后成功,“咸有九州”并且“处禹之堵”。那么也就说明在叔夷的历史观念中,夏便有九州,而商接替夏也拥有九州。在古人的历史观念中,九州象征着“一统”。也就是说,在叔夷的历史观念中,夏、商均是“大一统”的王朝。其次,叔向这段历史记述的目的在于夸耀祖先的功业,那么如果所言祖先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本身社会认可度较低的话,就不可能达到夸耀祖先的目的。由此观之,夏、商均是大一统王朝是春秋时期共识性的历史文化知识。与之相仿,秦公簋中也有夸耀祖先功绩的记述。其铭文记载:“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也就是说秦国人自认为其居住在大禹曾经统治的区域,并且为夏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通过秦公簋铭文的记载,我们也可以捕捉到两条重要的信息:其一,秦国人追溯祖先功业时,着重强调对夏王朝的功勋,这说明夏王朝的正统地位是被当时全社会认可的;其二,按照清华简《系年》等史料加以分析,秦国先人在周初被成王迁徙而来,与齐国叔夷的祖先并非同一族群,不同族群均将夏王朝奉为正统,这可见夏为正统王朝,这也是当时社会的共识性历史文化知识。秦国君主与齐大夫叔夷来自不同的族群,却均追溯祖先史迹与大禹的关联,也证明大禹和夏王朝所具有统一性和向心力。
总之,齐侯镈钟与秦公簋的铭文以坚实的史料向我们证明了,在先秦时期,不同族群均将夏王朝奉为正统,并且社会普遍认同夏代便已经是大一统王朝了。
由此可见,大一统观念并非自秦以后才开始流行,自夏代以来,中央王朝便有强大的向心力。正如谢维扬所说,“对古代中原王朝(夏、商、周)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产生过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却是完全可以确定的,”至今可以完整地从周边人群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观察到某个古代国家制度存在与发展的事实的案例,应该只有中原王朝(夏、商、周)一例追求大地域控制是中原王朝国家在国土结构上的明确特征,而且在三代王朝的经营中是一贯的”[45-46]。此说甚是。在这种巨大的向心力吸引下,华夏各个族群“都可从华夏历史传说或历史著述中找到本族的衔接口”[47]。由此可见,自中华文明起源之初,便是在统一性中孕育的,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不同族群不断凝聚,使华夏民族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开始形成的过程。
另外,在夏代以前,远古的中华文明也是以统一性为特质的。关于夏代以前的文明形态,学界仍多有争论[48]。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夏代以前,中华文明便具有了向心力,并且在这种向心力的驱动下一步步发展繁荣。可以说统一性这一文化特质,是自中华文明孕育之初就伴随着中华文明的。
需要强调的是,中华文明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的同时,还展现出了罕见文化包容度与融合力。这种包容度与融合力,正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多元性特质的体现。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各族群的文化在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并非是彻底消亡,而是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下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吕思勉认为的,中华文化“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收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49]这一点在出土文献的古史记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郭店简《唐虞之道》对于上古史事记述:“尧舜之行,爱亲尊贤……六帝兴于古……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也。伯夷典礼,夔守乐,逊民教也。皋陶入用五刑。”[50]按照简文的古史记述,在尧、舜时期,中华文明已经是统一的,禹、益、后稷、伯夷等不同族群的祖先在“协和万邦”的尧、舜统治下济济一堂,共谋天下繁荣。这可以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与包容性兼具的直观呈现。再如上博简《子羔》中记述夏、商、周三代,来自不同族群的祖先,大禹、契、后稷皆是无父感天而生,这一历史记述本身就反映了周人、楚人等不同族群古史系统的融合,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的和合共生[51]。上博简《容成氏》的历史记述则将整个古史划分为有虞一代之前的远古帝王时期、尧、舜、禹统治的有虞一代以及夏、商、周三代三个历史时期,其中对于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记述与当今所见传世文献相差无几。而在第一个历史时期,简文追溯了以容成氏为代表的八位古帝,这被学界认为是将不同族群的先祖纳入了统一的历史记忆[52]。
另外,通过出土文献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自身的文化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来看,楚人的历史记忆中存在以伏羲为祖的古史系统,这一古史系统中包含炎帝、祝融、共工、俊帝等历史人物,在望山楚简、包山楚简、葛陵楚简中经常出现所谓的“三楚先”,即老童、祝融、鬻熊[53]。这些楚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有的已经不见于当今传世文献中的上古历史记述,有的则有机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54-55]。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将不同族群的文化简单地拼合,而是对其加以结构性的吸收与融合,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通过大量出土文献,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华文明的孕育之初,便对周边不同族群的文明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格局下,不同文化多元共生,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中华文明在孕育之初便具有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为今天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体系和政治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文化依据,让我们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道路上更加自信。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以出土文献为基本研究对象,对中华文明基本特质展开研究,解决了依托传世文献难以解决的部分学术问题,从出土文献的可靠性、多样性两个方面,更为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性与连续性、系统性与丰富性、统一性与多元性等基本特质。这必将为我们“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56]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让原本就坚定的文化自信更为坚定。对于出土文献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