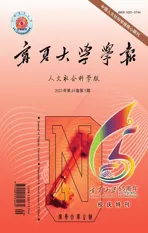能因能革:传统孝文化反思
2023-06-06张望玉
张望玉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传统文化,包罗万象,诸如哲学、宗教、法律、制度、风俗、文学、艺术、建筑、医药、天文、历法等,凡属于以往人类的文化创造与价值赋予,从有形的典籍器物,到无形的思想观念,都可归入“传统”范围。然而,“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在《什么是传统》中认为,“传统”是某一集团所代代相传的共同生活样式及观念,在时间上因为一脉相传的,所以有其统绪性;在空间上因为共同承认,所以有其统一性[1]。徐复观表示,“传统”具有民族性、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秩序性等五种特性,前三者是“传统”的构成因素,后二者是“传统”的存在形式。据此观之,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孝道经过长期传承与广泛实行,无疑成为中华民族在生活实践与社会秩序上的重要传统。历代统治者经常提倡“以孝治天下”,不仅以政治举措诸如礼制与法律的作用推进孝道的落实,还通过文化教育、历史编纂的途径宣扬孝道。如果考察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多部史书内题为《孝友传》《孝义传》《孝行传》或《孝感传》等列传部分,皆在表彰孝子孝行,诚然体现出传统社会对“孝”极为推崇。就“孝”的内涵而言,当代学者张祥龙曾经指出,孝指子女对年老父母乃至前辈亲人的照顾、尊重、怀念、继承,孝道则指对这种孝行的自觉化、深刻化和信仰化[2]。同样,在古代辞书如《尔雅》与《说文》中,“孝”通常被解释为“善事父母”。在传统语境中,这意味着子女对父母身体与情感的关怀,以至父母亡故后丧礼祭礼的实行。追本溯源,孝道思想源于先秦儒家的独到阐释。
一 源与流:先秦儒家独阐
先秦诸子争鸣时期,真正弘扬孝道的学派却仅有儒家,何以如此?我们可简要回顾。在墨家那里,虽然也期望“为人子必孝”(《墨子·兼爱下》),但由于提倡“兼爱”,难以区分自我父母与他人父母在面对利害时的次序,孟子为此批评墨子的思想为“无父”(《孟子·滕文公下》),批评夷之的思想为“二本”(《孟子·滕文公上》);再者,墨家提倡的“节葬”,也并没有得到儒家支持。在道家那里,老子在追求人性的某种原始或本然状态时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十八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道德经·十九章》),即使有质朴的孝慈理想,也并未过多讨论“孝”的实际建构,至于庄子,其所谓“至仁无亲”(《庄子·天运》),对于嵌入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亲子关系,似乎未能严肃考虑,只是追求某种豁达与自然。在法家那里,则认为“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商君书·画策》),怀疑“慈”对于“孝”的培养意义,仅认可法令治理;至于韩非说“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韩非子·难二》),即认为人心自私,否定孝亲情感的普遍意义,甚至说“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表示孝子在某些时刻必将违背统治者的意志。就法家而言,秦晖指出,法家为使皇权不受阻碍地延伸到臣民个人,在政策上“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在理论上“崇奉性恶论,黜亲情而尚权势”,在实践上“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3]。总之,与墨家、道家、法家相比,唯独儒家反复强调“孝”对于个人美德与社会秩序的意义。
第一,在根源上,先秦儒家将“孝”归根于人的本性,并强调孝道的实行有助于民众美德的培养与社会秩序的安定。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表示关爱父母是人之为人的良知良能。再者,荀子认为“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荀子·礼论》),即凡是具有血气与知觉的动物都具有对同类的感情,人是其中最为智慧者,因此对父母的爱也最为深沉。与此同时,先秦儒家积极肯定“孝”对于民众美德与社会秩序的意义,曾子提倡“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强调丧祭的实行能够促进民众品格的提升;有若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表示孝悌之人基本具有秩序意识。如所周知,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就“孝”与“仁”的关系而言,有若认为孝悌是仁德行为的起源,即孟子则直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并经常用“孝”与“悌”来分别解说“仁”与“义”,如“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事亲、亲亲即“孝”,从兄、敬长即“悌”,孟子以“孝”言“仁”、以“悌”言“义”,原因何在?对此,朱熹注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4]即“仁”的核心在于“爱”,关怀而不冷漠,“义”的核心在于“敬”,收敛而不放纵,在家庭生活中,爱父母与敬兄长即可体现仁义、培养美德,“事亲从兄”对于良心而言,最为真切、亲近、精深、朴实。
第二,在原则上,先秦儒家强调“孝”并非绝对或毫无原则地服从父母的命令,而是双向互动的美德。孔子主张“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周易》提倡“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表明儒家希望父子、兄弟、夫妇能够拥有各自应当拥有的美德,以维持家庭秩序。对于父子之间应有的美德,通常被表述为“父慈子孝”,如《大学》“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礼记·大学》),《左传》也有“六顺”之说,即“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再者,母子之间也应“母慈子孝”,《左传》中“五教”之说“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见先秦儒家的理想在于,亲子之间达成慈爱与孝敬的良性互动。至于父母犯错时,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倡无条件地服从或者无动于衷,而应委婉谏言,“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不能使父母陷于不义,甚至在荀子看来,“义”要高于父母的地位,即“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可作对比的是,在法家那里,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韩非子·忠孝》),强调维护统治者与父母的绝对权威,而具有片面性。
第三,在实践上,先秦儒家强调“孝”作为一种美德,要求在生活中善事父母,以及父母亡故后丧礼祭礼的实行。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对于父母而言,先秦儒家不仅强调物质性的供养,如“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与此同时,更注重情感上的诚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也表示“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既要有善良品格,又能真诚对待父母,使其愉悦。再者,先秦儒家对“孝”有扩展解释,而涵盖生活的诸多方面。在言说“不孝”时,曾子强调“居处不庄”“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即起居不端庄、侍君不忠心、为官不恭敬、交友不诚信、临阵不勇敢,五者“非孝也”(《礼记·祭义》),原因在于这些行为将引祸上身而连累父母;孟子也提及“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孟子·离娄下》),包括因为懒惰、赌博酗酒、贪财并偏心妻儿而不顾赡养父母,以及由于纵欲犯罪、蛮横斗殴给父母带来羞辱或危险。由此可见,“孝”即要求避免曾子、孟子所说的种种“不孝”。至于父母亡故后,“孝”主要表现在丧礼与祭礼的实行上,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并且要“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因此在父母逝世后,从哭丧到入殓、出殡、下葬,以及守丧、祭祀等,有详细的礼仪要求,而礼仪的核心在于哀、敬,即孔子所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正是由于礼仪的实践,使得孝子的情感得到更恰当、更深沉的表现。儒家之所以注重丧礼祭礼,一方面,在丧礼祭礼等集体活动中,礼仪是对共同体精神的一种培养与凝聚,也即是说,礼仪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互动,体现出“交融性”;另一方面,参与礼仪的人,由于与亡者的亲疏不同,礼仪规定因而不同,再者,由于不同身份的孝子诸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社会地位不同,因而在实行丧礼祭礼时,礼仪的规模、形式有所不同,体现出“差别性”,就“交融性”与“差别性”而言,两者实际上都丰富了孝道的内涵。
二 得与失:后世礼法实践
经过先秦儒家的阐释,孝道被视为人伦社会的应有之义,同时也得到后世统治者的推崇。对此,学界有观点认为,孝道成为文化传统,既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社会和国家的共同作用,这包括家庭、宗族、乡里的礼制约束,国家律法诏令的强制惩戒,以及通过树碑立传、悬匾建坊、封赏旌表等方式实现的正面引导,从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5]。就此而言,我们简要讨论礼制与法律两方面。
在礼制上,后世礼制规定孝道的多方面仪节行为。由于先秦儒家对“礼”的重视,后世儒家学者也经常注疏礼经、编制礼书而成为两千多年的学问,其中对于亲子关系的言说,即被纳入孝道当中,不合礼的行为将被视为不孝,面临道德上的负面评价甚至法律上的惩处。以《礼记》为例简要说明。一般认为,今通行《礼记》由西汉学者戴圣编纂,即《小戴礼记》,至于各篇的成书时间,则分散于先秦、秦汉时期。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小戴礼学入列,《礼记》作为《仪礼》的附属资料得到重视,至东汉时期《礼记》逐渐独立之后,地位日显,唐宋时期则长列官学,升格为“五经”以至“十三经”之一,对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礼记·祭统》载:“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赡养、丧葬、祭祀,作为孝道的基本要求,同时分别强调和顺、悲哀、诚敬的情感态度。在实际情形中,不仅父母亡故后通过丧礼祭礼行孝,父母在世时,《礼记》中关于父母的日常起居、子女的言行举止与家庭的财产经济等论说,同样涉及行孝。以《礼记·曲礼》为例,其中规定许多生活细节来阐发孝道,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即冬夏季节要关心父母是否温暖或清凉,每日傍晚为父母安置枕席、晨起向父母问候请安,在后世孝道实践中,“温凊定省”作为基本礼节长期履行;再如“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表示外出与归家都要通知父母,并且要交游稳定、术业正直;“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即父母在世时,不应许诺为朋友而死,不应私蓄财物;“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即规定父母生病时子女的言行举止,等等。然而,《礼记》中也有似乎并不完全恰当的规定,例如在向父母谏言时父母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内则》),再如因父母不悦而休妻所谓“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礼记·内则》),往往更强调“顺从”。
在法律上,后世法律影响孝道实践的合理与否。传统社会中,“不孝”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评价,更代表某些严重罪名,意味着刑罚惩治。以唐代法律为例,《唐律疏议·名例》表示严惩“十恶”,其七即为“不孝”:“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律条疏议“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6]。子孙若有此类控告、詈骂、诅求爱媚、另立户籍、分异财产、供养不周、违背丧礼等不孝行为,将面临绞刑、流刑或徒刑等罪刑。当然,法律在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也有顾及人情的内容,如《唐律疏议·斗讼》载:“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子孙若违犯祖父母或父母的教管,原则上将受徒刑两年,但也有限制条件,律条子注“谓可从而违,堪供而阙者。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律条疏议“若教令违法,行即有愆;家实贫窭,无由取给:如此之类,不合有罪。皆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7]。即因祖父母或父母的教管违法而子孙不从,或因子孙家贫而导致对祖父母或父母供养不周,则视为无罪,再者,即使子孙有不孝行为,但为保护家庭和睦,必须祖父母或父母告发后方可追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社会中法律也有另一面。从历史来看,尽管东汉至唐末约八百年间,以及宋代的法律中,父母杀死子孙将受罪刑,不过再往后,瞿同祖认为,元、明、清的法律较唐律宽容得多,父母并非绝对不得杀子孙,除了故杀并无违犯之子孙外,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被父母杀死,是可以免罪的。即使非理杀死也得无罪。再者,子孙不肖,法律除了承认父母的惩戒权可以由父母自行责罚外,法律还给予父母以送惩权,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执行[8]。由此可见,传统法律虽有促进孝道落实的作用,然而也存在维护父母权威的取向。
简言之,后世的礼制与法律在规定孝道实践时,也有不合理之处。徐复观曾经表示,传统社会的形态是“大一统的长期专制”,任何思想学说必然要受到专制利用,否则无法存在,即使被美化为天经地义的孝道也不能避免[9]。具体而言,先秦儒家并没有特别提倡“孝治”,只是重在培养美德,但是从汉代开始,“以孝治天下”被统治者大加提倡,“孝”被认为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为此,徐复观以《孝经》为例,详论其中被专制统治曲解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忽视先秦儒家对事亲与事君的区分,而将忠孝混同,从而助长君主专制。在徐复观看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论孝,往往归结到内心德性的要求,而《孝经》言孝,往往归结到权势、利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论政治,总是为了人民,《孝经》则为了统治者的祖宗[10]。实际上,自东汉开始统治者提倡“三纲”,其中“父为子纲”似乎逐渐远离先秦儒家提倡“父慈子孝”那种父子之间双向的美德关系。就“三纲”而言,尽管方朝晖辩护说,“三纲”的提出源于人们在行事中的作用具有主次、轻重之别,因此“三纲”在各尽名分基础上,更强调秩序、纪律,并非指向片面义务、绝对服从或人格上的不平等[11]。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传统政治框架中“纲”的一方往往易于自恃、专断。总的来说,后世礼制与法律对孝道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对此应有辨别意识。
三 因与革:当代传承发展
先秦儒家注重阐发孝道的美德指向,后世的礼制与法律实践在使孝道落实于民众生活的同时,也存在曲解的内容,主要是维护家长权威与专制统治。由此而来的不满,在新文化运动时,即有呼声认为孝道是只讲尊卑不讲平等,维护封建礼教、专制统治的工具,以使中国成为制造顺民的大工厂[12],甚至家庭也被批评为“万恶之原”[13]。然而,这种激进的态度,似乎忽视传统孝道的发展与变化可能。就传统而言,徐复观强调,传统是人类生存经验的综合、谐和,也是人类向前求生存的踏脚石。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常常是由它的传统加以征表。不过传统的本身是在不断地变化[14]。对于孝道来说,同样如此。那么从当代社会现实来看,又该如何审视孝道,并表达今日的态度呢?
事实上,由于人类历史的延续性,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心理等,仍然保留着历史的影响,这可说是“同一性”问题;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生活中的困惑时,人类也时常从传统中寻找答案或者思路,这可说是“有效性”问题。就“同一性”问题而言,传统孝道在当代仍然得到某种保留,主要体现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关爱,以及在对传统节日诸如春节、清明节的传承中,强化亲子之间的情感纽带。这些行为方式与心理趋向虽有生物性缘故,但是从先秦儒家对“孝”的阐释开始,经过后世思想与实践上的传承,已然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对于传统孝道的“有效性”问题,国家政策方面已然重视,例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将大力弘扬“孝老爱亲”作为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其目标是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15],再者,既称“优秀传统文化”,即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鉴别与审视,旨在探索有效性。
对于“同一性”与“有效性”问题,可参考西汉儒者扬雄的观点。扬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効也。”[16]即表示就理想的“道”而言,应当“能因能革”,“因”即传承,“革”即变革,传承在于保持内在价值,变革在于顺应时势,两者的协调统一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无论何种生存之“道”,扬雄“有因有循、有革有化”的观点,距今虽约两千年之久,其哲理依然深刻。从当代立场来审视孝道,也将面临“因”与“革”的问题。
先就“革”而言,孝道得以展开的当代社会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行为风俗的变化。对于传统社会中丧礼祭礼的诸多繁细规定,某些地区保留部分仪式之外,几乎仅有文化研究者在进行考察,其实历史上儒家学者也时有简化丧礼祭礼的想法。第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现代社会,理性、自由、平等、人格等观念已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法律已走出以家族、身份为本位,而走向以人为本、以权利为本位,因此传统孝道中维护家长权威或者说父权家长制成分则应革除。例如在清代学者编纂的《刑案汇览》中,大量案例表明,亲子之间产生冲突时,即使子女没有客观责任,然而为维护父母的伦理地位,往往对子女定罪用刑。而在当代司法实践中,这种观念已经被瓦解,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为家庭生活中亲子关系的和谐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因”即传承孝道的内在价值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对诚敬情感与仁爱美德的培养。从当代社会现实来看,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规模的缩小、个人私欲的膨胀等原因,引发亲子共处时间缩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下降、代际关系失衡等问题,似乎为孝行带来难题,对个人美德提出挑战。然而这些变化与挑战,并非取消孝道的理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17]子女在履行这项法定义务时,传统孝道实有助益。在儒家传统中,孟子主张“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曾子提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皆表示孝亲行为不仅要求物质供养,更重要的是情感态度与精神关怀。曾子强调,对于孝而言,赡养父母是基本要求,进而做到尊敬父母,再进而使父母感到安乐,最终在父母亡故后谨慎行事而不使父母蒙受坏名声,曾子称之为“能终矣”(《礼记·祭义》),即终身行孝。再者,儒家传统注重通过实行孝道,培养关怀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能力,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礼记》记载统治者与民众之间上行下效提倡孝悌,即“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礼记·祭义》),王夫之论曰:“孝弟之德统天下国家之治,而孝弟之实则爱敬是已。爱之推为贵老、慈幼以相亲睦,敬之推为贵德、贵贵、敬长以成顺治,皆立其本而教大备矣。”[18]即揭示孝悌的核心在于爱与敬,可发展为对他人的关怀与尊重,进而有助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教化。要言之,对于传统孝道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取向,诸如父慈子孝、母慈子孝,子女应当对父母保持诚敬之心并积极供养照顾,以及从孝道的实践中培养仁爱美德,进而促进社会的良好秩序,应当传承与发展。
总括而言,对于传统孝道,应借鉴扬雄所说“因”与“革”的统一,既不失孝道的原则与理想,同时又能避免曲解之弊,最终使孝道顺应时势、合乎时宜。徐复观曾经指出,文化是人所创造的,没有完全的人,当然也没有完全的文化[19],即文化观念往往适应历史情势而提出,同时也受历史条件所限制,当历史情势发生变化,文化的内容与效用也将发生变化。基于这种判断,徐复观强调,无论从观念或是实践而言,孝道在中国历史中影响深远,应当加以剖别,而不能简单以“拥护”或“打倒”二分法对待。相形之下,扬雄所提倡的“能因能革”不失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四 结语
学界观点多有表示,西方哲学并不注重家庭与孝道,张祥龙曾经指出,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没有家的历史[20],再有论者认为,西方的政界、宗教界和哲学界,均不以家为人类安全感、归宿感、归属感和幸福的首要来源。相反,家被附属、还原地认定为没有独立性而边界开放的“政治基层”“神意安排”“社会制度”或“个人契约”,诉诸人为的设计、干预、改造,乃至废除[21]。相形之下,在中国文化中,自先秦儒家不遗余力阐发孝道以后,经过后世礼制与法律的实践,家庭与孝道观念深刻影响着传统社会。然而由于传统社会的特殊形态,后世的礼法实践存在得失两面。在当代,基于行为风俗与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传统孝道则面临“因”与“革”的问题,以保持内在价值并适应时代要求。就此而言,对于当代孝道的理想状态来说,孝亲行为不应出于某种私人利益的交换,也不应出于某种外在规范的强制,而应出于子女内心的敬爱,使得父母生活安顿、精神愉悦;再者,当代孝道并不意味着片面的义务,而是儒家所追求的父母与子女各自美德的体现,因此也应考虑父母的要求是否符合道义,而非绝对服从,最终实现亲子之间的良性互动;至于当代孝道中丧礼祭礼的实行,仍以哀敬为旨归,礼仪形式则要适应当代文化。在所有孝道实践中,尤为重要的是培养子女的诚敬情感与仁爱美德,即从孝道中特殊性的情感,培养出普遍性的美德,正如徐复观所指出,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而最有社会生活实践意义的却是孝(包括悌),孝是出于人子对父母的爱,即是仁的根苗。孝的实践,即是对仁德初步的自觉、初步的实践,也即是对于仁德根苗的培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