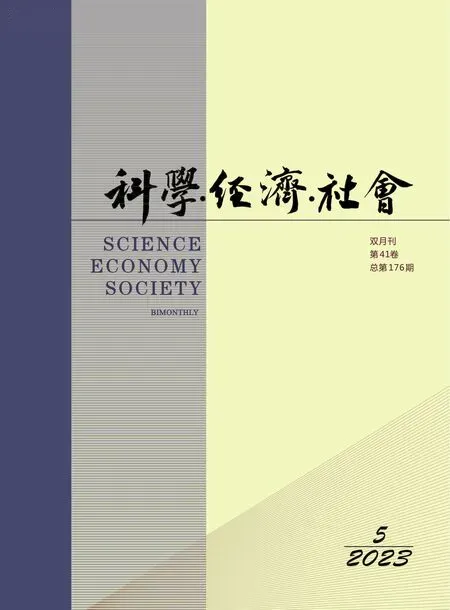伯纳德·威廉斯《论柯林伍德》小评
2023-06-05陈嘉映
陈嘉映
一
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对史学和哲学的目的和做法都有深入的思考:说到历史,柯林伍德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说到形而上学,他主张形而上学是关于绝对预设的学说。
他的论断常常能帮到我们,但读者也没有必要自限于此。历史没有定于一尊的目的和写法,这一点,单只想想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两部历史即可明了,然后再想想《春秋》和《太史公书》,接着再想想其他引人入胜的史书,例如《柳如是别传》那样的“心史”。历史写作如此,在我看来,哲学写作也是如此。
人们也许以为,诗歌、小说容许形形色色的写法,历史、哲学身为“学术”,似乎应该遵守更严格的程式。这个想法或有一定道理,但肯定不宜求之过严。古往今来我们奉之为大哲的写作即可作证。
这些不只是泛泛议论。伯纳德·威廉斯的《论柯林伍德》一文中提到,在柯林伍德眼里,那些注重可靠的分析性簿记的“小哲学家”所偏爱的写作,其目标似乎是想方设法防范读者有可能产生的误解,不断提供貌似周密无遗、表述精确的说明,牢牢控制读者的解读。柯林伍德面对的是一百年前的境况,今天呢?似乎变本加厉。哲学似乎只有唯一的写法,那就是,越像物理学论文越好;多像算合格呢?期刊编辑比写作者更有发言权。且不问哲学写作由此变得更有意义还是更无意义,单说防止误解这件事,似乎从未发生。
二
柯林伍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要理解行动者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必须理解他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他在回答问题时是怎么想的,例如,“凯撒是怎么想的,因此才跨过卢比孔河”。治史的要旨在于理解行动者如此作为时是怎么想的。史家有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确定凯撒是否、何时、如何跨过卢比孔河这些事实,但准备好这些事实,最终是要回答“凯撒为什么要跨过卢比孔河”。
“凯撒是怎么想的,因此才跨过卢比孔河”和“凯撒为什么要跨过卢比孔河”听起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但不同的表述有时含有不同的指向。“为什么凯撒要跨过卢比孔河”听上去是史家正常面对的问题,“凯撒是怎么想的”却让人犹豫——凯撒想些什么,这事似乎发生在凯撒心里,历史学家,或任何他人,怎么能知道凯撒心里的活动呢?这是所谓“他心问题”。
出于不尽相同的关切,哲学家、史学理论家、阐释学家,都会撞上他心疑难,他们也为解决这个疑难提出过各式各样的思路。威文里提到柯林伍德的主要想法:历史学家无法从外部确认凯撒的思想,他必须让凯撒的思想在自己心里重演,即亲身拥有与凯撒完全相同的思想①“在这种意义上,要了解‘某个人在思想(或者“已经思想”)什么',就包括自己要思想它。”。
只说到这里,恐怕难以释疑。单说一点:一个率领千军万马铁衣征战的统帅,他心里翻腾过些什么,当真能在一位皓首穷经的史学教授心里照原样翻腾一遍?
柯林伍德的表述——以及很多论者的表述②比如狄尔泰、海德格尔。——颇为误导,我的再表述误导得更远。“凯撒是怎么想的”不一定指凯撒心里翻腾过一些什么,实际上,几乎从来不指这个。一个囚徒挣扎着在一片锐器上磨捆绑他手脚的绳索,我们说,他想挣脱束缚,这个说法并不引导我们去关注在他心里翻腾着一些什么。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内部和外部,例如,看到囚犯的作为说囚犯想挣脱束缚,这算是“从外部来确认”他有何种思想抑或这已经包含了一些内部的东西。我想说的是,“行动者是怎么想的”未见得要被设想为行动者曾像学者那般明确严谨地对他人或哪怕对自己表述过这些想法。在这类场合说到凯撒想的是什么,主要指涉体现在凯撒行动中的思想,而不是声称凯撒当时当真曾用史家后来表述这些想法的方式想过一道。只说一点:史家通常要反复推敲,才能把行动者当时为什么这样去行动的想法严谨地形诸笔墨,而行动者当时若有这份推敲的功夫,他总是用来考虑应当怎样行动而不是用来反思他为什么要去这样行动。实际上,在其他多种场合,柯林伍德常常强调思想在行动之中得到表达。如果他坚持沿着这条主线来思考相关问题,也许就用不着发明“封装”这类颇可争议的概念了。
不消说,思想、行动、表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能用一个模式来概括。小偷行窃之际,不打算对任何人表达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完完全全体现在他的作为之中。游行示威也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的主旨就是表达。政府军公开处决游击队员,既是要事实上消灭这些人,也是在威胁未被消灭的游击队员和他们的同情者①杀鸡煮汤,既是要煮汤,也可能同时给猴看。。这些重重叠叠的分合,都是史家在探究“行动中的思想”时所要仔细分辨的。
三
上一段谈的是个广泛的问题:我们怎么了解他心。当然,只开了个头②关于他心,参见拙著《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第五章“闻知与他心”(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119-138页)。。而且,他心问题并不是一式的,临床医师、文本阐释者、史家,各自面对他心问题的不同侧面或不同重点。
什么是史学理解的特点呢?我们或许会认为,历史人物不同于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离开我们更远,所以更难了解,把他们带到我们身边于是成为一项更突出的成就,而这正是史家的本领所在。但这个想法不得要领③康熙的施政方针更容易理解还是我们同时代的某种当下的治国之道更容易理解?谁知道。。相比于了解和理解当代的俾格米人,苏东坡也许更易为我们了解和理解。
这个比较隐约现出史学和民族志的对戡。简单说来,民族志关注的是他者,而史学关注的则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过去;也不妨说,民族志关注的是作为对照面的他者,史学关注的是作为源头的我们④这一点今天不那么明显了,中国大学历史系也许可以考虑设立一个刚果史的专业。。威文对戡史学和民族志,不是沿着这条思路立论,但与这条思路互相发明。威廉斯的想法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在历史中,连续性和变化允许一种发展的、历时的理解,而纯然民族志的情形不给出这种理解。”其二,民族志学者可以由远及近、由外及内,渐渐深入到他研究的人群的所思所感,最后,他甚至可能大大改变自己,变得更像这些人那样去感知和行动——也许乐于如此也许只是潜移默化。简单说,最后他脱离了自己的社会,融入了他所研究的社会。历史学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他研究的社会已经消失,愿与不愿,他都无法融入其中。他是研究者而不是历史中人,这一点无法改变。
这两个提示都有助于我们探究历史理解的独特之处何在,在我看来,这两个提示,尤其是后一个,极富洞见。当然,到此为止,只是提示,其背后的丰富内容,还待我们逐步追索。
四
最后,再回过头来说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像克罗齐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类金句一样,其含义似乎一目了然,细论起来则人言人殊。我这里不揣简陋,也做一点儿新尝试。
首先我想提醒,这里的“思想”(thought)一词,所指甚为宽泛,也可以说成精神、心智、意义。实际上,在别的文本中,柯林伍德也经常使用这类不同语汇。前面已经说到,我们因此不可把“行动者的思想”视作明述的思想。
其次,上文多多少少已经提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并非意在否认历史包含好多维度,物质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然而,柯林伍德显然不赞成把历史界定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争夺史或诸如此类。从达尔文演化论问世那个时代起,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这在很多方面有益于人的自我理解,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带来了重大的混乱认知,其中颇为突出的一例就是混淆人类历史和生物演化。我即使不情愿也得承认,人经常禽兽不如,但仍然,人不同于禽兽。人类活动始终包含着对他为什么如此活动的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明确的还是含混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历史之为历史,历史之不同于生物演化,在我看,端系于此。也因此,我认为当柯林伍德坚持认为治史最终要回答的是“凯撒为什么要跨过卢比孔河”之类的问题,他把握着史学的真正宗旨。
在种种不同明确程度上,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做那,他正是出于这个“为什么”去做这做那。这也是人们通常所称,人依赖于意义生存:征服者的荣耀,上帝信仰,光宗耀祖,世界大同的理想。此处无法展开来阐论这一点,我举个也许有点儿怪异的事例。一群战士几个小时前生龙活虎,一面竭力杀敌,一面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生命,现在,被俘以后,他们排成一列,任由暴虐的敌人把他们驱赶到刑场,不做任何反抗。可以这么说吗——在俘虏行列里和在战场上一样,“生存本能”并未消失,变化的是生存的意义。若要套上“生存斗争”这个演化论用语,我会说,人的历史是为意义斗争的历史。我愿把这视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一个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