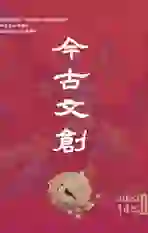论孔乙己在身份认同上的矛盾
2023-05-31严瑾
严瑾
【摘要】 孔乙己是鲁迅短篇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深受封建腐朽思想影响、深受封建科举制度迫害的迂腐麻木的悲剧人物形象。鲁迅借孔乙己的悲剧,为读者揭开了封建制度的面纱,将其血淋淋的“吃人”本质直露无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孔乙己的悲剧,无疑是出自封建制度的迫害;但同时,封建制度造成的孔乙己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矛盾,也是促使他走向毁灭的重要原因。就孔乙己在身份认同层面上的矛盾而言,可以分为“长衫客与短衣帮的矛盾”“朴学和理学的矛盾”以及“‘堂·吉诃德气与现实的矛盾”这三种。
【关键词】 《孔乙己》;身份认同;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4-003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10
一、长衫客与短衣帮的矛盾
在孔乙己的身份认同矛盾中,这一重矛盾是最基础的矛盾。在文中,鲁迅提到,“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1]”,这也就暗示了孔乙己那介于长衫客与短衣帮两个主要群体中间的尴尬地位。文中的“长衫客”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进店后“要酒要菜”,可见经济较为宽裕;而“短衣帮”以劳力谋生,连打个酒也要“唠唠叨叨缠夹不清”,可见其社会地位较低,经济也较为拮据。由于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并且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环境中,读书人的社会等级高,因此他在精神层面上自然地将自己划入“长衫客”的群体中去;而由于他“最终没有进学”,且“不会营生”“愈过愈穷”,经济水平和实际上的社会地位仍旧属于“短衣帮”的群体,心理上的身份认同和实际上的身份地位的差异构成了这一重矛盾。而不合时宜的心理期许同实际处境之间的矛盾,则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推动了孔乙己走向悲剧的结局。
(一)经济层面的矛盾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如柏蕴真老师所言,孔乙己是不可能没有能力以体力劳动谋生的[2]。鲁迅小说原文这样说道,孔乙己“身材很高大”,尽管“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但根据后文提示可知,这些伤痕是孔乙己偷书后被打的结果,不影响劳动,甚至如果孔乙己不去偷书,这些伤痕或许也不会存在。柏蕴真老师指出,孔乙己“哪怕已经穷到窃书的地步,也没有想过真正地自食其力[3]”,究其心理原因,这是由于在孔乙己的观念中,只有读书、当书生才是正道,被他视作旁门左道的其他谋生之路是对他读书人身份的侮辱。孔乙己曾以“君子固穷”为自己争辩,由此亦可见孔乙己心中有着浓厚的儒家君子情节,他既信奉着“不以穷困而改变读书人的操守”的道德标准,又以这个道德标准为自己惨淡的生活进行开脱,以至于“君子固穷”逐渐成了他那近乎偏执的心理安慰,他也在这扭曲了的心理安慰下对“自力更生”产生了排斥心理。
孔乙己自恃身为清高的“读书人”,蔑视身处社会底层的短衣帮群众,拒绝学习劳动和参与劳动,这就使得他不仅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也会被短衣帮排除在外、被迫接受来自他所看不起的阶级施加的精神压力。而孔乙己那微妙的自豪感,正是来源于封建社会背景下科举制对世人,尤其是读书人的洗脑,孔乙己已然接受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因而他无法使自己在继经济生活之后使自己的精神生活也沦落到与他所鄙夷的群体相当的水准。同时,这“孤高”的自守,也不能唤起在精神上与他同处一阶级的长衫客的同情与支持——毕竟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实际地成为科举制度下士子群体的一员。于是他飘零在两个主流群体之外,在遭遇经济层面的危机的同时,也迎来了丧失社会立足点的危机。
(二)社会层面的矛盾
其次,在社会层面上,如柏蕴真老师所言,“身无长物、没有立身之本的孔乙己,一贯以一种不屑置辩的清高态度对待短衣帮的酒客们,他无法融入民众之中[4]”,如前文所言,他在“长衫客”和“短衣帮”两个主流群体中都没有合适的立足点,并因自己性格上的扭曲遭到两个群体的耻笑,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双向的“看与被看”的关系。“短衣帮”在咸亨酒店中对孔乙己的议论,是表层上的看客心理,他们对孔乙己的遭遇感到有趣,却并不对他感到同情,甚至以他的悲剧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以欣赏孔乙己的惨剧为乐。孔乙己的看客心理则是深层上的看客心理,这来源于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的极端认同。尽管他生活拮据,但他仍宁肯多花一文钱进店买茴香豆,也要将自己与坐在店外的“短衣帮”拉开距离。这表现出他已然自觉地将自己排除在“短衣帮”之外,以审视和观赏的态度对待“短衣帮”。他对“短衣帮”的兴趣在于借他所拉开的身份距离进行自我欣赏,并以之麻痹自己,这具有很明显的回避和自我解脱的特征。不能否定的是,“短衣帮”的看客心理反应了旧时代底层人民的性格劣性,但同时也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孔乙己行为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孔乙己先划定了界限、声明了隔阂。总而言之,孔乙己对自己读书人身份的极端认同导致了他在社会生活中遭人排挤的状况。孔乙己的悲剧与他的这一重身份认同是分不开的。
二、朴学与理学的矛盾
朴学,是汉学中的古文经学派,是重视名物训诂及考据的学派,也谓清代学者继承汉代学风而进行训诂和考据的学派。梁结玲老师在《国粹运动中作为朴学学者形象的孔乙己》一文中指出,孔乙己的言行举止和治学“与清代朴学学者的治学门径完全吻合[5]”,这一观点在小说中并非无迹可寻。如孔乙己曾试图教授“我”的“回”字的四种写法,这一举动也就明显地反映出他对文字训诂的兴趣以及他的特长所在。梁结玲老师在文中也提到,“孔乙己的言谈无一涉及理学[6]”,他所时时念叨的“之乎者也”幾乎全部出自先秦儒家经典,而他偷书行为背后所反映的勤奋好学的品质,“与朴学重博学是一致的[7]”。因此,孔乙己可以说是一位十足十的朴学学者。
(一)与理学学者的矛盾
而孔乙己与“长衫客”——尤其是以与丁举人为代表的乡绅阶级的矛盾,正可谓是治学上的矛盾,也即朴学与理学之间的矛盾。在孔乙己身份认同的矛盾中,这重矛盾可谓是促使其走向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梁结玲老师在文中指出,由于丁举人信奉理学,因此他认为“有悖天理就可以被任意处置[8]”,而这与孔乙己的治学主张是有所区别的。从孔乙己从不欠账不还、“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以及尽管自己生活拮据也乐于分茴香豆等诸多细节可以看出,孔乙己是着有一定的诚信意识和仁爱思想的——这些思想与先秦儒家先贤所倡导的君子品行有着一定的相关性,而朴学学者又多重视先秦典籍,孔乙己或许正是受此影响而或无意或有意地构建起了他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尽管孔乙己“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所偷窃的多是“书籍纸张笔砚”,就算自己经济拮据也不曾偷窃财物,可见他也是有着一定的道德操守的。他的偷窃出于他对读书人身份的追求,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加强身份认同的过程。他的偷窃在他看来正是自己努力用功的读书人品格的表现,如同凿壁偷光一般,盡管手段并不十分道德,但其行为的内涵仍是值得称赞的。因此他将“偷书”美化为“窃书”,以“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来为自己辩解。在他看来,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就算行动上“有悖天理”也是可被原谅、值得称颂的美谈。然而他的这一观点不仅不像凿壁偷光的匡衡那般被世人所理解,甚至与丁举人等理学学者大相径庭。故而丁举人对孔乙己的偷书行为大加惩罚,以至于打断了孔乙己的腿,给予了他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上毁灭性的打击,最终与众人的非议一起直接促使了他的死亡。
(二)与科举制的矛盾
而治学上的矛盾也不仅仅表现于与理学学派的学者之间的矛盾,更表现在与科举制考试条件和选官条件之间的矛盾中。梁结玲老师在文中也指出,“清代的科举考试采用明制,以朱注四书为标准,考卷多程式化[9]”。而身为朴学学派学者的孔乙己,面对偏重于理学的科举考试制度时,他或许仍旧遵循了朴学的治学主张,也或许没能及时转向应试实用性的治学方式,故而“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常年失败的科举经历,使得孔乙己愈发以自己的在文字训诂及先秦儒教方面的才学为傲,以之作为维护自尊的最后的骄傲资本和使自己与他所鄙夷的“短衣帮”划分界限的精神慰藉。故而当被质问为什么连秀才也没考上时,孔乙己即使“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但也会立刻以“之乎者也之类”的话语来为自己开脱。朴学学派学者这重身份,实际上为孔乙己构筑了最后一层心理防线——一层他可以借之以为自己惨淡人生遭遇开脱的防线,一层可以让他沉迷于对自己“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幻想的防线。然而这防线终究是畸形的、虚伪的、不堪一击的。当丁举人打折了孔乙己的腿以后,他“却不十分分辨”,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他的朴学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他所向往的古代治学氛围已然终结。当他就算再度沉迷于训诂,而又很快清醒过来以眼神“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时,他的防线就已经被攻破了,他也已然清醒了。他认识到自己所长期依赖的学术理想和人生理想不能再为他遮羞,他那读书人甚至是学者的身份并不高高在上——他需要靠恳求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比被他长期蔑视的群体还不如。失去了心理防线的孔乙己,以赤裸裸的肉身暴露在“吃人”的社会环境下,最终因为无所依凭而走向了死亡。
“吃人”的封建社会及其已然僵化了的选官制度迫使社会底层的读书人构筑起这样的心理防线,而后又带着这终将破灭的心理防线一起,与社会底层的读书人走向他们共同的、不可抗拒的灭亡。
三、“堂·吉诃德气”与现实的矛盾
孟亮老师与许祖华老师在《孔乙己:丢了笔杆子的“堂吉诃德”》一文中指出,“堂吉诃德气”泛指“一切忽视现实的对于精神层面的迷狂[10]”,而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鲜明‘堂吉诃德气的人[11]”。
(一)历史与现实的矛盾
孔乙己身上的“堂·吉诃德气”,表现在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的高度迷恋,而这一迷恋在当时的社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属于“大环境下没落的封建科举和士大夫文化的致幻[12]”。孔乙己与堂·吉诃德同样沉迷于一个来自过去的美梦,堂·吉诃德沉迷于中世纪的骑士小说,并根据对小说中骑士的模仿,通过“行侠仗义”“游走天下”的方式,积极地实践和探索他的梦;而孔乙己沉迷于封建时代背景下士大夫及文人“出入庙堂”、为万民敬仰的梦,他认同并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而着迷,丝毫未能注意到外部环境的变迁,仍旧保持旧时代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以消极的心态固守他作为读书人的“清高”和“尊严”。堂·吉诃德的毁灭是内在精神世界的坍塌,而孔乙己的毁灭则是内外部双重压力作用的结果。于外,现实对孔乙己的迫害加剧了他的生存压力;于内,他苦苦维护的尊严终遭践踏的事实使他不得不认清状况——封建科举已然没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在当时的时代已然成为历史,终究无法实现。
(二)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而孔乙己的幻灭,也与他的人生理想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金家旺老师在《茴香豆:不可忽略的道具——〈孔乙己〉解读》一文中曾提到贯穿全文的茴香豆拥有着重要内涵——即茴香豆能使“孩子们围着他”,使他“自尊心得到满足[13]”;而分茴香豆的行为也不完全是为了满足孔乙己的自尊心,《孔乙己:丢了笔杆子的“堂吉诃德”》一文中,孟亮老师与许祖华老师认为,“‘一人一颗的公平态度,也可象征孔乙己对封建旧科举这一公平的‘黄金世界的寄托。[14]”除此之外,孔乙己“公平”的分法,也或多或少象征着他对先贤口中幸福的大同世界的期许。面对掌柜等成年人,孔乙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聊天”,这实际上暗示出孔乙己对成年人世界的失望。他“只好向孩子说话”、教“我”学写字以及分豆的行为,既是他对成年人世界的逃避,也饱含着他对年轻人的期许。一方面,他希望年轻人还有着对他人的善意,能够因他的行为及才学而给予他尊重;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视作他在大同世界中“幼有所长”的践行。尽管如此,他对大同世界的态度仍是混乱而复杂的。他在理想上认同大同世界,在现实中却因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无法达成“选贤与能”的社会状况而对这一理想产生绝望;他在思想上是愿意试图探索大同之道的,在现实中却因经济问题不肯再多分茴香豆。大同世界对他来说既是给他生存希望的人生理想,又是使他无数次陷入绝望的催命符;既是他乐于探求的理想世界,又是给他带来无力感的沉重包袱。
因此,茴香豆象征着孔乙己的三重人生理想——第一重是对个人自尊的高度渴望,第二重是对学术尊严的高度向往,第三重是对大同世界的高度期许。然而,这些理想到头来也只能是幻想。现实早已为孔乙己奏响丧钟,他赖以在社会立足的读书人身份已然衰落,他赖以保持自尊的朴学学者身份不受社会群体所认同,他赖以维持生命动力的大同世界理想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遥遥无期。他因此遭受到了来自社会现实和精神理想的双重打击,最终走向清醒,也最终失去了对其身份的认同感。当他被迫从“堂·吉诃德气”的幻梦中醒来时,迎接他的也只有落寞的悲剧结局。
孔乙己的悲剧,起于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偏差,终于他对身份认同感的消亡,这场落寞的悲剧由时代、群体和他自己共同造就。尽管孔乙己是一个值得批评的迂腐僵化的负面人物形象,但他的遭遇也令人惋惜,他的惨剧值得人们鉴戒。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0-273.
[2][3][4]柏蕴真.从个人困境到“科场鬼”悲剧——以《孔乙己》中“孔乙己”的一生为例[J].名作欣赏,2021,(02): 86-88.
[5][6][7][8][9]梁结玲.国粹运动中作为朴学学者形象的孔乙己[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 (01):21-27.
[10][11][12][14]孟亮,许祖华.孔乙己:丢了笔杆子的“堂吉诃德”——重读鲁迅小说《孔乙己》[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8(01):59-65.
[13]金家旺.“茴香豆”:不可忽略的道具——《孔乙己》解读[J].中学语文教学,2021,(02):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