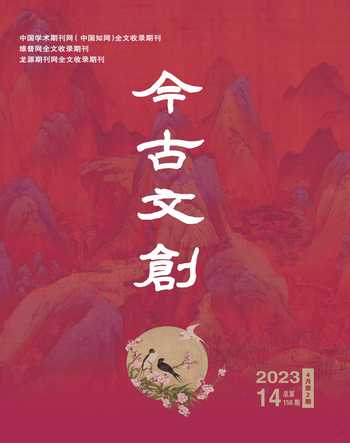虚构的存在之真
2023-05-31罗诗琳
罗诗琳
【摘要】 本文对《霸王别姬》小说和电影文本中程蝶衣“人戏不分”心理机制的分析,主要引用了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镜像阶段”理论探讨该心理机制的前两个阶段:小豆子最初形象的构成与性别认同转变的起点,以三界理论论述转变发生的动因和“人戏不分”的最终形态,呈现他从危机四伏的现实人生退缩到安全稳定的舞台世界的完整脉络,并最终得出性别乃至自我形象都是由文化和他者所共同建构的结论。
【关键词】 李碧华;《霸王别姬》;镜像理论;三界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4-0004-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01
昆曲剧目《孽海记》中,“思凡”唱段的名句“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在由陈凯歌执导、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霸王别姬》的华语电影中,被赋予了一重追寻主体意识的意义,成为一个书写自我认同焦虑的符号。
在谈及程蝶衣的自我认同过程时,人们往往遵循一种“同一即完整,混乱即破碎”的前提,认为“虞姬”肉体上的消亡达成了性别认同的一致,实现了一种涅槃式的解脱。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被人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完整自我,以及最终一定会回归的统一自我认同,其实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神话?或许所谓“真我”同样也只是担了虚名的空无。而在一众揭示个人存在之残破性与深层痛楚的理论中,拉康语境中的个人赝主体和大写的魔鬼他者①,无疑是一把最为冰冷残酷的手术刀,不仅令文本内人物对把握主體意识所做的一切努力变得毫无意义,也使得人们对“真我”存在之自信屡遭质疑。但本文并不旨在以其绝望的气质否定所有寻找自我形象认同的路径,而是通过对程蝶衣成长路径的梳理,试图在文本和理论本身之上,为如何处理个体与文化语境之间关系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一、“镜像阶段”理论:原初“我”被根本否定
尽管雅克·拉康②更多以“法国的弗洛伊德”这一称谓进入国人的视野,并且他本人也曾于1953年公开提出“回到弗洛伊德” ③,但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而言,这场回归被视作一次口是心非的“弑父”也毫不为过。
因为拉康最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下称“镜像理论”)的核心正在于一种无意识的自欺关系:所有人都在对“镜像” ④的指认中,无意间通过“我”对“镜像”的认同关系使得这个虚假的倒映成为主人。更进一步来说,正是因为人需要通过认同“镜中我”的形象才能获得同一性的体验,甚至这个关系式还可以被简化成“没有他者,自我就无法成立”,所以拉康对人之存在的根本否定就有了培植的土壤。由于他者对自我形象构建的影响无孔不入,人们对“真我”的追寻,在无法达到绝对真实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索“相对真实”的自我。
具体而言,“镜像阶段”是拉康于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指的是6—18个月大的婴儿在对自身镜像的首次认同中产生了自身机体完满性错觉的阶段。他借助了儿童心理学家瓦隆的镜像实验进行论证:人类婴儿和猩猩被同时置于镜前,二者对镜子中与自身所有可以看见的部分的行动完全同步的形象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猩猩对自己的镜像只会保持一瞬的兴趣,因为它很快就发现了镜子里自己形象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后注意力会被其他事物吸引;孩子则“会因此生发出一连串的运作,他要在玩耍中证明镜中的形象的种种运作与反映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周围物件的关系。” ⑥
二、起点:小豆子之“我”被二次否定
在前文所述实验中,需要注意到人类婴儿对自身镜像感兴趣的原因:这个形象让婴儿首次将自我从主客不分的混沌中统一了起来,获得了一种富有安全感的同一性体验,“安定了原始机能混乱” ⑦,从而能让婴儿习得如何“用新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身体”。⑧这一欲望正对应着小豆子在脱离母亲庇护后,逐渐对师哥小石头的关怀和“从一而终”的故事产生依赖的过程——因为二者都能给予他一种存在方式的确认,从而使他获得可以预期的安全感。
然而,喜滋滋的小豆子并不知道,就在这种看似成功的确认间,他已经无意识地杀死了那个破碎但相对真实的自己。这种想象式的总体性认同必然要付出代价,因为在文化人格和心理构建的过程中,“对于受空间同一性诱惑的主体来说,它(镜像)策动了从身体的残缺形象到我们称之为整体的矫式形式的种种幻想——一直达到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发展。” ⑨因此若只以程蝶衣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为转折点,梳理他将定义自己的权力让渡给他身边的“镜子”的线索,实际上仍然不够恰切。那个看似坚定地认同了男性身份的小豆子,本就是一个在文本之外的早期生活中遭层层阉割、放逐,甚至是无数次自我否定后的产物。因此本部分将借助拉康对“镜像阶段”的阐释,重新梳理和试图呈现程蝶衣心理机制形成的起点。
作为镜像理论概念重要依托的“镜子”,实际上是一种隐喻,并不单纯意指婴幼儿首次看清自身全貌的那面镜子。“镜子”同时指每个人在充分暴露于各自文化语境之前,他身边能根据他的言行给予他语言性和非语言性回应的父母、玩伴、师长等等,这些人都是他建构自我形象的参考。拉康将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所认同的自我形象称为“小他者”(other),但归根究底,这样的“自我”依旧来自他人的反射,甚至是投射。
因而在严格贯彻镜像理论的层面上,被学界投以较多关注且的确拥有多义性的第六指意象仍不能作为讨论的起点,毕竟小豆子蒙受“阉割”之痛时已经9岁。他甫一登场时秀气且倔强的形象对于观众或读者而言的确是初次见面,但对于人物本身而言,要成就这一形象并非蹈空而至,而是依靠过去9年中小他者和大他者的反复书写。尽管依拉康所言,原初“我”被篡位的始末微不可察,但李碧华通过妓女艳红的独白,呈现出了小豆子进入喜福成前的生活状态,从中能复盘出小豆子选择原始形象时有过的参照之镜。
文本中并未给出小豆子生身父亲缺席的原因,但从“想起一个妇道人家,有闲帮闲,否则,趴在药铺里搓蜡丸儿、做避瘟散,或是洗衣服臭袜子……”“但凡有三寸宽的活路,她也不会当上暗门子” ⑩可以一窥父亲的不在场对叙事的影响:小豆子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正因为缺乏另外的经济支柱,母亲才被迫沦落风尘。欢场的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出于“为之计深远”的考量,母亲最终决定将小豆子卖入戏班挣前程。
而在叙事之上,根据拉康对父性大他者的定义,父亲的不在场还能被视作一种主体边界界划失败的象征,这使得小豆子一生受困于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中。尽管他已经从早期生活中的小他者处获得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形象,但由于无法形成灵活且稳固的自我边界,在这种不分彼此的依赖中,镜像则成了又一个与小豆子残破主体水乳交融的母体。因此,他只能耗费一生向外部那个通过语言符号来确定的世界,求索另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也正是未来他将对自身镜像的畸恋,投射到段小楼身上的根本原因。
要理解父性大他者,首先要明确母性大他者的概念。拉康在解释大他者(Other) ?时,做了一个文字游戏:“母亲(mother)就是大他者(Other)”,这里“母亲”同样是一种隐喻,可以代表一切具备将婴儿的无意义哭喊带入到语言秩序中的功能 ?的人与事物。当然在文本中,这个母性大他者的确可以被指认为小豆子实质上的母亲,她必然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同时在小他者和母性大他者的位置上出席:对小豆子的言行做出回应,半遮半掩地保护着小豆子免于在文化环境中过曝,却又不得不引领他踏入律令在世的场所。因此小豆子在文本最初呈现的形象中,早已有一种既无法退居回前语言期的世界,也无法被社会规则所容纳的异乡人气质,为他将来痴迷“前朝丽影”以及被男人当作女人、被女人指认为男人的尴尬处境埋下伏笔。
在婴儿与“母亲”达成上述关系后,父性大他者就会来阻挠。婴儿逐渐会发现,“母亲”的背后还有“父亲”,并且“父亲”比“母亲”更厉害,所以他理论上应该转而认同“父亲”。但在文本中,小豆子望向母亲接待的嫖客时,那双“寒碜得能杀人的眼睛”,实际上是“弑父”仪式的一环——他试图通过对抗的形式拒绝那个能定义“母亲”的“父亲”,从而延缓他进入父性大他者所面向的象征界 ?的时刻。在那一瞬间,因为小豆子事先对“母亲”的占有,二者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分彼此的状态,所以他与自己的母亲共同陷入了一种即将被父性大他者吞没的焦虑与恐惧中。小豆子在对抗的,包含了父性大他者的其中一个面相:秩序与律令的尺度,即一条能帮助他纠偏自身定位的准绳。
尽管父性大他者与创伤性的体验形影相随,但至少在上述这一重面相的意义上,“父他”仍有帮助人建构稳定且拥有灵活尺度之自我边界的功能,因而小豆子的“弑父”必然会付出代价。这种选择的后果在电影中被诠释得更为明显:到喜福成的第一夜,面对其他师兄试图以小豆子母亲的妓女身份而对他进行社会区隔时,他选择以焚烧母亲留给他的大衣表达了无声的拒绝,同时也通过此举杀死了附丽在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母亲”,由此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功能缺失的类边界。但因为这层僵硬的边界无法进行自我调节,往往使小豆子陷入矫枉过正的境地——不是彻底拒绝,就是让渡自我。
他渴望能拥有归属,但又无时无刻不处在自我消融于他者的恐惧中。在他的眼里,尽管他已经通过烧掉对母亲最后的念想来投诚,但因为清秀的女相、对情感更高的需求以及对生命形态更敏锐的体悟仍与喜福成格格不入,于是充斥着其他目光与多种关系的现实世界逐渐被他判定为危机四伏、不值一过的场域,这才为他将来选择舞台上那份可以预期的安全感提供了可能性。而师哥小石头对他的关心、肯定和认同,让他映照出了又一个完整的镜像,拯救他于存在之残破的水火之中,于是小豆子才能毫不设防地模糊自己的邊界,与师哥共享那个稳定安全的舞台,向他投射“从一而终”的期待。
三、动因:第六指被“阉割”导致畸变
上一部分中,通过复盘小豆子早期生活中所有可能的“镜子”,追溯了程蝶衣进入所谓“雌雄莫辨”“人戏不分”境界的心理原点,并在指认出小豆子的小他者、母性大他者和父性大他者后,初步梳理出了程蝶衣形成如是心理机制的流程,但并未对具体转变过程进行论述。在这一部分中,将通过分析小豆子“第六指”的多重意涵,试图呈现出这一文本空间内最具象征意味的分水岭,是如何对程蝶衣的人格塑造和心理建构造成影响的。
第六指意象,以其“畸形”“妖异”等意涵,以及电影改编中的优秀呈现,成为程蝶衣形象分析中绕不开的课题。过去学界对小豆子的第六指意象研究,多集中在“断指”是对小豆子心理性别的第一次“阉割”的解读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艳红挥刀剁断小豆子的第六指,与男性在生理意义上的“去势”过程,在形式上达成了高度重合。同时,这与之后关师父(小石头) ?用烟袋不断在小豆子嘴内抽插,致使“鲜血从嘴角渗出,巧妙地把一幅处女破瓜图搬上了大银幕” ?,有艺术表达上的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借助拉康的理论,发掘出了除此之外的另一层喻义。
六指之存,无疑起到赋魅作用,而六指之去,不难联想到“断尾”母题。“断尾”是古代神话思维中“变形”观念的表现,源于先民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动物形态变化,如蛇蜕皮增岁、鹿脱角隐居、壁虎舍尾自救等。这些现象存在一个共同规律:一物变为另一物需要经历抛弃或改变身体的某个部位的过程。在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加工下,这一规律更多被呈现为生命形态的完全过渡或彻底变迁,乃至旧生命死亡和新生命诞生。至此,文本中“剁开骨血。剁开一条生死之路……” ?中有关“生门”与“死门”的隐喻呼之欲出。
因此,对“生门”和“死门”意涵的解读正是开启小豆子第一次过渡的钥匙。但有关“生门”与“死门”的具体内涵,则在艳红与小豆子二人的视角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相。
(一)艳红视角:断尾求生
在文本叙事的意义上,喜福成代表的是艳红眼里那个能让小豆子挣得前程的好去处,是使他能远离风尘习气、“自己成全自己”的一道生门。而小豆子的那只让他“当个凡俗人的福分也没有” ?的第六指却是他从死门跨入生门的最后一道障碍,母亲为儿计深远的苦心,驱动她斩断了这一阻碍,同时也齐根切断了她和小豆子之间的关系。从后面的文本中,不难得知自此以后母子再未相见。尽管程蝶衣有过托人写信又焚毁的行为,戒毒时梦里醒时不忘的也是“娘”,但他更多寄托的是一种对“母亲”概念的爱而不得,一种对回到与母性大他者之间骨肉相连关系的渴望,与他依恋的“前朝丽影”和舞台上的段小楼,实际上拥有同源的心理机制。
但在艳红的视角中,这段被抛弃的关系仍有耐人寻味的部分。第六指长在小豆子身上,就是他的一处病根,是绑缚他游向生门的脚镣。如果将生死门之间的阻碍这一要素提取出来,那么对于艳红来说,小豆子本身又何尝不是她的“第六指”——养大的男孩不便出入欢场,甚至说无须履行母职的情况下,她本就不必当上暗门子。尽管在民国初年的社会环境中,风月场所的女子从良后再融入主流社会依旧艰难,但至少根据艳红的价值序列,只要能脱离欢场,于她而言无异于撞开生门。
但在改善物质条件和实现社会价值的目的之外,由艳红主动切断关系,还意味着母性大他者自主同占有其的婴儿进行解绑,使得小豆子从主客不分的混沌子宫中,重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了一个从因尚在母体内部而无法被定义的对象到能被触摸其形的完整形象的过程,实现了从死门到生门的跨越。
(二)小豆子视角:再入狼穴
在拉康看来,婴幼儿初次面对世界时必须要面对一种破裂,即一个从感性行为和心理结构上建构主体和客体的艰难过程。由此可见,小豆子的重新“出生”,看似是一个崭新且充满希望的开始,但他“呱呱坠地”后,不会再有另外一位母性大他者,像他第一次物理意义上出生后,引导他去理解自身的体验、情绪,或确认一切难以名状的感受在文化语境的系统中是否有意义,是否被允许存在。因此他在举目四朓皆为荒芜的经验中,为了让再一次变得残破的主体拥有可供依靠的母怀,他选择了活在舞台世界,那套完全不会背叛自己且自洽的符号系统中。那么以小豆子的二次“出生”——被斩断六指后送入喜福成为界,打碎从前由小他者、母性大他者和父性大他者建构出的小豆子形象的母亲,无疑是将他送进了一道“死门”。
本就缺乏界划边界功能的小豆子在“死门”中的求生方式,只剩下回到那个虽需要让渡自我却绝对安全的母体当中去。那么小豆子所选择退居的舞台世界,即他的想象界,究竟为何能为他重新塑造出一个母怀?这就要对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厘清:想象界内,镜像与以此为参照而想象出的“自我”,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因为婴儿在惊喜于完整的“镜中我”形象之时,也会在想象中展开对这个与自己相似对象的抹杀,以期获得本体的唯一主导权。而此时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转移,则是通过使大他者成为一个第三方仲裁人的方式,打破原本镜像与“自我”之间时爱时恨的关系,将新的矛盾转移到社会关系上,从而起到调节的作用。但很显然,在文本中无论是幼时的小豆子,还是成年后的程蝶衣,始终在拒绝象征界中大他者的介入,尽管在“霸王别姬”故事的重复讲述下,象征界的规则依旧能通过转译的方式在他身上打上烙印,譬如“从一而终”的权力关系、“揭发姹紫嫣红,断井颓垣”时直面半梦半醒状态的痛苦。因此要理解小豆子的转变,还需从想象界对象征界的补全作用出发。
从最抽象的层面来理解,象征界即为文化本身。人类的文化看似合理,但无论是成文的规则还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经过不懈推敲其实都会发现漏洞,因此拉康认为“如果象征界是完满的,我们不会增加任何东西。”但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文化当中,面对各自文化中的漏洞,想象界就起到了缝合象征界中无法自洽部分的作用。在文本中,程蝶衣对舞台世界的“从一而终”补全了他被强行指认成“女娇娥”形象时的恐惧和无措,这是因为文化难以向他解释人要身受荒诞未知命运的原因,于是只能通过想象来假定“可以预期的安全感”必然存在的“事实”,使生活还值得一过。同时,他还触及另一个文化里的症结,例如因委身于袁四爷而被称作“像姑” ?,反映出的是男妓定位的尴尬,更是权力倾轧下身份异化的突出表征。程蝶衣面对被当作“亚女人”的风险,选择沉浸在为取霸王之剑可付出一切代价的想象当中来实现自我麻痹。在类似经验的不断堆叠下,程蝶衣逐渐开始以“霸王别姬”和各式各样的“前朝丽影”为千疮百孔的象征界打上一个个补丁,暂时抵御了语言对他想象界的毁灭性进攻。
四、最终形态:人戏不分
在前两个部分中,已论述过程蝶衣“人戏不分”状态的心理原点、转折路径,分别对应了程蝶衣从想象界不完全地转移入象征界和从象征界重新退居回想象界的两个过程。但它们离最终形态仍有一段距离,也不足以解释“舞台”为何是他在漫长坚持下选择的最优项。在拉康语境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一个重要的概念:对象a。它在文本中的具象,就是那方让程蝶衣痴迷半生的舞台。理解对象a,则需要先厘清实在界的概念。
实在界,是相对于象征界而言的那个不可名状的世界,它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在看似严密的能指链之间,必然会产生无法被语言定义的“剩余物”,这就是对象a,也被稱为实在界和象征界间遗落的碎片。
实在界“不可名状”的状态,意味着一片人身处其间就无法被指认,更无法被赋予意义的混沌,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死亡”。对于程蝶衣来说,“死亡”不仅仅指肉体上的消亡,更是一种所有存在痕迹被湮没后的虚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连接此岸与彼岸桥梁的对象a,即文本中的鸦片和同样有成瘾性的舞台,就是一种能让程蝶衣在存活状态下体验到的一种“小死”,它游走于存在与虚无之间的边缘,带来死亡焦虑的同时,也伴随着人在非理性过程中所能获得的快感。它在文本中表现为鸦片,反映出程蝶衣企图以惩罚自己的方式来找回对身体和“自我”的掌控感,因为他将面对一个京剧前途未卜,同时既有定义自我的方式能否存续仍尚不明朗的新时期。
上述快感,也正是拉康所说的“原乐”(pleasure within pain),即苦中之乐——诠释了舞台世界的两个面相,“苦”(难以名状的焦虑)和“乐”(欲望),对应了程蝶衣对暴露于现实社会后被杀死的恐惧,以及对光影世界中同一完满错觉的痴迷。从鸦片到同样有成瘾性的舞台世界,尤其是后者,总能引起精神共鸣,把他带入一个不在世的空间中去,当共鸣在剧场营造的气氛中不断流转,变大,有节奏地传递、交流的时候,悲与喜,爱与恨都仿佛到了一种特殊的境地?。二者都是以一种使得程蝶衣与秩序实现隔离的形式,让他暂时从大他者的围剿中得以喘息,让他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之间的不毛之地” ?,寻找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尽管进行自我区隔会让他变得面目模糊,使得“男人把他当作女人,女人把他当作男人” ?,但足以让他趋之若鹜。
在舞台上,程蝶衣进入了虞姬,以及形形色色的“前朝丽影”,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被定义的方式,一种在长期的文化书写下被固定的爱与美的神话。垓下自刎明志的虞姬,“宛转蛾眉马前死”的杨贵妃,她们不断被强调的惊人美貌与状似全部意义所在的爱情故事,也同样成为程蝶衣赖以生存的方式——尽管我让渡了自我,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目光能让我重新凝聚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因此那个看似让他卑微无耻、始终被动的“霸王”段小楼,反而是他的提线木偶,是一面强行留在身边的镜子。就像霸王定义虞姬一样,他要不断通过确定段小楼的位置来确定自我。程蝶衣所臻之爱注定在舞台世界外无根,因为他其实并不关心爱的内容物,甚至不在乎爱的对象,只是执着于那道能固定他的目光。正如他对着“四大美人的镜屏”自照,也仍觉“美人抢了视线” ?,才会钉死墙上那些能证明他过往存在的照片,还要“封得严严,谁也别想逃出生天”。
程蝶衣与舞台世界的关系,还在文本固有的戏中戏结构之外,呈现出一层嵌套得更为精细的结构。对象a本应该是连接象征界与实在界的桥梁,但对于程蝶衣而言,语言秩序就是接近被消解之恐惧的实在界,而在他幻想中永远安全稳定的舞台,则作为真实象征界的一角却被指认为他的全部象征界。那么在这层更小的结构中,能被指认为现实世界与舞台之间的对象a的,实际上就是那些“半梦半醒”的瞬间,同时承载了苦与乐的两重面相——戒毒时打碎所有镜子和框住“前朝丽影”的镜屏,戒毒成功的劫后余生,在被迫与段小楼互相揭发时绝望喊出的“我要揭发姹紫嫣红,断井颓垣”……
程蝶衣在自己的舞台上操纵着木偶,他描摹着“霸王别姬”的故事,书写自己的一生。登上戏台前的小豆子有在纸面上无法传达出的痛苦,文本之上的人们在求索那个相对真实的自我。如果还要不断追问,文本内还能容纳无限小的结构,文本外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世界。程蝶衣自认为能把握到的一点真实,也不过是能指链上微不足道的一环,经由无数他者的目光才沉淀出被他理解时的形态,毕竟本文的“自我”,始终建立在“没有他者,自我就无法成立”的关系式上。而文本之上的人们也不外如是,那个值得穷尽一生去求索的“自我”究竟是确有其名,还是一个代际传承的巨大谎言?
五、结语
在拉康看来,人就像碎片一样被抛却到这个世界上,但他关于原初“我”实则是徒有其名的论调,无疑否定了所有黏合自身、走向有序的努力。尽管他的理论拥有如此规整明确的结构,但某种程度上就和穷尽一生求索真理的人说出“人生就是毫无意义”一样缺乏说服力,因为求索的过程本身就构成了意义。
或许比起“自我”陷阱,人们更容易陷入“意义”陷阱中:最终的结果必须要“言之有物”,才算是不虚度年华。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意义”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其结果是否值得人们“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是它永远有一种吸引人们去证实与证伪的魔力?尽管用拉康的术语来说,这个意义就是典型的“深层大他者”,在最终能推导出象征界的空虚。
同样是面对不存在意义的符号本身,拉康由此推导出整个象征界,即文化本身的空虚,而文化塑造大他者,大他者参与建构所有个体,因而“自我”同样不存在意义,最终会遁入虚无。但在关注此世的精神传统影响下,这也同样能被诠释为:既然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生活在文化当中,那么本就不会有人能绝对忠实地保留原初自我的每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所有迈出的脚步都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主选择。因为只有当文化进入到个体后,律法才能开始实现,而与文化的不同关系,成就了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因此,程蝶衣与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呈现出了这样的关系,他的漫长坚持就是对拼凑出完整自我的尝试,而他选择自己碎片的过程,也在不断地为自己赋予意义。
他在生死门面前选择继续与能给予他同一性体验的镜像不分彼此地共存,但能落地行走的关系却往往始于分离——子宫内的胎儿在离开母体前无法与母亲之间建立伦理和情感层面上的关系,无法分清客我关系的婴儿自然也映照不出自己的形象。关系的实质是两个自觉个体间的同频共振,只有两个个体在关系中相互映照,才能更为完整地认知自我的形象。
注释:
①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页。
②雅克·拉康(1901—1981),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主要成就有以儿童心理学家瓦隆的镜像实验为依托、改造自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镜像阶段”理论,以及其晚期思想的集大成者三界理论。
③20世纪50年代,法国精神分析学界正处于危机状态,原有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力减退,各种潜在的发展方向初露头角。
④自我的最初完整形象。
⑤⑥⑦⑨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9页,第90页,第112页,第94页。
⑧里德:《拉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⑩????李碧华:《霸王别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第15页,第15页,第124页,第125页。
?深层的大他者在拉康的术语中,是“理应知道的主体”,即律法实现的场所内,被认为是理所应当掌握“真理”的对象,它的存在形式多样,形象、概念、规则、规律,不一而足。
?“母亲”会尝试解释、分析这些哭声,使得婴儿在多次互动中逐渐能理解自己的哭声可以带有意义。
?“象征界”(the symbolic),若要从最抽象的层面去理解,即为文化本身,一处人造的规则得以运行的场所;而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即为符号。
?李碧华原著中,完成这一动作的是关师父,而在陈凯歌的电影中,动作主体则为小石头。
?林勇:《“文革”后时代中国电影与全球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明清时期对男妓的称呼,即“男子像姑娘一样”,另说为“相公”的谐音。
?崔久成:《剧场中的创造与感知 从〈暗恋桃花源〉〈宝岛一村〉谈赖声川的剧场艺术》,《剧作家》2011年第5期,第98-100页。
?福柯:《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拉康.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0- 112.
[2]张一兵.不可能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
[3]李碧华.霸王别姬[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5-125.
[4]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2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