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与卫所之间
2023-05-31张万东
张万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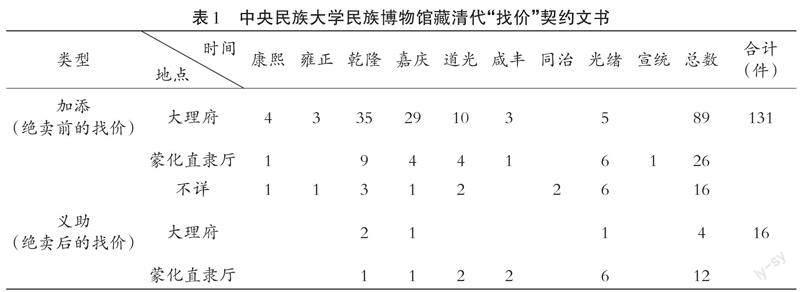
摘 要:秦良玉父亲秦葵的身份当为卫所武官,而非道光《忠州直隶州志》中所载“贡生”。秦良玉一身武艺与军事才干正是来自家庭的自然熏习而非秦葵的刻意培养。据现有史料可知,秦氏一家很可能出自忠州守御千户所。虽然石砫土司与忠州守御千户所分属两大制度体系,但在明代双方很可能存在私下的田土交易,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构成了秦良玉与马千乘婚姻的基础。作为秦氏家族的后人,廪膳生秦肇益利用修撰地方志之机,以“去军户化” “去蛮夷化”为目的,重构秦良玉的家庭出身,从而完成历史记忆中秦氏家族由“武”向“文”的转向。
关键词:秦良玉;卫所;土司;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3 - 0095 - 09
传统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也难以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西南土司区,女性却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土司上层,女性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少土官的妻子协助丈夫处理司内各事务,在土司内部拥有较大权威。夫死子幼时,她们还可以承袭丈夫的官职,成为受朝廷认可的土官。据廖丽研究,在西南土司中多有女性袭职土官的事例,袭职的比例在7%—25%不等1。可以说,女性土司是土司群体中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众多的女性土司之中,又以明末石砫土司的秦良玉最为著名。秦良玉曾协助丈夫马千乘奉调入播平叛,立下大功。马千乘去世之后,秦良玉代领宣抚使一职,率石砫土兵援辽、平奢、勤王,屡立战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得到崇祯帝题诗夸赞,成为名震当世的女将、忠君爱国的楷模。纵观既有研究,学者多聚焦于秦良玉的战功2。然而对其家庭出身这一问题却鲜有专文讨论。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往往与其家庭背景、早年的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正如布尔迪厄所言,人最初的文化资本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早期教育,语言、仪态、技巧、气质等具体化的文化资本通过继承性传递灌输给后代,并转化成“生存的样态”1或习性的外部财富2。秦良玉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女性的代表,究竟出自怎样的家庭?她为何嫁给石砫土司土官马千乘?关于秦良玉的出身,史料中有着怎样的历史书写?今不揣浅陋,拟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不过因学力和史料所限,文中不少环节尚止于推测,恳请方家赐正。
一、女土官与将家女
关于秦良玉的生平事迹的记载,最重要的文献莫过于《明史·秦良玉传》。该传文开篇记载:“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抚使马千乘。”3此处只交代了其籍贯,并未言及她的家庭出身。又据乾隆《石砫厅志》记载:“良玉,忠州人,秦葵女,字贞素,性颖异,饶胆略。幼通经史,工词翰。且与兄邦屏、弟民屏同习骑射,究心韬略。”4这段文字虽点出了秦良玉父亲的姓名及早年学习经历,但是对其家庭背景,特别是其父秦葵的身份仍未加说明,而这恰恰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根据《明史·秦良玉传》《石砫厅志》的提示,笔者又查阅了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发现了更为详尽的信息。
秦葵,字载阳,贡生,石砫土司秦良玉之父。好读书,不汲汲于荣名,尤长于兵法。尝谓其二子曰:天下将有事矣,尔曹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方称为吾子也。后良玉以一妇人晋职太保,子邦屏、民屏、孙拱明、翼明皆以武功著名,皆葵庭训有以致之,自号为鸣玉逸老5。
由上可知,秦葵为忠州贡生。与其他贡生多专注举业,希望科场扬名不同,秦葵志趣在于博览群书,且对兵法极感兴趣,并有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秦葵还预判出“天下将有事”,因此要求秦氏兄妹勤练武艺、研习兵法以报家国、以卫社稷。显然在州志修撰者的笔下,秦葵是一位深谋远虑、胸怀天下、精通兵法的奇人。因此秦氏兄妹的一身武艺与治兵才能皆来自秦葵的教授与庭训。关于秦良玉家世的这一记述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6。
然而笔者发现在其他文献中,却有不同的记载。《芝龛记》是清康乾时期文人董榕所写的一部戏曲。该书以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重大政治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明末两名女将秦良玉、沈云英的故事,其中秦良玉所占篇幅最多7。一般而言,我们不宜以戏曲剧本作为史料进行史学研究,然《芝龛记》本身具有较强的“尚实”倾向。《芝龛记·凡例》言:“事迹皆本《明史》及诸名家文集志传,旁采说部,一一根据,并无杜撰。”8可见其基本史事皆有依据。徐振贵注意到乾嘉考据学强调以史为据、无证不信的治学特点,对这一时期的戏曲创作有很深的影响,而《芝龛记》正是这种创作风气下的代表。他指出戏文中“诸忠成仙归真云云,显系虚幻传说”,但是基本事實“大率据实叙写”1。王瑜瑜亦言《芝龛记》《冬青树》等模仿桃花扇的作品在艺术成就上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依傍史书、摹写史实较《桃花扇》有过之而无不及”2。杨惠玲也提出《芝龛记》具有“史家之笔”的特点,“该作展示了明清之际政治、军事、宗教、民俗、文艺等领域的社会风貌,是一部材料富赡、巨细不遗的明清鼎革史”3。可见,作为一部戏曲,《芝龛记》中的部分内容虽有虚构,但在基本史实方面却是言出有据,具有较高可信度,在一定程度可作史料使用。在该书第一折中,描述了秦良玉送别哥哥秦邦屏参与万历朝鲜之战的情节。
我(秦良玉)家哥哥邦屏袭卫指挥,守卫忠州,兄弟民屏为本司左军统目。近因奉召征兵,东援朝鲜,家宣抚遵照宪檄,选兵五百,著兄弟民屏管领,随哥哥统忠州卫兵一同赴援,择于今日启行。夫君自守司治,兄弟先到家庭,儿家统兵,送至忠州江上,等候哥哥催点卫兵,会奇进发4。
万历年间,统一日本后的丰臣秀吉派兵侵入朝鲜,作为宗主国的明朝派兵援朝,石砫土兵亦在被调之列5。石砫土司宣抚使马千乘在接到朝廷的调兵命令后,随即选派五百土兵由秦良玉之弟秦民屏率领赴朝。与此同时其兄秦邦屏亦统领忠州卫兵增援朝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秦良玉有关的常见文献中,皆未记载其兄秦邦屏的身份,秦邦屏的事迹与功业主要是依托其妹“土司夫人”的身份而存在的。然而戏文却言秦邦屏为“卫指挥”,即卫所武官。这就意味着秦邦屏似乎并非普通百姓,而是具有某种“官方身份”。关于秦邦屏的身份,还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天启元年(1621年),秦邦屏之子秦拱明向朝廷奏称。
父邦屏奉命援辽,尽鬻家产,以为军资。沈阳之役,先登杀贼。父既齑粉,而三十口妻孥留滞京华,行乞求助,乞给偿所费金,以赎产业。其重庆卫所与臣接壤,绝军屯地尽没豪右。乞查驭拨二三十顷以赡孤寒,更念同父阵亡部落从重给恤。部覆:绝军屯地抚按查明无碍,给作祭田,其优恤银照例给散。报可6。
秦邦屏于天启元年(1621年)统帅石砫土兵在沈阳城外与后金军队交战中战死,其家属几十口滞留京华,无人照顾,而其在家乡的田地又被豪右所侵占。故请求朝廷拨赐田地“以赡孤寒”。引文中提到一个重要信息,秦邦屏所拥有的土地并非普通的民田而是军屯地。众所周知,明朝确立卫所制度后,为解决卫所兵士的军粮问题,将大量的土地拨给卫所,让士兵屯耕自给,称为军屯地7。既然秦拱明称自家的土地为军屯地,这也就说明秦邦屏一家当出自卫所。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宣慰司安位叔父安邦彦叛乱,史称奢安之乱。明朝遂任命朱燮元为主帅,征调各路兵马,进兵平乱。秦良玉所统辖的石砫土兵亦在征调之列。朱燮元在《会勘催兵科道疏》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来用土兵必用官兵监制,二臣(明时举、李达谊)独持议不用汉兵一人。不知浑河之战秦邦屏虽妹嫁石砫,实忠州人,久在省城练兵。又有战将如周敦吉、邓起龙等督之,故肯皆效死,非尽土兵之力也1。
当时科道官明时举、李达谊二人认为应完全任用土司兵平叛,而不应征调汉兵。朱燮元则以石砫土兵血战浑河之例加以驳斥,指出石砫土兵之所以在浑河之战效死,关键在于汉将的指挥。朱燮元专门提及秦邦屏:大家通常认为秦邦屏是以秦良玉之兄,即以土司家将的身份参与这次战争;但在参与此战之前,秦邦屏已“久在省城练兵”。此处的“兵”显然并非指石砫土兵,而应是汉兵。由此看来,秦邦屏的身份当为军官。故朱燮元认为,秦邦屏率石砫土兵援辽作战体现的是朝廷汉将统帅土兵,而非土司家将统帅土兵。
由以上3条史料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秦邦屏的身份为卫所武官。那么秦邦屏的这一身份是怎样获得的呢?上引《芝龛记》戏文中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邦屏袭卫指挥”,也就是说秦邦屏“卫指挥”之职是通过承袭的方式而获得的。根据学者的研究,明代卫所制度的一大特点在于武官的职位可世代袭替,而父子相继又是最重要的法则2。可见秦邦屏承袭的应是其父亲的武职。换言之,秦葵也应是卫所武官,而非闲居乡野的贡生。关于这一点还有两条重要的史料加以佐证。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兵科给事中薛凤翔在奏疏中提到:“职按秦氏(秦良玉)疏揭,久毓将门,历垂勋业,洗蛾眉以谭豹略,矢马革而奋鹰扬。”3可见薛凤翔曾阅览过秦良玉呈送给朝廷的疏揭,疏揭中秦良玉称自己“久毓将门”。显然,只有多代为武官才可称之为将门,这即可从侧面印证秦葵甚至秦氏先人也是卫所武官。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突破明军的包围,率部攻向四川,川省形势危急。兵部题请秦邦屏之子秦翼明为川东总兵,以期其能阻遏张献忠东进的步伐,挽救川省危局。在兵部呈送给明思宗的文书中称“秦翼明出身将胄,学富韬钤”4,此处的“出身将胄”与“久毓将门”异曲同工,都说明秦氏一家世代为将,绝非文人出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秦良玉出自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秦葵、兄长都是卫所武官。秦良玉的一身武艺与军事才华正是源于武官家庭的自然熏习而非如州志所言——“贡生”秦葵的刻意培养。父兄的职业熏陶是秦良玉成年后扬名沙场、成为一代名将的重要原因。
二、石砫司与忠州所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秦葵与秦邦屏皆是明朝卫所武官,秦氏一家为卫所军户,那么他们究竟来自哪个卫所呢?《芝龛记》戏文中秦良玉言:“我家哥哥邦屏袭卫指挥,守卫忠州……哥哥统忠州卫兵一同赴援。”即言秦邦屏是忠州卫指挥。然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二年(1379年)七月,“改瞿塘守御千户所为瞿塘卫,隶湖广都指挥使司。置梁山、大竹、忠州、达县四守御千户所,隶瞿塘卫”1。可见明朝曾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在忠州设立过一个守御千户所而非忠州卫。上文所引秦拱明的奏疏曾提到一点关键信息,即“其重庆卫所与臣接壤”,这说明秦良玉家族所属卫所并非重庆卫以及下辖诸所,但却又与重庆卫所接壤。而忠州守御千户所地界虽在忠州,却隶属瞿塘卫而非重庆卫,这一特点恰与秦拱明所述相吻合,由此笔者认为,秦氏一家当出自忠州守御千户所,秦葵与秦邦屏当为该所武官。
根据学者研究,土司的婚姻关系往往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石砫土司所处的武陵山区的诸土司一般选择同级土司、下属土司以及当地大姓作为通婚对象,很少跨出这一通婚圈联姻2。石砫司与忠州虽相距不远,但土司制度與卫所制度分属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彼此之间的制度联系也不多。石砫马氏土司为何选择与忠州守御千户所的秦氏联姻?或者说马氏与秦氏之间联姻的基础是什么?这对于我们理解明代西南地区土司与卫所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记载,我们只能通过间接史料加以推测。清雍正八年(1730年),四川巡抚宪德奏称:
据四川布政使高维新详称,遵行通省所属各府州县查报,除无寄庄、寄粮者不议外,惟查夔州府所辖石砫土司原有寄庄粮米一十石五升九合,归于重庆府属之忠州带征,每年就近支给忠州营兵食。而石砫司与忠州相隔窎远,征收粮米官有鞭长莫及之势,民有往返跋涉之劳,自应钦遵上谕更正改隶。前据夔州府知府周彬呈报,随行重庆府知府张光鏻议,详请将此项粮米折征米价隶该土司征收,径解司库……其忠州营兵食亦赴司承领,折色支给3。
由上可知,在雍正八年(1730年)之前,石砫土司每年需向忠州交纳一十石五升九合的寄庄粮米,忠州将这些粮米“就近支给忠州营兵食”。四川布政使高维新认为这样的征收方式于官民皆有不便,于是请求朝廷同意将忠州所带征的粮米直接折银后由石砫司解缴藩司,而忠州营则派人到司库承领官兵的兵食,如此就节约了人力,免除了粮米征缴过程中的跋涉之苦。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中提到石砫司需向忠州缴纳“寄庄粮米”之事。所谓“寄庄”,指的是去外府州县购买土地的行为4。石砫司每年需向忠州缴纳寄庄粮米,这就说明石砫司当是在忠州地界购置了土地,石砫与忠州两地在经济方面由此就确立了某种联系。那么石砫司与忠州守御千户所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是如何建立?又建立于何时呢?
据学者研究,清代前期军队的常规粮饷由户部拨发,地方一般不得染指5。忠州作为地方行政机构不能直接向忠州营的官兵拨发粮饷。那么史载忠州将石砫土司交纳的这部分寄庄粮米“就近支给忠州营兵食”的做法显然不合清朝体制,这又当作何解释?清朝建立初期,随着卫所的军事职能被八旗和绿营所取代,独立的卫所军政系统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由明代沿袭而来的都司卫所机构即被裁革,归并至州县系统1。据学者考证,忠州守御千户裁撤于康熙五年(1666年)2。虽然相关文献对于该所被裁革后的去向未加记载,但依慣例,被裁革的卫所通常都归并到最近的州县管理3。忠州与忠州守御千户所在明代虽分隶两省,但实为一地。因此笔者认为忠州守御千户所被裁撤后应是归并到忠州管辖。这就意味着,忠州接管了之前忠州守御千户所所辖的土地、赋税与军户。如果石砫土司购买的土地来自忠州守御千户所,其所交纳的寄庄粮米自然亦应由忠州接管、征收。忠州守御千户所作为一个军事机构,其所获得的寄庄粮米自然属于军队粮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清朝在裁撤忠州守御千户所之后,仍然在此地设置了新的军事机构——忠州营。对于朝廷和忠州而言,将这部分寄庄粮米“就近支给忠州营兵食”、延续其“军粮性质”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处理方式。因此,笔者认为石砫土司购置的土地当是来自之前忠州守御千户所的辖地而非忠州的辖地。
至于石砫土司何时购买了这些土地,史料并未明言。但据石砫《马氏家乘》记载,石砫土司还曾购置过其他司外土地、缴纳寄庄粮米。
公(马应仁),良公长子,袭父爵,诚朴忠良。太平日久,夷汉相安,撤去峒寨兵丁,令其服田,输赋为民,开垦荒芜,不数年尽属南宾原额。每年征收粮四百一二十硕五斗零,折银若干两,由丰都起解,藩宪谓之丰都寄庄钱粮,即今之秋粮也4。
马应仁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袭职为石砫土司宣抚使5。在马应仁主政期间,司内“夷汉相安”。于是他撤去峒寨兵丁,让他们垦荒种田,数年之后,颇见成效。然而,在这些土地之上所产生的赋税却“尽属南宾原额”6,由重庆府丰都县起解,并被称为“丰都寄庄钱粮”。这说明峒寨兵丁所耕种的土地并不在石砫土司辖境之内,而是属于丰都县南宾里地区。换言之,石砫司应是购买了丰都的田土,形成了寄庄地,才会有“丰都寄庄钱粮”之说。这个案例说明,石砫土司在明代有购置周边地区寄庄地的先例。由此笔者认为,石砫司购置忠州守御千户所田土之事大抵也发生在明代,而清代石砫司向忠州交纳寄庄粮米之事是这一行为的延续。
前文提到,为解决卫所军士的军粮的问题,明朝拨给卫所大量的屯田。军屯土地面积大致以各卫所的人数来确定,卫所人数越多,所获得军屯地的面积越大,军士应缴纳的“屯田子粒”数量也越多。这些田地本属国有土地,不能买卖。但是明代的军户为屯粮、屯草、加派、杂差、缺乏牛具种子所累,不得不也不能不典卖屯地7。据万历《郧台志》记载:“忠州千户所,原额军一千二百二十名,除逃故外,实在八百二十八名。”8可见至万历时期,随着卫所制度的衰敝,忠州守御千户所逃亡与身故兵士数量已超过明初额定人数的30%。这带来的后果便是余下的七成军士要承担整个卫所应缴纳“屯田子粒”的全数,压力颇大。忠州守御千户所之所以愿意将所辖军屯地私下转给石砫司,无疑是希望以石砫司每年所缴“寄庄粮米”贴补粮饷,减轻缴纳“屯田子粒”过重的负担。
综上所述,秦氏一家很可能来自忠州守御千户所,秦葵、秦邦屏当为该所武官。石砫土司与忠州守御千户所虽分属不同的制度系统和政区,但双方在明代已有经济联系,即忠州守御千户所将田土典卖给石砫土司,以收取寄庄粮米。可以推想,以“寄庄粮米”为纽带,石砫司与忠州所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为双方联姻提供了可能。
三、州志编纂与身份重构
如上文所述,既然秦良玉的父兄都为卫所军官,为何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却记载秦葵为“贡生”呢?州志编纂者这样叙述的依据又是什么?其实,早在乾隆时期,忠州曾编撰过一部地方志——《忠州志》。但在该志“人才”部分,修撰者并未为秦良玉父兄子侄立传,特别是在“明贡生”条目下,并无秦葵之名1。而在道光《忠州直隶州志》相对应部分,“秦葵”却赫然在列2。换言之,关于秦葵身份的信息是道光《忠州直隶州志》修撰者新添加的。宣统三年(1911年),秦良玉后人秦嵩年曾将秦良玉有关的各类文献汇集成《初印秦良玉传汇编》,在秦嵩年所作序中提及:“吾祖汝虞公尝以硕德宏材兴修郡志,即深病纪载之踳驳,思于良玉事有所篡述,未及操觚而逝。”3这说明秦嵩年的先祖汝虞公曾参加过忠州一部地方志的修撰,却并未明言是哪部方志。查道光《忠州直隶州志》修撰者名单中有“廪膳生秦肇益”4,而“汝虞”正是秦肇益的字。5由此可知秦肇益参与修撰的地方志正是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因此该志中关于秦葵身份信息记载当出自秦肇益之手。由明末至清中叶,时间跨度并不长。秦肇益作为秦良玉的后人,应不太可能遗忘其先人的出身,那么秦肇益为何要建构秦葵的贡生身份呢?这或许可以从秦氏家族在忠州社会地位的升降角度进行考察。
尽管秦良玉与其兄弟子侄在明清鼎革时立下赫赫战功,获得朝廷封赐,名显当世。但入清以后,天下承平日久,家族地位的维系与提升更有赖于科场扬名,然秦氏后人却科场失意,声名不显6。直至秦肇益,秦良玉家族中才有人得以成为生员。尽管这只是初级功名,但对秦氏家族在忠州社会地位的重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借助生员身份,秦肇益得以参加道光《忠州直隶州志》的修撰。李晓方认为,地方志本身的形成过程映射出地域社会中各方权力的此消彼长与社会文化的变迁7。当地的名门大族往往成为地方志修撰中的主导力量。掌握着地方志编纂权的姓氏宗族,往往在人物志中为宗族成员立传, 在其他各个卷类门目中设法安插有利于彰显宗族地位的资料,使得明清的一些地方志披上了浓郁地私家族谱的色彩,呈现出地方县志族谱化的特征1。可以说,地方志的修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地各大宗族势力的“竞技场”以及提升宗族地位的重要手段。故秦肇益利用撰写忠州方志的机会,在人物传中相继为秦葵、秦翼明、秦邦屏、秦民屏、秦拱明立传,2以彰显秦氏家族的声望。
刘志伟曾提出,祖先的正统性身份与文化认同是宗族在地域性竞争中获取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3。对秦肇益而言,撰写州志时对先人身份的书写关乎整个家族的荣辱及其在忠州的社会地位,但其先人的卫所军户身份却并不利于家族地位的提升。明初,国家的大政方针大体上以“右武”为特征,武职的品级、待遇较之文官有很大优势,卫所军户地位較高,处于社会中上层。然而从明朝中叶开始,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军队的作用开始下滑,军官与军户的地位亦随之衰落,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4。秦葵、秦邦屏虽为武官,但是从其屯田地被豪右侵占来看,他们的职位似乎不高,应属于下级武官。且与普通民户相比,军户所需承担的军役、屯田负担更加沉重,不少家境贫寒的军户甚至不得不典卖田地房产。为了避免拖累子女,普通民户往往拒绝与军户通婚。在法律上,军户的待遇也明显低于普通民户。5因此,内地卫所地区多对自己祖先的军户身份讳莫如深6。秦肇益重构秦良玉父亲的身份,其意图恐怕也在于帮助秦氏家族摆脱军户身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秦肇益重构秦葵的身份或许还与秦氏家族的族属有关。董其祥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察认为,“秦”通“覃”,而覃姓属土家族巨姓,所以秦良玉及其家族应源出覃氏,族属为土家族7。笔者赞同此说,但仍有可补充论证之处。根据《忠州秦氏家乘秦太保忠贞侯家传》记载:“太保名良玉,字贞素,忠州秦氏。先世有名安司者,元季避徐寿辉乱,由楚入蜀,居邵庆路,传二世,至国宝,徙居忠州,遂为忠人。”8可见秦氏先祖名秦安司,乃楚人,元末因避乱才迁居忠州。众所周知,土家族最为集中的地区,正是两湖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董其祥先生的观点。又《忠州秦氏始祖秦安司传》记载:“公(秦安司)生子二,曰国龙、国宝。明初凉国公奉命南征,道经九溪,以国龙能抚一方,擢授唐崖长官司,是为公之长子。国宝官黔江守御千户,是为公之次子。”9秦安司的长子名秦国龙,曾因功“擢授唐崖长官司”,唐崖长官司是湖北土家族地区的重要土司,其土官之职由当地大姓覃氏世袭。根据《覃氏族谱》记载,唐崖长官司土官覃忠孝奉命招抚蛮民一千五百六十二名,蒙兵部题授安抚职,并于永乐二年颁授左右菖蒲、活龙二副司,由黄璋、秦国龙分领10。由上可知,唐崖长官司下辖两个土司,即菖蒲副司与活龙副司,秦国龙便是活龙副司的土官11。一般而言,明清西南地区的土官绝大多数为当地少数民族的大姓。秦国龙被朝廷任命为活龙副司的土官以统辖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也说明秦氏为当地大姓,族属当为土家族。在传统社会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先祖的“蛮夷”身份显然是难以被正统文化所接受的。若要改变这种非正统身份,就要尽可能“培养”出祖先与士大夫文化的联系,确认自己的“汉人”身份,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1。秦肇益将秦葵塑造为士人,恐怕也期冀以此抹掉秦氏家族的“蛮夷出身”,构建出先祖的正统身份。
四、结语
土司制度与卫所制度是明代两大重要的政治制度,因分属不同的制度体系,既有研究对这两大制度的关联性研究相对不足。正如赵世瑜所言:“在有关土司制度,特别是西南土司的研究中,卫所军户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2而在有限的相关研究当中,学界关注的重点是卫所对土司的控御、遏阻3,这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王朝统治的视角。通过对秦良玉出身的分析可以发现,除军事震慑、政治控制外,忠州所与石砫司之间还以“寄庄粮米”为纽带,搭建起了经济联系和政治联姻。秦良玉身为卫所武官之后,却以明代西南土官的身份而威名显著,秦良玉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就正是卫所与土司两大地方力量合力形塑的结果。这是以往研究鲜有关注到的。
清代前期,秦良玉与兄弟子侄的军功光环逐渐褪去,秦氏族人又在科场失意,声名难显,家族地位失坠。道光年间,秦肇益以儒学生员的身份,利用参与写州志的机会,在人物传中为秦葵、秦邦屏、秦民屏、秦翼明、秦拱明立传。在为秦葵立传时,秦肇益有意构建其正统性身份,将其塑造为胸怀天下、满腹经纶的贡生,实现“去军户化” “去蛮夷化”的目的,从而提升秦氏家族地位与声望,完成秦氏家族由武向文的转向。
[责任编辑:龙泽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