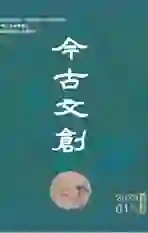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中的“物哀”美学
2023-05-30祝美佳
【摘要】日本新思潮派作家芥川龙之介擅长在短篇小说中重塑历史事件、构建世俗人生,批判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弊病。其作品构思巧妙、语言凝练典雅、意蕴深邃,虽以现实主义的锋芒直指时代与社会,但在主题的渲染、情感的抒发与自然的描写中蕴含着日本传统的“物哀”思想,使文章富有独特的哀情与美感。
【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物哀;人情之哀 ;世相之哀;自然之哀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1-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1.004
“物哀”是日本傳统文学和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初期,《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话、歌谣中萌发了“哀”的文学意识。平安时代中期,紫式部的物语论及清少纳言等的歌论促使物哀成为当时文学思潮的主流。直至江户时代,本居宣长将“物哀”建立为独自的理论体系,使其成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思潮。芥川龙之介在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自幼受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神往于江户情趣,所以他的作品在现实主义的批判中也不乏传统的“物哀”之趣。
本居宣长提出了“知物哀”的概念,主张“知物哀”就是通达之情,知事之心与知物之心,也就是能体会世间一切感动人心的善恶与喜怒哀乐的情感。学者叶渭渠在此基础上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对人的感动,对世相的感动和对自然的感动。本文试图从这三方面阐释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中的物哀美学。
一、人情之“哀”
本居宣长的“知物哀”论,首先是对人情的真实的肯定。他主张“知物哀”是以尊重人性中情的因素、人情的真实性为根本。芥川龙之介擅长剖析人物的内心,对人性的善恶予以细腻地刻画。
(一)恶之“哀”
波德莱尔《恶之花》序言中主张“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他对“恶”的审美与本居宣长“知物哀”美学有共通之处,“哀”的感受不仅限于“善”,而有喜、怒、悲、乐、爱、恨多种形式,能引起人的动心就是“哀”。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中对人性之恶的发掘尤其典型,突出表现在代表作《罗生门》《竹林中》与《地狱图》中。《罗生门》里老太婆在拔死人的头发用来卖钱,仆人见此受其启发剥了老太婆的衣服。资本主义下人与人激烈的生存竞争与冷酷的人情关系跃然纸上,人性之恶触动着读者恐惧、悲伤之情,继而引发了对恶的审美体验,这就是因知人情产生的“哀”感。《竹林中》以三个人物不同的叙述视角描写事件的真相,得出了三个不同的凶杀经过与动因。新颖的叙事手法表现了人性深处的阴暗面,人性之“恶”中蕴含着神秘、恐怖情绪的“哀”之意蕴。表现艺术至上论的《地狱图》更是把人性的恶发挥到了极致。画家良秀看着女儿在火中活活烧死挣扎的景象而感到实现艺术美的喜悦,他对恶之美的艺术追求达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整部作品笼罩着变态、阴森的恐怖氛围,读来无不悲哀。
(二)善之“哀”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中也有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名篇《橘子》有如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雪国》的物哀之美。“我”在阴郁的天气下怀着疲倦、无聊的心情踏上火车之旅。一位质朴、善良的农村姑娘治愈了“我”对庸碌、心灰意冷的现实世界的消极心理。作者对人性自然的“真”“美”“善”进行细腻生动地描绘:一个手上长满冻疮的姑娘从车窗上探出半截身子,将金黄的橘子朝孩子们的头上落下去。和煦的阳光照耀着这温馨和谐的一幕,姑娘朴素、温柔的人性之美打动了“我”,以至令“我”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恼。
《寒》写了保吉在目睹为救铁道上的孩子而丧生的道口值班员的尸体后,内心产生强烈的痛苦与同情,他体悟到生命的脆弱感与死亡的恐怖,又因冷漠的旁观者感到愤慨与失望。芥川龙之介通过对保吉细腻、敏感的心理活动的刻画,传达了人性的“善”的光辉与人道主义思想。“保吉感到,在凝着冻云的微微发暗的天空下,这只失落在站台上的孤孤单单的红色手套是具备着生命的。”对生命的敏锐体悟,对死者的哀怜与痛惜,无不体现出通达人情、顺乎人情的“善”的物哀美感。
(三)恋爱之“哀”
本居宣长认为恋爱最能表现出人情的“真实”,物哀在恋爱上是最深邃的。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中最能体现恋爱之“哀”的莫过于《秋》这篇佳作。才女信子和表兄俊吉情投意合,但信子为了成全妹妹照子对俊吉的心意,断然舍爱匆匆与他人结婚。但婚后信子在丈夫大男子主义的统治与淡漠的感情中悒郁不欢。文章中写道,信子为了排除沉闷忧郁,一直沉浸在快意的感伤之中。她时常失神地眺望着撒遍室外松树林的阳光,看着阳光在昏黄的暮色中渐渐改变着颜色。作者以细腻典雅的语言描写失去恋爱后信子的悲伤、悒郁的情绪,这种淡淡的哀愁是对人性最真实的描绘,这就是恋爱之“哀”的审美意蕴。由恋爱带来了嫉妒不久又引起了姐妹俩之间的嫌隙,信子与俊吉再度见面激起了照子的醋意。敏感的信子感到自己和妹妹的关系逐渐向陌生化疏远,这种心情使她的胸中结起一层寒冰。芥川龙之介对女性隐秘、复杂、晦涩的心理描写得非常细腻,这种真实的爱之哀,情之殇就是富有动人心弦的“物哀”之美。
二、世相之“哀”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直指人间世相,即对天下大事的关注与体悟。他在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下彷徨矛盾,对人性与世相持怀疑主义和悲观态度。因此在年仅三十五岁,他就因精神上的痛苦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芥川龙之介遗作《某傻子的一生》中一句“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句诗”[3]460道尽他的消极的厌世观。在短篇小说中,他的悲观主义依托人物的精神状态传达,无不给人以虚无、消颓、痛苦的“哀”之美感。
(一)幻灭之“哀”
芥川龙之介在描写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碰壁的作品中,透露出其对现实的幻灭感与寂寞感。《玄鹤山房》里老画家玄鹤在病危虚弱之时,忍受着家中复杂的人情矛盾,痛苦不堪。“玄鹤为了忘掉一切,睡觉就是极乐”,玄鹤在弥留之际对艺术、人情、财富感到虚无的幻灭感,给人以“哀”感的触动。作品中暗示的旧时代的消亡与新时代的来临更是一种道不尽的幻灭之“哀”。芥川龙之介遗作 《齿轮》《某傻子的一生》《侏儒的话》阐述了他生前的种种思想状况,反映了一个正直青年知识分子在丑恶的现实人生面前的无力与消颓。在芥川龙之介的眼里,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有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异化的人不过是竞技场里壮烈的牺牲品。人生如梦,人生如幻,唯有死亡是消除痛苦的终极归宿。
《尾生之信》是另外一篇传达芥川龙之介幻灭感的佳作。尾生在桥下等待女人的到来,但最后什么也没等到,反而被上涨的潮水淹没成为一具冰冷的尸骸。尾生的灵魂经历千年流转栖宿在“我”身上,“我”生于现代,却又一事无成,只有不分昼夜地虚度恍然如梦的人生。尾生之等待与“我”之一事无成都给人以消极面世、世事如空的幻灭感与徒劳的空寂之“哀”。
芥川龙之介的晚期作品《海市蜃楼》充斥着悒郁的“物哀”美感。作品中的“我”是个敏感、脆弱,多情的“知物哀”者,他隐秘复杂的心理变动传达出人生如梦的虚无感与幻灭感。以青年男女的时髦打扮与自由恋爱象征的“新时代”,对“我”而言是一种朦胧的时代变迁的危机感。“我”看到沙丘上的木牌感到毛骨悚然,在梦中梦到前几年采访的女记者,思绪在意识之外缥缈。“海市蜃楼”如一面虚镜映照着现实、幻境、过去与未来,一切都如沙子营造的假象如梦如幻,真假相生。这种人生的不确定性与意识的漫无目的给“我”以恐惧的忧虑与幻灭的“哀”感。
(二)孤寂之“哀”
芥川龙之介在对人生世相的观照中,除了揭示根本性的人生虚无的幻灭之“哀”,还广泛关注了社会中“小人物”生存的凄凉困境,他们孤立无援备受嘲弄,象征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孤独感与人与人之间淡漠的人情关系。
芥川龙之介借《孤独地狱》中一个纵情酒肉美色的僧侣传达了他孤独的境遇,“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一个受孤独地狱折磨的人”。僧侣禅超沉迷酒色以忘却尘世纷扰,但最终没在忘却中摆脱痛苦。这是作者对人生世相警醒而深刻的认知,敏锐的悲观主义情绪仍流露出浓重的“物哀”。
《火男面具》塑造了一个如阿Q式的滑稽人物平吉,他贪图享乐,爱好喝酒,醉酒后爱说谎话和跳舞。他颓唐与轻慢的生活态度成了大家眼中的乐子,看客们对平吉的表演指指点点,直到其栽倒死去也没唤起他们的同情心与怜悯心。平吉一生经历荒诞、可悲、可笑,连死也是热热闹闹的。他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夸耀自己的过去,以滑稽的跳舞哗众取宠,实在是以一种荒诞不经、戏谑的态度对抗生活的不如意与内心的孤寂感。芥川龙之介借此想表达的正是现实人生中小人物悲凉、空虚、可悲的人生境况,以及对人生寂寥感的“哀”愁。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写了武士大石因多种价值观的冲突与激荡引起的哀愁。原本令他满意的忠义之举受到了意料不到的反响,民间纷纷效仿其复仇精神闹得沸沸扬扬,为复仇伪装奸细寻花问柳违背了其内心的道德感,激起其阴郁的不快与自我谴责。大石在其他家臣兴致勃勃的谈笑声中默默退至庭院,他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寂寞与哀情包围着自己。大石的寂寞一方面来源于“浮士德难题”中自我需求的满足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二律背反的人类永恒的矛盾,另一方面来源于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寂寥感。他与其他家臣对话间微妙的距离感,他内心的隐忧与家臣们一味沉浸在复仇成功的满足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突出了人类精神的孤寂感与人情间的淡漠。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颇有作者自传的意味,表现了知识分子孤僻、封闭、窘困的生存境遇。因未喝过母乳与贫困的家境,信辅自小就敏感自尊,与外界格格不入。学校里卑劣的老师欺辱他,他对交朋友也毫不关心,而乐于揶揄鄙夷他人。他只是沉迷于书籍中,养成忍受孤独的性情。“但是带给他的东西,毕竟还是落寞的孤独”,芥川龙之介借信辅的前半生表达了自己孤独、苦闷的生活窘况,给人以生之寂寥的“哀”感。
三、自然之“哀”
自然与日本古代文学意识的萌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美和色彩美成为所有日本文学上的美形态的原型、日本文学和美学的基础”,日本以亲和的态度对待自然,并将自然作为重要的描写素材或美学意义融入文学作品,与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情绪相互协调升华为艺术美。以自然营造氛围,渲染情绪,从而傳达“物哀”思想是日本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作品中都有炉火纯青的典范。
(一)“秋”景衬“哀”情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中有大量秋景的精彩描写,小说设定的时令也大多发生在秋季,因为“秋”的节令最符合日本感伤性、情绪性的民族特质,容易引起“哀”感。
《舞会》是芥川龙之介对欧化之风下浮躁与浅薄的日本社会的批判。鹿鸣馆是明治维新后建立的供西化的达官显贵消遣的场所,被当时传统的日本人指责为“媚外外交”。与华丽热闹的鹿鸣馆舞厅不同,外面的世界是“冰冷的空气的下层,从庭院地面飘上来的苔藓的气味和落叶的气味,微微带有凄凉的秋天的气息”。芥川龙之介以秋季的寂寥渲染了感伤的氛围,助以对西化后日本社会与国民的绝望、悲哀之情的抒发。
《庭园》写了一个豪门世家的衰落,小说多次以秋季作为情节发生的时令,给人以浓重的寂寥感。如庭院后山发生的火灾在秋天,老二离逝的时节是深秋时分,老二送葬后,廉一“总像是不知所措似的,瞅着深秋时节的水和树……”。小说还以节令的变化营造了自然生死轮回的流逝感,给人以情绪上纤细微妙的“哀”感。庭园经历世代的流传,在后辈的挥霍与自然的灾害中荒芜,无论老二如何修补也难现往日辉煌。芥川龙之介以庭园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象征,实际上表达了对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下消解衰败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惋惜与悲凄之情。
前文提到的《秋》更是把“秋”作为“哀”的意象为文命名。信子、照子与俊吉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诉诸为“秋”这一哀象,实属精妙异常,暗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别样滋味。“秋天……信子在带着轻轻寒意的车篷底下,浑身都感到寂寞凄凉,她不禁深有感触地想到这秋天了”,芥川龙之介在此篇中把“秋”与“恋爱”结合,塑造了自然与人情交织的“哀”感。
(二)雪、月、花之“哀”
日本文坛有一句名言“雪月花时最怀友”,“日本文学尤以雪、月、花作为其自然美乃至整个美意识的核心,残月、败花发展为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物哀文学思潮生成之源。”。自然景物是最能表现细腻朦胧的情思的,这与日本淳朴性、感伤性的民族情绪一脉相通。
芥川龙之介无疑也是将自然作为生命的活力融入作品中,尤在《大川的水》中借以对大川的爱传达对东京与祖国的爱。故土的水承载着他所有情绪的哀感,触动他敏感纤细的依恋感与寂寥感,大川的水是芥川龙之介古朴纯正的情感土壤。
动物寓言小说《小白》有三处提到了月。第一次在小白沦为丧家之犬时面对棕色小狗到其家住宿的邀请,小白望了望天空,看到了上空露出了皎洁的新月。月相的新旧残圆容易引起世事无常的哀愁感,此刻小白或许会想起往日主人的温存,而此刻只有新月映照着无家可归的自己。第二次月出现在小白回家之时,一轮明月挂在高大的棕榈树的树梢上。明月高照,月的光亮连通人情的团圆,小白终于回到了主人的怀抱。日本尊重、顺从自然,甚至把自然当作对话、和谐相处的共同生存的对象。在日本文学中,自然被赋予人情味,是与人的精神紧密契合的。小白对着寂静的月亮自言自语起来:“月亮啊!月亮啊!”月极易引起人的慨叹与感怀,也成为通达人情的观照对象。
四、结语
从“物哀”美学的角度对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进行观照,可以发现在现实主义风格之外,其作品还延续了日本传统幽微凄清的“物哀”情调。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在自然意境的阴郁营造,人情关系的敏感刻画,悲观的生命意识中流露出浓厚的“物哀”观。这种带有日本独特精神内蕴的“物哀”也是其作品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文潔若.芥川龙之介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芥川龙之介.河童[M].秦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刘振生.时代的文学 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51-54.
[5]王向远.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 ——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J].江淮论坛,2012,(05):8-14.
作者简介:
祝美佳,女,浙江衢州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