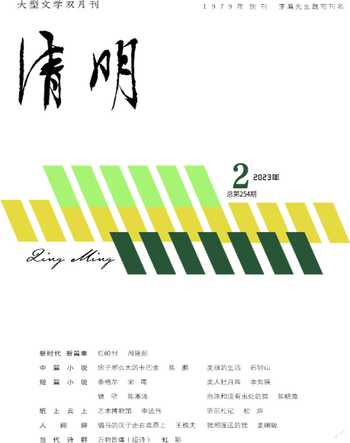泡沫和没有出处的猫
2023-05-30陈晓霞
陈晓霞
天阴得最厉害的那一阵,欧兰决定出去走走。老魏在墙上看她,她说,就透透气,很快回来。她不想让老魏看出自己的坏情绪,就用最快的速度换了鞋,抓起雨伞走下楼。闷热的空气里掺着一丝雨前的清凉,她用力吸了几口气,这才觉得心里撬开了一道缝。
老魏三个月前离开了她,一点征兆都没有。他最后问她的一句话是:你摸摸我的脉还在不在?这事给她留下了后遗症,她看见任何一样东西忽然倒下,都会立刻冒一身汗。汗水黏糊糊湿嗒嗒的,使她看上去像一只水淋淋的惊弓之鸟,让她烦躁。她到镜子前面端详自己,看到的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那上面皱纹纵横,像一块干巴巴的荒地,没有丝毫返青的迹象。
欧兰决定今天就把那事做了。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做一件特别的事,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这得感谢银行的提醒,一大早他们就发来短信,祝她“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生日快乐”。作为一个退休的语文老师,欧兰原谅了句子的别扭,只把 “特别”二字记到心上。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她倒是真的可以过一个挺特别的五十八岁生日。
她上了公交车,在暴雨到来之前赶到华辉超市。这里够大,而且热闹明亮,最重要的是这地方没人认识她,她可以从容地把货架上的东西看个够。她想象自己拉着一张网,从超市的这头拉到遥远的那头,像渔夫那样把水里的东西一网打尽。这时候她看到有个老头儿正毫无计划地往购物车里放东西,欧兰一眼断定这是个新手,是个像老魏一样不懂柴米油盐的甩手掌柜。他这样的人进超市,一定是家里遇到了特殊状况,不得已才派他仓促上阵。老头儿把车子装得满满当当,那是足够他这年纪的人消耗两个星期的量,而那些蔬菜水果显然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欧兰费了好大力气才忍住没过去纠正他。她以前总是毫不客气地纠正老魏。她多年的纠正让老魏有了一双羔羊一样驯服的眼睛。现在这双眼睛又在她心头闪了一下,让她忽然感到了心痛。
欧兰转向另一行货架。她的购物车还是空的,没什么需要的东西,买回去也是浪费。当然这次例外,她要买瓶酒。
她要买瓶酒,然后约个人,最好是米遥,一起到超市顶楼的餐吧里把它喝掉。米遥曾是老魏他们公司的会计,有年中秋老魏出差,米遥和同事帮忙把福利送到家来,欧兰还以为她是来公司实习的大学生。其实那时的米遥已经二十七岁了。人随着年龄增长会不断改变天然的相貌,欧兰自己就因为不能生育脸上早早添了焦灼之气,米遥却很好地保持了原生状态,甚至脑门上還有一层孩童那样无辜的绒毛。后来欧兰不止一次地回想米遥那天的模样:白皙,纤细,安静,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那是全天下男人都喜欢的样子,老魏当然也不例外。尤其听惯了欧兰在课堂上养成的高门大嗓,米遥的轻声细语在他听来无疑是“如听仙乐耳暂明”。
欧兰先拿了瓶红葡萄酒,想了想又换成了干白,因为她觉得这更符合米遥的清净气质。其实她只见过米遥一面,并不确定现在的米遥是否还如当初一样温雅。而米遥能不能认出她也是个问题。自打老魏去世,欧兰就不再染发了。以前染过的头发被一茬茬剪掉,如今只剩下一头雪白,远远望去,像顶着一团小型的云朵。欧兰借着玻璃橱窗瞥了一眼自己,忽然很想知道米遥对这些白发会作何感想。
地点选在“觅骨记”。不是欧兰热爱酱牛骨,而是从这里望出去,能一眼看到弥河大桥上的滚滚车流。桥是二十年前建的,每日每夜都有无数车辆匆匆而来,带着决绝的气势和短促的啸音划过桥面,跃入对岸的楼丛人海。有段时间,老魏也奔波在这些车流里。欧兰曾替他计算过,他在上午下班前三分钟离开办公室,趁大家还没起身,电梯尚且空闲,飞快地下到地下车库,发动汽车,驶过弯道,来到地面。此时下班音乐刚好响起,老魏踩着第一个音符跃出停车线,像陡然而起的一阵风掠过大门,朝弥河东岸疾驰而去。午休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来去要用七十分钟,刨去两头停车、上楼的时间,老魏在米遥那儿只能待上十分钟。这中间他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屏住急促的喘息,把来自他血脉里的那一团骨肉小心地抱在怀里。襁褓里有只嫩笋样的小手,老魏想捏住它,又怕弄折它,只好改用嘴唇把它轻轻衔住。那会儿他可真像一棵人形大树,风不吹,树不摇,任凭心脏在胸膛里面横冲直撞,恨不能就这样脚下生根,从此和这婴孩生长在一起。可惜十分钟转瞬即逝,父子俩还没完成一次像样的沟通就又要分离。时间已经不多了,老魏不得不像年轻人那样小跑着下楼,投入到下一场狂奔中。
他一定忘记了膝盖的疼痛——他们家族人人都有一个粗大突出的膝盖骨,像树上的瘤子,过早地把笔直的树干侵蚀成了一根朽木。他只管沉浸在中年得子的微醺里,欧兰想象得出,接下来的整个下午老魏脸上都挂着莫名其妙的笑。他对所有同事语气轻柔,态度温和,仿佛他们都是些娇嫩的婴儿,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只是下班后他还要再待上一会儿,待到人去楼空,才去卫生间对着壁镜吐气,搓脸,深呼吸,左左右右检查蛛丝马迹,直到把那个婴孩带给他的异样神态消除干净,才换上中年人的稳重表情开车回家。
那真是一段糟糕的日子。欧兰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斗士,每天枕戈待旦,等着米遥来鸠占鹊巢,或是老魏实言相告。她因等待而肃穆,又因肃穆而冰冷。她心里长满了尖锐的冰凌,只要两人胆敢开口,她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却迟迟没有行动,这倒让欧兰不知所措。本来只要他们摊牌,欧兰就会退出;只要她退出,老魏和米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生活在一起。可他们既然不敢,欧兰也就绝不开口。从知道真相的那一天起,欧兰喉咙里就长出了一把锁,把这个秘密牢牢锁住。她眼见着老魏一天天瘦下去,像一块燃烧的木炭,把一切可烧和不可烧的都投入火焰,却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她觉得自己像一个驯兽师,在笼子外看着狮子拼命奔跑,却迟迟不肯发出休息的指令。她想,这个可怜的男人,他就要被自己累死了。
晚上七点左右老魏会准时回家。他的话忽然有点多,简直就是喋喋不休,除了品评饭菜的味道,还要说些单位的笑话。那些话在饭桌上突兀地弹跳,本身就像一个笑话。欧兰微微扭开身子,尽量和他保持距离。老魏还是太大意了,不知道过分的正常恰恰就是不正常。她把冲到嘴边的一句话咽下去,临时换成另一句:
“今天忙吗?”
他说还那样。
“你们午餐是不是很差劲?我看你总是饿得很。”
果然,老魏茫然地眨巴着眼睛,对当天的午餐全无印象。他的记忆在过去的日子里翻腾了一阵,才驀然想起,来往于弥河两岸的这些日子,他根本没有吃过午饭。
他慌乱地去看欧兰,谢天谢地,她收拾碗碟去厨房了。
她不要听他解释,不要他被逼得满嘴谎话,宁愿在他山穷水尽的一刻悄悄放他一条生路。
她也不会告诉老魏,他在桥上来回奔波的那段时间,她去哪儿了。十八年前的华辉超市还是一幢七层高的百货大楼,欧兰记得很清楚,七楼边门的插销是坏的,从那里可以畅行无阻抵达天台。那些日子,她每天都站在天台上,举着望远镜朝大桥眺望。镜头里,弥河大桥的钢铁拉索像巨大的翅膀直插天空。
欧兰注视着桥上的车辆,同时也注意到了自己的可笑。一个从教多年的中学老师,竟然想借助一只旅游景点上买来的望远镜,窥探丈夫的秘密行踪。她根本看不清桥面的情况,越看不清,她就越觉得从那里经过的每一辆轿车都是老魏开的那辆,因而那些轿车也就毫不留情地从她的心头一再辗过。每天中午她都要爬上天台被辗轧,仿佛不这样她心头的疼痛就找不到出口。如果不是有一天一个小个子保安把她给轰下来,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那个甩满鸽子粪的天台上站多久。
天很热,小个子保安因为疏于换洗而体味浓郁。他的孩子也许就在欧兰所在的学校读书,如果在校园遇见,他说不定会对欧兰献上最谦卑诚挚的问候。但现在他在她面前趾高气扬,把她当成小偷或者危险分子那样大声训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谁让你上来的?赶紧给我下去!”
她被推了个趔趄,差点跪倒在扶梯上。丝袜磕破了,露出了羞涩的大脚趾。欧兰像只惊慌的鸭子,被那个男人推搡出来,扑向太阳下晒得发烫的自行车。她为自己的狼狈感到羞耻,第一次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了愧意。她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丝袜塞进垃圾桶,然后迈进浴缸,把自己泡进冷水里。那一年她四十岁。那是她人生的分水岭。从那以后她就彻底告别了冲动和感伤,只剩下冰封万里的一派平静。
当然,她承认,所谓冰封万里其实并不总是恰当的,因为愤怒的暗潮从来没有停止过汹涌,坏情绪时时抵着她的舌头,使她忍不住想把积攒的怒火化作狂风巨浪拍向老魏。有一次老魏错拿她的口杯刷了牙,她没等他把嘴巴清理干净,就夺过杯子丢进了垃圾桶。老魏吓了一跳,冒着满嘴泡沫问:“怎么了这是,啊,又怎么了?”欧兰红着眼睛吼一声:“你他妈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
她及时咬住了嘴唇,防止那件事情脱口而出。这些年她绝口不提那个秘密,就是为了把风筝的长线攥在手里,把对老魏的惩罚延长得久些,再久些。如果不这样,她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事情却不是这样的。有年冬天,她带学生参加市里的诗词大赛,回来时正赶上一所小学放学,他们的大巴车在蜂拥而出的家长和孩子们中间搁浅下来。欧兰懒洋洋地望向窗外,看见老魏牵着一个男孩正在过马路。他在年轻家长们当中显得老气、黯淡,像一面久经战火的旧旗子,让人怜悯。小男孩显然想摆脱他,一路都在甩手发脾气。老魏赔着笑脸亦步亦趋,欠了账似的为孩子打开车门,把他护送到后座上。欧兰从大巴车上俯视着老魏,惊讶地发现他已经开始谢顶了,下颌的轮廓正被脖子上的松垮皮肤逐渐淹没。他还不到五十岁,脸上已经有了七十岁的力不从心。他甚至连装潇洒的劲头也没有了,只剩下求饶般的讪笑和赖皮。欧兰不确定这是不是她想要的结果——看他自作自受,看他自食其果。如果是,她为什么一点也不高兴?如果不是,她明明就是这场惩罚行动的实施者。人群吵嚷着从车旁经过,欧兰拉上窗帘,把自己丢进暗影里。
欧兰从此开始了长久的胸闷。
医生建议她做“减法”,断舍离。任何有碍于她健康、快乐、轻松生活的事情,今后都必须坚决放弃。她平静地实施了,包括提前休岗,参加社区活动,不再朝老魏发火。多少年下来,她基本上成为一个丢掉执念、平衡欲望、简约生活的人,只是她仍然高兴不起来,好像“高兴”只是夹在书本中的一个枯燥词语,与她已经毫无关联。平静才是她的常态。
那天她就在平静中看了他一眼。
他来她的小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每天来这里做墙绘,她下楼锻炼的时候就会看到他。欧兰不记得老魏有什么绘画天赋,这孩子却有本事把乏味的墙壁变得妙不可言。他几乎能挽救一切无用的东西:裸露在砖墙外的塑料管,失去遮挡意义的窗户,几级戛然而止的台阶,都被他巧妙地收纳进绘画里,变成奇妙世界的一部分。因为这面缤纷的墙壁,这个老旧小区散发出一种少有的懒洋洋的舒适感。
开始,欧兰只是因为那张脸停下脚步。这张脸在报纸上出现过,十八岁的墙绘爱好者,好几个小区都有他的作品。按说她应该调头走掉,把他和他的涂鸦远远丢到身后去,她却没忍住看了他一眼。不仅看了,而且还像个八卦的数据分析师,试图计算出老魏和米遥在那张脸上各占了多少股份。她甚至用上帝的视角在他们之间画了几条线,那些线让他们的亲疏远近一目了然。
欧兰想,他可别朝这边看。偏偏他就朝这边看了,而且像对所有欣赏者那样给了她一个好看的微笑。这个笑一下把欧兰的线给搅乱了。她只好退一步想,孩子是没错的,何况还是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她远远地还了他一个笑。
他叫“没有出处的猫”,至少他让欧兰这么叫。有一次因为雨来得急,她给他搭了一把手,把工具收进遮阳棚,他和她就熟络起来。
欧兰短暂地思考了一下这名字的含义,放弃了追问。她说她叫“泡沫”。
男孩问她为什么叫泡沫。
她想到了“身如泡沫亦如风”,“泡沫风灯成一笑”,但她不打算解释这些,自己终归就是挥手之后不留下一片云彩的一颗泡沫而已。她为自己临时编的名字小小伤感了一下。
雨点在遮阳棚上跳着,砰砰地响。
她朝他笑笑:“没什么意思,瞎叫的。”
“猫”却给了她一个欣赏的眼风:“做老师的吧?一般女人可想不出您这样的名字。她们喜欢叫‘一帆风顺,要么就是‘空谷幽兰”。
“猫”不认识“泡沫”,“泡沫”却知道“猫”。那天老魏忽然说要喝一盅,欧兰就知道他难受坏了,他需要和人聊一聊。报纸她看了,老魏当然也看了。十八岁青年在采访中提到的黢黑的楼道、寂寞的小屋、树叶在夜风里神秘摇动的童年噩梦,还有他为了躲避独自在家的恐惧,不得不用画笔给自己制造一个安全世界的煎熬,都让老魏觉得自己罪该万死。烈酒把他辣得涕泪横流。老魏几次找到欧兰的眼睛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欲说还休。实际上他一句话没说就把自己灌倒了。醉了的老魏第一次肆无忌惮地躺倒在沙发上,扯过一个靠垫,捂住了自己的脸。
欧兰想起有一些夜晚,老魏也曾在黑暗里这样哭过。没有声音,只是肩膀在克制中小幅度抖动。欧兰没开口,那把大锁还习惯性地锁着她的喉咙,何况他的哭绝不是因为她,而只与弥河对岸的母子相关。哭过的老魏发出深长的鼾声,他在熟睡中终于放下了迎合的笑脸,露出了深深的疲惫。欧兰看着他,心中飞过一个念头:她有多久没心疼过这个男人了?当年她曾经是多么爱他。
“猫”说他已经画了三个小区,后面还有几个小区等着他。欧兰说改天去看一下,男孩说:“干吗改天?现在就带你去。”他麻利地歸置好工具,推出电动自行车,让欧兰坐在后座上。他骑得很快,风鼓着他肥大的白色T恤,一下一下扑到欧兰脸上。欧兰想起襁褓里那只嫩笋样的小手,断定耳边呼呼而过的不是风,而是一去不回的匆匆时光。
欧兰本没打算请他上楼,这无疑是个冒险的举动。但她看到墙上一张半遮面的男人面孔后改变了主意。她决定让男孩看看老魏住过的地方。上楼的时候她步子有点飘,不得不伸手抓紧了栏杆。她回头看看男孩,看他还有没有返回去的可能。男孩以为她累了,说:“要不要我扶您?”她急忙说:“不用不用,我行的。”
她用老魏的杯子给他盛了水,让他坐在老魏常坐的椅子上,甚至,他旁边花瓶里的百合花的香味也是老魏爱闻的。男孩有副让人羡慕的结实肩膀,欧兰想,这身体的一半基因本该是和她结合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他才成了老魏和米遥的结合品。
“您爱人不在?”叫“猫”的男孩站起来,打量着房间里的摆设。他对老魏留在博古架上的小八音盒产生了兴趣,摇了几下,客厅里立即响起清脆的《铃儿响叮当》。欧兰的心陡然紧跳几下,如果他推开卧室的房门,就会看到老魏正在墙上看着他。还好,他的注意力只在房子的面积和层高上。他说:“什么时候我和我妈有套自己的房子就好了。”
他站的位置,正是老魏倒下的地方。欧兰忘不了老魏那天的样子,像是突然踩空,又像正慢慢陷入沼泽。他眼神惊恐,似乎希望她来拉一把。最后他说:“你摸摸我的脉还在不在?”她慌乱地把手摁在他的手腕上,说:“在的,老魏,脉搏还在!”她飞快地找到手机,向120通报了他们的位置,又赶紧回到老魏身边,让他靠进自己怀里。他们两个都有些抖,但她听到,自己正用一个语文老师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他:“医生就要到了,老魏,没事的,你相信我!”
她记得,茶几遮挡了部分光线,暗影盖住了老魏的半张脸。
现在,老魏就藏在那扇门后,像是专门等着这场邂逅。他也许会直接从相框里走下来,把这个男孩紧紧拥进怀里。老魏,老魏!你儿子来了,你在想什么呢?欧兰僵在茶几边,直到男孩下楼,也没完全理清头绪。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欧兰每天坐到电脑前,制作一本电子相册。从老魏的祖母开始,她把他的父母、叔伯、姐妹全部请进相册里。他们脸上或多或少地打着些魏氏家族的烙印,明白无误地告诉观看者,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关联。轮到老魏的时候,照片多起来,欧兰不得不另建一个文件夹,按时间顺序,把他从百日照到去世前的228幅照片排列起来。扫描到他俩的合影时欧兰犯了些犹豫,她端详一阵,最后还是把自己剪裁掉,只留下老魏一个人在湖水边、高塔下、小桥上漫无目的地微笑。她还记得他们在那些地方的一些对话,它们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让她耳朵微微发热。
这是她给“猫”的礼物,事关他的出处。欧兰转动鼠标,看老魏在相册里再活一次。他在她眼皮底下又一次长大,上学,当兵,工作,从水嫩到英俊,从健壮到消瘦,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所有的期盼、热爱、幸福、烦恼,到最后都将归于沉寂。她作为一个事后的归纳者,能做的,只是尽量把相册做得完整些,把最真实必要的说明备注到页面上,以便那孩子对自己的来处有个更全面的了解。如果有一天在天堂相遇,欧兰会对老魏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她把最后一笔房款转进银行卡,房产证的办理她打算让米遥去做。新房子是老魏单位组团买的,比市面上便宜不少,如果不是特别挑剔,140平方米的三居室应该能安放下米遥母子的后半生。
这些年她一直拒绝听到米遥的消息。她就当米遥消失了,或者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女人。她只有把米遥屏蔽在另外一个世界,才能安心过她自己的生活。现在,她却要将米遥从老魏的手机里打捞出来,面对面,把一些事情讲给这个女人听。
因为,笼子空了,风筝飘了,老魏走了。无论多少爱恨,这场人生大戏都到了该收场的时候。
她打算把一个优盘、一张卡、一瓶酒,一样一样地从身上掏出来,像是剥离掉身上最后的铠甲。交接完这些,她就可以无牵无挂,和几个老伙伴一起,去做她盼望已久的长途旅行了。
窗外,暴雨已经倾泻多时,雨水把角角落落的污垢扫荡出来,在下水口形成一个大大的漩涡。路上没有行人,只有一些车子在大雨中急速逃窜。欧兰不知道米遥看到短信没有,或者看到了会不会来。对面楼群已经亮起了灯光,光线在雨中显得缥缈而又执著,就那么任凭雨水粗暴地敲打着,覆盖着。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