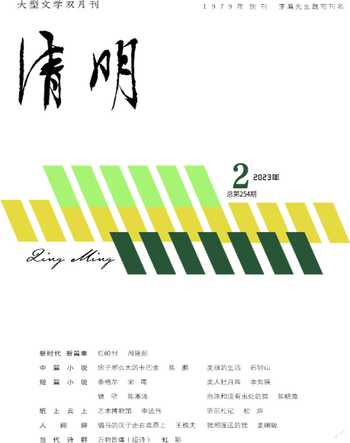大路上讲话
2023-05-30时国金
时国金
一
有时,我感觉很幸运,生长、成长在金宝圩。这方水土承载着我的喜怒哀乐,留存着我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记忆。
年轻时拼命地想离开家乡,现在是一有时间就想回到故乡。有故乡的人,一离开家,浓浓的思乡之情,即从那时起,始终萦绕在心头。
现在工作的城市离老家100里左右,开车回去也就个把小时。只要双休日不加班就驱车而回。不为什么,就是想找老乡聒聒谈,听听那圩乡醇正的方言和那方言里存放着的趣事和人情。就是想脱去上班的正装,离开逼仄的水泥森林,走在阡陌田垄,轻松舒适,随意自在。
离开家乡越久,越觉得圩乡话柔软亲切。语言需要环境,只有回到故土,才能激活那些沉睡在心底久违的词汇,再一琢磨,便觉口齿生香,余味悠长。
读中学时,很羡慕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同学。我自卑只会讲地方土话,常被耻笑“从各里到个里”,也曾努力学说普通话。随着年纪的增大,离故乡越来越远,对于圩乡的语言却反觉得越来越亲切,在外地也常常为偶尔听到一个讲老家话的人而惊喜。
圩乡人学说普通话是很难的。圩乡话属于吴方言中的宣州片铜泾小片,发音,词汇和声调与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就像北方的京剧和南方的黄梅戏,一个是雄浑苍凉的高山,一个是平展婉约的水乡。长期生活在圩乡的人,出去工作后,很少不留有圩乡口音。
但也有例外。我在原乡政府工作的前任同事朱君,从未离开过圩乡,凭着自学却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被市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栏目遴选为男主播。可见那普通话说得不是一般的好了。我接任后,乡里的广播站站长告诉我,他为了练习说普通话,两年时间用坏了三台盘式录放机。天赋是一方面,功夫也非同一般了。
我是语言天赋比较差的那种人。現在还清楚记得,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水阳江上的东方红一号载人轮船还在每天从芜湖到宣城,往返一次。表哥孟喜正好是初中毕业,带着我一道去宣城二舅家玩。到了雁翅轮船码头,远远就听到汽笛的鸣叫。表哥说:“挤上船再补票。”我们紧赶慢赶像泥鳅一样挤过了长长的跳板,顺利地上了轮船。船是三层,已载满了人。逆流而上,经水阳、新河庄、油扎、庙埠,到东团湾码头,已是斜阳残照。船到码头,一张长长的跳板连接到堤岸。堤岸上有验票的工作人员。一路上表哥已把票价研究了个透,他悄悄和我说:“我们就说是从油扎上船的,只要两毛钱,雁翅是八毛,两个人可省下一块二呢。”说完就揣给我一张两角的毛票。
表哥留着一头长发,穿着喇叭裤,走在前面,洋腔怪调地和验票员糊弄了几句,补交了两毛钱上岸了。
快轮到我了,一想到要扯谎,心咚咚直跳。我跟着人群往前走,努力提醒自己不要怕。
“票呢?”
“没买,补票。”
“哪里上的?”
“油扎。”
“瞎扯,一听你就是水阳佬,一边站着。”
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就这样被自己浓厚的圩乡口音暴露了行踪。我乖乖地站在一边,一言不发,感觉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脸上,火燥火燎。
这时,一位穿白衬衫的干部模样的小伙子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对着验票员用普通话说:“我们一道在油扎上的,让他走吧。”
验票员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收了两毛钱,放我上了岸。
我追上在路边等我的表哥,他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哎呀,忘记和你说了,你这个土老逼,要说普通话呀。”
二
老家话是土得掉渣。美丽的玫瑰叫“刺介子”。捕害虫的青蛙叫笡翎谷鸡。有的词,翻遍《辞海》也找不到发音,找不到对应的字。垾子的垾在《新华字典》中就没有这个发音。最新的电脑里也打不出来这个字。划船的小桨,我们称为苗子的,也没有这个词,后来,我就用杪子来代替。睡觉,圩乡的话是“歪告”,土!但后来读到《红楼梦》中有相同的表述就释然了,甚至有些自诩的意思了。当然,也有本地的街上人,讲“睡告”或“歪觉”。一个词,半江瑟瑟半江红,一半普通话的发音,一半方言的发音,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真正的洋腔怪调了。
圩乡有两种人,很容易被人说为洋腔怪调的。一是读书回乡的,一是当兵回来的。他们在圩乡话语中常常夹杂着普通话的句子,词汇,发音,大家听着就很别扭。有时候大家就把他们说的词汇当作笑料,讥讽为“种田不如老子,烧饭不如嫂子,打枪中不了靶子,说话还带调子”。那时,圩乡人很排斥外来语,要想融入这片土地就要入乡随“话”。遇到外地人在这儿生活的,就直接以他们的语种称呼,什么“上海佬”“江北佬”“湖北佬”等等,这里面多少有些无伤大雅的地域歧视的意思了。
这样,圩乡的语言就有非常大的吸附力。我们村上有六个兄弟,他们的爷爷辈,是从湖北迁来的。从我记事起一直以为他们是本地人,因为到他们这一辈已经能够讲一口地道的圩乡话了,丝毫感觉不出他们曾是外乡人。到城里工作后,我发现同样和他们祖辈一道移民宣城南乡的,传了几代,大多还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
有的圩乡话有些粗俗不堪,但却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甚至精准到纳米级程度。如对动物发情的观察,圩乡话丰富复杂,同样是牲口发情,不同的牲口就有不同的表述。
狗,叫打链。为什么叫打链呢?铁匠打链是有动静的。一打铁,二打铁,叮叮当当,炉火闪烁,煤灰飞扬。赤膊上身,锤子一敲一敲,很有韵律,那绝对是体力活,技术活。狗子打链就不同了,不声不响,不选地方,不问时间。道路上,稻场上,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那里,屁股对着屁股,默默的,两条狗,一公一母,较着劲。当然也有公多母少,雌雄失衡的时候,一群狗相互追逐,把正在生长的油菜、麦苗打倒一大片,惹得庄户人家跳脚大骂。骂谁呢?无所指,心疼而已。这就叫狗子“起草”,因为母狗叫草狗。
一次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大家激情昂扬,歌声一路。到了一个村庄的村头,依然高歌猛嘶。春夜的乡村是安静的,一群小公鸡头(圩乡人对青春期男孩的称呼)的歌唱便声震田野。正当大家十分忘情又嘻嘻哈哈之时,村头人家的大门打开了,同学的母亲大声骂道:“你们起草啊!”
大家顿时安静了下来,这话就太重了,这是骂我们都是狗子,且是正在发情的狗。估计那时人人脸上都像贴了红纸。太扰民了,却不自知,惭愧得很。大家一路走回去,不再作声。后来,我们白天从那里走,从不敢正眼看同学的母亲,却发现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来去。想来,那天晚上她并不知道是我们一帮家伙,但我从此总是对她没有丝毫的好感。
牛,就不叫起草了,谓之“起云”。夏日,天边一片云脚渐起,黑压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狂风中席卷而来,蔚为壮观。牛,作为圩乡的最大牲畜,为了爱情,也绝对有这个气势。有时几头牯牛争红了眼,扬蹄狂奔,以头相撞,以角相逐,直斗得田野尘土飞扬,云烟弥漫,地动山摇。有的村庄为了确保本村的大牯牛立于不败之地,用煮熟的山芋戳进坚硬的牛角,待牛角受热柔软后,再用锋利的镰刀把牛角修尖,让这头牛在角斗中更有杀伤力。真佩服这片土地上的先人,有如此的想象力,为牛的爱情创造了“起云”这么一个词,实在伟大!
而母猫发情就不同了,圩乡人称“叫号”。春天的夜晚,整个村庄惊天动地,像小孩没奶吃了一样,叫得撕心裂肺,说它“叫号”也是相当贴切了。
普通话里绝对没有分得如此之细。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种爱在语言里的蔓延。是圩乡人,与每一头牲畜,甚至每一种生物相处中,细心观察、平等相待、真诚惜护的体现。是一种独怜幽草,心系苍生的情怀。只有俯下身子才能看见蚂蚁就在脚下爬行。正如海子的诗所写的“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记得在老家,燕子在屋梁上做窝,每家每户都会用一只竹篮子在窝下兜着。这样既防止刚孵出的小燕子掉出来摔死,又不让燕屎洒落地面破坏堂前的干净卫生。每家每户的门都是木质的,且不严丝合缝,出外劳动,走亲访友,主人都會把锁好的门往里推一下,以便留出燕子回家的门缝。主人不在家,燕子俨然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于是,房子也不会寂寞,叽叽喳喳,生机无限。这不就是圩乡人心底的“春暖花开,面朝大海”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远远地落伍于圩乡的先人。比起他们,我们显得麻木,粗疏,不能融入这片天地,也可以说太自我了。实际上应该是现代科技和城市生活,在我们与这片土地上的风雨雷电,草木花卉,猪狗牛羊之间,设置了一道无形的交流屏障。面对着丰富的自然不再那么心动于中,情发于身。
三
家乡语言的源头有的又直承文言,有点高雅的味道。如今仍有许多文言词汇活在口语中。圩乡人称老婆为“内眷”。媳妇专指儿媳妇,是公婆对儿子内眷的称呼。还有如聒经(讲故事),关饷(开工资),静烦(僻静),枵(薄),晏(晚)等等。在形容词后面直接加一个语气词“煞”表示程度,相当于普通话前缀程度副词“很”。如痛煞(很痛苦),吓煞(很害怕),喜煞(很快乐)等。
圩乡水多,水多鱼多。所以吃鱼杀鱼这项活动比较频繁。鱼下锅之前这个被清理的过程,在圩乡一直传承着古汉语中的说法——徲。每一位水嫂不仅有烧鱼的手艺,还有徲鱼的本事。
家乡的方言保留了古汉语最大的也是最优美的一个声调——入声。它和粤语、闽南话一样,语音层次更丰富更复杂,听起来更优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入声字已经消失了。所有入声字都被派入了普通话的现代四声中。而圩乡方言却保存了中古音系,有大量的入声字。如家去、雪白、磉壳、圪蚤、嚇怕、斫稻等等。
有一句俗话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里的“孩子”应该是“鞋子”,稍一思量便知,为了打到一只狼,要置孩子于不顾,不近情理了。“鞋子”在圩乡话中就读“hái zi”,这是古音在吴语方言中的遗存。所以这句俗语本意是,要想捕捉到狼,就要不怕多跑路,不怕浪费鞋子。如此,就合情合理了。
许多唐诗用我们圩乡方言来朗诵,便觉完全合韵。如唐卢纶的《春词》:北苑罗裙带(dài),尘衢锦绣鞋(hái)。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mái)。如杜
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xiá),
白云深处有人家(jiā)。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huā)。圩乡话骂一个人不正经,就说这个人“斜撇倒歪”,这里的“斜”就读xiá。
圩乡话中对时间的表述,也有一些古汉语的影子。如封岁(除夕晚饭后的一段时间),旧年(去年),赫朝(昨天),中朗(中午)等。
圩乡人文化底蕴深厚。重伦理,崇礼仪,忠孝传统,耕读传家的理念根深蒂固。于是方言中便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和地域文化。圩乡语言很形象,讲起来特有嚼头。一次,我们车行在水阳江畔的堤岸上,看到江里的铁驳船上装载的货满满的,有人就说:“个船啊装的扑浪浪。”没有了普通话副词加形容词的那种平淡,而是船扑波浪,十分动感。此外,小孩子把鸡和鸡蛋,叫“嘎嘎鸡”“嘎嘎蛋”。象声词在前,既生动传神,又体现出浓浓的爱意。
圩乡方言中只有“对弓”,没有“笔直”,是直接来自军事用语,也可以说“对弓对”。因为金宝圩就是东吴大将丁奉率领军士围湖屯垦的杰作。至于把“闪电”叫作“擦黑”,就更有意思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表述了。“闪电”可以说是见景是景,“擦黑”就很明显带着一种憧憬了。
圩乡人讲一个人智商高,办事灵活,就说这个人“灵空”。情商高,做事麻利就叫“麻溜”。麻溜的反面叫 “脚色”,在普通话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了。女孩长得好看叫“体面”,也可以用复词——“这个小孩长得体体面面”。当然,也有的圩乡话讲起来显得有些刻薄。如“看人家拉屎喉咙痒”,骂喜欢闲逛的人叫“跑风”“跑骚”等等。
圩乡的方言柔软,在口语化的过程中,为适应口语的不可重复性,突破书面语的简洁简练,衍生出大量的“子”式词。即在名词后缀“子”字,使这些词带上感情色彩。如鲤鱼包子(腿肚子),妈妈娘子(妇女),寡屌汉子(单身汉),手巾捏子(手绢儿),火萤子(萤火虫),呜蜂子(蜜蜂)等等。也有“伙罗”式后缀词,如叔妹伙罗(妯娌),姻亲伙罗(连襟),兄弟伙罗等等。这些词在圩乡口语中的出现,让圩乡话听起来更加婉转抚媚,温柔细软。吴韵乡音,特色明显。
奇怪的是,圩乡话里没有“左”和“右”这两个概念,左手叫反手,右手叫正手。方向上就是东南西北。房屋建造一律坐北朝南,出门就说,朝东,朝西。甚至连圩乡的沟渠开挖,也是要么距东距西一条龙,要么距南距北一条线,格格整整。小时候上体育课,老师让向左转或向右转,对圩乡孩子挺费劲,一个口令,大家两边各转各的是常有的事,因为自小没有“左”和“右”这个认知。
有一句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圩乡话中有许多打着“老人家”的名义而流传已久且充满智慧的谚语和俗语。这位“老人家”是圩乡人心中地位显赫的权威人士。小时候奶奶不让我喝汤,她说:“老人家说,吃饭若喝汤,走路要人搀。”我说:“你不就是老人家吗?还有哪个老人家?”她哈哈大笑,说:“老人家就是老人家,传下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圩乡一位聪明的老人,是圩乡多少代智慧老人的集合。他说的话是大家在生活中代代相传、积淀,不断扬弃、丰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经验、道理的总结。如关于做人的:穷不失志,富不癫狂;嘴稳手稳,处处好安身;纸里包不住火,雪里藏不住尸。如批评懒汉的:横草不捡,竖草不拈,踢倒油瓶不扶。如形容人不能脚踏实地,讲得多做得少,不能知行合一的:晚上想想一千桩,早上起来是个青桩。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当地气候的谚语:鸡叫中,鸭叫风;乌云盖东,晴不到中;雪不烊,候老娘;东打雷,西擦黑,有雨不在当地落;雨落霉头,烂掉犁头;干净冬至邋遢年。
还有如说人刚愎自用是“茅屎缸上的一块石头又臭又硬”;说人不会思考叫“搬到鼻子当枕头”;骂人没有骨气是“烂泥扶不上墙”;说一件事注定没有结果是“痴狗望着羊卵脬”,这绝对比北方话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生动传神接地气。至于“官众堂屋鸡屎臭”这一句,简直就是经济学术语“公地悲剧”的通俗版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人心是相仿的,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是顶级经济学家,还是偏居圩乡的乡叟野老,只要遵循常识,追求至真,对规律的认识都会殊途同归。
圩乡话中也有些词汇和普通话完全对不上号。外面人无论从发音还是字面都找不到搭界的地方。如:量子—水桶,藏—囥,蚯蚓—卧涗,癞蛤蟆—叫浆癞蛤宝宝,调解—开交,巫师—马甲等等。
四
一个地方有方言,就会有用方言演唱的歌曲,也会有用方言演绎的戏曲。这是农耕文明时代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是人们辛勤劳作之余的彩头,也是生活中情感倾诉的方式。圩乡自然也不例外,山歌,船歌,栽秧歌,打麦歌,打夯歌,颂春歌等,不一而足。圩乡老老少少不说张口就来,也基本上个个都能来上一两段。
出门山歌进门戏。圩乡人曾经看戏成风。如今,这圩乡深处的荒腔走板,已然与土生土长的方言一道与冬日的夕阳斜挂西山,面对着清冷的大地,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丝乡愁的慰藉,还有那淡淡的念想。
夕阳的余晖渐渐散去,村庄上空的炊烟弥漫成夜色中的迷雾。一面红旗在大队部的土台前风展猎猎,碧水漾漾的沟稍里停满了四面八方划来的船只。喧闹的锣鼓声响彻原野。这里正在演戏,一盏汽油灯高悬台前,照得台前台后一片明亮。土台没有麦克风,演员全是本队的社员,全凭一副好嗓子,高时如天外鸣鹤,低时似花下呢喃,演的人全情投入,看的人随戏转情,聚精会神。
台上演的是《智取威虎山》。这时正唱到第九场,高波向少剑波报告,小火车遭到土匪袭击,一撮毛炸死,栾平跑了。这时只听台上传出一段对白:
“报告二○三,不得了,小火车炸得了。”
“两个土匪呢?”
“一撮毛炸死的了,小炉匠跑的咯。”
“杨子荣同志有危险了。”
演员也许是忘了台词,也许本身识字不多,有的对白就是按照当时的场景用本地方言自由演绎。看戏的人多是本地人,因而并不觉得违和。
台上一本正经,台下一片哄笑。
那天,刚到生产队下放的知青听了这混搭土气的对白,笑得合不拢嘴。多少年后,当年的知青成了我的领导,每遇到我就会提起这段往事并感慨,圩乡话真有意思!
教戏的是从高淳请来的戏剧名角方师傅,一表人才,满腹才情,教得十分认真。那时每个人都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渴望用戏剧激发出那贫乏的业余生活中潜伏着的精神诉求,每个人排戏、唱戏的热情十分高涨。女主角“阿庆嫂”,身姿曼妙,婀娜有韵,唱腔线条婉转,酣畅中蕴含着明丽,细腻中彰显着清爽,真是声如燕鸣,甜蜜而纯美。虽是农家子女,却在乡村舞台脱颖而出,自然也受到了方师傅的格外关照。
当年方师傅虽已近而立之年,却因出身问题,依然单身一人。终于,日久生情,方师傅和女主角排戏之余谈起了恋爱。有人提醒方师傅,“阿庆嫂”已被父母口头定亲给正在服役的军人。方师傅说:“礼字归礼字,法字归法字,我们两个你情我愿,不怪事。”
哪知对方的家属知道后,一封信写给了部队,部队派人来调查,方师傅随即被关进了牢房。自此戏班子散了,从此圩乡田野的夜晚,无论风雨如晦,还是弦月高悬,又沉浸在一片冷冷清清的寂寞之中。
“阿庆嫂”终是不甘父母的安排,男方也不再接纳“身败名裂”的她。后来有人在圩乡,看到她蓬头垢面,头戴一顶柳枝苇叶扎成的帽子,跣足而行于荒野,哀哀离离,词不成调,“阿庆嫂”把生活当作了舞台。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把一颗受伤的心妥妥地融入到了清澈的大沟。
多年后,方师傅重返生活的舞台,常说的一句圩乡话就是:“人家的事情,明明白白;自家的事情,惑里惑脦。”浓郁的乡音中吐露出对人生的透彻和无奈。
五
故土多情,乡音有韵。我在城里住的是学区房,圩乡人陆续进城读书,陪读的家长一开口常常能听到熟悉的乡音,一发声,那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于是便很自然地用家乡的方言相互聊上几句。临再见,被陪读书的孩子永远是标准的普通话说:叔叔,再见。
我想,这一代陪读的父母,大概是圩乡能熟练掌握圩乡方言的最后一代了。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我们的吴韵乡音,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终将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失。
總有那么一天,圩乡的后人也能听懂柴可夫斯基、莫扎特,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却终究听不懂这里不同鸟的叫声,辨别不出这里每一棵草的名字,忘记了那一口婉转妩媚,温柔敦厚的吴侬软语。
终究会这样的。
责任编辑 曾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