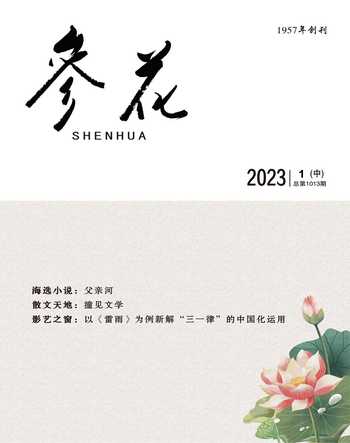刨花飘香的岁月(外一篇)
2023-05-30王垄
春风习习,桃红柳绿,在莺歌燕舞之间,老家的小院子里又传来了“扑哧扑哧”的声音,一位乡村木匠浑身上下落满了木屑。只见他拉开弓箭步,前腿弯,后腿撑,腰部稍微前倾,双手平端刨子,十指紧扣刨沿,用力推刨。随着他娴熟连续的动作,一串串刨花打着卷儿从刨口中吐出,在眼前轻轻弹跳、飞跃一下,便以优美的弧形曲线,轻盈地落到地面,层层叠叠的刨花堆积如小雪山。随之,一股股迷人的木香升起,弥漫在农家天井的每一个角落……
以上是我儿时无比熟悉的场景,如今却只能偶尔在梦中呈现。那从木匠师傅的刨子里神奇涌出的刨花,如瀑布,似卷云,薄如蝉翼,芳香四溢,曾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过无穷的乐趣。也许现在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刨花,有必要科普一下。刨花,顾名思义,是木匠用刨子在木头上刨出来的薄片,弯曲叠卷,形似花朵,因此叫作刨花。打小时候起,我就对刨花情有独钟、很是着迷,觉得它们一片片、一朵朵的像可爱的小仙女,薄薄地卷着、调皮地跳着,犹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又似淘气十足的精灵。
那年头,木匠被称为手艺人,父母常教育我们说:“不好好读书,将来没出息,就学个木匠手艺混饭吃!”可我倒觉得木匠挺能干,全庄也没有几个。印象中,刘姓一家基本都是木匠。我们常去刘家玩,看那一屋子的木匠工具,诸如斧子、刨子、锯子、尺子、墨斗、凿子,等等,一件件被磨得滑溜溜、油光光的,仿佛被岁月打了一层浆,每一样都有神秘莫测的力量。其中,刨花的“制造者”刨子对我诱惑很大。记得小学课堂上,老师让我们猜一个谜语,谜面是“奇怪奇怪真奇怪,脊背上冒出花儿来”,打一木匠工具,我能一口报出谜底——刨子。
用刨子刨花的目的在于使板材变得更加平整、光滑,这也是木匠的基本功。老师傅刘延山是庄上带徒最多的木匠。他有过一只红木刨子,据说是祖传的宝贝,表面特别光滑、油亮,刨口锋利无比。拿在手上沉甸甸的,非一般人能轻易使得。他推刨时,手眼身腰步协调动作,富有节奏感,能让我情不自禁地望上半天。老刘刨出的木卷从刨子“脊背”上的孔缝处飞出,白花花,香喷喷,好看又好闻。多年以后,我一吃涮羊肉,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老刘师傅的刨花,二者是不是太像了?
想当年,农村人打家具、修木船等,都得请木匠。木匠一上门,少不了刨花满地、木香弥散。槐树的刨花气味微甜,桑树的刨花带着泥土的芬芳,柳树的刨花略显苦涩,松柏的刨花有股松香味儿……不同木质刨出了不同的花香,每一种都能使我沉醉、入神。过去的乡村,柴草也是金贵的,刨花是上好的柴火,不容浪费。我最乐意替母亲“收集”刨花:用一只柳编的篮子装满刨花,使劲儿压实,愈满愈好,然后倒进锅屋的灶膛边,引火做饭的材料就有了,我也顺带弄了一身青草和野花杂糅的刨花香。有一次,我竟在一群木匠钉船(新打一条船)的刨花堆里睡着了,梦见刨花自由铺展着,随心所欲,松软飘逸,它们飞舞着,飞成了家乡天边的云彩。炊烟袅袅中,大地一片丰收、欢乐的景象……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家家户户的家具都买现成的了,加之老木匠相继作古,木匠手艺无人肯学,故乡的木匠近乎消失。镇上仅有的一家木器店也全用机器代替人工,基本不见老式木匠活儿的踪影。唯有清香扑鼻的刨花还时常像彩云一样在我梦中美丽,我知道,刨花飘香的岁月,早已沉浸在我的脑海,镌刻在我灵魂深处。
母亲的酱瓣
那一次,陪八十六岁的母亲逛超市,老人家在调味品专柜前逗留了很久,盯着各种各样的豆酱若有所思。我根据母亲的意思,买了一瓶豆瓣酱给她,回家吃了以后,母亲却略有失望,喃喃自语道:“不如从前的酱瓣好吃哟!”
母亲口中的酱瓣,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乡下人晒的豆瓣酱,老家一律称之为“酱瓣”。那时,能够吃到的“咸”(土语读“韩”音,“菜”的意思)很少,腌菜、腌萝卜、腌臭卤等是庄上家家户户必做的事,大伏天晒酱瓣也是农村随处可见的风景。打记事起,我就在夏天看母亲晒酱瓣,一年又一年,一年也不落。母亲晒的酱瓣色好味美,现在想起来,仍像陈年老酒一样,在唇齿之间历久弥香。
母亲的酱瓣多用黄豆晒制,有的年份也会用蚕豆或豌豆来做。这些豆子都是故乡常种的,不稀奇。但作为制酱的原料,所用的豆子却马虎不得,母亲总是经过筛选(有破损或虫眼的一律不要),然后用淘箩子将豆子淘干净放在撇缸里浸泡,等豆子一个个发胖了,再倒进铁锅里,烀到恰到好处的熟,捞出锅在大竹匾里爽干凉透,滚上一层面粉。接下来就是“焐酱”,母亲会将弄好的酱料包裹起来,“藏”在被胎或穰草里焐上几天。这个程序很关键,一缸酱好不好,取决于焐酱时有没有焐出真正的“酱黄子”,也就是看成团的豆子上见不见铜绿色的霉斑。可别小看了霉豆上那如刚孵出窝的鸡雏鸭仔身上绒毛般的“外衣”,只有先白后碧、嫩黄间杂浅绿,才是纯正、均匀的颜色,表明豆瓣发酵得很正常。如果长出“黑毛”,一缸豆子就报废了。印象中,母亲制酱从未失过手。
母亲有时也会动用“小劳力”。焐酱、晒酱少不了乡村纯天然的宝物——艾叶、荷叶等。母亲便让我们去野地、藕塘里采摘,用来垫底和覆蓋。母亲也用我们打来的芦秫、玉米,甚至苘麻的叶子代替过,效果大差不离。晒酱的过程得有十天半月,那些日子,农家茅草屋门口,火辣辣的太阳下,一个个酱架子上支着酱缸。一股股特别的酱香味一天比一天浓郁,它们随着热风在庄子里飘荡,那是我至今难忘的芬芳。当年母亲给我们的任务是“看缸”:母亲的酱瓣日晒夜露,酱缸上没有盖子,顶多覆一条干净的三角首巾或一层白纱布,也有用一块细眼渔网遮挡的。母亲说,这样晒出的酱瓣才会鲜得吊人胃口。白天,我们要对酱缸进行守护,防止鸡狗以及苍蝇蚊虫等的破坏,母亲们的辛苦劳动可不能白费了。我们还会按照母亲教会的法子,适时用一根长长的竹筷或长柄的勺子在酱缸里搅拌,使豆瓣发酵均匀,上下一色。母亲告诉我们,当酱缸里的酱料一天天稠实、颜色也由土黄变深红时,酱瓣就算晒成了。母亲用食指尖蘸一点放到嘴里尝尝,还会弄一小块给我们咂味,真的是“又甜又香,吃了过江”哩。母亲笑了,仿佛只要有一缸酱瓣在,心里就有了底气。我们也跟着笑起来。
母亲的酱瓣救了饭桌上的不少急。酱瓣属于“百搭”的佐菜,既可以在饭锅头上炖熟了,用来吃粥、下饭,也可以在烧菜时放上酱瓣调味,无论荤菜素菜,都能蘸着酱瓣吃,那浓浓的酱香味道,总会让人忍不住垂涎三尺。记得我到离家很远的乡镇读高中时,母亲让我带过几回豆瓣酱。当我与同宿舍的好友分享时,没有一个不夸母亲晒的豆瓣酱“真好吃”的。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大大小小的商店、超市里都有了五花八门的豆瓣酱在出售,庄上再也不见晒酱的了。如今,母亲年事已高,做不了晒酱一类的事了,母亲那柔和鲜美的酱瓣永远成了美好的回忆。某一天和母亲一起在老家看电视,竟然看到传统晒酱的画面,看着那一坛坛、一缸缸老式的酱瓣,我和母亲仿佛都闻到了酽酽的酱香,便觉得时光倒转,回味绵长。
作者简介:王垄,笔名阿黾,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被选入《中国新诗人成名作选》《中国当代诗歌导读1949-2009》等近百种选本,部分被译成外文。出版诗或散文集18部。长篇散文诗《柳堡风》入选江苏省作家协会第十批重点扶持文学工程项目。
(责任编辑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