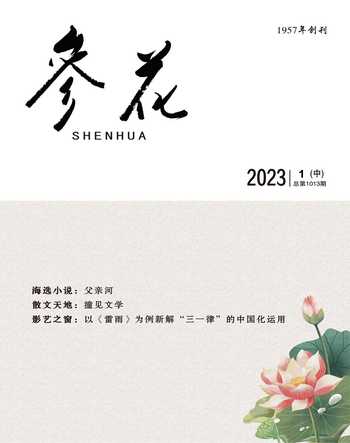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异秉》的重写与身份问题分析
2023-05-30王熳琳
汪曾祺在1941年发表的《灯下》与后两版《异秉》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在《灯下》中,王二没有说出那句“大小解分清”,情节上的差异显示出《灯下》与两版《异秉》主题上的差别。汪曾祺对《灯下》的改写,不仅改变了小说的主题和框架结构,也影响了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学徒陈相公和卖熏烧卤味的王二的形象都有所改变,因此,本文立足于《异秉》的重写,以探究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身份问题。
一、《异秉》的前身——《灯下》
《灯下》这篇小说以散点透视法写成,“写一个小店铺在上灯以后各种人物的言谈行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1]从来买丝麻糖的顾客开始,小说中的各种人物依次亮相。在他们的谈话中,王二与陈相公这两个人物始终处于边缘位置,他们更多的是聆听别人说话。在《灯下》中,王二和陈相公的身份背景都未交代,读者无法从现有的文字中得知这二人的过往,仅能依据小说对两人的描写为其画像。陈相公是一个一脸胡子且有些憨傻的壮小伙,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上还留有一份天真。他会在汽油灯亮了时,心中有小小的得意,也会在老炳离开时,吐槽老炳拿了杯子不放回去。与尚在店里旁听插话的陈相公不同,从未进店的王二更像一位局外人。小说开始时,王二的生意正忙,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仅可以将商品麻溜地拾掇好交给客人,还能一瞥钱即知数目,甚至不忘招呼其他顾客。待生意不太忙时,他本想进店里坐一会儿,然而回头看到儿子在打盹,他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小说没有对王二的家庭关系和生意情况做更多展开,然而王二行事干练的形象却立了起来。
创作《灯下》时,汪曾祺还是学生,但他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已有“神韵”,这种“神”的凝聚来自汪曾祺对人物言行举止的精妙刻画,只凭空想是无法描绘出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的。汪曾祺的祖父开过两家药店,汪曾祺以前经常去药店玩,他对中药的加工极为熟悉,甚至还摊过膏药。尽管这篇小说是“小城灯下的人物速写”,[2]但作家取材于生活,小说与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很贴近的。
二、1948版《异秉》与王二的塑造
1948版的《异秉》对《灯下》的改写,反映了汪曾祺源自生活的经验变化。在从学生身份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中,汪曾祺越发体会到生活的不易,身份的改变使他愈发了解人民大众的生活。早在1946年8月,汪曾祺在上海找工作时就屡屡碰壁,他后来的一些工作也是托别人帮忙找来的。[3]汪曾祺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与前路的迷茫,正如他所言:“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4]所以1948版的《异秉》不再是无主要人物与情节的闲谈,而以善意的揶揄道出其对生活的思考。体现在创作上,最明显的是王二成了中心人物,这首先表现在小说耗费了大量篇幅为王二的出场做铺垫。小说前十一段描绘了保全堂内的布置和在店里闲聊的客人,这些客人都在等待王二。然而小说再次将王二的正式出场延宕,之后的段落详细介绍了王二的摊子。在第十七段,王二才终于出场,因此,在这一版《异秉》里,王二是绝对的中心人物。
1948版的《异秉》,从家庭和社会关系两方面为王二画像,小说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将王二身份的变化道出。这一版以陆先生之口引出“王义和”号,由此点明店与摊子的差别。尽管王二只是租了旱烟店的半间门面,但他的生意已实现由摊至店的转变,这使他的阶层得到提升,王二的社会身份因此发生变化。小說分两种情况对王二身份的变化进行叙述,一种是王二自己与其社会关系中的“他者”进行比较,另外一种则是“他者”对王二的凝视。在这店里的人都不是有优越感的人,但王二却是极有分寸的。在店里时,他从不随意打断别人的谈话,因为这里不仅有店里的“先生”,还有在外面做过师爷的人,这些人是会识字、写字的文化人。因此,当王二从其社会关系出发而与“他者”进行比较时,他的目光是向上的,王二对比的不是学徒之流,而是“先生”“师爷”之辈。王二在进行这种对比时,将店堂里的人群进行了“社会类化”。“社会类化”指“将对象、事件和人进行归类,找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群别”,[5]对王二而言,店里的“先生”,还有客人“师爷”都是其外群体。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王二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尽管他已发迹,但他对这些能写出一封“某某仁翁台电”的人是“不敢乱来”的,由此可以看出王二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指的是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表现为三个层面,即价值认同、职业认同和角色认同。”[6]王二对读书人的尊敬体现了沿袭下来的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指个体对社会的基本原则及行为规范的认同”,[7]这也体现在王二的行为上,他听人讲话时是谦虚的,他坐着时“像做官的见上司一样,不落落实实的坐”。[8]
但王二也并非自轻自贱之人,他对未来也有美好的畅想,当其他人叫他“二老板”进行恭贺时,他的心也会激动地跳跃。这种激动实质是王二对自己所处阶层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更为明显地表现在众人推求缘何王二能发迹时他的反应上。“王二这回很勇敢,用一种非常严重的声音,声音几乎有点抖,说:‘我呀,我有一个好处:大小解分清。大便时不小便。喏,上毛房时,不是大便小便一齐来。他是坐着说的,但听声音是笔直的站着。”[9]前半部分穷尽笔墨描写王二的谦虚并非作家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是将王二平日的谦虚与其最后的勇敢形成鲜明对比,如此反差,显示出王二对自己的真实认知:他将自己归类于“穷达”,他认同那句“一个人多少有点异像,才能发”,而“大小解分清”则是他认为自己不同于常人的能力,这就是王二对自己身为常人的不认同,对其身为异秉人士的认同。
“他者”对王二的凝视首先体现在店里人群对王二的称谓上:平时与王二经常往来的人都对他改了称呼,叫他“二老板”,这是店堂里的那群人对王二的新的社会定位,这一声声“二老板”也展现了其他人对王二发迹的羡慕。小说在末尾以简短的笔墨道出王二从清贫至富裕的发家史,篇幅不长,却表明王二的发迹并非一蹴而就,他是从辛苦中走出来的。正因为辛苦,王二可以发迹,所以其他人也会以王二自照,是不是他们也有这样的一天。有这样想法并付出行动的是学徒,即《灯下》里的陈相公。相较于《灯下》,这一版的陈相公更加边缘化,甚至连“陈相公”这个称谓都失去了,小说对他的称呼就是“学徒的”。这并非说他不重要,正是因为他,才有了最后那句“学徒的上茅房”,也正是这句话道尽了作者对普通人善意的嘲弄。学徒认为王二是“幸运儿”,这与其他人对王二异秉的追问是殊途同归的。在当时,普通人无法为自己觅得真正的出路,于是只能找一些虚无缥缈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与王二相比,白天做不好活儿会被骂的学徒才是最边缘的。从学徒对王二的凝视中可以看出,学徒对自己所处群体的不认同,因此,他才羡慕王二的发达,正是这种对发达的渴望使学徒在最后付诸行动:他去上了个茅房,企图找出自己的异秉。
三、1980版《异秉》与陈相公的身份焦虑
1980年距1948年,已过三十二年,汪曾祺在这三十多年间,身份几经变换,丰富的人生经历也使他对生活有了不同层次的理解。总体来说,在这段时间,他的工作尚算安稳。后在1961年回到北京担任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在此期间,汪曾祺时常去剧本故事的发生地体验生活、收集素材。[10]这些创作经验使汪曾祺在创作观上发生了变化,他身份的改变使其在创作时对普通人更多了一丝温情,在叙述小人物的生活时,不再是揶揄与冷嘲,而是阅遍人间酸甜苦辣后的一声苦涩的叹息。他的创作也因此发生了改变,1980版的《异秉》最大的改变,是将陈相公与王二一同突出来。
1980版的《异秉》有三条线,第一条是王二和他的熏烧摊子,第二条是保全堂和陈相公,第三条是保全堂里的夜生活。小说先从王二写起,介绍了王二及其家庭和熏烧摊子后,又叙述了王二的发达与街上其他店铺的败落,尔后详细介绍了保全堂的人事制度及学徒陈相公的一天和其挨打的日常。紧接着,小说写到夜晚的保全堂高朋满座,也因此引出了张汉对王二异秉的发问,最后以陈相公上茅房大解做结。小说脉络清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愈见饱满,较之前两版,王二与陈相公的形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這一版里,小说以后街人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反衬王二家庭关系的和谐。和谐的家庭关系离不开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努力,王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其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1948版中,获得新身份的王二尚未良好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待人接物时尚显拘谨。但在1980版里,王二变得从容了。在前一版本中,当店里的人聊到“雷打泰山庙旗杆”之事时,王二明明想插一嘴话,可因为夜里还有零星几个生意而没进店里,直到快八点才收摊进店。1980版中,小说以几处生活细节上的变动将王二身份变化后心态上的变化展现了出来:王二不仅端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边听人聊天,边用眼睛顾着摊子,他的生活也有了很多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可以不用在意钱与时间而自由地去茶馆听书了。王二未发达前,听书需要再三思虑的主要原因就是其身份问题,内因在王二自己,他怕花钱、花时间,也怕别人议论。别人的议论就是王二忧虑的外因,别人的看法则反映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小商贩所处的社会地位不高,因此,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奔波操劳的,他们应当做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事,怎么能时常消遣享受呢?其二就是过年推牌九时,他可以不再犹豫地下注,不再犹豫,自然是因为他有钱了、发达了。这种生活和心态上的变化,展现了王二身份焦虑的消失。在这两版里,王二都认同了异秉之说,认为自己的“大小解分清”确实是一种异秉,这其实是王二身为一个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认识。
陈相公的身份焦虑与王二不同,因为他是保全堂的第四等人。小说对陈相公的刻画从其平凡而又琐碎的一天展开。陈相公是全保全堂起得最早的人,他不仅要做晒药、收药、碾药、摊膏药等杂事,还要倒涮“先生”们的尿壶。陈相公的生活是充满苦与泪的。他经常因为做错事挨打,尤其是有一次收药时,因踩空导致泽泻翻进阴沟,他挨了许先生的打。可他被打的时候是不敢哭泣的,只有晚上一个人时才敢将心中的委屈哭诉出来,陈相公地位的低下由此表现出来。他没有反抗,因为他认同这种人事等级制度,也因为他身在远方的寡母,在他眼中,学徒挨够三年打就可以养活自己的母亲了。陈相公的身份焦虑与其处于店里最低的地位有关,但他还是渴望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并为此做了努力。首先是在每天睡前背《汤头歌诀》,因为“药店的先生总要懂一点医道”,这是他在为自己谋划前路,等到他学完生意,就不再是学徒了,因此,他认为自己多学一些技能总是有用的。其次就是在每月初一、十五给赵公明元帅和神农爷烧香时,他格外虔诚,赵公明元帅在民间与发财进宝相关,神农爷则与救人治病相关。陈相公对这二位神仙恭敬的态度其实反映了他心底的渴望:是不是自己越虔诚,便越能得到神仙的眷顾。除此之外,他还在听王二说完自己的异秉后就去厕所尝试解大手。与前一版的冷嘲不同,在这一版里,汪曾祺将自己对小人物悲苦生活的体恤融进了文字之中,因此,在读者为陈相公迫不及待上厕所而会心一笑后,会深觉其中的苦涩。
四、结语
本文以《异秉》的三次重写,探究了小说中人物的身份问题。以散点透视法所写的《灯下》是汪曾祺学生时代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却并未触及普通人民对地位和身份变换的渴望;发表于1948年的《异秉》以王二为主人公,叙述了王二的身份焦虑问题,但小说对老百姓则以冷嘲居多,这与作家本人当时未明的前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至1980年的第三次重写,汪曾祺则怀着悲悯的心,以幽默的方式将陈相公和陶先生这些小人物的悲苦一一道来,而隐藏于这些人物的笑与泪的背后,则是他们对身份的焦虑,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70-77.
[2]杨早.四十年间 三写《异秉》——兼论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J].南方文坛,2020(03):5-15.
[3]徐强.汪曾祺文学年谱(上)[J].东吴学术,2015(04):118-132.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5][6][7]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5(01):21-27.
[8][9]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0]徐强.汪曾祺文学年谱(中)[J].东吴学术,2015(05):116-130.
(作者简介:王熳琳,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