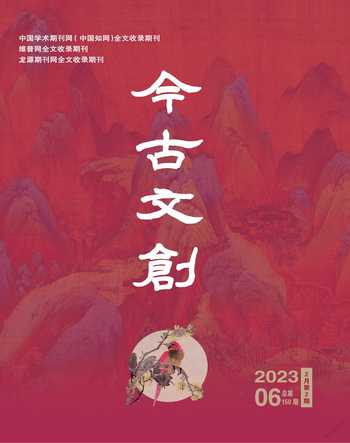论《搜神记》中人鬼恋情节体现的文化内涵
2023-05-30何雨晴
何雨晴
【摘要】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人鬼恋情节由来已久,且逐步发展壮大,《搜神记》中的人鬼恋情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人鬼恋情节呈现的状态有所不同,体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对人鬼恋的描绘有不同的模式。《搜神记》中的人鬼恋情节独具特色且情节描写更加细腻。本文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探讨了《搜神记》人鬼恋情节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包括天人感应、乐生恶死、男权意识等文化内涵。
【关键词】《搜神记》;人鬼恋;天人感应;乐生恶死;男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6-002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6.006
《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的故事情节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意蕴丰厚,现选取人鬼恋情节部分对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搜神记》中人鬼恋情节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有天人感应、乐生恶死和男权意识三个方面。
一、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学说实际上是一个和人鬼恋情节一样的渊源已久的概念,天人感应最早也可追溯到上古神话时代,这又不得不联系到上古时期的巫术文化。天人感应的天命观早期是和巫术息息相关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天人感应观念与巫术的联系逐渐淡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以后,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从西汉中晚期,社会上开始流行谶纬之风。这样一来,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笼罩着天人感应思想是顺其自然的,这是这一学说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天人感应思想和五行学说,阴阳之气的联系十分紧密,而《搜神记》中有专篇《论五行》,文中载“天有五气,万物化成……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苟禀此气,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有此气。”[1]说明干宝对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气化生的,同时,浊气化成的是怪物,和气化成的多是圣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干宝又在《临川刀劳鬼》中说道“气分则性异,域别则形殊。生者主阳,死者主阴。”[2]因此,想要达到阴阳调和的状态,必然要通过祈求上天,由上天降下祥瑞或灾难的方式。
尽管天人感应思想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但在人鬼恋情节中那些感天动地,令鬼物通过方术或现身托梦的方式得以诉衷肠、让鬼物死而复生的场景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天人感应。这里把天人感应的政治色彩平淡化并不是否认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是回归天人感应学说发生之初,即天是最初的权威,后来提到的君主权威实际上也都借助天的旨意让自己的权威发生作用。《搜神记》中人鬼恋情节体现的天人感应更多的是由于人内心真挚的感情才能够发生的,感性色彩浓厚。
《李少翁致神》中汉武帝因为对李夫人思念不已利用李少翁的致神之术成功见到了李夫人的魂魄,虽然李少翁可能是迫于权势或金钱的诱惑才为汉武帝作法,或者为了显示自己的法术高超,但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思念和深情也许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营陵道人令见死人》中营陵道人的同郡人说了一句“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3]营陵道人便帮助他见到了自己的夫人,营陵道人设法让他见到亡妻,一部分原因也是被同郡人的话感动了。这两则故事天人感应的中介均为方士,通过方士的帮助,上天对挚情之人的祥瑞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断头语》中断头的一句“使君,我相从,何图当尔”,[4]足以看出由浊气化成的鬼物对史良的怨恨,断头能够直接说话,是上天对史良行为的惩罚,也是对女鬼降下的祥瑞,让她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怨气。《苟奴见鬼》中的夏侯恺因为担心妻子,化身鬼魂陪伴在其左右,这也是上天对夏侯恺降下的祥瑞。《產亡点面》中米宗元那个因难产而死的、脸上点着墨点的妻子出现在他的梦里,这是对米宗元和妻子降下的祥瑞,二人可以在梦里再见一面。《紫玉与韩重》则是因为韩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于墓前”,[5]紫玉的鬼魂现身和韩重互诉衷肠,尽了三日的夫妻之礼。这也是上天对二人至真爱情的嘉奖。
其实最能体现天人感应思想的是《王道平妻》和《河间女》,这两篇文章中的女主人公都经历了死而复生环节,这是上天对人鬼之间至真的爱恋给予的最高层次的嘉奖。能够达到这样结果,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其一,生人悲痛不已,前往死者的墓前诉说不舍之情,情不能已。
其二,掘开死者的坟墓或者打开死者的棺木。
死而复生,二者缺一不可。
《王道平妻》中的王道平在听到爱人的死讯之后的表现是这样的“平悲号哽咽,三呼女名,绕墓悲苦,不能自止”,于是他祈求上苍“然汝有灵圣,使我见汝生平之面”[6],这与《紫玉与韩重》中韩重对紫玉的不舍之情可以一较高下,而紫玉未复生的重要原因是,紫玉并未像父喻告诉王道平自己还可以通过开棺复活一样告诉韩重,韩重也并未执行掘墓开棺的行动。
《河间女》中的男主人公知道女主人公的死讯之后,到了她的坟墓面前,“欲哭之尽哀,而不胜其情。”[7]于是,掘开了女主人公的坟墓,打开棺材,女主人公便复活了。这里的男主人公虽然没有得到女主人公的提示,但仍旧执行了这一操作,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王道平妻》的故事他早有耳闻,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男主人公情不能自已的诚心打动了上天。
《王道平妻》内容结尾处的一句话,已经显示出天人感应的思想的渗透。这句话是这样的“实谓精诚贯于天地,而获感应如此。”[6]
《搜神记》人鬼恋情节中的天人感应是此类情节发生的基础,只有天人之间能够感应互通,才能达到生死之间的转换,进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二、乐生恶死
生死问题向来是人们思量最多的问题,魏晋时期的人们更加不例外,尤其那个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主体意识的高扬促进了乐生恶死这一生死观的发展和确证。这一点,在《搜神记》人鬼恋情节中表达得更加清晰。冥婚习俗在学界被认为是人鬼恋情节的直接来源。中国民间习俗中会为早夭或死时无后的人进行婚配,冥婚习俗本身就蕴含着人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将人类世界的婚配延伸至死后的世界,传达着人们对死后世界的向往。“自周代制‘迁葬‘嫁殇禁律到民国二千多年间,冥婚之风长盛不衰, 无论庶民百姓还是帝王大夫,均尚此俗 。”[8] 可见,魏晋时期仍旧是存在这种习俗的。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把魏晋文人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对人生短促的感慨的核心归结为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如王羲之说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9]表面看似悲观、豁达,内在却含着对生的渴望和留恋。可知魏晋时期兴起的人鬼恋故事,情节或喜或悲,都在不同角度和层次上传达着作者的、那个时代的对生命的渴望。死去如同活着,是对这种态度最好的诠释。
与道家“齐万物,一死生”观念不同,儒家的观念是乐生恶死的。孔子、孟子、荀子都曾对生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0]《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11]《搜神记》人鬼恋情节直接体现儒家乐生恶死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人鬼在相貌、生活等方面基本无异。
其二,男女主人公传达着强烈地向生意识。
其三,对生死两种不同生命状态的差别对待。
《李少翁致神》篇中汉武帝见到的李夫人仿佛生前模樣,就是个身影也能勾起他的思念。死后的李夫人仍旧和生前的李夫人一样。《营陵道人令见死人》中,同郡人可以通往亡妻的棺木里与其言语,而并未觉得亡妻异常。《断头语》中的女子虽然只有头,但还是可以像生时那样说话,像生时那样有愤怒的情感。《苟奴见鬼》中的夏侯恺虽病死,却仍旧想着取回自己的马,担心自己的妻子。《产亡点面》中的亡妇虽然脸上被点了墨点,但相貌仍旧是从前模样,以至于米宗元能一眼认出是梦中来的自己的妻子。《王道平妻》《河间女》和《贾偶》中的主人公则更加明显地表达了向生的态度。父喻说:“妾身未损,可以再生,还为夫妇。且速开冢破棺,出我即活。”[12]这是女主人公拥有强烈的生存欲望。河间女死后,男主人公发冢、开棺,女即苏活。这里是男主人公想要复生爱人的强烈愿望。贾文合和后来的妻子是在复活之后成婚的,阴间的结缘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契机,为人之后的成婚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两人的阳寿未尽,因此两人复活之后的而结合是愿望也是必然。《紫玉与韩重》《驸马都尉》《谈生妻鬼》《卢充幽婚》几篇文章详细地叙述了凡男和女鬼的相处,是对冥婚习俗整体的呈现,同时结局女鬼(意味着死亡状态)的退场,凡男(意味着活着)的独自出现,对生死的态度高下立见。《西门亭鬼魅》结局中人们对西门亭的恐惧足以看出他们惜命的态度,以至于不敢上楼,怕自己亡发失精。《钟繇》中钟繇因为受女鬼诱惑,偏离了原来的生活常态,为了回归正轨更好地活着,他听从了左右的建议,尽管不忍心但还是伤了女鬼的大腿。以上种种情节都体现着浓厚的乐生恶死的色彩。
三、男权意识
仔细阅读《搜神记》涉及人鬼恋情节的十四篇文章,不难发现,这其中的人鬼情未了的主人公大多是男人和女鬼的爱情故事。台湾学者叶庆炳在《魏晋南北朝的鬼小说和小说鬼》中说“故事的女主角一定是鬼,男主角一定是人;从来没有一篇男鬼与女人的爱情小说,或女鬼与男鬼的爱情小说。”[13]为什么人鬼恋的男性大都是活着的,而女性都为亡魂?这是引发人鬼恋情节蕴含男权意识的重要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也是学界重视人鬼恋情节蕴含男权思想的重要引线。
《搜神记》中人鬼恋情节体现的男权意识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故事中生人的角色大都是男性,女性均为亡魂形象
汉武帝、营陵道人的同郡人、史良、米宗元、王道平、河间男、韩重、辛道度、谈生、卢充、郑奇、钟繇都是人鬼恋故事中鲜明的生人形象,李夫人、营陵道人同郡人的妻子、渤海女子、显姨、父喻、河间女、紫玉、秦女、睢阳王女、崔少府、西门亭女鬼和好妇则是各有特点的女鬼形象。联系前文论述的乐生恶死观念,可以得出男性处在更被世人所肯定的生命状态,女性处于被世人厌恶的生命状态。这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夏侯恺和贾文合,二人均属人鬼恋情节中少见的男鬼形象,尽管如此,由于故事叙述的主体对象仍旧偏向男性一边。《苟奴见鬼》主要写夏侯恺现身想要取走自己的马,担心妻子,坐在西壁大床,想要同他人饮茶的活动。《贾偶》篇无论是文合和弋阳县令女儿在亡魂状态相遇时还是复生之后二人交往的进度都是贾文合在主导。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男性作家的性幻想和白日梦,如李建霞在《论男权意识在〈搜神记〉人鬼恋故事中的体现》一文中说道“长期处于禁欲主义道德的淫威下,男子在现实中遭到压抑的情欲,必然要在文学的世界里挣脱束缚。”[14]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从更加深层的角度揭示男权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二)伦理纲常在故事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主要内容的三纲五常体现着儒家伦理观,同时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教条。这里以《王道平妻》《河间女》《贾偶》为例,详细论述故事中体现的对伦理纲常的遵守。《王道平妻》中的王道平和父喻是“誓为夫妇”[15]的,可见并没有得到双方家长的同意,在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于天的古代,二人活着的时候不能在一起,是一种必然。《河间女》中的河间郡男女是“私悦”[16],二人天人永隔与王道平和父喻一样,是必然。《贾偶》中的贾文合虽然想和弋阳县令的女儿“相交于今夕”[17],但弋阳县令女儿对女子清白的坚守并未让贾文合的想象成真,二人经过弋阳县令的同意在一起。
人鬼殊途,是另一种伦理,贯穿了《搜神记》的全部内容。在《搜神记》人鬼恋故事中,只要是有一方的生命状态是亡魂或者说死亡,二人就不可能会在一起。除了《王道平妻》《河间女》《贾偶》中的死而复生使得人鬼恋转化为正常的生人与生人的恋爱,二人的恋情才得以维持。其他诸篇,结局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悲剧的。
这两个方面的伦理内容其实是父权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着男权意识。
(三)故事中的女性的工具性明显,可被随意对待
这里以《断头语》《驸马都尉》《谈生妻鬼》《卢充幽婚》《钟繇》四篇文章为主要分析对象。
《断头语》中史良对自己喜欢女子没有嫁给自己的态度是愤怒,一气之下杀了女子,并残忍地将女子的头投入火中燃烧。女子的生命可以随意被抹杀。《驸马都尉》中的辛道度在与秦女同寝三日以后不仅获得了金枕还因此做了駙马,而此时秦女作为鬼魂却再没被提到,好像女鬼只是男子显贵的跳板。《谈生妻鬼》和《卢充幽婚》和《驸马都尉》的道理是一样的,但《谈生妻鬼》和《卢充幽婚》中的男主人公不仅得到了女鬼所赠之物,还收获了与女鬼的儿子,不仅他自己,他的儿子也过上了好日子。这里的女鬼并没有母亲该有的对舍弃孩子时的不舍,仿佛只是一个生子工具。《钟繇》中的妇人明明前一天还是钟繇喜欢的对象,后一天却被钟繇砍伤大腿,受伤严重。
综上,足以见出《搜神记》人鬼恋情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因为蕴含了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搜神记》中的人鬼恋情节才能以文化内涵为中介而受到读者的喜爱。
参考文献:
[1][2][3][4][5][6][7]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273,286,45,243,364,327,328.
[8]景圣琪.异域人间:《搜神记》的鬼文化[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27-29.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2.
[10](春秋)孔丘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98.
[11](战国)孟轲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198.
[12]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327.
[13]张诗芳.《搜神记》中的“人鬼情未了”[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02):76-78.
[14]李建霞.论男权意识在《搜神记》人鬼婚恋故事中的体现[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6(01):109-111.
[15][16][17]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26,328.